“恐惧”与崇高的关系决定着悲剧崇高说不成立
时间:2014-09-29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5870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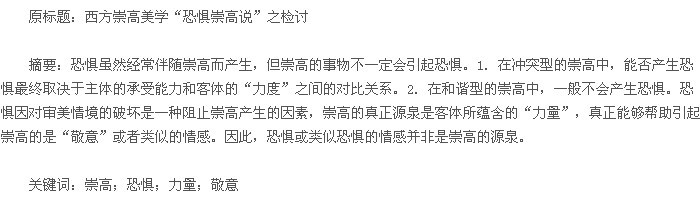
一、引言
审美主体在进行崇高的审美判断中往往会有“恐惧”的感受,因此“恐惧”与崇高美学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博克在理论上把它们联系起来之后,整个的西方美学就一直顺着这个理路前进,虽然康德曾经试图摆脱它的影响。康德说“谁恐惧着,他就根本不能对自然界的崇高作出判断,正如那被爱好和食欲所支配的人也不能判断美一样。”但他却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一个对象看作是可恐惧的,而又并不由于它感到恐惧。”
以后的美学家们大多就是在博克的理论框架内讨论,于是认为恐惧产生崇高的理论最终把悲剧也拉到了崇高的范畴之内。可见“恐惧”与崇高的关系在西方崇高美学大厦中的基础性作用。
按照审美客体的不同,或者说按照审美判断复杂程度的不同,可以把崇高分为“自然的崇高”、“人的崇高”和“艺术的崇高”三种。本文将从最“简单的”即“自然的崇高”谈起,涉及的审美对象主要是前两类。鉴于艺术之崇高的复杂性,作者将专文讨论。虽然最初朗吉努斯是把“崇高”作为一种文体的风格来讨论的,或者说是一种演讲效果,但是早期的美学家如博克、康德所关注的崇高主要是着眼于自然物体。当然,博克论文中的自然物还包括动物。
博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崇高美学发展史上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虽然对博克的理论进行了批评,但这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博克对后来美学家的影响。博克受了经常伴随崇高的“恐惧感”的误导,而错误地把能够引起恐惧的事物判断为崇高。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人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康德是在力图摆脱博克的理论,而在心灵中寻找崇高的根源。
席勒把崇高分为“理论的崇高”和“实践的崇高”两类。后一类即“实践的崇高”又分为“威力之观照的崇高”和“激情的崇高”。这“激情的崇高”对应的就是悲剧。席勒把悲剧艺术确定为“激情的崇高”,其依据就是它与“威力之观照的崇高”一样,对象的危险性造成人在感性上的恐惧感:“实践的崇高的对象对于感性必须是可怕的,一种灾祸必须威胁到我们肉体的状态,而且危险的观念必须使自我保存本能处于运动之中。”
他把悲剧与崇高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客体的“可怕性”在主体的感觉为“恐惧”,这明显是受到了博克理论的影响。
博克之崇高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这种因生命受到威胁而导致的恐惧感。他说,“任何能引起痛苦和危险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怕的,或者和可怕的东西有联系,或者起一种引起类似恐惧的作用,便是崇高的源泉;也就是说,它能产生一个人的思想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感。”
可以看出,“恐惧”与崇高的关系决定着悲剧崇高说能不能成立。
二、“恐惧”与“力量”:来自审美实践的反驳
朗吉努斯所说的崇高与博克所理解的崇高是有很大差异的。据朗吉努斯的观点,虽然热情在崇高的风格产生的五种条件中列在第二位,有了强烈的情感却不一定会产生崇高,因为有些热情是卑微的,“去崇高甚远,例如,怜悯、烦恼、恐惧。”
他所指的能够产生崇高的是作者那种恰到好处的“慷慨激昂的热情。”
朗吉努斯所举过崇高的例子有阿罗欧两个儿子“打算把奥萨山叠在奥林匹斯峰,/ 把葱茏的伯利翁叠在奥萨,攀登天空……而他们居然成功。……”有埃阿斯悲壮的沉默,天马的步伐和海神波塞冬的威力,也有上帝创世纪时说“要有光,于是有光;要有大地,于是有大地。”
以及埃阿斯向宙斯祷告,请求光明的照耀好让他们战死沙场。
其中除了荷马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中神或者人的威力可以威胁到人的生命,或许可以使胆小的人感到恐惧外,人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赞叹与讶异。
博克在论述崇高时,关注的是崇高的客体对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效果,他的论述是逐渐向“恐惧说”偏离的。
在着名的《关于崇高和优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一文的第二部分,博克集中讨论了崇高所能引起的各种情感。
自然界中的崇高客体引起的最高效果是“惊讶”、其次是“羡慕”、“敬畏”和“尊敬”。
他注意到了与惊讶相伴的往往还有“恐惧”,但却受了这一现象的误导,认为能够引起恐惧的事物,也是崇高的,比如说毒蛇及其它各种有毒的动物。
他引用希腊和拉丁语中用同样的词来表示“惊讶”和“恐惧”的事例来证明两者的亲缘关系。
此后他在文中的论述就一变而以“恐惧”为核心,列举了能够引起恐惧或者痛苦的因素,朦胧、力量、缺乏的状态、巨大和极小、无限、宏大、强光和黑暗、巨大的声响及其突然的开始和停止、断断续续的低沉的震动的声音、动物在痛苦或遭遇危险时的叫声、甚至包括使人不悦的味道和气味。问题是,崇高虽然经常引起恐惧,却不必然会引起恐惧。就拿他在文中所列举过的大海和星空来说,就有相当多的人甚至大多数人都不会害怕,除非当时的天气很恶劣。即使是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中主体也不一定会恐惧,但此时的海与天无疑是崇高的。那么崇高与恐惧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恐惧非但无助于崇高的产生,反而会阻碍主体做出崇高的判断。所谓的审美需要必要的心情,当一个人在逃命时,哪里会顾得上是崇高还是优美。崇高的客体往往引起主体的恐惧感,但恐惧只是崇高的客体在主体引起的诸多感情之一。换言之,崇高的客体引起主体的主要情感是敬意。如果要用一个主观情感的标准来判断客体是不是崇高的,那也应该是“敬意”而不是“恐惧”。博克本人的论述就是从“崇敬”及类似的情感开始的。
崇高的事物最根本的特点是“力量”,而且只有这种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时才会被主体判断为崇高。法国的巴希与英国的布拉德雷就认为只有“力量的崇高”一种,这就抓住了崇高的本质特征。所以朱光潜先生把崇高称为“最上品的刚性美”,揭示了崇高与优美的本质区别在于客体所蕴含的力度。当这种力度接近主体所能容纳的限度时,客体就会被判断为崇高。当然,客体所蕴含的力度并不总是在主体所能容纳的限度之内,非常接近或超过主体承受能力的力度就会使主体产生恐惧。所以崇高的产生是一个对比的结果,取决于主体的承受能力和客体之间力量的对比。火山喷发对于某一主体是崇高的,另一个人可能会被吓得逃走。弄潮的渔民可能会欣赏海上的巨浪,可是同一条船上胆小的人有可能会被吓得扒在船里不敢露头。有的人可以站在悬崖之上俯视脚下的千里江山,也有的人根本就不敢到跟前去,那些中等胆量的人可以抓紧山上的岩石、藤蔓或者树枝,放胆一望,一边感到峰顶的景色无比壮观,同时又战战兢兢,害怕会掉下无底的深渊。成人判定闪电中夹着雷鸣的坏天气为崇高,小孩子可能会被吓得哭着到妈妈那里寻求保护。人们误以为恐惧是崇高产生的标志甚至是源泉,因为两者确实经常相伴出现。在实际的审美实践中,主体的感受经常是敬意与恐惧的混合体。审美过程中,客体展示的力量不见得是正好只产生敬意不产生恐惧的,而且能够产生一点恐惧的客体能在主体的心里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这多出来的恐惧感却不能被误解为崇高的标志,当恐惧强烈到一定程度以后,崇高就被破坏殆尽,只剩下恐惧了。客体在多大程度上是崇高的,取决于客体的力度与主体承受能力的对比。
三、分类探讨:和谐与冲突
根据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吸引和排斥可以把崇高分为冲突型与和谐型两种。前一种是传统的崇高美学所集中探讨的对象,如“天边高高汇聚挟着闪电雷鸣的云层,火山以其毁灭一切的暴力,飓风连同它所抛下的废墟,无边无际的被激怒的海洋”之类。这一类崇高的客体与审美主体之间是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客体所展示的力度对主体在吸引的同时有一定的排斥(但不一定要产生恐惧)。用康德的话说,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快速交替的排斥和吸引。”
通常而言,崇高加上丑所产生的效果是冲突型的,因为丑本身就是对主体的一种排斥;此外,当客体蕴含的力度几乎要超过主体的承受能力时,也会产生冲突的效果。比如正在喷发的火山,或者飞泄而下的大瀑布,虽然可能景观很美丽,但这种崇高是冲突型的,因为主体如果靠近会有生命危险。崇高与美结合,便成为美的崇高,与丑结合,便是丑的崇高。美的崇高更靠近美这一端,冲突的崇高更靠近“崇高”,因为单纯的崇高当力度接近主体承受能力的临界点时是冲突型的。能够产生恐惧的崇高属于冲突的这一类。恐惧的原因有两种,或者是因为所显示力量接近人的承受能力而令人恐惧,如乌云闪电之类。或者是因为形象的丑陋,如巨大的鳄鱼。单纯的恐惧则不具审美的效果,如毒蛇、蜥蜴可以产生恐惧,但不可谓之崇高。巨蟒可以有崇高的效果,因为它巨大的身躯。此种可以威胁人生命的动物,在主体的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崇高,如在动物园中观赏或者影视中看到。否则,它们所产生的恐惧便会把崇高破坏殆尽。
另一类崇高则往往为美学家们所忽略,它大概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壮美,其特点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往往是力量加上美构成。如果主体愿意放开他的心胸,他与客体之间可以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如繁星闪烁的夜空,万里无云的草原,风平浪静一望无际的大海等。如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如此的和谐,那么这一类的崇高就一般不会引起恐惧感。既不丑也不美的崇高如果蕴含的力度不是很大,也可属于这一类。
不管崇高的客体是美还是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体现了一种正向的力度。这种力度在主体所产生的效果如康德所说就是“敬重”。这种情感是由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差距造成的。客体在某方面处于一种有吸引力的强大优势,从而引起主体的“臣服”感,这种感觉就是敬意。如果单纯是力量,引起的可能是“敬意”,也可能伴有“恐惧”,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主客体之间力量的对比。审美过程需要保证正向力度处于优势,因为它是审美的前提。如欣赏火山或者飞瀑时如果主体的生命受到威胁,由于审美的心情被破坏,也就产生不了崇高。在上论分类讨论中可以看出,崇高的客体不一定会在主体的内心产生恐惧,最典型的莫过于和谐型的崇高。
冲突型的崇高能否产生恐惧最终取决于客体的排斥力和主体的承受力之间的对比关系。
四、问题的复杂化:人的崇高
如果对真实的审美现状作一个概括,那么就是多样性,人们因为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受教育的程度而对相同的人物作出截然不同的审美判断。当然关于人的崇高在西方谈得比较少,康德所讨论的客体里就没有人,他把崇高归结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只有很少一些西方美学家如叔本华认为人可以是崇高的。
人是天生与善恶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目前既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一种社会现实。审美的情趣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学里判断一个人是否崇高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为判断的标准不像判断纯粹的自然事物那样简单明了。自然事物的判断主要是凭一个人的直觉或者说是直接的感觉,而关于人的判断很多主体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上善恶这个标准。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判断时不加这个标准,于是便出现了比自然事物的判断更多的不一致。会有很多人把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拿破仑、甚至希特勒作为崇拜的偶像而忽略了这些人都是侵略者。盲目的崇拜者之所以会把侵略者当成英雄人物,因为他们或者是邪恶的帮凶而没有意识到恶对于自己的威胁;或者只是从间接的渠道了解这些人物,只看到了侵略者的力量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危害,因为这些主体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私利,只要杀的不是我,哪管别人的死活。对于这些崇拜者而言,如果以上人物要杀的是审美的主体,那么他们就不会继续崇拜他们了,而是会跪下来请求被饶恕。可见恐惧正是崇高的大敌。而那些正义感比较强而又对历史很了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值得崇拜的,因为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之上的,除了那些死去的士兵之外,还有很多无辜的生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甚至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很幼稚很愚蠢,是应该被鄙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最终成为自己骄傲自大的牺牲品。不是有文天祥慷慨就义吗?在文天祥看来,元朝的武功可以消灭他的生命,却不可能使他屈服,利诱也不可能使他动摇。在这种主体面前,哪里还有什么崇高?因为他本身就是崇高的。此种能够使敌人敬仰的精神,体现为人格所展现的力量,正为崇高的来源,并非因为能使人恐惧。
实际的审美判断是如此的复杂,因为除了善这个分界以外智慧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种力量。大多数的西方人恐怕更崇拜上帝而不是耶稣基督,因为上帝是以一个惩罚者的姿态出现的,是力量的代表。有些人则认为耶稣基督能够为他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在自己遭受痛苦时还不生怨恨,这体现了比惩罚别人更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客体的人如果被判断为崇高,其前提就是这个人所体现的“力量”使主体产生了崇敬之情。如果某个人在主体内心引起的是恐惧而非敬意,那就产生不了崇高,典型的例子是神话中的魔鬼形象,不管它有多么的强大,绝不是崇高。另外一种复杂的情况是,既有恐惧,又有敬意,可称之为敬畏。上帝在一些人心中就是这种效果,上帝以其至善可使基督徒臣服,此种宗教性的情感的实现在美学上是主体排斥的力量被客体的力量完全摧毁的结果。此种摧毁能够产生,因为敬意毕竟战胜了恐惧,不是主体能不能抵抗这种力量,而是主体不愿意抵抗。与中国文化中对圣人或者佛陀的敬仰相比,二者过程不同,结果却相同。
崇高与美善的共性就是都体现了一种正向价值。崇高作为正价值的审美范畴不仅是一种必要,更是一种现实。而恐惧与恶体现的是负价值,是与崇高不相容的。善恶是与文艺相伴而生的,它在作品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内化在其中了,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主观而功利的。审美实践中的主体从理论上是可能摆脱功利主义的,但这不是普遍的审美现实。
五、结论
就本文所涉及到的自然物和人的崇高来说,崇高的客体不一定会产生恐惧,而且有一些类型的崇高如和谐型的,不会引起主体的恐惧。有时候才出现的“恐惧”因为不具有必然性而不能作为崇高产生的标志,当然更不能成为崇高的源泉。在主体而言,“敬意”或类似的情感因为总是伴随崇高出现因而可以作为主体情感上的标志。产生这种敬意的客观原因为客体所蕴含的“力度”。
当客体是人时,力量加上善可以使人产生敬意甚至是“臣服感”,因而最终产生崇高。但力量与恶的结合却有可能产生恐惧,这时就没有了崇高。即使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以恐惧为前提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崇高的真正源泉是客体所蕴含的力量,而非恐惧,前者的根据在客体,后者作为一种情感在主体。如果要在主体找一个崇高产生的标志,那就是敬意或类似情感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康德 . 判断力批判 [M]. 邓晓芒 , 译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2.
[2] 席勒 . 席勒散文选 : 论崇高 [C]. 郑法清 , 谢大光 , 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3]Burke, Edmund.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Harvard ClassicsVol. 24) [M]. 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1909.
[4] 朗吉弩斯 . 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 论崇高 [C].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5] 巴希 . 康德美学批判 [C]// 蒋孔阳 . 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着选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6] 朱光潜 . 西方美学史 [M].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7] 朱光潜 . 文艺心理学 [M]. 上海 : 开明书店 ,1936.
- 相关内容推荐
- 创新社会治理与美的关系研究引言2016-07-20
- 长城崇高感和优美感的此消彼长关系研究2014-09-10
- 中国美学中对立关系的具体体现2015-11-26
- 美学的色泽及其与心性修养的关系2015-01-29
- 美本质上是事物的一种关系属性(本科)2014-11-19
- 美在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2015-07-22
- 休闲的概念、发展历史及其与审美的关系2014-12-05
- 经验与审美的关系2016-0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