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社会家庭关系的伦理方式转向
时间:2015-08-07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7967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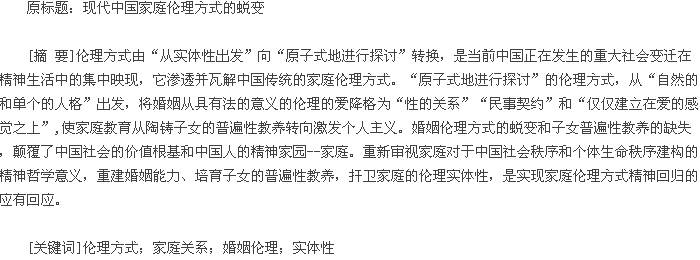
现代中国社会家庭关系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婚姻关系不稳定、子女缺乏普遍性教养。性过度开放、婚姻契约化,“闪婚”、“闪离”成为影响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更有随政府楼市政策变化而随意解除和缔结婚姻的合谋。骄纵任性的子女也使得家庭生活疲惫不堪。这一切表明在家庭内部最重要的横向和纵向两大关系--夫妻、父子中,伦理同一性素质和能力正在遭遇严重危机。这一危机的本质是家庭正面临“伦理方式”的重大挑战。
一、现代社会伦理方式的哲学转向】】
黑格尔曾断言,“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
[1]173换言之,人类建构伦理的方式有且只有两种:“从实体性出发”与“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前者是有精神的,后者是没精神的。“精神”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以“普遍物”为前提,以“单一物”与“普遍物”这一实然向应然转化与同一为逻辑,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判定“精神”的重要标准。
“从实体性出发”是“有精神”的伦理方式,“实体性”是类的“普遍本质”或“普遍物”在具体伦理实体中的体现,“从实体性出发”就是从普遍物出发。具体说来,普遍物作为形而上的彰显类整体公共本质、共体,它统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永恒性相比,作为一种偶性存在的单一物只有分享普遍物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类存在,单一物之间基于对普遍物的信仰和分享而缔结在一起,这是“理一分殊”、“月映万川”的关系。“从实体性出发”将普遍物凝结于单一物身上,并成为单一物之间有机连接的灵魂,由此实现群体伦理秩序的组织与建构。
“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伦理方式是没有精神的,它缺乏体现公共本质的“普遍物”这一应然预设,代之以实然状态的以自然冲动和主观任性冲动为行动逻辑的“单个的人”为出发点。“单个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子式存在,其人格特征为,“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1]197“单个的人”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物”为内涵的同一性基础,而以“集合并列”的方式,即“一个人把自己的经验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便寻求那些与他有共同经验的人,以便发现共同的意义”,[2]137建构为满足相互需要形式的普遍性。这种基于“单个人”的自然冲动和主观任性而建构形式普遍性的伦理方式,因缺乏内容的普遍物而充满任性,无法实现稳定和谐的伦理秩序。
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精神意象,表现为伦理方式由“从实体性出发”向“原子式进行探讨”的根本转向。它“破”传统伦理实体与普遍物,“立”被从有机的伦理实体中“揪出”的单个人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就是从16世纪开始贯穿整个西方文明主线的现代主义的特质。“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它们都逐渐让位给个人。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立个人,他拥有自决权力,并获得完全自由。”
[2]61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这一转向描述为“共同体”向“社会”的蜕变,他将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群体,如家庭、村庄等称为“共同体”,“社会”则是个人基于利己目的的联合体。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则从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一传统价值体系在美国小城镇的终结,揭示了这一精神转向。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的伦理实体以个人为基本单位,建起缺乏普遍物的形式普遍性即假定集合体--社会。总之,依赖单个人的主观冲动和任性,不是从普遍性而是个别性出发,设计共同生活的伦理方式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精神标识。
二、“从实体性出发”的家庭伦理方式】】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国社会的伦理方式已经发生改变。几千年来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家园的传统伦理实体及其承载的伦理传统遭遇重大解构,代之以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瓦解了人们曾经共同分享的伦理秩序,其中最为深刻的危机来自中国家庭伦理方式的蜕变。
家庭作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就是一种客观普遍物。夫妻、子女是家庭中最基本的两种伦理关系,符合精神要求的家庭伦理方式,是从这一自然的伦理实体的实体性出发,将作为偶性存在的个体,从自然的同一性提升至精神的同一性。实体性、普遍物是婚姻的目的。黑格尔指出,“婚姻的客观出发点则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弃自己自然和单个的人格”[1]177.在这里,“一个人”和“统一体”就是家庭。双方意识到这个统一是实体性的目的,抛弃自己自然和单个的人格,恪守实体性和普遍物,超越自然本性的冲动、激情和一时特殊偏好等的偶然性,从而将婚姻提升至它作为实体性的东西应有的合法地位。所以“从实体性出发”的婚姻伦理方式,坚守普遍物即家庭的伦理实体性,当事人双方作为个体的人格自然性和主观性都是必须扬弃的对象,因为“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是精神性的爱,必须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1]177缔结婚姻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人性提升和升华。
婚姻的缔结是男女双方对家庭这一普遍物的恪守,实现了普遍物与单一物的统一,确立了普遍物应有的统摄性地位。子女作为父母爱的实体性定在或客观化,是家庭的重要成员。父母不仅给予子女以自然生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传递普遍物,陶铸子女的精神生命,即教会他们“如何做人”.传递普遍物就要矫正子女的任性,即父母必须从家庭的实体性出发对子女基于自然本性和主观任性的个别性,以纪律加以约束,灌输普遍物。具体方式是作为构成普遍性的父母,以权威方式将普遍物陶铸到子女的意识和行为中去,子女服从父母并内化普遍物。对子女普遍性教养的培育是父母的义务也是子女的权利。为此,黑格尔指出,“子女有被抚养和受教育的权利,……同样父母矫正子女任性的权利,也是受到教训和教育子女这一目的所规定的。”他认为父母对子女教育中使用惩罚的意义在于,“对还在受本性迷乱的自由予以警戒,并把普遍物陶铸到他们的意识和意志中去。”
[1]187所以,“从实体性出发”的家庭伦理方式,父母以权威的方式将伦理普遍物传授给子女,使其获得实体性的意识和意志,成为精神性的存在。
无论是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子女教育,从实体性出发的家庭伦理方式,始终坚守普遍物至上,以普遍物与单一物的统一为主线,扬弃基于自然本性和主观任性的个别性,使作为偶性存在的个体成为分享家庭实体性的成员,无论是夫与妻,还是父与子,在家庭中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这种统一中的一个成员。
[1]175从传统“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代“家-单位-国家”模式,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建构一直遵循着“从实体性出发”的伦理方式,近年来随着急剧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家庭伦理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
三、婚姻伦理方式的蜕变】】
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文化的快速流变,伦理传统和伦理实体遭遇了重大解构,现代人的婚姻能力下降,越来越没有信心和耐心为了家庭的实体性而努力扬弃自身的个别性。缺乏对家庭实体性的信仰和恪守,婚姻双方当事人因固守自身的特殊性而无法实现精神上的统一,即成为“一个人”.没有坚实的精神基础,脆弱的婚姻经不起风雨,一旦遭遇某些困难,各自独立的个人就会随意解除婚姻。婚姻越来越演变为一场只为满足双方在特定情境下的某种共同需要的形式。这就是无精神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婚姻伦理方式所诞生的怪胎。
与“从实体性出发”的婚姻伦理方式相比较,“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的婚姻伦理方式,因为缺失“普遍物”的应然前提,所以此处“单个的人”就是现实层面除实体性之外包含多种属性(自然属性、主观任性等等个别性)的人。这样的婚姻伦理方式是以自然人、独立的权利主体和主观任性的人为出发点,分别将婚姻理解为,“性的关系”、“民事契约”和仅仅凭借“爱的感觉”,这三种婚姻的伦理方式不仅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所批评的,也是当前中国社会解构婚姻神圣性的极具破坏力的社会现实。
从“自然人格”的单个人出发,将婚姻降格为“性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婚姻中的双方或一方对婚姻的理解停滞在性的相互吸引阶段,这就为家庭的瓦解埋下了伏笔。在这种理解中,自然冲动成为婚姻的全部内涵,人被剥离得只剩下本能。黑格尔指出这种观点,“只是从肉体方面,从婚姻的自然属性方面来看待婚姻,因此,它只被看成一种性的关系”[1]177.事实上,婚姻作为直接伦理关系包括自然生活的环节,但是这种感性的属于自然生活的环节是被设定在婚姻的伦理关系中的,精神主宰自然冲动将婚姻提升至实体性的现实。然而,从自然人格出发的人,双方或一方认为婚姻就是满足自然欲求的形式。这种从自然人格出发的婚姻,没有“实体”概念及对“实体性”的信仰,无法向精神性环节提升,亵渎了婚姻的神圣性,并且也现实地影响了婚姻的稳定性。这股对婚姻无所敬畏,任由自然欲求涌动的暗流正在从根基上颠覆家庭,调查显示,当前中国社会“性过度开放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的占42.3%”[3]384.
以独立的权利主体为出发点的契约化婚姻。这突出地体现在对于家庭财产的分配与使用方面。缔结婚姻的双方将婚姻理解为一种民事契约。为保障独立权利主体的权益不受侵害,双方在法律意义上彼此约束达成协议。从婚前的财产公证到婚后的“AA制”,彼此间不是努力成为“一个人”,相反却在维护各自的独立性。黑格尔认为,家庭财产是家庭作为“一个人”的外部定在,是家庭实体性的现实形式。换言之,家庭财产(财富)是夫妻双方对家庭共同体的关怀和增益,是一种伦理性的东西,它作为共同所有物,为家庭成员所共有。
[1]185因此,夫妻任何一方作为家庭成员不能以独立主体的身份拥有特殊所有物。但在以民事契约方式存在的婚姻中,双方从婚姻缔结伊始就是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而存在,没有家庭实体性的意识和成为“一个人”的意志。没有精神纽带连接的婚姻成为一种买卖,然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中年轻一代所青睐的婚姻伦理方式。调查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婚姻中的个体自我权利意识浓重。新兴群体中64.4%、大学生群体中81.5%的人虽然认为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感情”,但对于“婚前财产公证”这种高度理性化的行为,在新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中认为“双方同意就行”的比例却高达49.3%和55.2%、“值得提倡”者分别为20.4%、17.2%[3]581.在经济发达的苏州,企业人员中有40.7%的人认为“双方同意就行”,持“值得提倡”的人为25.1%,“有必要”的为6.6%,持反对意见的为27.5%[3]462.在经济欠发达的盐城市,认为“没必要”的为61.3%,但“应该”的持有率也有33.8%[3]480.这预示着现代中国社会对婚姻的一种趋势。黑格尔指出,“将婚姻理解为仅仅是民事契约……双方彼此任意地以个人为订约的对象,婚姻也就降格为按照契约而互相利用的形式。”
[1]177这是典型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伦理方式,双方是以独立的权利主体而存在,并以“互相利用”为目的。这完全颠覆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如前所述,婚姻以“实体性”为其规定性,当事人在他们单一性中的独立人格是被扬弃的对象,代之以对实体性的服从与恪守。在家庭中,只有基于实体性存在的“成员”而没有独立的个人或权利主体,相反,独立的权利主体的出现是家庭瓦解和实体性丧失的标志。所以,以单个的人为出发点,以实现自身利益为目的,以普遍性的形式为中介的契约化婚姻,从源头上背离了婚姻的伦理本性,是缺乏单一物(个体)与普遍物(实体性)统一内容的“没精神”的形式婚姻。
以主观任性的单个人为出发点,将婚姻仅仅理解为爱的感觉。黑格尔指出,“认为婚姻仅仅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是应该唾弃的观念。
[1]177通常人们对婚姻的理解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事实上,婚姻始于爱的感觉但又不能仅仅止步于此。因为爱作为一种感觉包含主观偶然性,婚姻需要将最初的爱的感觉提升到稳定的精神层面,即由最初双方的倾慕之情上升为对于新诞生的“一个人”即“家庭”的信仰,体现为坚守实体性,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使之成为稳定的精神纽带。
仅仅建立在爱的感觉之上的婚姻观,以个体的主观感受为出发点,缺乏对实体性的信仰。实际上,个体只有在服从实体性中扬弃主观任性方符合婚姻的伦理精神,然而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令人担忧的是,爱的感觉缺失成为随意解除婚姻关系,甚至不顾及无辜的第三方(孩子)的利益极端自私行为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调查表明,对于婚姻的看法和遭遇婚姻破裂时的选择,传统的婚姻观念占主流,68.2%的受访者认为“从家庭整体考虑,为了孩子应当相互迁就,实在过不下去才能离婚。”但是一些非主流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如“婚姻应当是自由的,有更满意或更合适自己的就离婚”占受访者的15.9%,[3]382“婚姻是人们缓解生活压力的一种形式,轻松愉快是主要目的,否则可以解除”,持有这种态度的青年知识分子高达47.1%.[3]501在年轻一代的婚姻中,“闪婚”、“闪离”甚至以确认爱的感觉为目的的“试婚”现象都已不再陌生。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婚姻或许因此而成为一种遥远的传说。
总之,以上三种婚姻观所表达的,是以自然的、独立的单个人为出发点的“原子式”探讨,是缺乏实体性信仰的伦理方式。从实体性出发的婚姻伦理方式中需要扬弃的个别性、主观任性,在“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伦理方式中得到张扬,它拉开了家庭伦理方式蜕变的帷幕。
四、子女普遍性教养的缺失】】
现代家庭中,子女普遍性教养的缺失也表明家庭伦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家庭教育的伦理使命在于,父母作为权威将普遍物陶铸入子女的意识和意志,使之获得伦理的自由与解放。但是在社会高速变迁和技术日益统治世界的时代,传统经验不足以有效应对新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受到影响,父母的权威地位因此受到挑战。“权威”的失落意味着父母与子女这一纵向实体性传递链的断裂。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出于对子女生存状况的深切担忧,父母主动放弃传统陶铸伦理普遍物的权威教养方式,转而激发子女的个人主义倾向。子女的个别性不是被扬弃的对象,相反是被培育和鼓励的对象。家庭教育从“实体性出发”转向从“个别性出发”,家庭不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被现代性渗透并沦为传递现代性的重要载体。这是从内部威胁瓦解家庭并向社会输出“原子式”个体的最具破坏性的力量。
当前为了使子女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父母按照效益原则,培养子女具有竞争力的各项技能,如获取学业上的高分、参加各种活动以获得潜在地能够为将来升学或就业带来收益的荣誉。父母密切搜寻各种有利于提升子女竞争力的机会,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子女如何获得更多关注,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孩子在与他人交往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目的取向,善于转化互动,使对方调整措施来迎合他们的需求。这些孩子虽然也经常参加一些活动,以培养与他人顺利共事的能力以及团队精神,但其出发点是实现个人特殊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个人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目的,其他人以及与他人共同形成的形式普遍性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
[1]197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说,“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这种意识在家庭阶段就已经播下了种子。
这种缺乏实体性和普遍物传递的家庭教育同时也改变了家庭的伦理秩序。父母为了培养子女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利意识,抛弃了传统家庭教育中对于实体的尊重与遵从,一切从个人出发,在子女面前父母已不再是代表普遍物的权威,而与子女平起平坐。父母与孩子之间没有清楚明确的界限,子女被赋予更为自由而宽泛的权利,时而被当作成年人,时而回归小孩子,致使子女在自我认同时发生角色紊乱。他们俨然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为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与家长据理力争,挑战父母的权威,使家庭生活混乱不堪。
这种父子之间的伦理方式,本质上就是以个体而非实体性为出发点,以特殊利益而不是普遍物的陶铸为目的,所培育的不是个体基于家庭自然伦理实体所形成的爱的感觉,而是以自我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积极扞卫自身权利的意识。父母没有履行对个体进行伦理教化的义务,使子女在家庭中获得实体感的熏陶与确立,相反,从家庭阶段就开始将子女培养成为“原子式”的存在。子女不再是家庭的成员,而是独立的权利主体,这从根源上解构了家庭的实体性。黑格尔说,“家庭的伦理上解体在于,子女经教养而成为自由的人格,被承认为成年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并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自由财产和组成自己的家庭。”[1]190然而在当前中国家庭中,子女未经教养成为自由的人格,却已成为独立的人格、任性而为的个体。
“从实体性出发”代之以“从个人出发”,基于实体性统一的家庭成员沦为主张独立权利的主体,家庭作为“整体性的个体”正在遭遇从普遍物向“原子式”单一物(即自然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严重危机,这是真正的精神危机。
五、家庭伦理方式的“还家”努力】】
家庭作为自然的伦理实体,一直是中国社会伦理同一性建构的源头与基石,其文化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当前中国家庭伦理方式的蜕变其深远影响在于,家庭伦理同一性能力的弱化和解构,必将最终导致社会凝聚力的涣散。扞卫家庭的伦理实体地位,重回饱含精神气质的家庭伦理方式是当务之急。
正如黑格尔所言,“以单个的人为基础”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伦理方式是没有精神的。历史表明,以解构传统“从实体性出发”伦理方式为标识的现代社会变迁,使西方社会深深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恐慌中。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2]74为应对该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mtyre)、泰勒(Charls Taylo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纷纷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重归伦理实体性,找寻伦理方式从原子式探讨向实体性回归的道路。
在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社会,家庭就是神圣性的源泉,它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更是社会的结构范型;它不仅是个体自然生命的发端,更为个体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是中国人生活的重心和全部,集自然功能、经济功能和精神给养于一体的最坚实和最温暖的堡垒。家庭的实体性作为普遍物是成员的实体和共体,是个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真理,个体只有作为其成员才能够感受和理解生命存在的意义,直至死亡,才最终完成了其作为个体的全部使命。通过“人伦”本于“天伦”的建构原则及其“家-国-天下”的外推方式,家庭情感被不断扩展为更高、更广的层面,“乡愁”、“故土”、“祖国”等等都饱含着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同样,“鳏寡孤独,人生最苦”,失去家庭依托的人孤苦伶仃,令人同情。离家的人即为“游子”,“回家”是最能激发中国人情感共鸣的语词。如果没有家这一实体存在,也就无所谓“游子”,“游子”是有出发点的个体,无家意味着没有出发点,当然也没有归属,那么单个的人就是一个四处游荡的幽灵。家庭实体性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解放,相反是一种没有归期的孤苦流放。
当前中国社会需要树立文化信心,遵从文化传统,坚信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迁,家庭的源始性地位是不应改变的,这不仅是家庭自身存在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在现代化过程家庭受到一定冲击是很自然的,但不能够任其涣散,因为家庭实体性的瓦解和伦理方式蜕变,并非家庭在现代化巨潮中的宿命。相反,它可以为个体提供抵御现代化冲击的庇护,我们应该自觉地维护其应有的实体性地位。东亚地区国家的现代化与家庭凝聚力的调查表明,“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4]
中国社会需要进行一场家庭伦理实体意识的再启蒙,以健康的社会风尚引导和培育年轻一代的婚姻能力,恪守家庭的实体性,保障婚姻的稳定性;唤醒父母对于子女普遍性教养的教化和引导,培养子女的健康人格。扞卫家庭的伦理实体性,回归实体性的家庭伦理方式是我们面对社会秩序巨大变迁所造成挑战的应有回应。
[ 参 考 文 献 ]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 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3] 樊浩。中国伦理道德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 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3)。
- 相关内容推荐
- 阮元慈善活动思想与践行2015-06-23
- 阿昌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观2014-12-22
- 工程师社会伦理责任的由来、问题及强化途径2015-03-11
- 现代西方生态伦理主要思想2016-07-05
- 中国传统女德与《女诫》的女德教育思想2015-03-01
- 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看道德合理性论证2014-09-11
- 风险社会与公共健康伦理阐释2014-11-27
- 古代律令中的孝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2015-01-09
- 上一篇:威廉姆斯对科学和伦理学的辨析
- 下一篇:伊斯兰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