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戏剧政治话语功能的消长
时间:2014-09-04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4898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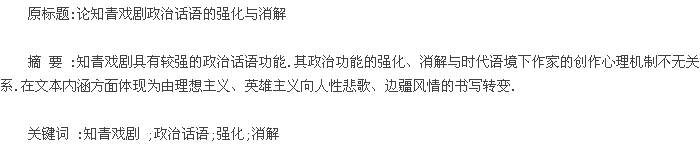
毋庸置疑,知青戏剧带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文化现象.其政治话语功能的消长是由时代语境和作家的个性气质等因素决定的,而作家对这种政治话语的钟情与疏离,也是主体创作心理机制运行由偏离走向正轨的过程.
一、知青戏剧政治话语的强化
文革结束前的知青戏剧政治话语的强化,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它是昔日长期过度诠释文学政治化以及作家特殊创作心理机制生成的必然结果.作家的这种创作心理惯性固化与创作立场的跟风游移最终导致了主体创作意识的形成与审美定向的暂时迷失.而知青戏剧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非理性的张扬,也是最受戏剧批评家们指责和非议的地方.
(一)时代语境的强化
知青戏剧的横空出世是与"上山下乡"运动分不开的,它是政治化及社会运动的产物.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号召青年到农村去 :"青年啊,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1]
开始关注知识者和广大农村的关联.而把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来宣传却是从五十年代动员农村中小学生回村务农开始的.随后,六十年代初又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大批城镇知识青年情绪高涨,背离长期生活的城市,步入了被自己诗化了的理想农村.红卫兵运动风潮的迭起,又把这场政治运动推向了高潮.作为一向对政治敏感而又富有使命感的作家,则把这一思想与历史断裂错位下所产生的奇异现象很快变成了文学现实,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
(二)作家创作心理机制的固化
早期的知青戏剧,极力践行了"文学服务于政治"的创作宗旨.这种创作心理机制形成并付诸于文学创作实践后曾给知青戏剧带来了声誉,但也使之沾染上无法拭去的污点.当然,这种创作上的一度迷失,是作家对历史的文化误读和创作话语权的失语.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知青运动兴起并蓬勃展开,使得作家对这场运动产生了好奇.带有绚丽而又神圣光环的领袖意志使得他们不愿或者不敢去怀疑这场运动的性质就很快地融入到其中,有的甚至成为了知青中的一员.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不是冷凝旁观,审视静思,而是激情澎湃,歌唱赞美.于是,形成了特定背景下的特殊的创作心态."观念在体现之时必受外界影响".[2]
文革结束前的中国知青戏剧由于过分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和作家非理性的判断,很少有人把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得悲惨消极.显然,这违背文学的艺术规律,成为了宣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声筒.呐喊和呼吁成为了戏剧创作的主旋律.早期知青戏剧的创作引发的关注和思考主要集中于这种由领袖所发起一呼百应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起到了多大作用?农村的艰苦生活经历,是否对知青起到真正的锻炼目的?青年们的人生价值是否在背离城市后得到真正的实现?这些都是知青戏剧最令人思考的地方.
一开始,知青戏剧就表现出他们面对未来的迷茫和彷徨.《朝阳沟》中的王银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下乡之前,她就犹豫过,来到朝阳沟后看到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连山羊的叫声都富有诗意,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但城乡生活的差距和生产劳动中的丑态百出又使她产生回城的想法.如此犹豫彷徨反复多次,但总能神奇地战胜自己的心魔,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为何早期知青文学在展示所谓落后意识向进步方向转变时,大都缺乏嬗变的必要动因呢?这恐怕也只能说明作家对自己的叙述功能产生了怀疑,或者,他们根本就不能找到能自圆其说的内在驱动力.
知青戏剧非理性的传达还表现于人物的无所畏惧、无所不能的英雄主义,如《山村新人》中的方华和《边疆新苗》中的江雷.他们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知青的典型代表,领袖话语是他们信奉和坚守的神圣诺言.时代激流中的磨砺使他们在斗争中显得更加自觉,更加自信而游刃有余.其宏伟的人生理想,完美的形象性格,无坚不摧斗争精神以及顽强的革命意志都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作家为了塑造知青高大全的形象,往往在其成长的人生历程中设置类似于体育运动项目的栏架或水池等障碍来加以考量,如父辈浓厚的落后意识,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知青们总是大智大勇,运筹帷幄,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挽救了生产损失,教育了落后群众.
剧作家也渲染了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村的大有作为,使其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实际中去,做到学以致用,理论和生产实际的相结合.《朝阳沟》中的兴修水利 ,《春光曲》中大搞试验田,《山村新人》中的建电站,自制水轮机,《北大荒人》中的机车改良实验等等.知青们在简陋的条件下,或改良品种,或革新机械,除了机车改良遇到较大的挫折外,其余大都一帆风顺.总是能够大获成功而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可见,本期的知青戏剧创作是作家作为强制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因此,作家在展示这一思想内涵时,往往忽视事物内在矛盾的复杂性,不注重过程,只注重结果,理想主义显现无疑.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关键问题.政治话语对文学渗透的限度往往左右着文学的叙述功能,文学的艺术价值,甚至对文学价值的历史评判.文革时期的戏剧,过度诠释了其政治功能,异化了戏剧艺术的审美需求,使得知青戏剧蒙上了无法抹去的诟病,正像乔纳森·卡勒所言"不是文本记住了什么,而是它忘记了什么 ;不是它说了些什么,而是将什么视为想当然."[3]
文学家的任务如果沦为了政治的留声机,那不仅仅是文学家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可见,早期的知青戏剧由于政治功能的强化,非文学因素的过度渗入,丧失了文学的纯粹性,因为"戏剧是绝对的,为了能够保持纯粹性,戏剧必须摆脱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戏剧除了自身之外与一切无关."[4]当然,知青戏剧文学完全摆脱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二、知青戏剧政治话语的消解
文学只有摆脱了其政治的束缚和制约,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文学能力".[5]历史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文革时期的政治化倾向已逐步沉淀消解,不再成为左右作家主体创作意识的主宰.知青运动的退潮,政治风险的规避使他们理性地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带来的历史性的灾难,主动对历史进行修复,开始了精神的自我救赎.此时的作家和知青们的主体意识已开始觉醒,他们已经开始怀疑这场运动的实质,也朦胧地感觉到它给个体及国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原本立下的扎根于农村的誓言也失去原有的鲜亮色彩,原来所表露的献身于农业建设的决心也开始动摇,原先所背弃的城市重新具有了莫大的引力.所以,这时期的戏剧作品不再展示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复杂的阶级斗争,而是或揭示知青在肉体和心灵上受到的双重戕害,或抒写边疆地区的诗意风情.从而,反映知青戏剧创作理性的回归.
(一)人性悲歌的理性书写
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运动的脚步并没有立即停歇,而是仍然按着预定的路线惯性前行.但上山下乡的话语表述已不再是光鲜崇高的行为象征,而是一种带有被迫或有侮辱性质的古老行为--发配.《北京往北就是北大荒》中的勤子为了给患病的母亲过生日,仅仅挪用公款六元六角六分钱,则被发配黑龙江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而与之同行的小柳儿只是因为偷过一块手表而成为了一名拓荒者.因此,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少了一份崇高,而更多是渗透了浓重的悲剧意味.
《桑树坪纪事》以知青朱晓平的视角,描写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被城市文明导化的桑树坪人民的生存状态.剧本借桑树坪这个古老的中国象征,通过桑树坪遗留下来的生存法则,现实的生存困境,展示了其生命窒息和自我虐待的精神贫困.《二十岁的夏天》写咕咕岛上某农场连队由谣传岛上有麻风病而引发的人性悲剧.知青们生活在孤寂的小岛上,挨整批斗,自由遭阉割,人性被蚕食.岛上有麻风病的谣言传开之后,排查隔离,任何人不准离开小岛.正常的人性受到挤压变形后开始显现丑陋可怕的一面,他们互相的猜忌、指责甚至诬告.小黄毛因为身上有白斑病受到怀疑而投海自杀 ;小杨柳因为一时的懦弱没有挺身保护而倍感自责也发了疯.谣言被揭穿后,正当大家暗自庆幸的时候,更大的毁灭性的灾难海啸却来了.海水翻腾,山崩地裂,小岛被吞噬了.人性的悲剧以自然的恐怖灾难形式显现了出来.
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年代,知青们的人生理想和心理诉求是很难得到实现和满足的.他们精神痛苦的负累也大大加强了,因为"当人的乞求努力受到挫折或阻碍,不能达到或接近预期的目的,就产生痛苦."[6]而这种伤痛是不会轻易地能够医治与抚平的.《WM我们》展示了人生理想的倒置和复归.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为其理想重构所展现的拼搏精神,而是屡屡受到打击后悲观厌世、自暴自弃的无奈和无望.这是一种典型的知青时代后遗症,也是时代悲剧的象征.
总之,新时期的知青戏剧由于基本上摆脱了政治因素的束缚,更多地关注知青在这场运动中道德的迷失,人性的虐杀.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青戏剧是作家谱写的一出出不折不扣的人性悲歌.
(二)边疆风情的本真彰显
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大大消解掉了政治话语的影响,文学本真价值的理性回归为这种文学体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作品除了展示了历史断裂错位下人性的悲剧,还书写了浓郁的边疆地域风情.知青作家大都亲历过"上山下乡"这场运动,在边远荒漠地区生活过,战斗过.对于景物的描写,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塑造,往往更能做到更本真的话语书写.因此,知青戏剧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知青戏剧边疆风情的诗意美主要表现于带有地域特征的环境铺设、营建以及绽放于边疆荒原上美好人性之花的抒写与赞美.戏剧关涉的场景往往是边远或边疆地区特有的自然风物.它们集中于黑龙江垦区、新疆垦区、云贵高原、黄土高原等.把边疆地区的自然风物,美好的人性集中带到中国当代戏剧中来,是中国戏剧作者的一大贡献.这里既有白桦树、地窝子、草甸子、雪爬犁、大烟泡,大酱缸 ;又有原始森林,戈壁荒滩、万里沙海,大漠漫漫,鹰翔碧空,长河落日、湖水荡漾、热带岛屿、椰林沙滩等等.知青戏剧在表现自然美的同时还展示了人性美与劳动生活的悲壮美《.天雪》除了歌颂兵团人的那种坚毅顽强精神外,还有在严酷的环境中,所绽放出的一朵朵美丽而又纯真的爱情之花,尽管,这种爱情之花开放得短暂甚至有的未曾开放就已凋零,但却馨香无比,令人回味无穷.有恋人石牛和毛妮那种爱情的凄惨美.他们风雪之中赶车外出借粮炭,回来后却被冻成了冰坨子,石牛永远地离开了这片荒原.有香兰和马长胜这对准夫妻大无畏的可歌可泣的崇高美.面对残暴越境的暴动分子,为了祖国的尊严,他们以壮美举动护住国旗,在界碑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戏剧还给我们展示了她们的劳动壮美,一种连任何艺术家都很难完成的雕塑美.女兵团战士在夏天大漠中拉犁耕地时,由于补给不足,没有单衣,汗水湿透棉裤,他们就脱光衣服身上涂上了泥巴奋力前行,成为了荒原之中一道永恒的亮丽风景.
新时期的知青戏剧更是写出边疆特殊的地域风情,自然和人性的融合.《天雪》中美丽的雪山,神秘的蓝月,茫茫的戈壁与美好的人性交融在一起 ;《北京往北就是北大荒》戏剧场景的描绘更是诗意盎然 :
达子香迎风盛开,兴凯湖就像万匹野马在撒欢 ;窦婶家院套很大,有果树、菜园、渔网和吃不完也买不出去的鱼.一种和谐安乐富足的农家气氛扑面而来.窦婶家永远都充满着活力,红红的炉火,玻璃上贴着红艳艳的窗花,墙上挂着红辣椒串.窦婶也如北国的自然一样,泼辣、圆滑、顽强、刚烈、坚韧.
在北大荒练就了一种在人类最难生存的荒野边塞中求生的本领,练就了一种无畏的不懈的愈挫愈勇的顽强品质.北大荒知青的这顽强坚毅性格不能不说是窦婶人格魅力对其造成的影响.这种品格是他们人生中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戏剧作家所要表现的北大荒主体精神外化的主旨.
文学永远无法完全脱离政治,问题的关键是作家怎样找寻到它与政治完美融合的契合点,"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7]
这是知青戏剧创作者努力所要追求的.新时期的知青戏剧最大化地消解了其政治倾向带来的负面效应,理性地回归到文学本职功能上去.这是知青戏剧自觉完善的成功蜕变,也是知情戏剧最值得肯定和褒扬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51.
[2]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54.
[3]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7:42.
[4]彼得斯丛狄,王建译.现代戏剧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5]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60.
[7]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3.
- 相关内容推荐
- 探究戏剧艺术上萧伯纳对易卜生的继承与超越2015-03-06
- 舞台灯光在戏剧表演中的功能研究2016-08-16
- 戏剧演出中舞台灯光的影响结论与参考文献2016-08-16
- 探讨张彭春先进的戏剧美学思想2014-09-04
- 山庄戏剧对中国话剧的启示2016-04-06
- 契诃夫戏剧作品中象征的特色2016-06-23
- 象征艺术在契诃夫戏剧中的应用研究引言2016-06-23
- 楚剧表达和呈现的思想与艺术特色2014-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