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比较看中文“美”的词性其及意义
时间:2014-07-18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5733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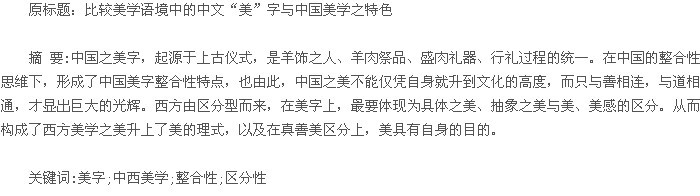
美的观念,首先从美字中体现出来。萨堤威尔(Crispin Sartwell)在其《美的六个名字》一书中,呈现了六个文化中不同的美字所内蕴的不同词义:英语中的beauty 是围绕着渴望而来,希伯来语中的 yapha 是围绕着生长和繁盛而来,梵语中的 sundara 是围绕着神圣而来,希腊语中的 to kalon 是围绕着理念而来,日语中的wabi sabi(侘寂)是围绕谦卑和求缺而来,印第安纳瓦霍语(Navajo)中的 hozho 是围绕着健康与和谐而来 ,六个文化的美字,显示了不同文化的美的特点。同样,中文的“美”字,也有中国文化独特的内蕴,并由之突显了中国美学的特色。
一、中文的美字:起源、词义、特点
中文的美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之中,按照《说文解字》:“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
美与善同意。”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从本质上是味美(甘),再由味美到一般的美。从这里可以想到为什么中国远古文化里。饮食之器、彩陶和青铜如此普遍和辉煌,并成为礼器。后来青铜九鼎成为王朝的象征符号,而“神嗜饮食”(《诗经·楚茨》)成为中国上古之神不同于其它文化之神的鲜明特色,朝廷与家庭的宴请在中国文化中占重要的地位。二是从起源上与羊和大相关。这里的羊不仅仅是羊肉,而是远古之时中国西部以羌为名号的众多的牧羊部落,而羌的一支姜进入中原,成为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皇中的神农,五帝时的炎帝,皆为姜姓。禹兴起于西羌,商的主要对手是羌,姬姓的周与姜姓的太公望联合,使西方的周成为中央王朝。而大,则为远古巫师型领导人。上古领导的力量来源于天,因此,孔子说“惟天为大”(《论语·泰伯》)。上古领导因效法天而成为大,因此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论语·泰伯》)。庄子也讲:“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所共美也。”(《庄子·天道》)大,具体为上古仪式中的巫师型领导人。而在以羊为名的羌姜部落,仪式中的巫师型领导人则体现为以羊为装饰的大人。大羊为美,实则羊饰之大人为美。中国上古时期的大人,除了来自西方的羌姜为羊饰之人,还有东南西北各类不同装饰的“大人”。大皋少皋应为以太阳为饰,如翟、翜、翇、翆、翌、翏、习、翚、翠、翨等,都突出了上部的羽毛。如羿,《说文》曰:“古诸侯也,一曰射师。”还有翇,《说文》曰:“乐舞。执全羽以祀社稷也。”巫和灵,是以玉为装饰的。还有用武器型的器物装饰头上的,如钺、辛、干、瞂。《山海经·海内西经》曰:“凤皇、鸾鸟皆载瞂。”《太平御览》卷八十引《春秋元命苞》曰:“帝喾戴干。”《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引《应瑞图》曰:“颛顼首戴干戈,有文德也。”而皇帝之“皇”和夏朝之“夏”,在古文字中,都是有着装饰的大人形象。可以说,中国上古东西南北各种仪式中有着不同装饰的大人,在多元一体融合成华夏的进程中,最后是羌姜的羊饰大人之“美”获得了文字上的胜利。然而,羊饰大人是在仪式中成为美的,仪式是一个整体,因此,从羊从大,不仅是羊饰大人,还体现在盛羊肉的礼器,以及礼器中所盛的美味。而仪式是为了整个氏族部落的利益而进行的,其性质是善,因此,美在词义上的第三层意思就是“与善同意”。《说文》曰:“譱(善),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意。”譱在上古与一种神判仪式相关。当有人争执不下、各言其是时,则由神羊之角去抵,以决定谁是谁非。因此,“譱”的字形是羊在两个言之中。以羊为神判应是羌姜族的仪式,在其它部落中则有以牛、鹿、廌为神判的。
后来由羊而来善,占有神判中善的词义。而义即古文中的仪,象征整个仪式的形式外观。美善仪,是一种由上古仪式而来互文关系。
由《说文》述说且在远古历史中可以得到印证的美字相互关联的三层含义 ,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美来源于上古仪式中的整合性。美是羊饰之人、盛羊肉之礼器、礼器中之羊肉、羊人以诗乐舞食的方式行礼之过程。以及仪式体现出来的由美内蕴着的善的内容和目的。形式中的羊人、羊肉、礼器是空间性的,行礼过程的诗乐舞表演则是时间性的,仪式时空合一对应着天道的时空合一(律历)。因此,上古仪式的整合性之美,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原型。
其次,中国之美的整合性是以天人合一中的人为中心的,在上古仪式中是以人神合一中的羊饰之人为核心的,饮食之器、器中饮食、行礼之乐,都围绕着这一核心而组织起来。上古仪式进一步演进到夏商周中央王朝建立之后,羊饰之美演进为以帝王之美为中心的朝廷之美,即由都城宫殿陵墓、服饰衣冠、旌旗车马、礼数威仪、诗书舞乐形成的自身整合性结构。当士人在先秦崛起,形成士人的文化定性,继而在魏晋形成自身的审美趣味之后,与天合一和与时消息的士大夫的庭院成为中心,展开为诗、文、书、画、琴、棋、园林,再加上宋代以后的茶、文玩待的整合性之美,构成了士人与朝廷有所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美学体系。宋代以后,经济高涨,城市繁荣,印刷媒体的产生,以城市勾栏瓦肆为中心和以乡村戏台为中心的娱乐体系兴起,出现了小说、戏曲、版画、年画等大众审美形式。特别是小说和戏曲,前者以叙事者为中心,后者以舞台为中心,形成了天地人各门艺术一体的整合性之美。中国之美在演进中展开来的三大相互关联的美学体系,是整合性的。
再次,中国之美的整合性体现在五官美感的平等上,其特色通过对味美的强调而鲜明地体现出来。《说文》不但有“美,甘也”,以及反过来的“甘,美也”,还有“旨,美也”。在《尚书·说命中》有“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传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这里“旨”已经提升成为一般性的美,词义类似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里在讲一种乐之前说一个定性的感叹词“美哉”。味在中国之所以属于美感,不仅在于古人对美味佳肴旨酒有一种独特的品赏力,也不仅在于因这一美味嗜好让中国饮食体系特别地丰富,更在于中国文化的整合性。《国语·周语上》讲:“味以行气,气以充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这句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味与领导人的言论和国家的政治相关,更在于味与气的相互转化。中国的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人禀气而生,也是一个气的人体。就像人之大与天之大相通而让人之美具有了宇宙普遍性一样,味与气的内在同一性也让味之美具有了宇宙之美的普遍性。
最后,中国的整合性之美体现为“美与善同意”,即把美与善相关联,其结果是美成为外在的善,善成为内在的美。即美是外在的漂亮,善是内在的德性。这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复杂内容和非常丰富的复杂演进。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只有当是善时,才具有正当性,成为值得追求的正面之美。而当美背离善时,就失去了正当性,成为负面之美。正因为这一性质,在《尚书》中很少看到“美”字。整个《尚书》,美字只出现了两次,一是《说命下》的“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二是《毕命》的“商俗靡靡……实悖天道,敝化奢丽……服美于人”。两篇都是梅赜文本,如果像不少学者那样视其为伪,那整个《尚书》就没有“美”字。当有必要出现美字时,用的是内含着善而又具美感的“休”字。“休”字贯穿于整个《尚书》之中,共出现 39 次,几乎全被西汉的孔安国(传)和唐代的孔颖达(疏和正义)明确地注释为“美”。同样,在《诗经》的《颂》《雅》中也没有一个美字。《颂》中要表达美之义时,用得最多也可以说是《颂》中美的核心的是“皇皇”;《雅》中要表达美之义时,用的最多也可以说是《雅》中美的核心的是“威仪”。
中国美学以上四个特征,都与中国文化的整合性思维方式有关,在中国美学的四个特征中,五官美感平等,造就了中国之美在一切领域的泛化,美与善同意,造就了美字进入不了中国美学的价值高位。这两大特点,在与西方美学的比较中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
二、从中西比较看中文“美”的词性其及意义
中国文化讲究整合性,一个字也是如此。在中文中“美”既是名词(如西施之美、居屋之美、山川之美),又是形容词(美言、美德、美差)、感叹词(美哉,好美)。
而且美不仅指客观之美,还指主体的美感,如“色之于目也,有同美焉”(《孟子·尽心下》),“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庄子·齐物论》)。美只一字而可多方流动,正是中国整合性思维的体现。在西方,美,首先要分成名词(美)和形容词(美的),如希腊文中的χαλλοζ和 χαλóζ,拉丁文中的 pulchritudo 和 pulcher,英文中的beauty 和 beautiful。前者更强调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后者更突出客观事物之美与主体感受的关联。进而,有个别事物之美和普遍一般的美,这样名词也需要两个:一个用来指个别的具体之美,一个用来指一般的抽象之美。这里,西方语言基本上用形容词充为名词指具体之美,而原有名词作抽象之美。
在区分性思维的指引下,西方关于美字的使用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别高级感官(视听)而来的美和由低级感官(味、嗅、触)而来的美。亚里士多德宣称,只有高级感官感到愉快的才算美,而低级感官感到愉快的不算美。二是心灵是高于感官的,因此心灵感到愉快的也算是美,比如柏拉图的着作里常看到的制度之美、法律之美、道德之美、思想之美。用现代美学的眼光来看,如果说第一方面是力图在把美与非美区别开来,那么第二方面又是在把美与非美混淆起来。在古希腊和中世纪,这两个方面交互出现,似乎与中国古代一样都是一种泛美的观念,但其实是不同的。西方的泛美观是在区分性的原则中出现的,而中国的泛美是在整合性的原则中出现的。中西之间的一个最大差别在于美由于区分而走向文化的高位,这就是柏拉图的美的理式的出现。
西方区分性原则在美上的进一步演进,在近代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用于纯粹审美意义的美。这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在哲学上的整体区分,真、善、美形成各自不同的领域。在主体方面,真对应理性之知,善对应意志之意,美对应感性之情。在知识上,与真对应的是逻辑学,最典型地体现在科学和哲学上;与善对应的是伦理学,最典型地体现在宗教和道德信仰上;与美对应的是美学,最典型地体现在艺术上。这样,美一方面仍然像古代一样,与低级的感官快乐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与古代不同,与科学、哲学、宗教、伦理区别开来,形成了(从主体上说的)美学或(从客体上说的)艺术哲学。这一区分,一方面在于艺术的演进,即经过古代的与手艺和科学不分,到近代的与手艺和科学区分开来,形成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等美的艺术,其目的就是追求美;另一方面在于美感的演进,在近代它既不同于一般感性感官的快感,又不同于理性概念的快乐,而是一种超功利概念的快乐。而这一超功利超概念的快乐,只有在艺术上才可以纯粹地获得。美感与艺术的结合,构成了西方美学即艺术哲学。西方由区分性而来的美,与中国由整合性而来的美的最大差异就是西方的真、善、美是平等的,三者共同构成了宇宙、上帝和人的整体;而中国的真、善、美是有等差的,美只有体现真和善时才是正面的,偏离真和善时则是负面的。因此,中国的美被从文化的高位上排斥出去,这就是《尚书》和《诗经》的《雅》《颂》无美字的原因。
在西方的区分性原则中,美可以自身就是目的,从而真、善、美可以并列,而在中国的整合性原则中,美如果以自身为目的,就有可能偏离文化的方向,只有以善为目的,美才是值得肯定的。
三、从美到美学:美学语汇与中西美学的演进
西方对美字的区分,重要的在于两点:一是具体之美和抽象之美的区分。在这一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美的本质是什么,从而把作为现象的具体之美与作为本质的理式之美区别开来,开创了西方美学追求美的本质而形成美学体系的基本理路。二是美与美感的区分。美感是感觉印象与思想的合一,因而既是感觉又带有认知理性元素于其中。当西方近代重要思考由外在感官与内在感官的趣味问题之时,美的问题变成了美感的问题,从主体上来讲,这就是从夏夫兹伯里到康德用美感(区别于感官的快适和概念的愉悦)来对美进行定义。从客体上讲,就是巴托对美的艺术范围的确定,来对美进行定义(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美就是区别于真和善的与美感经验相对应的客体)。而主体的美感和艺术的美感,都远远不止于对美之感,霍布斯、丢勒、歌德、西布里等都提出过多种多样的美学类型,当时最着名的是柏克和康德提出的美与崇高。20 世纪理论家回望过去,认为除了美与崇高之外,还有 pictur-esque( 如画),构成了不同的美感类型。然而,无论是美之感、崇高之感,还是如画之感,都属于 aesthetic(美感或审美感或美学感)。而当 aesthetics 于20 世纪初进入东亚,日本学人用汉语“美学”去与之对译,中国学人又确认了这一对译。而西方的 aesthetics(美感学)之所以在中文里成了美学,在于美字在古代汉语里兼有美和美感两种词义。只有当在现代汉语里,特别是经过苏俄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汉语学术语汇的规训之后,美与美感区别开来,“美学”对 aesthtics 的对应才变成了一个问题。
对于本文来说,需要思考的是:西方美学基本是由具体之美和抽象之美与美、美感的区分而来,而中国之美,则是由一个美字圆转展开,这构成的中西美学各自的特质是什么? 另外,西方美学由于区分性而把美升到哲学的理式高度,而中国之美由于整合性却升不到文化之道的高度,这里面内蕴的中西美学各自的特质是什么?
最后,讲一个与中西美字甚有关联的当代美学的演进问题。西方文化从近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正在从区分走向整合,在美学上,以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三大领域突显出来。
这三种美学都要求从康德的纯粹的审美感受中超越出来,而走向一种与功利、生活、自然乃至与概念相关联相互渗的美学,这好像是走到了与中国古代的整合之美上来了。但是,这只是一种肤浅之见。西方美学无疑会在全球互动中超越自身,也会吸收中国古代整合性美学的长处,然而并非离开西方由区分性美学带来的特色。因此,中国当代美学面对西方美学的新转向时,对其实质应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要清楚,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是一种朝向 beauty(美)的方向的演进,而 aesthtics(美感)除了美之外,还有更广大的领域,比如在 20 世纪以来有着巨大影响的荒诞、恐怖、媚世、堪鄙等。因此,展望未来,从西方 aesthtics(美感)的角度,而不从中文“美”的角度去思考中西美学乃至全球美学的演进,是甚为重要的。而要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梳理中文“美”字的起源、内容、特点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又显得重要起来。
参 考 文 献
[1]古文字诂林编写组. 古文字诂林(第四册)[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张法. 美:在中国文化中的起源、演进、定型、特点[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3]李学勤. 尚书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波兰]塔塔尔凯维奇. 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M]. 刘文谭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相关内容推荐
- 中西味觉审美特点差异成因2016-05-07
- 中西味觉的审美差异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2016-05-07
- 中西审美观、审美精神及审美情趣的对比分析2016-01-26
- 中西艺术早期对自然的学习2015-07-27
- 封孝伦和袁鼎生的生态、生命美学思想比较2014-09-10
- 中西方审美之对比及当代美之思考2014-09-29
- 海洋在中西方文化中位置与特点及中国海洋美学建立2014-07-18
- 中西美学中有与无的差异2015-09-01
- 上一篇: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差异分析
- 下一篇:从“美”字义的理解谈中国古代美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