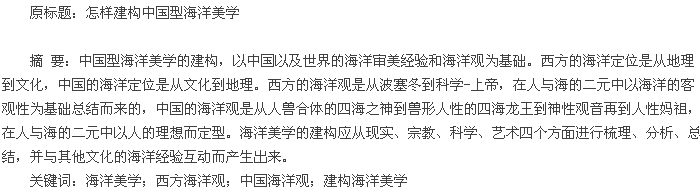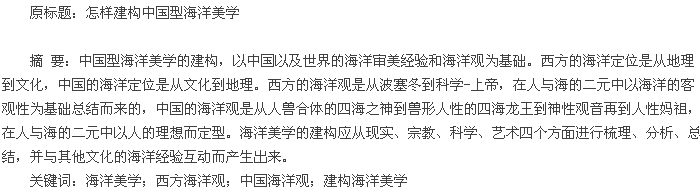
一、建立海洋美学的文化基础
海洋美学在中国的提出,显示了海洋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时代日益为中国人所认识。所谓海洋美学,就是把海洋作为审美对象。海洋为什么是美的,由人的心理中的审美心理结构决定,而审美心理的建构,在相当的程度上,由人的文化模式决定。中国海洋美学的提出,同时意味着中国面对海洋的审美心理的建构。建立什么样的海洋审美心理就与人类的海洋观联系起来,因此,中国型海洋美学的提出,要重新审视中国和世界的海洋观。
当美国学人站在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立场,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世界史的演进,于是世界成了从地中海时代到大西洋时代再到太平洋时代的演化史。
这一演化史中的三个关键词,就最前面的词而言,从美国人提出太平洋时代,日本学人即以应和以来,到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起飞,再到美国、中国、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1989年亚太经合会(APEC)的成立并很快把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都包括进来,世界的主轴和动力已经转到了太平洋。一个太平洋时代已经开启。就大西洋时代而言,自现代性在西方兴起,现代型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首先从西欧向美洲扩张,全球的中心围绕大西洋建立起来,环西岸是欧洲列强,环东岸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而且从中产生美国这样的新兴大国。虽然大英帝国的殖民区远伸到印度、南亚、澳洲,但整个世界事务是由环大西洋的国家主导的,也可以说大西洋时代。
越向古代就越有问题。地中海文化自公元前700—前200年的繁荣,只是轴心时代的三大中心之一,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崛起就有不同于地中海文化的特点,因此,地中海时代只是表明作为三大中心之一的地中海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不过,地中海文化以海为中心的特点,显示了其与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之处,而且为引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西洋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意义上,从地中海时代到大西洋时代再到太平洋时代这一世界史观,开启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太平洋时代的海洋观是由西方主导的海洋观。日本紧随美国提出太平洋时代,也是在其公然宣称脱亚入欧之后。而太平洋时代的真正到来,不仅是美国和日本以及由英国文化而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中国、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太平洋西岸的拉美国家,因此太平洋时代的海洋观念是多元的。对于中国的海洋美学来说,认识人类海洋观的多样性与认识人类海洋观的共性同等重要,对于中国型海洋美学的建构而言,首先应认识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西方的海洋观和中国源远流长内蕴深厚的海洋观。
虽然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于旧石器时期就已经建立,但由神庙文化标志的人类文明则基本是大河文明,除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是山地丛林文明,四大文明都以河为核心。埃及是尼罗河;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到巴比伦辉煌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是恒河与印度河;中国是长江与黄河。然而由神庙时代到轴心时代,产生了哲学突破的三大文明显出了各自的差异。看印度文化中的各种宇宙图式,宇宙的中心是须弥山,然后是四大洲,然后由海水环绕,宇宙是以山为中心,地在四围,海在边缘。看中国的宇宙描述,以京城为中心,然后是四方各州县,边缘是四海。而在古希腊,绘制世界地图的第一人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r,前610—前547年)就把希腊放在地球的中心,而古希腊从欧洲大陆东南伸向地中海,这样地中海基本上成为世界的中心。
作为希腊地理学的数学传统之祖的阿拉克西曼德绘制的世界地图是如此,作为希腊地理学的文学传统之祖的赫卡特(Hecataeus,前550—前476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也是如此。“所有希腊的思想家都认为对称布局是完美的属性之一,最为对称的形状就是圆形。”
因此,希腊的世界地图大多都画成以地中海为中心,围绕着海的是欧、亚、非的陆地,再外边是大洋。因此,三大文明都有海,但海在三大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同的。但无论海在各大文化的宇宙结构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各大文化都在自己的模式指导下进行海的文化运作和美学运作。为紧扣本题,且略去印度文化的海洋观,只看中西海洋观的差异。
二、海洋在西方文化和美学中的位置、性质、功能
地中海是古代西方世界的中心,各大文明都围绕着地中海进行扩张,希腊的荷马两大史诗都是海的主题。《伊利亚特》是沿着海路的对外征伐,《奥德赛》是通过海洋的阻扰而回归故乡。这一去一来的循环,都是围绕海而进行的。海风、海浪、海神、海妖,更主要的是与四者相关联而且在其中载沉载浮、勇敢拼搏的人,构成了西方之海的主要形象。大海既带来财富,又带来危险,大海美丽而又充满诱惑,贪婪而又内蕴凶残,构成了西方之海的主要性格。海商、海盗、海霸作为海洋美学的三大主题在地中海的东西南北五彩缤纷地闪耀。希腊与波斯的争霸主要在海上进行;亚历山大帝国首先是统制地中海,然后向陆地深处进军;罗马与基太迦的斗争就是围绕着地中海上的霸权争夺。带着利益和荣耀的斗争性,以及由斗争而带来的和谐,在和谐中体会到形而上理念的深邃,构成了地中海文化、哲学、美学的核心。基督教归化了西欧,十字军东征的目标仍然是地中海边的圣地以及海边城市中的财富。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古代的地中海中心造成了西方的海洋文化性格,使得当现代社会产生时,西方列强开始了由大西洋向全球的帝国-殖民-霸权-科技-经济-现代的大进军,而在这一全球和殖民争夺中,英国继西班牙、荷兰、法国之后成为最大的海上强国,而后起的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继英国之后成为最大的海上强国。
所谓的大西洋时代,就是在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列强主宰整个世界的时代。从海洋观来说,大西洋时代的海洋只是地中海时代的扩大版而已。虽然因上帝、理性、科学的加入而在外在旋律上有所变化,但在内在精神上却始终如一。笛福《鲁宾孙漂流记》(1719)体现了人在海上独立地创造文明的精神。海明威《老人与海》(1952)写出了人在海中失败的坚强。约翰·沁的《骑马下海的人》(1903)中一家三代都死在海中而义无反顾。麦尔维尔《白鲸》(1851)中亚哈与白鲸同归于尽写出了人与海斗的决心。康拉德小说中的诸多船长在海上艰辛中的大智大勇,与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红海一样坚定和伟大。库柏的海洋三部曲《领航人》(1824)、《红海盗》(1827)和《水妖》(1830),从标题上可以看到古希腊海文化的身影。然而,在近代西方走向海洋的惧海与喜海、斗海与玩海、恨海与亲海的多重交响曲里,一种科学的精神突显出来。比如《白鲸》里突出了关于鲸的体系性的科学知识结构,又如凡尔纳《海底两万里》(1869—1870年)中以科学的框架展现了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地中海、红海以及北冰洋和南极海域的海上海下奇观。
大西洋时代的海与地中海时代的海比较起来,从神话向科学转化。海呈现的仍然是美丽和神秘,只是这美丽和神秘的后面不是海神的兴风作浪,不是海妖的诱惑歌声,而是大海的自然属性。在古希腊,除了波塞冬这一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大海神,还有各种各样的海神:奇观之海神陶玛斯(Thaunas)、破坏之海神福耳库斯(Phorcys)、危险之海神刻托(Ceto)、力量之海神欧律比亚(Eurybia)。在近代,海的各种现象后面没有了海神,但海仍然充满奇观、力量、破坏、危险。而现代人用以面对大海的不是神话的知识体系,而是科学的知识体系,大海的威胁不是来自海中的神灵,而是来自未知的自然。然而,面对大海,现代的西方人与古代的希腊人一样,有不怕困难的巨大勇气和不服输的斗争精神。现代人面对海洋的斗争性,在精神气质上仍然与古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Alkaios)写的诗歌《海上风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前浪才去后浪涌,拼命挣扎抵挡;
船墙须堵严,方进安全港。
不要失措张皇,决斗正在前方;
以往挫折切莫忘,此番定把好汉当。
正是带着这样的精神,西方文化从大西洋时代进入太平洋时代。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中,海洋在西方人的眼中一以贯之而又多方面地展开。只是在太平洋时代,海洋不再像大西洋时代那样仅由环绕大西洋的西方列强去面对,而是由环太平洋的不同而多样的文化去面对。因此,多元的海洋观将在这里展开多方面的理论互动,而中国的海洋观正是这多元中的一种。
三、海洋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与特点
中国文化自远古伊始就与海洋相联,在中国滨海由南到北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西东兴遗址,海南三亚落笔洞、东方、乐东遗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遗址,台湾八仙洞长宾文化、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营埔文化和凤鼻头文化遗址,福建富国墩贝冢遗址、壳丘头遗址、昙石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龙口遗址,即墨遗址,蓬莱、烟台、威海、荣成遗址,以及辽东半岛沿海的小珠山遗址等,都是极为典型的贝丘遗址(所谓贝丘遗址,就是在史前人类居住过的地方,出土了大量人类食后所抛弃的贝壳和各种蚌类的堆积)。
而在1.8万年前与海有相当距离的北京山顶洞人的众多装饰品里就有穿孔海蚶壳。而由石之美而来的玉和由蚌之精而来的珠,构成了中国人以珠宝冠名的美的系列。与海有关的珠与贝,前者成为美饰的系列,与珠有关的字都具有美饰的性质;后者成为财富的系列,有贝字旁的字多与财富相关。这两个系列在汉字上的定型与远古时代先民与海的长期接触和实践相关。此后,夏之时,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诗经·商颂》讲契的孙子相土的海上活动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鲁颂》讲鲁人的功劳有“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春秋之时,齐、楚、吴、越,皆成为海上强国。《左传·僖公四年》齐恒公攻楚,楚成王向齐桓公传话,用的语言是:“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用北海和南海来彰显两国的特点,表明海洋实践在两国的观念中占有的重要位置。
虽然中国的海洋实践开始既早且多样而丰富,但中国的文化模式决定了海洋在中国文化中的性质。如果说,西方文化在地中海起源时,其宇宙图式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四周包围着陆地,陆地之外是大洋。而中国的世界图式,以《尚书·禹贡》为例,虽然此文列出了中国地理上的九州,但九州又是一个东西南北中的五方世界,即以京城为中心,东西南北四面展开,每五百里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里,五服的具体里数更应看成是一种空间秩序象征,突出了五方结构,即以京城为中心,然后是东南西北四方,然后是接连四方边缘的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最后是四海。整个世界是由海所包围的。海既是陆地之边,也是文化之边。战国时思想家邹衍,不以儒家的京城四方四夷四海为然,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这个大九州说,仍然是东西南北中的五方世界,仍然以四海为东西南北的陆地之边缘。
在世界图式中作为边缘的四海,在中国的综合性-关联性-互渗性思维中,首先,构成世界边缘的实体。如《尚书·益稷》所说:“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又如《尚书·立政》所说:“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因作四方边缘的四海的存在,中国型的天下图式得以完成。其次,从边缘这一本质立论,在边缘四海必然居住着的在文化上低于华夏的夷蛮。《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张华《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水中,盖无几也,七戎、六蛮、九夷、八狄,形类不同,总而言之,谓之四海。”这里用六七八九来称谓蛮、戎、狄、夷,形容四夷种类之多。越远越近海,其夷性越重。最后,由于海与夷的关联,夷性的本质同时也是四方边缘的地理本性。因此,不从中央到四方来看,而从四方边缘的四海来看四方,四海又可用来指四方。郑玄对《周礼·校人》中“凡将事于四海山川”,注曰:“四海犹四方也。”由于有边缘性的四海,而完成了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天下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边缘可以从本质上定义,但难以从具体上把握。因此,作为五方世界边缘的海,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三大文化特征。
第一是夷。夷这里主要突出的是既非华夏文化且低于华夏文化又尚未被华夏文化所归化的性质。因此,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与对海的夷性的定性和认识相关联。两千年间,这里产生了非常丰富的故事。“海”成为中国文化“以德服远”、“天下归心”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是荒。荒主要彰显的是处在遥远的边缘,《广雅·释诂一》曰:“荒,远也。”
五服中,最远之处为荒服。朱熹对《离骚》“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注曰:“四方绝远之国。”《尔雅·释地》释“四荒”曰:“觚竹(孤竹,相传北方山戎所居之地),北户(极远的南方),西王母(最西),日下(东方日出之处),谓之四荒。”
贾谊《过秦论》把“囊括四海”与“并吞八荒”相对,点出了海作为荒的特点。“荒”是不同于理性的荒唐,同时又包含着未能认识或不可认识的一面,刘熙《释名》说:
“海,晦也。”晦,即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晋人张华的《博物志》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晦又有奇特幻化的一面,《国语·晋语》就说:“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海市蜃楼则是海之化的典型体现。从而显出第三点:奇。奇不仅是景象之奇,如曹操《观沧海》讲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还有事物之奇,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中包含的鲛人故事。更有因其荒而产生的蓬莱神话与海外仙话。正如白居易《长恨歌》讲的“忽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一样,海的由远而荒而奇,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关于海的多方面的丰富故事。而海的夷、荒、奇,漫衍出中国文化关于海的独特而多面的观念:海之夷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教化对象,郑和下西洋既是中国朝贡体系的完善过程,又是中国文化向海夷的教化过程;海之荒产生了中国文化关于海的无穷想象;海之奇不但有海上丝路而来的八方宝物,还有海上奇观而来的神灵故事和奇幻传说。海即是边缘,具有夷、荒、奇的特点,但中国的综合性关联性思维,又用了多种方式来把握海的特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中央的最中间处,朝廷的宫苑里,用园林的艺术方式安排了海外仙山。虽然《三秦记》讲“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是否确切有争议,但汉代宫苑筑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则是确实的。至此而下,直至明清京城中南海里的瀛台,呈现了海既在四方的边缘,又被放在中央,这样一种中边互渗的观念,体现了容纳万有的中国文化对海的把握与玩赏。
四、中国古代海洋观念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以上关于中国海洋观念的特点是从中国自身之中得出的,从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出中国海洋观念的另一些特点,而了解这些特点,对于建构中国型的海洋美学也是必要的。
第一,中国关于海的定义,首先是确定的文化规定,然后由之引出地理概念。这与西方的海洋首先确定地理现象,再从文化观念赋予地理现象以文化性质截然不同。中国的四海观念由观念性的五方模式而来,这一模式把海规定为华夏边缘。作为华夏边缘的具有夷、荒、奇特点的四海,在东、南两面皆可以实指,因为中国东面和南面具有海的地理事实。北海和西海却一直难以确定。北海最初是指渤海,即春秋时齐桓公所谓的其国处北海,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即讲齐是“表东海”。中国古代东海又往往被称为南海。但东南二海在地理上是确切的,北西二海在地理上却甚不确切,由于文化模式的要求,又必须把北西二海从地理上标志出来。于是《史记》将中亚的里海称为北海:“奄蔡……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俄罗斯东部的贝加尔湖称为北海,因此《汉书·苏武传》讲苏武在北海牧羊。西海呢?《山海经》的《南山经》和《海内经》都讲到西海,前者讲“《南山经》之首曰鹊山。
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后者讲“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国名曰壑市;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国名曰泛叶”。沙与国在何处,皆无从考,从而有西海之词却不知何处。西汉王莽时期,羌人献鲜水海(即今青海湖)和盐池(今罗布泊),遂把前者定为西海,把金城郡改置西海郡。这是从海为华夏边缘这一本质内涵引申而来的。随着西域开通,中国对丝绸之路上的地理知识日益增长,西海为何,就依照华夏边缘这一核心本质而重新确定和改动:“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
以今地理度之,当时葱岭以西诸河流西流入咸海或里海,故西海非今咸海即里海“。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
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其强盛时占有今叙利亚、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和印度河以西,故此“西海”应指今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即印度西北部。《水经注》曰:“雷翥海,即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犁靬之东,东南连交州海。”条支以西的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东汉与魏晋时即指罗马帝国,南北朝及隋唐指东罗马帝国。大秦又称拂菻,隋唐时,“西枕西海,南枕南海”,“西海中有市”。从隋唐时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来看,此处西海,当指地中海。
无论西海的地理怎么变,其西海的命名都围绕着华夏边缘这一核心进行。由西域向外展开来的各地的湖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海,除了华夏边缘这一文化因素外,中国文化关于海的性质之观念也产生了作用。这就关系到中国文化关于海的另一特点——第二,中国关于海的总体性质、基本结构。
在中国天下观总体里的海,其整体性,是用“水”来总括的。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讲:“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
是以水为根本来进行的宇宙生成,由中心太一(天帝北辰)生成水、天、地。这是一个天上地下的整体。阴阳五行中,水是五行之一,与金、木、火、土构成一个整体。水的变化在宇宙的整体变化之中,《庄子·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这是一个地(北)与天(南)的运动,同时又是鱼与鸟的互变。在这一水的总体性质中,溪、沼、湖、泊、江、河与大海具有同质性,因此,湖海、河海、江海,可以同用。李斯《谏逐客书》云:“河海不择细流,故以成其深。”
细流进入黄河,众河进入东海,其理一也。水的最高级是有龙居住,而小的水池、中的江河、大的四海,皆可以有龙,刘禹锡《陋室铭》说“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样,西域远处的湖泊被命名为海,紫禁城中的湖被命名为北海、中海、南海,不仅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把湖称为海有关,也不仅在于这样用有文化的象征意义,还在于中国文化中水的同一性,以及中国思维关于结构中各部分的关联性的互渗性。正因为中国之水的同质性,中国之海是与江海同质的水,而非与陆地对立的海。从水的总体性质看海,也是中国文化中海的重要性质之一。
第三,中国之海的性质和结构,体现在语汇结构之中,这里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海与洋这两个概念。在西方,洋大于海,印欧语言里,海是mere,既可指sea(海),又可指lake(湖)。反映的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原有观念,当印欧民族来到地中海边,产生了希腊、罗马等文化,进入地中海沿岸各文化的文化互动和竞争,共创了辉煌的地中海文化,海就显示了自己的特征。在希腊神话中,宇宙分为三界,天、冥、海。海神波塞冬作为海之王,彰显了海的重要性。而希腊语的okeanos(洋)则是更大的海,洋,作为与地中海相对的词,围绕着整个大地,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而在中国古文里,海是四方的边缘,最大。洋在《说文解字》、《山海经》、《玉篇》中都是一条河之名。洋在古汉语里着名的不是作为水名,而是作为形容词,《诗经·卫风·硕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毛传曰:“洋洋,盛大也。”《庄子·秋水篇》里河伯“望洋向若而叹”,这里“望洋”作为词组解,释义甚多。而把“洋”作为单词,《康熙字典》解释为“澜也”,即海的盛大波澜。引而申之,《诗经·大雅·大明》讲武王伐商之时,“牧野洋洋,檀车煌煌”,“洋”为广大貌,《中庸》“洋溢乎中国”义同。总之,洋可以形容湖水、河水、海水之貌,而不是海的同义词。《新唐书》、《旧唐书》的《地理志》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量涉及海上丝路,但只用“海”而未用“洋”。有“东南海行”、“南入于海”、“缘海东行”等语句。入宋之后,海上贸易日趋重要,对海进行更细的划分随之重要起来,徐兢在宣和五年(1123)出使高丽,作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可以看到关于海洋语汇的变化。书中卷三十四至三十九讲“海道”的一至六,可见海是总名。在海道中,除了经过各种山、礁、屿、岛等外,还经过了苏州洋、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这些用洋命名的水域明显是海的一部分。但洋虽是海的一部分,还是海,在抽象的意义上可以用“洋”字代替“海”字。于是出现“风正即发洋”、“放洋得顺风”、“洋中不可住”、“出洋过苦苦苦”、“望洋再拜”等“洋”与“海”完全可以互换的语用。
元代进一步将“海南诸国”分为东西洋。有的文献如陈大震的《南海志》,则更细分为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等。
纵观元代有关着作可知,当时的东、西洋划分,以今马六甲海峡为界,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西洋水域(北印度洋)似以印度半岛南端故临为界。其西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东非沿海等称西洋(或大西洋),其东的孟加拉湾为小西洋。东洋水域(西太平洋),以渤尼为界,其西称大东洋,其以东则称小东洋。
中国沿海水域,如上文涉及过的,有白水洋、青水洋、黄水洋、黑水洋、莱州洋。在南海中,有七洲洋(西沙群岛)、乱礁洋(浙江定海之南)、昆仑洋(越南南端东面海上)等名称。总而言之,洋小于海。这在明代的《职方外纪》中有明确的表述:“从大东洋至小东洋为东海,从小西洋到大西洋为西海,近墨瓦蜡尼加一带为南海,北极下为北海。”
此书为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艾儒略所着,但明代传教士写书是与中国士人合作,在中国士人自认为也被传教士们承认明显高于西方文化的明代,此书的合作者庞迪我和熊三拔的中国观念和中国语汇影响了艾儒略的定稿。艾儒略在坚持西方地理学的同时,顺从了中国的五方世界图式。与艾儒略的调和中西相一致,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明中把在西方洋大于海观念中的oceano(葡萄牙语的“大洋”,即英语的ocean)用音义并用方式译成中国观念的海大于洋的汉语“何摺亚诺沧海”。西方的洋大于海与中国的海大于洋,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语汇表述问题,更是一个文化上的观念模式问题。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海是与夷联系在一起的,而鸦片战争以后,当西方打败中国,海洋上来的西方人否定自己的“夷”性,要求用“洋”来代表其先进性。1858年的《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以后涉及西方列强之处,一律不得用“夷”字。中国被打败之后而奋起直追西方,让“洋”字与先进关联起来。西方来的东西,汽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雨伞叫洋伞,西式学堂叫洋学堂,朝廷处理与西方相关的事务叫洋务,新型的军队叫北洋水师和北洋新军,西方人叫洋人……总之,由海上来的西方的人、事、物,不再与“夷”(边缘、落后、低级)相连,而是与“洋”(中心、先进、高级)等同。而世界图式也由海大于洋的中国型地图变成了洋大于海的西方式地图。然而,理解中国从古代的海大于洋到现代的洋大于海的语汇转义,以及由这一转变所内蕴的复杂内容,对于当前的海洋美学建构也是重要的。
第四,海的浩大、变幻、难测,从远古以来就产生了海神观念,而中国海神与西方海神的不同,构成了中国海洋观念的独自特点。西方的海神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他作为海的主宰,管领着海妖、海怪等整个海族。自己手执三尖叉,乘坐金鬓铜蹄的马驾车,出没于海之上、海之中、海之底。传说中,当他把三尖叉戳向大海的时候,大海巨浪翻滚,船沉人淹;当他一挥巨手,狂暴的大海又顷刻风平浪静,宛如平川。而波塞冬,正如希腊城邦中的个人,是具有个性的,喜怒无常,以自己的好恶决定海上船与人的安危。海神有时也伸出救援之手,使大海平静下来,佑护航海者安全抵达彼岸。小埃阿斯(Aias)对他不敬,就死在他制造的海难中,奥德修斯不与他搞好关系,他就在其海上归途中设置了重重阻碍。
波塞冬这样的海神,内蕴着西方文化中的冒险、征服、掠夺、欺诈、霸权的基本特征。近代以后,西方人以海的知识和航海科技为武器,在海洋中纵横,进行的仍然是冒险、征服、掠夺、欺诈、霸权的勾当。只是在知识和技术能掌握的范围内就趾高气扬,在知识和技术不能掌握的范围内就或祈祷上帝、听天由命,或归之于上帝的对立面魔鬼,或归之于科技尚未达到的未知与神秘。海神对人的祸福两面,成了由科技能掌握的一面(福)与由上帝(未知、魔鬼)决定的一面(祸)。简而言之,西方的海神,从功能上讲,是从波塞冬到上帝(以及上帝的对立面魔鬼或科学型的未知与神秘)的演进。中国的海神则呈现为从怪物之神到人性化的龙,到佛性化的观音,再到人性化的妈祖的演进过程。从远古到先秦,海神系统地在《山海经》中表现出来,《大荒经》中的东南西北经,分别讲了东海有神曰禺,南海有神曰不廷余胡,西海有神曰弇兹,北海有神曰禺强(《大荒东经》说是禺京)。
这四海之神皆为人面鸟身之类的怪体。后来的着作,如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太公金匮》)也曾把先秦时的四方之神作为四海之神,即东海之神曰勾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薄收,北海之神曰玄冥。但在先秦的理性化中,这些本有丰富内容的神只剩下一个名称,少有形象和事迹,而最与水相关的是龙。龙作为水神,由江河而向大海的延伸,经过佛经把印度的作为水中之主宰的神蛇一词译为汉语的“龙王”一词,龙王一词反过来与中国龙主水和主雨向海的演进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四海龙王观念。在宗教领域,成书于隋唐前后的道教着作《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三《龙王品》中记载了以方位分区的“五方龙王”和以海洋分区的“四海龙王”。在朝廷制度方面,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封四海海神为王: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但以龙为海洋之神和海洋之王,源于远古图腾崇拜中的兽型王,虽然加以理性化,仍带有原始遗性,因此,纵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龙王形象,可以说有好坏、正反、悲喜的不同呈现,这说明,龙王作为具有多面性的海神,虽然有其应有的功能,但并未达到中国文化的理想性。于是由佛教传统而来的观音,在由印度的男相演变为中国的女相的过程中,因其本有的海上性质,海上护航和救难成为其神性功能之一,从而大慈大悲的观音成为护海之神。但护海只是观音千万种功能之一,算是兼职。到宋代,产生了妈祖。观音由印度神系而来,妈祖则是中国本土所生,由人而神。妈祖信仰由福建莆田的海边产生,进而传向中国乃至中国以外的海域,并从民间上升到国家,从宋到元、明、清,得到各代朝廷的褒封,进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妈祖不但在民间福泽广布,而且在郑和下西洋、郑成功和施琅收复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中国文化的海神演进,从《山海经》的人兽混合型海神,到龙王的兽形人性型,再到观音的宗教神性型,最后定格为由人而神的妈祖慈母型上,显出了中国海神不同于西方波塞冬的特点,她由人而来,充满人性,身为女性,满怀母爱,由观音而来,大慈大悲。如果说,波塞冬显示了海在客观上的无常,尤其是与人的敌对性,那么,妈祖则显示了人希望中的理想性。波塞冬的形象是在人与海的二元对立中由海的本性而来的,妈祖的形象则是在人与海的二元对立中由人的本性而来的。中国文化在海神上的宗教和审美塑造上的不同特点,在妈祖这一最后定格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建立中国型海洋美学
回到海洋美学的建构上来。中国的海洋美学,一方面并不是一种新型的美学,而是美学面对的新的领域——海洋,或者说,随着中国文化的当代演进,海洋正在成为文化的重点,从而成为美学的重点,因而海洋审美成为文化演进的重要方面,就此而言,海洋美学只是把美学原理运用于海洋而已。但是当海洋美学进入中国美学视野之时,正是世界美学发生重大转变之时,即从由区分型美学(这种美学以艺术为主体)转向交汇性美学(这种美学以艺术与各领域的交汇为特征),因此,海洋美学的建构在于从各个与海洋相关的方面,特别是从已经具有一定系统性的门类中聚合成一个新型的美学领域。就此而言,如下方面,可以被总汇进海洋美学中来。
首先是现实中海洋的自然景观,从渤海到南海,人们在生产、生活、旅游中对中国广大海域的经验和感受,成为构成中国海洋美学的现实基础。其次是在历史上积累的生活中具有海洋因素的系列,比如粤菜在八大菜系中的独特性之一,是由海味的体系构成的。正是在对粤菜海味的色香味的品尝中,海洋之美浮现出来。粤菜海味系列的形成内蕴海洋美学的中国因素。再次是科学中的海洋,自近代以来,用科学的观念去看海洋,构成了审美心理的主要方面,海洋的科学观察呈现的景观,海上的航海实践形成的经验,海底的科学探测透出的景观,让海洋奇观以科学的方式呈现,并以科学为基础(即只从自然而拒绝神迹的方式)升华出审美经验。复次是宗教的海洋,海洋既有人可以掌握而产生美感的一面,又有人不能掌握而产生悲恐的一面,可以说这也是科学局限的一面和人生充满命运感的一面。在这里,海洋与宗教相结合而产生一种宗教性的海洋美学,在西方这就是古代的波塞冬与近代的上帝在海洋审美中的作用,在中国,这就是龙王、观音、妈祖在海洋审美中的作用。最后是艺术中的海洋,艺术是生活中美感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各门艺术,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摄影、戏剧、电影、电视……有形形色色的与海洋有关的故事,而其中包括了中国人独特的关于海洋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如何从古今的海洋艺术中梳理、分析、总结出中国型的审美经验,是建立中国海洋美学最为重要的一面。
另一方面,中国型海洋美学并不是中国古今海洋审美经验的相加和总汇形成的,而是在面对世界的海洋美学并与之互动之中,特别是现代以来的中国海洋经验已经与世界各文化的海洋经验尤其是西方的海洋经验紧密地交汇在一起,因此,在总结中国由古到今的海洋经验的独特性的同时,如何把中国的海洋经验与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海洋经验结合起来,构成一种面向世界的海洋美学,并以此进入太平洋时代的文化互动,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几条思路说起来很简单,深入下去却很复杂,正如前面讲中国海洋观的特点与中西海洋观的比较所初步呈现出来的一样。因此,中国型海洋美学的建立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1] 何芳川:《太平洋时代和中国》,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 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 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尔雅注疏》,郭璞注,邢昺疏,李传书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 张华:《博物志校证》,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 王念孙:《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朱熹:《楚辞集注》,蒋立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 贾谊:《贾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2] 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国语》,长沙:岳麓书社,1988.
[14] 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5]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7]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 李斯:《谏逐客书》,载《古文观止》,成都:巴蜀书社,2011.
[1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朴庆辉标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20]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修订本),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21] 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
[22] 杜文玉,王颜:《中印文明与龙王信仰》,载《文史哲》2009年第6期.
[23] 叶贵良:《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4] 周晓薇:《古代典籍中的龙王及其文化寓意》,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