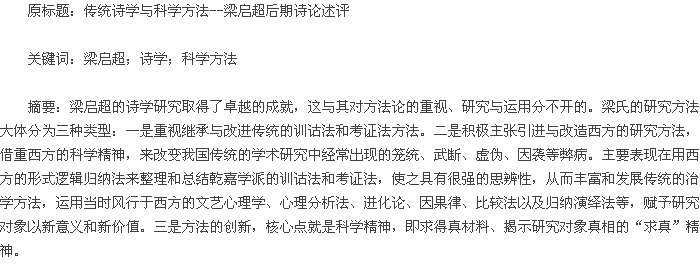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位着作等身的学者。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对方法论的重视、研究与运用分不开的。他是传统方法的发扬者,也是西方科学方法的率先提倡者。梁氏重视方法论,首先集中于研究史学,同时也运用于传统诗学,成效很好,成绩卓着。我们知道,梁氏的国学基础原是很深厚的,对风行于有清一代的训诂和考证的方法,从小就很熟悉,运用也很自如。但是当他发现欧美学界所运用的各种科学方法对治学有很大价值时,便提出学术研究也要 “变法维新”,特别是后期在西游欧美之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运用科学方法。所以他后期的学术成果更丰硕,无论是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越前期。梁氏在方法论问题上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是一笔很丰厚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开发和研究,他的不倦的探索精神和成败得失之处,对于我们今天革新传统诗学研究的方法,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对科学方法的重视与界定
梁启超对研究方法问题的重视与强调,在中国近代甚至上溯到古代的学者中,都是极其罕见的。他的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历史统计学》《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等,都是方法论的专着。他的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就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传统诗学的一部迥异于前人的诗论专着,在诗歌的表情方法上,作了新的分类,别开一新生面。而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以及 《屈原研究》《情圣杜甫》《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论着,其中有运用改善了的传统方法,有运用刚刚从西方输入的新方法,从而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梁启超在学术研究上能言前人之所未言,从许多旧的材料中阐发出新的意义,除了博学和观念更新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重视运用和更新治学方法。孔子所说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两句话,经常被他引用,几乎成为他谈治学经验的口头禅。 “器”是什么?就是治学方法,“利其器”,就是要不断地改善方法,创新方法,使之具有科学性,这是科学研究能出新成果的先决条件。在梁启超看来,“事”与 “器”,学问和方法两者的关系是后者决定前者,前者有赖于后者。在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一文中,梁氏对此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他说:知识是前人运用他们的方法研究出的成果,检验知识和发展知识也要靠改进和更新方法,只重视知识而忽视方法,那就要受前人的局限,永远不能超越前人, “我想亦只叫诸君知道我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必要寻着这个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他还很风趣地引用旧小说中关于吕纯阳点石成金的成语故事作比喻加以说明:
“我不要你点成了的金块,我是要你那点金的指头,因为有了这指头,便可以自由点用。”“所以很盼诸君,要得着这个点石成金的指头---做学的方法---那么,以后才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辨正师傅的是否。”[1]8梁启超在治学中就是得益于这个点石成金的指头,他用以教人的也就是让后学训练自己的指头,使之点石成金。
那么什么样的指头才能点石成金呢?换言之,什么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呢?方法当否在于科学性,在于有无科学精神。梁启超在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把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方法内在的特质看待,使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形神合一,赋予科学方法以明确的义界。他说:“有系统之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2]3这段话,梁氏分三个层次加以说明: “第一层,求真知识”,“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个 ‘真’字”.
如何求真?梁氏说: “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2]4,从种种不同的视角,运用多种方法,去弄清这件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个性特征,以达到对这件事物的真知。但这还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探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求得系统的真知识,才算进入到第二个层次。由表层进入深层,梁启超说: “凡做学问,不外两层工夫。第一层,要知道 ‘如此如此';第二层,要推求为什么 ’如此如此‘.”[3]78怎样才能得知 “为什么如此如此”呢?梁氏提出横向联系和竖向联系两条途径,以探求系统的真知识。“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 “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所谓因果律,“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变化,这叫做因果律”.[2]6换成简单的公式,即 “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4]3但是因果关系又是很复杂的,不是单线 的,而是 复 线的,是 “交光互影”的,“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道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乙、戊……等等关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关系。”[2]6搞清事物间复杂交错的关系。
以求得涵盖面较广的系统的真知识,并由此归纳出近真的公例,从中找出规律,作为行为的向导,从已知来推算未知。对某一项目的研究,至此似乎可以暂告一段落,但梁氏的方法论中,还包含有更高的-个层次的要求,即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要能 ’传与其人‘”. “传与其人”,并不是指使人接受现成的研究结论,而是教人以艺,传人以器,授人以柄。即使人 “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2]7,别人接受此方法,既可以检验此项研究的结果,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也可以应用此方法于他项研究。
以上三点,就是梁启超赋予科学方法一词的主要内涵,也是他方法论的主要的理论框架。从中可见梁氏的方法论,是一个层次分明、步骤清楚、严密周到、有迹可寻的理论系统。梁启超就是应用这付理论框架,从事于多项学科和多种项目的研究,同时他又采用改善和创新了许多具体方法,充实和丰富了这付理论框架的内容,从而在学术活动中,获得新成绩,开创出新局面。
二、对传统方法的运用与改进
梁启超说:“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1]9纵观梁氏在科研中运用方法的事例,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传统方法的应用与改进,二是引进与改造西方的研究方法,三是方法的创新。
现先就第一种类型说,梁氏对于以辨伪存真为要务的传统的训诂法和考证法,是极为重视的,是充分予以肯定的并尽力发挥其效能。所谓训诂法,一是释字义,了解古书字句的确切含意,以便准确无误地运用这些材料;一是注事实,可以和原着材料互相发明。所谓考证法,主要应用于材料上的广搜博考,求异同,辨真伪,并在这些材料上归纳推理以求其真。后者被梁氏称之为归纳考证法,尤为他所重视,评价极高:
“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5]249梁氏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也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肯定乾嘉学派的治学成就: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其归纳考证的程序是: “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6]45梁启超之所以如此重视乾嘉学派训诂和考证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有助于求得真事实。有助于尽可能地占有最可靠的材料,而一切科学的评价和判断,都是建立在全面而又很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梁氏研究某项专题,一般都是分两步走的:一是求得真事实,一是予以新意义和评出新价值。即材料求其真,评价求其新。而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甄别,正是乾嘉学派之所长,运用和改善清儒的考证的方法,就是梁氏求真的主要手段,所以他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 《补编》二书中,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 “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7]80.事实上,清儒的训诂法和考证法并不等于近代科学家所应用的归纳研究法,而是梁氏运用了形式逻辑之归纳法。整理和总结了乾嘉学派方法论的精华,批判和摈弃其弊病(如为考证而考证、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等),成为符合科学精神的新的考证方法。
梁氏运用了已经改善了的新的考证方法,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创立了辨伪书的十二条标准,辨伪事的七条标准和验证真书的六条标准等,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这些辨伪存真的具体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参考与使用价值。
对于传统诗学的研究,梁启超也是采用这种被他改造过的新的考证法,求得新材料,作为进一步研究和下判断的依据。如 《屈原研究》从屈原的作品中的材料,考证屈原放逐后到过哪些地方。从 《涉江》中含有纪行性的诗句,推论屈原在衡山度过较长时间的流放生活,从而对 “峻高蔽目”“霰雪无垠”之类的诗句的解释,就有较为可靠的依据。又如对屈原作品的篇目考查,东汉的王逸和西汉的司马迁意见就不一致,司马迁认为 《招魂》是屈原的作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王逸则认定是宋玉之所作,梁启超依据验真书的第六条标准和证伪书的第十条标准,判定 《招魂》为屈原之所作,至今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难提出有力的反证,而这篇重要的作品,无论是研究屈原或宋玉,都有很大的价值,又如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文,对 《古诗十九首》作者和时代的考证,可谓证据充分,推理严密,前无古人,其结论为现代学者所接受,成为研究 《古诗》乃至五言诗史的重要依据。
总之,乾嘉学派所创立的考证方法,经梁启超用科学的精神和思辨的形式,加以整理、归纳、批判、吸收,扬弃其弊病,吸取其精英,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求真的很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