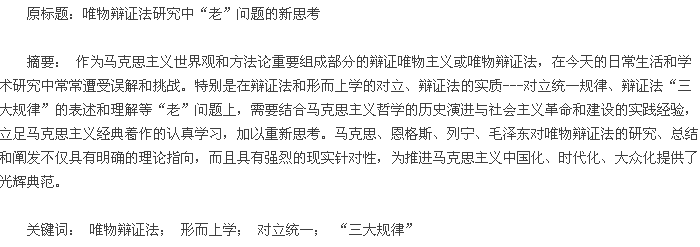
2015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然而,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中,唯物辩证法却经常遭受误解和挑战,以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出现教师避重、学生就轻的现象。
其根源不外乎: 第一,将唯物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要么将其视为无法加以经验证明的玄想而简单抛弃,要么照本宣科或是机械僵化地扞卫其规律、范畴和观点。第二,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片面强调经验实践的决定作用,忽视理论的科学意义。相应地,对于包括唯物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持一种xuwuzhuyi的态度。第三,盲目追随某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在对唯物辩证法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抽象否定、外在贴标签,缺乏自身的理论反思和主体性定位。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代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并且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此,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解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去寻求。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注重“哲学史”和“经典文本”这两个重要环节,“原原本本阅读经典”,在对唯物辩证法研究的历史梳理中澄清误解、回应挑战,“努力掌握看家本领”.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何以可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对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有着明确的界定。作为两种思维方式,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辩证法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 形而上学则用孤立的观点看待世界,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二是辩证法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认为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 形而上学则用静止的观点看待世界,否认事物在本质上是发展的; 三是辩证法用矛盾的观点看待世界,认为矛盾是事物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形而上学则认为每一事物都与自身同一,根本否认事物内部存在矛盾。在种种分歧中,是否承认事物内部存在矛盾,以及如何用概念的逻辑反映事物的矛盾运动则构成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
然而,了解或具备一定哲学知识的青年学生常常对此产生疑问,特别是根据与“形而下”相对应的“形而上”,或者说追求“终极”真理的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解来质疑唯物辩证法。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作为同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待世界,并且否认矛盾构成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是作为哲学自身对于绝对本质、最高存在的探索,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或“元物理学”( metaphysics) .
《易经》中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表达的就是这一含义。由此,自然就会产生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为什么会用“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具有终极本质探索含义的概念来表达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 或者换句话说,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如何对立起来的? 二者的对立何以可能? 对于这样的问题,需要回到哲学史的发展中去得到真正的解决,而非简单的否定或是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分歧。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爱智慧”本身就是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的探索; 而辩证法在此过程中扮演了破除幻象、引导人们走向绝对真理的角色。从词源上说,“辩证法”( dialego) 本身具有“谈话、论战的技艺”的含义。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本身被作为一种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除了被看作是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外,也是认识“理念”的方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除了被作为“研究实体的属性”、“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的方法外,还经常在逻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当然,在古希腊哲学中,这种“辩证法”本身是服务于“实体”、“理念”的认识的,也就是说是从属于“形而上学”的。这一特征实际上也贯穿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之中。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尤其是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才第一次被区分开来。客观地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到哲学史上去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发现其中存在的辩证思维的要素,但是真正将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的,或者说,明确将辩证法作为自身方法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小逻辑》绪论中,黑格尔指出: “透彻理解和认识辩证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整个说来,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和一切活动的原则。
同样,辩证法也是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1]( P156)虽然黑格尔也提到“辩证法在哲学中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他明确指出“在现代,主要是康德又促使人们注意辩证法,使辩证法重新受到重视,而且他是通过我们已经提到的所谓理性二律背反的贯彻这么做的,而在理性二律背反中涉及的问题决不是对双方论据的单纯反复辩驳,决不是单纯的主观活动,而是要指出每个抽象的知性规定只要像它自身表现的那样来看,都会直接转化为它的反面”[2]( P15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强调了辩证法与“过去的”、“康德以前的那些形而上学”( “片面知性规定”) 的差别。严格说来,黑格尔并没有明确指认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歧,准确地说应该是反对一种“旧形而上学”,建构一种以辩证法为原则的真正的形而上学。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概念的运动原则不仅消溶而且产生普遍物的特殊化,我把这个原则叫做辩证法”[2]( P33)。在此基础上,明确指认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歧,并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概念来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超越的是恩格斯。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是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即针对“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3]( P251)。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他们互相间的联系; 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 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 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4]( P360)。早在1859 年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书评中,恩格斯就曾提到黑格尔的思维方法( 辩证法) 的独特性。他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5]( P12)。
这里自然也就引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概括起来,我们可以用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颠倒来加以解释。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到的,“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他( 黑格尔) 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 来,以 便 发 现 神 秘 外 壳 中 的 合 理 内核”[6]( P22)。正如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评价( “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 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的完成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探索历程,这一点需要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实践加以分析展开。
由此可见,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是专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所涉及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之间的区别。这里的形而上学不是抽象的、作为哲学代名词的形而上学,同样,辩证法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辩证法,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形而上学不同含义的区分,以及对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思想史背景的说明,并不是要否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分歧的科学价值,而是在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意义上理解这一对立,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价值。在思想史语境重构的基础上就不难理解: 强调从矛盾对立统一出发理解唯物辩证法,并非一种可以被随意搬弄挪用的诡辩技巧( “变戏法”) ,而是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获得的“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对于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方式的科学再现。这也就提示我们,唯物辩证法的确立首先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的基础上( “思维的历史和成就”) ,经过艰苦探索所形成的与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反思直接相关的一种科学的“理论思维”.唯物辩证法本身同样需要在新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中,面对形形色色的转型了的“现代形而上学”,实现辩证法合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这首先表现为有关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理解和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