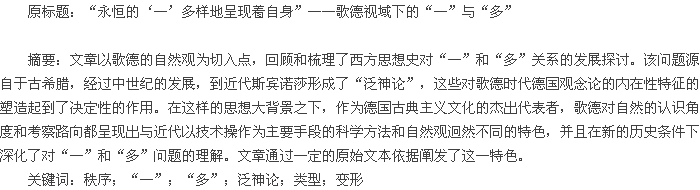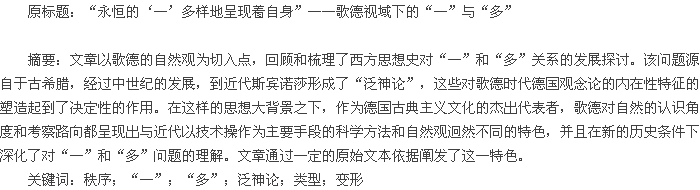
大诗人歌德同时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的博物学家,他在矿物学、气象学、头盖骨学、颜色学、植物学等诸多自然学科领域造诣匪浅,同时也备受争议。如何把握歌德的自然观,有待于我们不断地深化对歌德乃至整个德国古典主义的理解。文章拟结合德国思想史的大背景,就歌德为什么从事自然研究以及他眼中的“一”与“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一番解读尝试,希望为理解歌德的自然观提供一个有益的补充。
一、秩序或本原
歌德为何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拜当时西风东渐的启蒙运动所赐。长于思考的德国知识分子很快洞悉到启蒙本身的局限和隐含的危机:启蒙所依靠的法宝无非是理性批判和科学的自然主义,前者最终把哲学送上了不可知论的绝路,后者是用自然因果律解释万物,所有的观点、理论和解释都必须讲求形式逻辑上完美无缺的证据,若非如此,就必然作为愚昧和迷信的产物而毫不留情地打倒。在这种思路支配下对自然对象的研究考察,必然表现为采取割裂的、片面的、孤立的方式,如此我们看到的只是彼此分裂的标本,远非生命实体本身。而按照自古代、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生命一定必须是鲜活的、整体的,是不可须臾分割的。在古人那里一切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这样的传统今天只保留在歌德一个人的自然研究论着之中。自近代以降,西方人眼里的自然变成了可以由人任意地条块分割、予取予夺的对象,而歌德的生活哲学恰恰跟主流的意识形态相反,他从来都是整体地、宏观地感受和体验天地万物,绝不接受近代科学那种单一地倚重于知性的思维方式。此外,西方主流思想界(只有浪漫派算是一个例外)普遍认为人的理智和精神高于自然,而在歌德看来,自然非但不是一个被精神超出的低等物,反而是一个生生不息运动的主体,而且它的运行自有一套严格的、颠扑不破的规律。所以他才会说:“唯有自然一点不开玩笑,它永远真实,永远严肃,永远严厉,也永远有道理;缺点和错误永远由人负责。自然藐视不够格的人,只委身于够格而纯真的人,并向这样的人泄露自己的秘密。”
智慧起源于惊讶,而歌德自小就讶异于自然的力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大千世界里面一定有一种神秘的秩序在悄然地发生作用。至于非实体的精神财富,在歌德看来,“即使在抽象的智性(Intellektualitt)中,在那看似自由飘荡的玄思中,在柏拉图的理念王国中,在斯宾诺莎对上帝的智性的爱(amor intellectualis Dei)中,在康德的纯粹理性中……同样都有一种意志、一种统治的欲望在起作用”。这里所谓的“意志”、“统治的欲望”无疑就是一个我们看不见其大脑的主体。在对自然的懵懂体验中,年幼的歌德慢慢认识到:世界是在由绝对者带动起来的某种力量下存在着的。
这就是秩序的力量,秩序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它给一切都赋予了生命。所以,歌德的自然研究出发点便是寻找并体验这样的崇高秩序。这一点他纵然没有在日记、书信乃至自传里明确阐发,我们也能够从他关于自然的理论沉思甚至日常言谈中偶然透露出的信息中倒推出来。作为自然科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歌德与浮士德一样要用精神之力参透宇宙万物,同时也使自己升华成一个宇宙。
前文已述,歌德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文精神的特色,这与同时期绝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家根本不同。在他眼中,自然万物固然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整体,矿石、云、植物、动物都是一个进程的展现,而不是像博物馆里展品的随意摆列。
因此歌德所追求的秩序是动态的(beweglicheOrdnung)。他研究自然的中心任务就是:在自然变化的进程中,把统摄着一切生成变化的秩序所引起的所有可描述的变形揭示出来,歌德深信,只有在发展和变形中,类型才实现了自身。所以,歌德的研究出发点根本不是一般科学意义上现成的分类学,而是“越出常规的概念秩序,直指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然整体”。
歌德大规模的科研工作大致是在他进入魏玛公国参与政务活动(1776年)以后开始的,《浮士德》剧中主人公在出场之际就发自心底地呼喊道:“逃吧!起来!逃到广阔的国土去!”
这片“广阔的国土”并不只是地理空间的含义,而是包含了他整个生命维度里的纵深空间。也就在这里,歌德实在地体验到了理性主义的新生,从而开启了德国古典主义的帷幕。不过相比青少年时代而言,此时他对秩序和本质的回归已经上升了一个高度,他努力要使原本单一的秩序和本质呈现出多元的层次。为实现这个目的,他从实际的研究中发展出了一对概念:“类型学”(Morphologie)和“变形学”(Metamorphose)。“类型学”又叫“形态学”,在方法上强调对生物体及其族群的总体构造研究,先验性地探讨演化时生物的结构改变,比较生物体间的差异,而非仅就生物个体本身进行分析。
在歌德那里,“类型学”衍化成了一套在运动中对自然形态进行把握的学说。自然形态虽然受到自己的规定,但是在每个发展阶段又都超出了自己。用今天的生物学术语来讲,歌德的“变形学”研究的就是细胞分裂所带动的植物繁衍,只不过在歌德时代还没有建立起“细胞”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歌德那里,“变形”并非意味着对“原型”的扭曲或畸变,而是类型的实现方式:一方面,类型对变形具有支配性、统辖性;另一方面,变形所体现的种种个别性、特殊性都只能在类型的覆盖下才能存在。
二、泛神论
泛神论是歌德自然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17、18世纪的欧洲,为了避免和教会的矛盾,启蒙的推动者们对中世纪神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他们依旧承认自然是上帝的产物,自然界里的丰富多样的系统也是上帝预先安排并架构好了的,每个系统如同分好类别的铅字盒,按照上帝的计划将每一件事物按部就班地分配其位置。这就是当时盛行于英、法这两个启蒙大国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其深重的影响,它导致人们盲目信仰理性和自然主义,最终演变成可怕的精神怪兽———xuwuzhuyi。
在歌德生活的时代,大多数德国文化精英都预见到了自然神论隐藏着摧残信仰之魂的巨大危险,因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之分庭抗礼的泛神论。泛神论主张上帝与宇宙、自然以及人同为一体,在人的自身内部就能感觉到上帝神力的存在,换言之,泛神论就是要在世界内部寻找上帝的力量和作用,包括自然科学里所讲的自然规律与类型,都是这种力量的表现。
在歌德一生最重要的朋友之中,作为导师的赫尔德是难以取代的,让·保罗盛赞他一身集有六种天才。赫尔德的最大功绩就在于继哈曼和莱辛之后,当仁不让地担当了德国泛神论的领军人物。何以如此?
20世纪的着名日耳曼学者贡多尔夫揭开了这个谜底:“在当时的德国,能够将人类世界、历史和社会的一切外观形态,尤其是将人类的语言古迹体验并释读为神性力量的活泼泼展现、生效和发展的人,只有赫尔德一个。”
在神学家赫尔德的带动下,年轻好学的歌德不仅很快接受了泛神论的世界观,并且摆脱了狂飙突进期间的那种单纯而略显狭隘的生命观局限———即把自然界的生命仅仅视作生命体个体的内在冲动结果,认为理性、形式只对生命起到消极的阻碍和束缚的作用。通过泛神论,他重新认识了理性、精神、合乎法则者(das Gesetzmige)、赋形者(das Gestaltende)这一系列概念,认识到自由与理性并不是天敌,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这个世界以生命力的,原来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秩序力量———自然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神性,即无限的形式理念(Formideen),这就是说,理性、秩序与自由并不是不共戴天的死敌!既然自然是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既然精神、秩序、本质同时作用于天地万物,那么精神与自然、质料和形式、无意识的冲动和有意识的意志最后就一定能协调一致起来。以歌德为首的德国思想家和艺术家以此为基点开创了崇高的古典主义世界观和艺术观,其最后归宿就是自由法则与美的理念的统一。
在歌德的时代,德国的大思想家多数倾向于泛神论,按此教义,上帝超越于一切有限的事物之外,又现实地体现其力量于万事万物之中。另外,按照泛神论的解说,天国就在人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充斥着大量肮脏、虚假和丑恶的世界本身就是完美的上帝,而应该理解为:我们这个世界是发展中的上帝、趋向完满的上帝。
上帝的精神附着在人类的身体上,伴随着人类一步一步跨上新的台阶,向着最高真理攀登。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类精神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发展的一个环节,必然要被下一个阶段否定,因此生活的真理就在于我们表现其错误,而每一次表现又都有其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和错误性的存在,成为人类自我发展的动力。在绝对真理充分展现之前,人类的历史就是由错误对错误的克服构成的。
1780年创作的断片《自然》,集中展现了歌德皈依了泛神论之后成熟的世界观。从中我们充分领略到,歌德眼中的世界根本不是彼时启蒙运动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可计量规律支配下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可见、可感、可见诸于形式的秩序统摄下的无限丰富的现象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活泼泼的“生成”(Werden),而不是静止的“存在”(Sein):她只有少数几根动力发条,但这些发条永不磨损,一直起作用,永远是多姿多样的。运动和发展,是她身上永不枯竭的生命;可她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她变化不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她不识何谓休息,停滞不前从逃不过她的诅咒。
此时的歌德早已成功地摆脱了青年时代质朴的自然主义,有意识地向着观念主义回归,说白了就是要为生活和艺术寻找确定的秩序:“她的脚步是从容的,她的例外是少见的,她的道理是不可变更的。”
为实现这一目的,诗人不能不回归一度遭到废弃的理性概念手段。同时,歌德虽然服膺于斯宾诺莎的学说,但在他看来,斯氏那种严格的数学概念推演方式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这不仅仅是歌德不喜欢思辨玄想的个人禀赋使然,也是自然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不可能被理性一网打尽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这样的矛盾性在歌德的文字断片中也不时可见,例如:“在她内部是永远的生命、生成和运动,然而她并不向前移动”,“她把人笼罩在黑暗之中,可又总是促使他去追求光明。她使人依附于土地,所以人累赘迟缓,可她又偏要人行动利索”,“每时每刻她都在作最遥远的旅行,而每时每刻她都到达了目的地”。
如前所述,僵硬的、知性的自然科学研究就是一张现实版的普罗克洛斯忒斯之床,对待自然它只能用现成不变的尺度粗暴地裁剪掉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留下的只是拼接起来的标本死物。对待艺术家创造的有生命的作品只能动用艺术的手段,而单靠概念思维的哲学便有力不从心之感。
因此,多专多能的歌德决心投身于艺术,而这篇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泛神论特色的自然观和艺术倾向的《自然》断片也成为了德国观念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三、“类型”概念的前身———理念、至善、一、上帝
歌德为什么如此钟情于泛神论?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泛神论的主旨与古希腊的文化精魂极为投合,而歌德自幼接受希腊古典文化的全面扎实的教育,是希腊风的倾心迷恋者,关于古希腊他从来不吝于溢美之词,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数这样一句:“在所有的民族之中,把生命的梦编织得最美妙的无过于希腊人。”
毋庸置疑,希腊是歌德终身追随却又无法企及的目标,歌德本人也非常明白,比起他所仰慕的远古先贤,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非常“不利于一个天才的发展”,如果不满足于庸人的生活而想干出一番事业,就“不得不竭尽全力,克服重重障碍、摆脱某些谬误”。
不过,歌德所生活的时代也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科学的飞跃发展有助于更深透地观察自然现象的细节,从而更稳健地接近事物的最终本源。同时,希腊文化的深厚积淀也使歌德明白:单凭自然科学这一门面向很窄的学问就想达到对自然世界的精确观察和通透理解,那是人类理性的愚妄,要把握有质料的、感性的内容,非整体的、综合的、动态的方法莫办,在歌德看来,他的“类型”方法论就是他研究自然的不二选择。
西方哲学的一大特色是对本原的执着追求,本原就是事物追求的总方向,并且这样的总方向只能是一个,不能是两个或更多,这就是最早出现的“一”。同时,希腊人普遍感到丰富杂多的特殊经验对象无法形成知识,相反,具有恒定性和持久性的对象却容易形成知识,所以,“思想专注的不是事物的特性,而是事物的共性,这种共性是同一‘类’事物所共有的”。这样的共性,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在西方哲学中被称为“概念”,在柏拉图那里就被称作“理念”。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申明,感性的对象不同于思想对象,作为后者的理念才能被思想。理念形成一个自存的世界,它使世界上的事物成其所是,给万物的混沌以秩序,去辨认类似者,区别不同者,在“多”中领悟“一”。总之,柏拉图将各种事物的存在指向都称为“理念”,而所有理念的最高指向,即事物的终极指向,就是“至善”。不过,“理念论”这样一个天才学说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理念的分有者和被分有者相互分离,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柏拉图本人,终其一生,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为了克服理念与感性事物分离的困难,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四因学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形式因大体上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只不过有时亚里士多德还用“形状”(morphe)、“范型”(paradeigma)代指它。
柏拉图主张理念在具体事物之外,具体事物分有或模仿该理念而存在,亚里士多德修正说,形式与事物不可两分,形式在事物中,同质料相结合而存在。在《形而上学》的第七卷和第八卷中,他集中说明了这个论点。在“一”和“多”的关系问题上,他与柏拉图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也认为个别事物就是一种完整的实在,是实体,理念或者形式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诸种个别事物的共性,是存在于“多”中的“一”,而这种“一”,即形式,才是真正的本体,或者说具体事物所要追求的目标。形式不仅仅是每一事物的概念和本质,它还是事物涌现的目的所向和实现这一目的的力量之源(即动力因),亚里士多德洞察到具体事物的形式之上还有某种更高的引导性力量,他称其为“目的”,目的因或者是事物具体形态之上更好的形态,或者是诸种事物构成的总体趋向,而全世界乃至全宇宙的总趋势是至善,他又称其为“一”、“隐德莱希”、“不动的推动者”。在《形而上学》中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论点:第一,原因不能是无限系列,否则会引起无穷倒退,而目的因就是系列的终点(994b9—13);第二,运动者不完善,不完善的东西要追求完善,不动的推动者才是完全的现实,或者说神性的本体(1072b3—1074a30)。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对“一”和“多”的问题做出了较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为他的回答使“一”作为“多”的本质结构(形式、目的)内在于“多”当中,使得“一”作为“多”不可缺少的原则在“多”当中本质性地存在着。
中世纪的人如何消化古代的“理念”学说?本文因篇幅所限,只简单提一提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普罗提诺和库萨。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超越的“一”的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的发展学说做了一种混合,发展出自己的“流溢说”:“‘一’作为绝对者,通过流溢产生世界的多个层级:精神、灵魂、个体物构成的感性世界,直至作为非存在的极端界限的无形式的质料。通过流溢的方式,‘一’内在于世界的多样性之中。太一、精神、灵魂,这三个最初的本质性是‘一’的三种形态。”
按照普罗提诺的说法,理念召唤世间万物,万物也趋向理念,太一通过精神对事物产生吸引和召唤;并且,这四个层次由高到低逐层吸引,同时也由低到高逐层向上回复,直至回到作为本原的“一”。这种生生不息、由低向高运动不止的设想与德国古典主义的精神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普罗提诺对“一”与“多”的关系解说仍旧停留在古代世界观,对于解释人格主体化了的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仍有欠缺。为此,库萨提出了他自己的四个统一性思想,来表达“一”与“多”、统一性与他异性、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这四个统一性思想分别为:神性或绝对的统一、理智、知性和感性。作为世界结构的精神运动,这四个层级属于精神运作和存在显现的四种方式。
它们各自处在不同的精神阶段,共同构成思想的动力运动,实质上是同一个事物的多种存在和展开方式。这四种统一性在运作中又是彼此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
在库萨这里,上帝是掌握着无限精神的“一”,它的力量贯穿了世间的全部存在,即“多”,其运动方式又超过了有限精神的理解力,而作为有限精神的个体的人,才能不一,对于四个统一性的把握侧重点不一,但他们又都渴望与上帝接近。这样一种绝对者遍在世界之内的图景奠定了德国古典主义时期整个内在性思想的基础,不夸张地说,一半的德国泛神论者都是库萨的学术子嗣。
四、“类型”与“变形”
歌德和赫尔德坚信,看似无序的大千世界一定被一种统一的秩序力量统摄着。从德语单词“Wes-en”我们也可以看到,该词兼有“本质”、“存在”及“存在者”的意思,说明德语语境中的“本质”就是我们感官所及的种种自然现象的根据,所有现象都依仗于这种在先的根据的支持。所以,在泛神论者看来,不存在纯粹脱离本体的或然、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原形式、原秩序的掌控之下。由此歌德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类型学”和“变形学”。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渊源和演变,莫光华已经在他的着作中有过详细交代,本文不做重复,这里只强调一下其精神实质:“类型学”是一种自然观科学,其精神体现为在诸多局部中体验整体,于整体中体验局部,这些局部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完成了的部分,而是自身有机运作的一个动态体系里的一个个环节,互相之间血肉相连,相辅相成而不相害。要描述这样的局部,只有将它们放置在一个有机的、成长着的自然生命体的背景下才能有效地进行。“类型学”描述的就是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自然形态。“变形学”的任务则是:假道于有限的局部细节,见微知着地把握总体性的自然。
1790年,歌德完成了《植物变形记》(Metamorphose der Pflanze),在这部作品中,歌德阐明,植物的生长是以一个环节紧跟着一个环节展开的,从子叶到叶子,从叶子到花朵,再从花朵到种子。这所有的变化过程都是在一种有机中心的推动下完成的,而该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植物外形的变化。就单株植物个体而言,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各个器官的大小也不相等,生长速度也不一样,这就是说原推动力的外在表现是有差异、有变化的,然而整个植物却无可阻挡地向上生长,每个器官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共同重复着同样一个基础形式。后来歌德在同名诗歌中这样写道:
爱人啊,这园中的万千花朵纷然杂陈,它们令你眼花缭乱、困惑迷惘;你虽听出了许多名称,却有更多名称野蛮地喧嚣着,在你的耳中你推我攘。
所有形态彼此相似,每个形态各不相同:这部合唱诠释着一个秘密的法则,一个神圣的迷此前歌德已经通过“比较骨学”(vergleichende Osteologie)的研究,确定外形上千差万别的脊椎类动物属于同一类属,因为支撑它们身体的骨骼都执行着相似的功能,在整体结构上的作用是大同小异的,这个发现最初只是让他朦胧地认识到一切脊椎动物都共属一类,开始奠定“类型”(Typus)概念的基础。
随着植物学和动物学研究的齐头并进,歌德认识到,自然一方面是按照明确的形式和模式塑造生物的外在形态,然而这种塑造本身又存在着极大的自由,里面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歌德于是惊叹:
“自然在创造中展开生命。”这一发现毋宁说超越了常识,需要人们不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的肉眼观察,打开心灵之眼才能理解。既然生命形态的塑造可能是无限多样的,而这种塑造却又受制于形式理念,那么必然产生这样的疑问:后者是怎样产生这种制约作用的呢?歌德足足探索了16年时间才开始在《动物变形学》(Meta-morphose der Tiere)中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同名的诗歌片断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一问题试探性的描述:
那位女神,她遍施丰厚的生命之馈赠,却能无忧无虑,不像有朽的女人们总在担忧:自己的孩子得不到可靠的给养;可她不会担忧,因为她已双重设定那至高的法则:她对每一个生命都施加了限制,让他们轻巧地发现适度的需求和不可限量的馈赠,她将需求和馈赠遍地播撒,那些多方面贫乏的孩子,只要他们踊跃地努力,她就大方地施予恩惠,未受教育的孩子们在她的规定下向着四方徜徉在这里,自然女神“双重设定”下的“至高法则”实质上就是对形式理念如何作用于生命形态这一问题的回答:自然给万物所定的法则乍看之下似乎是模棱两可的,这个法则对于自然生命采取的是有收有放的态度,对于外在形态,生命体可以享受无限的自由,而对于其内核,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统一的形式理念。内在的限定是永恒不变的,任何想改变它的人为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无功:
正因为如此,才不致出现这样一种动物:它口中生满獠牙,同时头上又长出犄角;所以,让狮子长出犄角,这是连那永恒的母亲也绝不能办到的造型接下来,诗中写到自然让每一个生命都“轻巧地发现适度的需求和不可限量的馈赠”,时隔两百年,对“需求”(Bedürfnis,单数)和“馈赠”(Gaben,复数)这两个词的释义已经今非昔比了:所谓适度的需求,是指人在求取真理能力上的有限性,一方面人根本就无法达到神或者至善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有能力在某些个别的时候或场合偶然获取对神性或最高真理的某些理解。女神的“馈赠”播撒是毫无偏私又难以计数的,而获得了馈赠并不等于就能马上转化为才能并修成正果———所有的新生命者都是心智有限的“未受教育”者,他们只有付出踊跃的努力,才有希望通过脚踏实地的生命实践真正发挥自然馈赠的作用,从而自己成全自己。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诗里面,以自然女神为主语的动词“设定(法则)”、“施加(限制)”、“让(他们发现)”、“播撒”为过去时,强调了自然法则绝对的先在性;“遍施(馈赠)”、“施予(恩惠)”是现在时,强调法则运行的永恒性。
歌德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年过五旬,可以想见,只有经历过多年风雨沧桑历练的人,并且是目光敏锐、心眼洞开、勤于并善于思考学习的人,才能把握诗里面所讲的自然母亲所设定的双重法则,用诗的语言来总结那就是“永恒的‘一’多样地呈现着自身”。
五、结语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歌德是一位富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卓越的洞察能力及思考能力的诗人、智者,他的自然研究,是在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论过度膨胀、传统受到质疑的历史时代下对人和世界关系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在“一”和“多”这样一个哲学难题上,柏拉图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们都过于忽视感性经验,片面地侧重于高度抽象的理论思辨,从而使得他们的学说缺少事实依据的有力支持。亚里士多德虽然具有比他老师丰富得多的经验头脑,但由于科学观察手段的局限,感性事实和理性思维的结合问题在他那里也没有得到十分成功的解决。自启蒙以降的科学家又只会拘泥于实证功夫,他们研磨出来的数据或事实之间的关系也是呆板的,没有生命力的,完全背离了古人探发的秩序之道。歌德在这样的形势下勇于探索,既积极地接续了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有益教诲,又在研究中深化了上帝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并用新的科学方法提出了深刻的、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虽然也没有获得科学界的支持,但歌德的自然研究的积极意义无法抹杀:他阐发了生命形式从低到高依次逐步演进的规律,极具目的论特色,客观上给人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积极向上的信心和动力,即使与几十年后横空出世的达尔文“进化论”相比,其思想成色也不遑多让,当然这两者的比较是属于另一篇大文章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