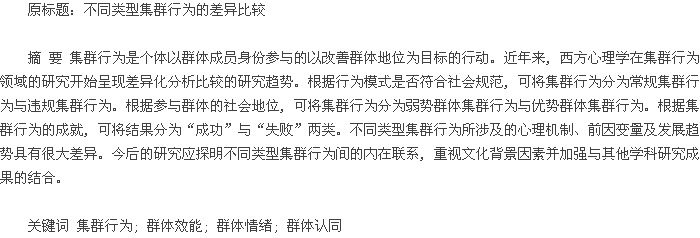
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是群体成员参与的以改善群体现状为目的行动, 具体可表现为请愿、游行、集会、抗议、罢工、示威、甚至骚乱、暴力冲突等多种形式。关于集群行为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 自上世纪 80年代来, 心理学视角下的集群行为研究开始兴起,对集群行为心理机制的分析与探讨成为了集群行为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当前, 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心理学关于集群行为的研究现状进行过专门的介绍, 具体包括集群行为的测量方式、前因变量、组织机制以及参与模型等问题(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弯美娜, 刘力, 邱佳,杨晓莉, 2011; 郑昱, 王二平, 2011; 陈浩, 薛婷,乐国安, 2012); 同时, 很多学者也进行了部分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薛婷, 陈浩, 乐国安, 姚琦,2013; 张书维 , 2013; 张书维 , 王二平 , 周洁 ,2012 ), 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的是集群行为的一般性心理特征。近年来, 随着实证研究资料的不断积累, 西方心理学在集群行为领域的研究开始呈现差异化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即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于对不同类型集群行为的相关心理机制进行比较分析, 如不同情境、场域下人们参与集群行为的认知过程是否具有差异?参与动机的不同是否会影响之后的运动发展趋势?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情绪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本文主要按照集群行为模式与社会规则的关系、集群行为参与者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及集群行为的成就结果这三个类别范畴对集群行为心理机制的差异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介绍, 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1 集群行为的心理学研究概述
尽管集群行为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但对“集群行为”这一概念本身学界内当前却缺乏精确、严格且具有共识性的定义。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形, 是因为集群行为往往与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紧密相关, 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会衍生出很多新形式。因此, 精确的定义会将很多特异或新生现象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例如, 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最广为引用的对集群行为的概括是 Wright, Taylor 和 Moghaddam(1990a)所提出的:“如果某人像所属群体典型成员那样去行动, 且其行动旨在改善所属群体状况,那么他/她即是投入到了集体行动中。”根据这一定义, 集群行为是一种旨在提升所属群体地位的行动策略。但实际上, 很多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目的是提高外群体的地位或权益, 例如, 白人会组织和发起黑人民权运动, 异性恋也会参与反同性恋歧视活动。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集群行为, 但并不符合上述定义。
尽管具体定义在学界还存在争议, 但广义层面上的集群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 行为参与者的身份是群体成员, 而不是独立的个人, 群体可以是具有明确社会意义的身份类别, 如同性恋、学生、机械工人, 也可以是广泛意义上具有共同信念、价值观或权益诉求的政治团体, 如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McGarty, Bliuc, Thomas, & Bongiorno, 2009)。第二, 行为以群体的姿态出现, 即行为表现形式是集体化而不是个人化的, 但这并不意味参与者是在同一空间、时间行动的, 例如, 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在各自独立的物理空间发起请愿书。第三,行为的目标与社会群际关系有关, 其旨在改善某一个或几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 受益群体可以是内群体, 也可以是外群体(Wright, 2009)。
在关于集群行为的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集群行为的心理动员机制, 即哪些动机因素会促使人们投身到集群活动中。经过 20年的积累, 目前在该研究领域已公认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s)和群体效能(group efficiency)是影响个体参与集群行为的三大前因变量。“群体认同”概念源自社会认同理论, 指个体与群体基于群体成员身份意义的心理联系, 也就是个体将群体成员身份整合进其自我概念的程度度(Tropp &Wright, 2001; 张书维, 王二平, 2011)。个体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越强, 就越有可能代表那一群体参与集群行为。“群体情绪”概念来自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theory), 它是情绪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ies ofemotions)在群体水平的延伸, 具体指个体针对特定事件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生的的情绪反应(Smith, 1993)。当群体积累了强烈的愤怒情绪时,就有可能爆发集群行为。“群体效能”概念则指群体成员对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群体目标的信念(Bandura, 1997), 它反映的是成员对本群体所拥有资源的主观认识(Klandermans, 1984)。当人们相信群体有能力改变当前境遇时, 发起集群活动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大(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陈浩等, 2012)。这三种因素对人们的集群行为参与既有独立的解释作用, 同时也具有相互作用的机制。
除以上三大主要变量外,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人们参与集群行为的意愿还会受到诸如理想信念(ideology)、道德信仰(moral convince)、社会卷入程度(social embeddedness)、系统公正感(systemjustification)、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及个人的焦点调节(regulatory focus)、拒斥敏感性(rejectionsensitivity)等因素的影响(B?ck, B?ck, & GarCia-AlBaCEtE, 2013; Becker & Wright, 2011; Thomas,Mcgarty, & Louis, 2014; Van Stekelenburg, Anikina,Pouw, Petrovic, & Nederlof, 2013; Zaal, Laar, St?hl,Ellemers, & Derks, 2011)。另外, 很多学者对集群行为的研究并不再局限于探讨常规集群行为的预测变量, 在横向拓展维度上, 研究者开始针对集群行为多样化的特点关注不同类型集群行为的调节因素; 在纵向拓展维度上, 研究者则开始强调集群行为的动态性特征。对集群行为心理机制的差异化比较研究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趋势。
2 不同行为模式集群行为的差异比较研究
群体成员为改善群体社会地位而发动的集群活动可具有多种行为模式。如果要对不同形式的集群行为进行分类, 最基本、最直观的类别范畴往往涉及到集群行为的激烈性、合法性与道德性。Wright 等人(1990a)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根据集群行为模式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而将集群行为分为常规集群行为(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与违规集群行为(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前者指符合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在内的既存规则的集群行为, 如和平游行、联合签字抗议等, 这种集群模式较为和平、温和, 且不具有暴力攻击性; 与此相对, 后者则指违背了这些规则的集群行为模式, 如冲击政府、破坏公物等, 这种集群模式较为激烈、极端,且通常涉及暴力冲突。Stephen和 Chenoweth (2008)对 1900 年至 2006 年的集群行为资料进行分析发现, 各种社会背景下常规集群行为与违规集群行为都普遍大量存在。以往关于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常规性集群行为进行研究。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关注违规集群行为在预测变量及后果影响等方面与常规集群行为的差异。
2.1 群体效能感知的差异
群体效能是决定个体是否参与集群行为的核心因素之一。当人们相信通过内群体的共同努力可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实现群体目标时, 会更主动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也就是说, 人们所感知到的群体的力量可以驱使他们参与集群行为。
然而,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 这种预测作用只适用于常规群行为模式。当涉及到违规集群行为时,群体效能感与人们集群行为参与意愿则具有负相关性的关系。
低效能感易导致极端行为, 这一假设已得到很多 研 究的 证实 (Moghaddam, 2005; Ransford,1968)。Tausch 等人(2011)将效能感与极端行为之间的关系引入到对集群行为的研究中。他们认为,效能感的缺乏是促使人们参与违规集群行为的重要动力。如果当前的政治系统或社会环境导致群体成员认为内群体没有足够的能力达到预期目标,那么他们则更可能付诸于违规集群行为。实际上,过往的研究资料就显示, 当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是稳定的且改善群体地位的合理渠道被完全封闭时, 弱势群体成员会更倾向于做出具有对抗性、极端性、暴力性特征的破坏行为(Scheepers, Spears,Doosje, & Manstead, 2006; Spears, Scheepers, &Van Zomeren, 2010; Wright et al., 1990a; Wright,Taylor, & Moghaddam, 1990b)。
另外, Scheepers等人(2006)特别指出, 违规集群行为并非只是弱势群体在绝望时无目的的宣泄手段, 这种行为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功能, 研究者称之为“再无可失(nothing to lose)”策略。也就是说,对于使用合理合法手段无法改变不公遭遇的弱势群体, 即便他们不进行任何活动, 他们的社会地位或福利待遇也不会有所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通过发动或参与极端的、非常规的集群活动, 尽管可能无法直接达成目标, 但可以引发社会关注, 影响公众意见; 也可以引起对立群体的强势反对, 从而再次成为被害者, 争取第三方的同情; 或可以扰乱当前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环境,为今后社会运动的长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群体效能感对常规集群行为与违规常集群行为不同的预测作用已得到了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 Tausch 等人(2011)以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穆斯林团体抗议移民政策等事件为背景进行研究调查发现, 群体效能感对个体参与常规集群行为的意愿(如联合签名反对、游行)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 对个体参与违规集群行为的意愿(如毁坏公共建筑、袭击警察和反对者)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Louis 等人(2011)对一个反全球化集会的参与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他们关于民主集会的效能感与对暴力手段的支持程度间具有负相关性, 即当参与者认为和平手段是无效的时,会更支持暴力行为。
此外, Reijntjes 等人(2010)研究曾指出, 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知觉是影响他们判断常规集群行为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系统公正的前提下, 人们认为常规集群行为可以改变群际关系,因此会选择温和、非暴力的集体行动作为抗争手段; 而在系统不公正的前提下, 人们会认为常规集群行为无法改变当前社会状况, 因此会选择极端的、破坏性的集体行动作为抗争手段。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在 Thomas 和 Louis(2014)以澳大利亚反捕鲸运动为背景进行的研究中, 一部分被试在实验前阅读有关 “国际捕鲸协会”内部腐败的新闻, 通过这条新闻, 向部分被试宣称由于一些靠捕鲸致富的国家向协会进行了贿赂, 国际捕鲸协会可能将捕鲸合法化。研究结果显示, 在这种情况下, 向被试展示当前存在号召“禁止捕鲸”常规集群行为反而会提高被试对违规集群行为的支持。Owuamalam, Issmer, Zagefka,Kla?en 和 Wagner (2014)对德国低教育群体的研究也发现, 当假设政府打算削减对低教育群体职业培训的经费时, 被试对社会系统公正的评估可以预测他们参与违规集群行为的意愿, 即被试越认为社会系统不公正, 就会越不愿参加规范集群行为, 并越支持极端的违规集群行为。也就是说, 在权力系统存在腐败或个体对社会的公正性持悲观态度的情形下, 他们会认为温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是无效的, 因此会更加支持暴力抗争。
2.2 情绪体验的差异
现代群体情绪理论认为, 群体情绪是个体对内群体遭遇社会情境或事件的功能性反应, 当群体成员感知到群际不平等时, 会对内群体及对立的外群体(即优势群体)的能力、特质、责任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继而产生相应的群体情绪和行为应对意向。因此, 不同的集群行为模式具有不同的情感成分(Troost,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以往关于集群行为的研究显示, 群体成员因相对剥夺而产生的群体愤怒情绪是导致集群行为的主要情感因素。Becker, Tausch 和Wagner (2011)认为, 群体愤怒情绪主要激发个体参与常规集群行为, 涉及到违规集群行为时, 群体蔑视(contempt)情绪则对人们的参与意愿具有更显着的预测作用。
Fischer 和 Roseman (2007)曾对这两种情绪进行过比较研究分析, 他们指出, 虽然愤怒和蔑视都是个体面对不公正境遇而产生的敌意性负面情绪反应, 具有相似之处, 但是这两种情绪在所暗含的社会关系指向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区别。其中,愤怒情绪导致的敌意行为往往会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且这种敌意行为的目的在于改变对立者的态度或行为, 因此, 愤怒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的情绪, 它暗含着最终欲求和解或妥协的意图, 由愤怒情绪主导的集群行为在努力改善群体现状的同时会将敌对程度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一般不会违反社会常规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相比于愤怒, 蔑视是一种破坏性更强的情绪, 当产生蔑视情绪体验后, 个体往往不会与对立者寻求和解, 反而会加深与对方的敌对性。愤怒和蔑视情绪之间具有一定的发展关系, 当人们最初的抗争策略没有起到作用时, 愤怒情绪可能会转变为蔑视。在群际关系中, 群体蔑视会引发对外群体的去人性化与排斥感, 而心理距离、道德排斥与去人性化则会降低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斗争时对社会规则与道德标准的坚持, 进而导致将违规行为合理化。因此, 相对群体愤怒, 群体蔑视情绪更容易激发群体成员参与极端的、暴力的集群活动。愤怒与蔑视情绪对常规集群行为和违规集群行为的不同预测作用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Tausch 等人(2011)以德国学费上涨事件为背景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 学生由拟上涨学费事件而产生的群体愤怒情绪可以显着预测他们参与常规集群行为的意愿, 但与他们参与违规集群行为的意愿不相关, 而学生由此事件产生的群体蔑视情绪可以显着预测他们参与违规集群行为的意愿,但与他们参与常规集群行为的意愿无关。另外,研究者以英国的穆斯林团体作为实验对象也证明,群体愤怒情绪可以更好地预测常规集群行为, 而群体蔑视情绪可以更好地预测违规集群行为。Becker 等(2011)的研究也曾证实, 人们参与温和集群行为的意愿主要与外群体导向的愤怒情绪有关, 而人们参与激进集群行为的意愿主要与外群体导向的蔑视情绪有关。
2.3 对中立方动员效果的差异
集群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真实社会生活中, 集群行为的爆发会对公众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研究显示, 一场抗争运动是否可以成功的达到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运动能否影响或塑造公众的观念(Louis, 2009)。成功的集群行为往往可以使公众认识到当前社会环境的不合理性, 并将旁观者或中立者转变为支持者。而规范集群行为与违规集群行在对公众的心理影响方面具有一定差异。在一般情况下, 旁观者会更加支持和平的、温和的抗议手段, 极端性、暴力性的行为会被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判断为违反道德准则, 人们会对类似行为活动感到恐惧和厌恶, 因此, 违规集群行为会减弱抗争动机的合理性, 引发旁观者的谴责, 甚至会使旁观者认为发动者没有足够的能力达成目标,进而降低人们的支持。Stephen和 Chenoweth (2008)的资料分析结果显示, 非暴力抗争行动的平均成功率可达到 53%, 但是暴力抗争行动的平均成功率只有 26%。相比于违规集群行为, 常规集群行为可以更好的向中立者传达现状的不合理性, 并动摇公众观点, 赢得公众支持。
Thomas 和 Louis (2014)对此假设进行了实证探索, 研究者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反煤层气开采运动为背景, 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当地居民)阅读关于使用非暴力抗争手段(签名)或使用暴力抗争手段(投扔东西)反对煤气层开采的新闻, 之后再完成问卷。研究结果显示, 相对于阅读暴力抗争新闻的被试, 阅读非暴力抗争新闻的被试会更支持抗议运动, 对运动参与者有更少的敌意, 并更倾向于认为开采计划是不合理的。该研究说明,非暴力的集群行为会减弱旁观者对抗争活动的敌意, 同时更好地表达触发事件的不正当性, 从而提高旁观者对抗争活动的支持。而 Becker, Tausch,Spears 和 Christ (2011)的研究也发现, 暴力集群行为的参与者会认为他们的行为不会被他人甚至内群体的其他成员所支持, 因此参与暴力集群行为后参与者对集体行动本身的的认同会增加, 但内群体的群体认同感则会降低。
3 不同参与群体集群行为的差异比较研究
按照集群行为参与者在群际关系中的地位及他们与利益诉求方的关系来区分, 可将集群行为分为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集群行为与优势群体(advantaged group)集群行为。早期关于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人们为了改善内群体境况所发动的集体行动。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等聚焦于理性选择的解释取向,只有在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参与集群行动。因此, 在社会关系中遭受不公对待的弱势群体会发动集群行为, 而优势群体则应该努力维持现状。然而, 现实中常有一些优势群体成员会行动起来支持弱势群体,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进行抗争, 但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 且他们的行动反而有可能危害到所属优势群体的地位或利益, 这种现象即优势群体集群行为*。例如, 男性可能会反对工作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富人会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对穷人减税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并对优势群体集群行为与弱势群体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比较研究。
3.1 情绪动力的差异
在情感驱力方面, 优势群体集群行为与弱势群体集群行为具有很大差异。以往的大量研究证实, 由相对剥夺而导致的群体愤怒情绪是激发弱势群体成员参与集群行为的主要情绪因素。但对于优势群体来说则不仅仅如此, 一方面, 群体成员可能会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感到愤怒, 另一方面, 群体成员也会为内群体在不公关系中受益而感到内疚(guilt)、羞愧(shame), 并对外群体(弱势群体)在不公关系中受损而感到同情。因此, 促使优势群体参与集群行为的主要情感成分既包括聚焦于内群体所产生的愤怒与内疚情绪, 也包括聚焦于外群体所产生的同情(sympathy)情绪。
Leach, Iyer 和 Pedersen (2006)指出, 如果人们认为内群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具有不合理性, 且内群体对这种不合理的群际关系及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公对待负有一定责任, 就会产生基于群体的情绪体验。群体成员会担心群体的行为违反了道德标准, 因而会因群体道德形象受损而产生内疚甚至愤怒感。在这些群体情绪的促使下,优势群体成员则可能会发起、参与或支持一些为对立的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集群行为, 以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负面情绪感受, 补救内群体的道德名誉, 修复对内群体的道德认同感(Lickel, Schmader,Curtis, Scarnier, & Ames, 2005)。
愤怒与内疚情绪对优势群体集群行为的启动作用得到了大量数据支持。例如, Leach 等人(2006)对澳大利亚公民的调查研究发现, 非土着居民越认为他们相对于土着居民的社会优势地位是不合理的, 那么他们体验到的群体内疚及愤怒情绪就越强烈, 而这两种情绪都可以显着预测他们对旨在改善土着居民地位集群活动的参与意愿。Iyer,Schmader 和 Lickel (2007)的研究证明, 当美国与英国公民观看关于伊拉克混乱现状的报道后, 群体内疚情绪体验可以显着预测他们参与要求英美撤军活动的意愿, 而愤怒情绪则可以预测他们对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这一政策的支持。Shepherd,Spears 和 Manstead (2013)的研究也显示, 当假设英国教育部门会对威尔士留学生提高学费时, 英国的大学生(优势内群体)针对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愤怒、内疚和羞耻情绪可以预测他们参与抗议活动的意愿。另外, Paladino, Zaniboni, Fasoli, Vaes和Volpato (2014)对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参与集群行为的情绪动力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们以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对女性的侮辱歧视事件为背景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女性参与反性别歧视活动的主要预测情绪是愤怒情绪, 而男性参与反性别歧视活动的主要预测情绪是内疚, 研究者认为, 男性被试通过参与扞卫女性权益的活动可以补救内群体(男性)名誉, 维护自我道德尊严。
除内疚与愤怒情绪外, 当优势群体对群际不平等关系的关注聚焦于弱势群体时, 还会对弱势群体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情绪反应, 而同情情绪则会降低优势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偏爱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 优势群体会为实现公正的理念而提高与弱势群体进行资源共享的意愿, 甚至以放弃或损害内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例如, Iyer, Leach 和Crosby (2003)发现欧洲裔美国人对非裔美国人遭受歧视的同情会增加他们对社会公正的支持。Harth,Kessler 和 Leach (2008)的研究则发现, 大学生对移民遭受歧视的同情可以显着预测他们是否同意移民儿童参加大学体育活动。因此, 由关注弱势群体不公境遇而产生的群体同情情绪也会促使优势群体成员发起或参与为弱势群体谋福利的集群行为。例如, Iyer 和 Ryan (2009)的研究证明, 在反性别歧视运动中, 女性参与者的主导情绪是因性别歧视而产生的愤怒, 而男性参与者的主导情绪是因性别歧视而产生的对女性的同情。Becker 和Swim (2011)的研究也证明, 对女性遭遇性别歧视事件更同情的男性会更愿意在反性别歧视的请愿书上签字。
3.2 对群际不平等关系归因评价的差异
根据群际情绪理论与情绪评价理论, 群体情绪是群体成员对触发事件或情境进行认知评价的结果(Lazarus, 1991; Smith, 1993)。因此, 与群体情绪体验密切相关的集群行为趋势会受群体成员对社会关系综合评价的影响。激发弱势群体参与集群行为的愤怒情绪具有明确的对外指向性, 也就是说, 弱势群体会对外树立一个受责难的目标(通常是权力机关或对立的优势群体)。当群体成员认为所属群体的不利处境不合理且外群体对此负有责任时, 集群行为参与意向将会加强。但当群体成员认为外群体对群体的不利处境不负有责任或无法责难外群体时, 将体验到悲伤、失望等情绪,而这些情绪反应则会抑制集群行为参与意向(Walker & Smith, 2002)。因此, 将群体不公或不利归因于外群体是弱势群体成员参与集群行为的认知评价基础。
不同于弱势群体集群行为, 优势群体集群行为的情感成分(内疚、愤怒)主要指向内群体。只有优势群体成员认为群际关系是不合理的且内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利地位负有一定责任时, 才会愿意参与支持弱势群体的集群行为。因此, 将群际不公关系归因于内群体是优势群体成员参与集群行为的认知评价基础。这种归因评价对集群行为参与意愿的影响已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Leach 等(2006)等人的研究证明, 优势群体成员越认为内群体对群体关系的不平等负有责任, 则越可能产生愧疚及愤怒情绪, 并更愿意参与目标在于改善弱势群体地位的集群行为。Stewart, Latu,Branscombe 和 Denney (2010)也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假设, 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者首先使白人学生被试了解到当前教育系统中存在歧视非裔学生而优待白人学生这一不合理现象, 之后, 通过实验操作使一部分被试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群体努力消除这种不平等, 使另一部分被试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之后测量他们是否会因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种族歧视而感到内疚, 并是否愿意参与反歧视抗争活动。实验结果显示, 如果被试认为内群体(优势群体)无法通过集体行动改善这一现状, 那么他们的内疚感会较弱, 参与集群行为的意愿也较低。也就是说, 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 优势群体成员会认为内群体对弱势群体不利地位不负有相应责任, 因而内疚感与抗争意愿都会较弱。此外, Saguy, Chernyak-Hai, Andrighetto 和Bryson (2013)以以色列的犹太人(社会地位优势群体)和阿拉伯人(社会地位弱势群体)间的种族不平等关系为研究背景, 通过实验证明, 当犹太人被试因被指控具有种族偏见而感到被错怪后, 他们会将内群体相对于外群体的优势地位视为更加合理的, 并降低他们支持弱势群体进行抗争的意愿。研究者认为, 在被错怪的情况下优势群体成员可能会认为群际间不平等关系的原因不在于内群体, 因此会减少他们为改善外群体境况所作出的集群努力。
3.3 群体认同的差异
群体认同是集群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个体对某一社会群体的认同感越强, 就越有可能代表那一社会群体参与集体行动。因此, 对于弱势群体成员来说, 他们是否会参与集群行为主要取决他们与内群体的心理联系及所愿付出的承诺, 当个体对内群体抱有强烈的认同感时更可能参与到以改变群体现状为目标的集体行动中。这一结论已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而对于优势群体成员来说, 他们参与集群行为的意愿并不在于对内群体的认同强度。根据Subasic, Reynolds 和 Turner (2008)的政治团结模型(political solidarity model), 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的支持与帮助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认同感, 当优势群体成员认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道德信念和奋斗目标时, 更有可能为了改善弱势群体的权益而发动或参与集群行为。McGarty等(2009)提出的观点群体(opinion-based group)概念也指出, 如果优势群体成员与弱势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信念和理想, 那么优势群体成员不再是代表外群体、而是代表新形成的观点内群体去行动。例如, 如果白人认同黑人实现种族平等的信念, 则更可能会为实现种族平等而支持旨在提高黑人社会地位的群体行动。研究者证实了优势群体成员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认同感与他们集群行为参与意愿间的关系。
White (2008)进行质性研究分析发现, 将自己认同为女权主义者的男性会更加愿意参与各种形式的反性别歧视集群行动。Wiley, Srinivasan, Finke,Firnhaber 和 Shilinsky (2012)则以实验证明, 通过实验操作(强调持男女平等观男性的优点)加强男性被试对女权主义者的认同, 可以提高他们参与支持性别平等集群行为的意愿。另外, Van Zomeren, Postmes,Spears 和 Bettache (2011)针对香港社会在工作就业方面对内地华人的歧视, 以香港公民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对内地华人具有更强社会认同感的被试更愿意参与反歧视内地华人的运动。
4 不同成就结果集群行为的差异比较研究
集群行为具有动力性(dynamic)的特征。以往心理学对集群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集群行为的前因变量, 然而, 参与意愿与实际行动只反映了集体行为动力性过程的初始阶段。在现实生活中,当真实集群行为爆发后, 对立方不同的回应方式会影响群际冲突的发展趋势, 参与者对抗争形势的评估会影响下一步的行为策略, 集群行为具有随情境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特性。甚至很多情况下,仅仅“行动参与”这一过程都会对参与者的心理状态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 集群行为会对个体产生灌能(empowerment)的作用, 在共同行动中, 群体的凝聚力得以强化, 信念目标得以巩固, 因此群体成员的认同感及效能感都会有所提高(Drury& Reicher, 2005)。
近年来, 对集群行为动力性特征的研究已构成了集群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取向之一。在集群行为发生后, 参与者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集群行为的实际效果, 按照最为简单直观的维度来划分集群行为的成就, 可将结果分为“成功”与“失败”两类。对集群行为结果的评估会因参与者心理特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同时, 不同的结果对参与者的情绪感受等心理因素及行为趋势也会产生不同影响。
4.1 行动认同感差异影响成就评价
传统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theory)、期望价值理论(expected value theory)等工具理性取向的理论认为人们参与集群行为的目的在 于 改 善 所 属 群 体 状 况 (Klandermans, 1984;McCarthy & Zald, 1977), 因此, 只有行为被视为有效时人们才会参与集体行动, 且只有在群体现状得以切实改善的情形下集群行为才是有价值的。然而, 大量研究显示, 很多情况下参与者尽管会对活动所宣称的成就是否能达成感到怀疑, 但依然会参与到群体行动中去。例如, Tyler 和McGraw (1983)对反核武器的参与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一些参与者实际上对抗议的效果不报任何期待。Winterton 和 Winterton (1989)对 1984 至1985 年英国矿工罢工行动的研究发现, 很多罢工者对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实现最初的目标持很悲观的态度, 尽管如此, 他们依然准备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支持这一行动。这说明, 很多情况下集群参与者对集群行为成就的评价并不仅仅是基于提高群体地位、改善群体现状或影响政策制定等具体目标是否可以实现。Kelly 和 Brein-linger (1996)指出, 在一些旷日持久的集体抗争中,抗争的参与者常常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还要承受个人在经济及其他方面的牺牲, 并且他们很清楚即使行动成功, 获得的收益也会很少, 但他们仍然坚持行动下去。一种可能性是, 对于集群行为参与者来说, 所谓的积极结果并不一定是具体社会关系的变化或群体地位的提高, 他们重视的是抗争运动本身的发展, 以及在此过程中群体信仰的确认及价值观的表达。例如, Einwohner(2002)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研究发现, 当他们的运动没有达到既定目标时, 这些运动参与者也会更多的强调运动积极的一面, 如使公众认识到了这些问题, 引发了社会的讨论等等。很多研究也发现, 在不知道具体结果的情况下, 参与集群行为本身就可以引发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Leary,2006; Louis, 2009; Becker et al., 2011)。
因此, 群体成员如何评价一场集群行动的成就或价值会受他们对行动认同感的影响。对于行动认同感较低的参与者, 他们重视的是短期内目标是否可以达成, 是否可以通过向对立者施加压力以达到活动所宣传的目标。而对行动认同感更高的参与者, 他们则更重视群体行动是否可以团结吸引公众、表达内群体的价值观与理想信念以及 建 立 长 期 的 抗 争 运 动 (Blackwood & Louis,2012)。例如, Hornsey 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 经验丰富活动者的集群参与意愿主要取决于集群行为是否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与可持续性, 对于从未参加过集群行为的个体来说, 他们参加集群行为的意愿则取决于他们知觉到的群体行动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只有他们认为集群行为可以实现清晰具体的目标才会参与其中。
此外, Blackwood 和 Louis (2012)以澳大利亚和平主义者为被试进行的纵向研究也证明了类似结论。研究发现, 在反政府出兵伊拉克活动中, 随着事态的发展, 对这一行动持更低认同感的被试,他们对行动成就的评价主要取决于该行动是否动员了民众的支持及是否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但这种效应在高认同者群体中则不存在, 也就是说,对于高认同者来说, 即便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毫无成就的集体行动。这证明, 人们对集群行为成功与失败的判断标准会受对集群行为的认同感的影响。
4.2 成就结果归因差异影响情绪感受
集群行为参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 参与者会对群体抗争的成就进行评估,因此, 集群行为的成功或失败会引发参与者不同的情绪感受。例如, Drury, Cocking, Beale, Hanson和 Rapley (2005)质性研究发现, 当人们描述成功的集群行为时, 会报告积极情感体验, 如愉快、高兴、骄傲等; 而当人们描述失败的集群行为时, 则会报告消极情感体验, 如恐惧、挫折、失望等。
由于群体情绪体验是集群行为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 不同的情绪体验则会进一步影响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和行为趋势。在 Zomeren, Leach和 Spears(2012)提出的关于应对群体不利的双路径动力模型中(dynamic dual pathway model), 评价和应对策略之间存在循环作用, 群体成员对群体地位、群体能力的评价会产生应对策略(参与集群行为),而应对反应也会作用于再评价, 并对情绪体验及进一步的行为策略产生影响, 集群行为与情绪体验间具有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
Tausch 和 Becker (2013)的研究也指出, 在集体行动中, 不同的行动成就结果会引发群体成员不同的情绪感受。他们在实验中区分了两种对应于不同结果的情绪:因成功而体验到的自豪感,以及因失败而体验到的愤怒感。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在德国学生抗议政府征收学费事件中, 随着抗议运动的发展, 集群行为的阶段性胜利会激发参与者的自豪情绪, 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会以群体效能为中介激励参与者进行持续抗争; 而集群行为的阶段性失败则会引发参与者更强烈的愤怒情绪, 且愤怒情绪也会提高参与者继续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此外, 该实验还发现, 参与者对集群行为结果的情绪反应与认同感、效能感等因素都具有相关性。首先, 学生对抗议活动的认同感可以显着预测他们在面对成功事件时的自豪情绪强度及面对失败事件时的愤怒情绪强度, 即参与者对抗议活动的认同感越强、心理投入越高, 那么就更容易因集群行为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因集群行为的失败而感到愤怒。再者, 参与者在活动初期的效能感可以显着预测他们之后面对失败事件时的愤怒情绪, 也就是说, 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能力越信任, 就越容易因集群行为过程中遭受的挫折而感到愤怒, 进而再次投身集群抗争中。
除此之外, Tausch 和 Becker (2013)还提出可以将韦纳的归因理论与集群行为的动力性研究相结合。按照韦纳归因理论, 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经历的归因主要基于控制点、稳定性及可控性三个维度。其中, 控制点指当事人将影响其成败的因素归因于个人(内控)或外在环境(外控); 稳定性指当事人认为影响其成败的因素在性质上是稳定的或不稳定的; 可控性则指当事人认为影响其成败的因素是否能由个人意愿所决定。研究者认为,人们对集体行动成功或失败的归因解释会对情绪体验及行为趋势产生重要影响。例如, 当集体行动取得成就时, 如果群体成员更多地将行动的成功归因于内部原因(群体的力量、团结), 则会产生自豪感, 强化效能信念; 而当集体行动遭遇挫折时, 如果群体成员将行动的失败归因于内部原因,则会体验到羞愧, 丧失对内群体能力的信任, 归因于外部原因(社会环境、机遇), 则可能体验到愤怒, 并进而更积极的进行对抗。再如, 在稳定维度上, 如果群体成员认为导致行动失败的因素是稳定的, 可能会产生绝望, 并退缩或付诸于极端的暴力行为。因此, 归因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在不同的背景下, 面对相似性质的行动结果有的群体成员会安之若素、情绪稳定, 而另一些却情绪波动很大。这种归因假设与一些已有研究结论是相符的, 但目前仍缺乏系统的实验探讨。
5 总结与展望
集群行为现象一直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过往社会心理学对集群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人们为什么要参与集群行为”, 然而, 集群行为本身具有表现形式多样化及发展过程动态化的特点, 因此,不同类型及不同发展阶段集群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很大差异性。近年来, 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 这种研究视角由普遍性向差异性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弥补了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行动模式的遗憾, 加深了人们对于集群行为的过程及相关心理机制的理解。迄今为止, 研究者基于集群行为不同模式、不同参与主体及不同结果所开展的差异化比较研究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证资料, 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 因此, 本文主要按照这三个维度对差异化研究进展进行了阐述。除此之外, 也有学者根据其他的特性对集群行为进行了分类并总结了相关差异, 今后的实证研究可以对这些研究取向进一步拓展深化。例如, Zaal 等人(2011)将人格特征引入到对集群行为的研究中, 他们以焦点调节理论(regulatoryfocus theory)为基础指出, 按照行为动机倾向可将人分为提升定向型(promotion focus)和防御定向型(prevention focus)。提升定向型个体凡事以“希望、理想、抱负”为动机, 而防御定向型个体则以“责任、需求、义务”为动机。研究发现, 提升定向型个体对集群行为的评价主要基于行动所能达到的成就及价值, 而防御定向型个体对集群行为的评价则主要基于行动本身的必要性(Zaal, Laar,St?hl, Ellemers, & Derks, 2012)。防御定向型的个体参与群体行动时更容易为了实现目标而支持使用极端的、敌意性的抗争手段(Zaal et al., 2011)。
Qiu, Lin, Chiu 和 Liu (2014)则按照集群行为发生场域的不同将互联网集群行为与传统集群行为进行了差异对比, 研究者指出, 同传统集群行为相比, 互联网集群行为往往是自发的, 缺乏组织性,参与者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某一群体的福利或促进长期社会变革, 当触发事件的发展结果令参与者感到满意时, 集体行动也就随之而停止了。
当前,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关于不同类型集群行为的差异比较研究已取得诸多重要成果,但很多研究方向仍属空白, 有待今后研究的填补与扩展。首先, 当前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某一特定分类维度展开的, 然而, 不同的分类维度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一场集群事件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具有多重类别属性, 如“弱势群体长期非暴力抗议活动”。更为重要的是, 不同类别间可能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例如, 由于优势群体参与集群行为主要是基于羞愧、内疚、同情情绪, 其主要目的是修复内群体的道德声誉, 而弱势群体参与集群行为的主要目的往往在于为内群体谋取实际的利益。因此, 弱势群体成员参与集群活动时可能会更加在乎活动的成就结果, 更愿意投入到长期的抗争运动中去, 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对抗性的、暴力的违规集群行为。与此相对应的, 资料分析显示, 弱势群体发动规范集群行为与违规集群行为的比例都比较高, 甚至可能在抗争运动中交替或同时采用这两类集群模式。但很少有资料显示优势群体成员会为了改善弱势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而参与或发动违规集群活动。因此, 今后关于集群行为的研究应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集群行为间的内在联系, 探明集群行为在不同分类维度上的发展及演变趋势。
其次, 未来的研究应特别注意探讨文化因素与集群行为的关系。文化因素对一个地区集群行为典型特征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 尽管暴力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这一看法深植于当代当代西方文化, 可在许多其他文化和传统社会中却并不一定如此。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 在某些地区, 人们使用集体暴力的方式改变社会关系是一种惯常的选择。这些地方的暴力倾向其延续时间之久, 超越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历程(Rowe, 2007))。因此, 只有全面的考虑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的文化背景因素,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
再者, 由于集群行为研究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 因此, 心理学家在对集群行为开展具体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 将社会心理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结合。例如, Van Stekelenburg 等人(2013)根据社会学对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提出社会嵌入性(socialembeddedness)这一概念, 用以指代个体与内群体的接触、互动频率。研究者认为, 在社会网络中,个体与内群体的联系越强, 就越容易形成群体观念, 针对触发事件的个体不满情绪也可以越快演变为群体不满情绪, 因此, 社会网络在集体行动动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对荷兰一个新兴社区的纵向实验研究证明, 在社区刚刚成立时与其他居民接触更频繁的社区居民, 会在之后该社区反“修建清真寺”运动中有更强的群体效能感、认同感及不满情绪, 并更积极的参与抗议活动。
Thomas 等人(2014)的实验也证明, 社会互动可以提高被试参与极端集群行为的意愿, 引发群体极化现象(group polarization)。可以预期, 将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相结合, 对于全面揭示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为社会管理实践提供技术指导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薛婷, 陈浩, 乐国安, 姚琦. (2013).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 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心理学报, 45(8), 899–920.
张书维. (2013). 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意向: 群体性事件的双路径模型. 心理学报, 45(2), 1410–1430
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730–1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