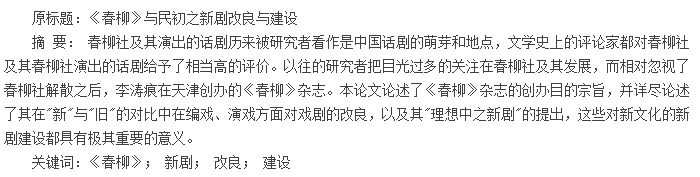
春柳社及其演出的话剧历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中国话剧的萌芽和地点,文学史上的评论家都对春柳社及其春柳社演出的话剧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看似春柳社从其兴起到衰落与天津都没有太大的联系,以往的研究者把目光过多的关注在春柳社及其发展,而相对忽视了春柳社解散之后,李涛痕在天津创办的《春柳》杂志。虽然《春柳》创刊于1918年12月,至1919年10月即停刊,前后共出八期,但是"《春柳》对于南北话剧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
《春柳》是天津首次创办的戏剧月刊,可以看做是天津新剧改革与建设的公共空间,其上先后发表了南开新剧团创作的剧本《一念差》《新村正》,并发表了李涛痕、齐如山等戏剧理论的文章。该刊以"改良戏曲,针砭社会"为宗旨,以戏曲改良、新剧之探索为主要内容,为南北话剧艺术的融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而查阅相关的文献及研究资料发现,研究《春柳》杂志的相关成果仅有研究者陈均发表在《戏曲研究》第七十七辑上的一篇《〈春柳〉杂志与民初之戏剧改良》,对《春柳》杂志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事实上,《春柳》杂志的创办与天津戏剧的改革不无关系,李涛痕、齐如山等人在《春柳》中提出的关于新剧的改革与提倡,对于中国新剧的改革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改良戏剧、研究戏剧之《春柳》
在《春柳》杂志的第二期,春柳旧主的一篇《春柳社之过去谈》[2]回顾了春柳社的过去、发展及其衰落,以及春柳社与《春柳》杂志的关系。"春柳社者,创始于前清丙午年,彼时留东学子,有感于中国旧戏之宜改良及西洋新戏之宜研究。
遂集合同志而组织春柳社。予倩我尊镜若及涛痕,皆为社中干事。"其中还详细记载了《黑奴吁天录》的演出盛况,"日本之大文豪顾曲家及新闻记者,皆存好奇之心,及观黑奴吁天录之内容,无不惊叹,又以为中国人演戏之能力,不图以至于斯也。"《黑奴吁天录》在日本大获成功并取得好评,一时造成轰动的效应,日本的戏剧界也望日本各优努力,以学春柳诸子之态度。在《黑奴吁天录》大获成功之后,春柳社"每年开会两次,皆受欢迎。"然而,好景不长,"越三年,诸子毕业,先后回国。习政法者入仕途,学工商者兴实业。"从日本回国之后,从事新剧的人很多都先后转行,造成了新剧人才的大量流失,"而始终不忘演剧者,当以予倩、镜若、露纱绛士数人。"之后,回国以后,虽然有"镜若等组织春柳剧场,为国内新剧之正宗,与他团体不同,故欢迎春柳剧场者亦众"."先是春阳社者,闻春柳社之名,而在上海组织。"之后,在春柳社的影响下,国内也纷纷组织了一些新剧团体。然而,春柳社毕竟没有春柳旧主所设想的那样蓬勃发展,而是日渐衰落"惜乎春柳同人,未能聚已散之萍踪",涛痕在日本又坚持了七年之后因经费不足而回国。对于春柳社的日渐衰落以至于最终解散涛痕是很痛心的,"至今涛痕既已回国,上海之春柳剧场,又复解散。则春柳社之名,恐不复存于世界。"可见,春柳旧主李涛痕回到天津之后,希望春柳社继续延续其精神,所以创办了《春柳》杂志。"此春柳杂志不可不兴。或春柳社将来之可以复出也欤。"[3]
《春柳》杂志,凝聚着旧主李涛痕对于春柳社复出的希望。
《春柳》杂志的宗旨为"改良戏曲"、"研究戏曲".在《春柳》的发刊词中,作者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阐明了创办《春柳》的宗旨即"改良戏曲针砭社会".客有问于涛痕曰:"春柳杂志,胡为而编辑之也,夫春柳之目的,非所谓改良戏曲针砭社会者乎,有学校,有报纸,有演说,有小说,皆有维持社会之能力,胡为乎改良社会而必期之于戏曲也耶。"涛痕从学校、报纸、演说、小说与戏曲的不同的维持社会之能力方面论述了戏曲在维持社会之能力方面独特的作用及意义。从戏曲的普及程度讲,戏曲普及的是大多数民众,"社会之程度高下本不能齐,学校报纸演说小说之能力所不及者。恒占大多数,而此大多数之人,莫不酷嗜看戏。"进一步而言,由于戏曲与文字、历史、美术以及国家进化都有关系,戏曲可以发挥自身的社会功效,对大众施加影响,以达到戏曲改良社会的目的,即"然后可以促进社会之程度。得以驾欧凌美焉。"因此,春柳旧主认为"此所以欲改良戏曲针砭社会,而谓为不可少之杂志也夫。"[4]
在《春柳》的栏目的设置上,也突出了其重视戏曲的重要性以及"改良戏曲针砭社会"的目的。其中设置的主要栏目"旧剧谈话""新剧谈话"自不必说,是关于戏剧的理论的建设,其中设置的"文苑"栏目和"小说"栏目也与"戏"密切相关。文苑栏的征稿启事:"欢迎投稿以戏为限咏坤角者恕不登载",小说栏的征稿启事也同样写道:"小说以曾经演戏或能作脚本者为限,不能演戏无关社会人心者不录""欢迎投稿,凡小说之与社会有益而能编戏者本社极为欢迎"之类的句子。其中,还穿插设置了"名伶小史""剧场杂评""戏剧词典"和有关戏剧的"杂事轶闻"等栏目,丰富了杂志戏剧改良社会的目的。不仅如此,《春柳》杂志体现了戏剧的理论与创作并重,在剧本的刊登上,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旧剧脚本如《哭祖庙》《马前泼水》《女子爱国》和新剧脚本如《新村正》《一念差》等,丰富了《春柳》的内容。
二、"新"与"旧"的对比中新剧的改良与建设
在《春柳》关于新旧剧的讨论中,关于新剧与旧剧,虽然分成为两个栏目"旧剧谈话"与"新剧谈话"分别展开,但在实际讨论的过程中,新旧在对比中展开。《春柳》的前三期,齐如山发表了五篇文章,"旧剧谈话"栏目中发表了《论旧戏中之烘托法》《论编戏须分高下各种》、《论观戏须注重戏情》,"新剧谈话"栏内发表《新旧剧难易之比较》《论编排戏宜细研究》,而这几篇文章从具体论述的问题来看,侧重在新旧的对比中关注新剧如何建设的问题。所以,在《春柳》杂志的理论阐释中,对于新剧与旧剧的批评与研究,被研究者放置于同一视野。而《春柳》杂志对于新戏的建设与提倡正是在这种"新"与"旧"的对比中展开论述。
研究者注重分析"新""旧"对比中新戏与旧戏各自的难易之处。齐如山从编戏、演戏、布景三个方面对比了新戏与旧戏的各有难易,在新与旧的对比中充分体现了辩证的思想。[5]
从编戏方面来说,旧戏正角是隔一场出来一次或隔两三场出来一次的。在这种情况下,配角的场子最难编。"编的太用力了,仿佛喧宾对主。编的太省事了,又看着索然无味。"而新戏是由几幕构成的,正角在幕与幕之间可以休息,所以出场比较自由灵活,这样一来,正角与配角的戏都比较好编。从这方面来讲,旧戏比新戏难以编排。但是,从每一幕的具体的情节来讲,新戏比旧戏难以编排。因为旧戏在场子上的情节是很容易的:"或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或有几句好白,或有几句好唱工,便不显冷淡。"而新剧却是一幕有一幕的难处。在每一幕中"情节也得有味,穿插也须得宜。话白也得精神。倘若有一处不满足,这一幕便显着松懈。一幕松懈,一出戏便丢失大半。"因此,从编戏的角度来看,旧戏与新戏的编排各有其难易。从演戏方面来谈,旧戏向来不讲究布景,一切的事情,都是摸空,就是平常所说的大写意。新戏则不然,无论何处,都有布景,一切与真的无异。新戏"与动作一层,虽然容易,于形容一层,却比旧戏还难".齐如山用"涕哭一层"举例来说,"在旧戏中稍微一哭,用袖子一拭脸,便算完事。在新戏中,布景一切,都是处处同真的一样。所以形容一切情节也须较真。然也不能同真的一样。"所以,从表演的层面来讲,新戏比旧戏难。再从布景方面来看,旧戏场子碎,三五分钟就是一场,布景的工夫比演戏的工夫大,所以布景一层最难讲究。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旧戏也可以不讲究背景,所以旧戏的背景也容易。而新戏场子长,在每场休息的间歇可以布景,所以场上绝不显忙乱,这是新戏容易布景的地方。"但是新戏布景要耗费许多财力,然而仍然不能保证让所有的客人满意。这样看来,反到更难。"[6]
所以,从布景方面来看,从不同的角度看,新戏与旧戏都有其难处。虽然新戏旧戏各有难易,但齐如山认为还是新戏好。因为新戏情形较真,感化人的力量比旧戏大。作者看似从与旧戏的三点对比中突出新戏的难处,然而这正是新戏需要注意的地方,新戏的编排需在情节、说白方面下一定的工夫;在演戏时要注重动作的真实性;及其布景要尽量做到逼真,让观众满意。
而李涛痕认为,新戏更难于旧戏。[7]他的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同样从新戏的编排上来说,"至于编新戏者,更难于编旧戏。旧戏有一定之模范,但不越乎规矩,斯亦可矣。新戏则不然,处处宜注意精神,情节稍差,令人欲睡矣。"[8]
旧戏由于其有一定的程式性,所以有一定的模式可以借鉴。新戏的处处注意精神,加深了其编排的难度。从戏剧编排的角色分配上来说,旧戏是一人二人为正角,其他的都是配角。"配角虽劣,尚不能掩正角之美。"新剧则不然,"正角固不待言,虽配角亦宜有精神,否则全戏无精神矣。"新旧剧对于角色的要求,令其编排难易有别。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者认为,是因为"新戏纯用白话,不用唱,自无锣鼓。观者但注意于台上之二三人,或三四人四五人,此少数者有一劣角色。同在台上之人,必不能接合无缝。"从表演者本身来说,新戏是讲究动作的规范性和台词的通俗易懂的。作者以舞台动作来举例:"又如三五人同坐,其坐势亦不能重复。若一人袖手,一人以手支颐,一人跷其一足,一人伏案,一人仰天而视。然必须各合地位方可。"新戏对于表演者在舞台上的表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于演员的台词,新戏则要求"不以俗语重"."于是俗语亦相去愈远。夫以中国之文话而唱戏,其高尚不可企及。如以小学生互相背诵经书,其能受人欢迎者几稀矣。"所以作者认为,台词通俗易懂的原则就是使用官话。而对于表演者来说,除了使用官话外,还要字眼清楚,气力充足,"尤难者则为扮女子,亦必使远处得闻妙语。则较之扮男子者更不易矣。"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看来,新戏更难于旧戏。
新剧既然如此之难,那如何改良与建设新剧,自然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新剧,李涛痕、齐如山等人的论述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今日之新戏".李涛痕认为中国现今之新戏,分为两种,"一是无唱之新戏,一是有唱之新戏。无唱之新戏,本为新戏之原则,是即Drama也。在舞台上任意说话,三五分钟即为一幕,无一定之脚本,第一次所演,恒与第二次所演者不同,或增或减,自由为之。"这样没有脚本的无唱之新戏太过自由与随意,主角也可以随意更换,造成了戏剧的"情节两茫然".李涛痕认为,这样新戏,是由旧伶改造而成,言语和动作,是离不开旧戏的。而这样的新戏还常用旧伶演出,在舞台的动作和台词上受到旧的俗套的影响。这样造成的影响使得"不知旧戏之人物,在演者以为新戏无板眼,无强调,信口而出,容易混过去。殊不知新戏之难更胜于旧戏。"而李涛痕认为有唱之新戏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戏,只是在旧戏的基础上加上了时装而已。而《一元钱》《一缕麻》《自由宝鉴》等戏,也可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但其为过渡戏,也不是新戏。在李涛痕看来,新戏必须是"以无唱为原则者也。"[9]
齐如山则认为中国新戏大致分三种。一种是"旧样子的新戏",是"偷旧戏场子",以演的时候长为好,其实大半滑头,毫无长处。一种是"仿电影的戏".近似于变戏法,跟新剧二字,相去更远。一种是"仿西洋的戏".和演说类似,丝毫没有艺术的新意,不过齐如山认为,这样的戏剧还是稍有戏剧的模型的,比第二种似乎强一点。而真正意义上的新戏,齐如山认为是"西洋的戏".[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