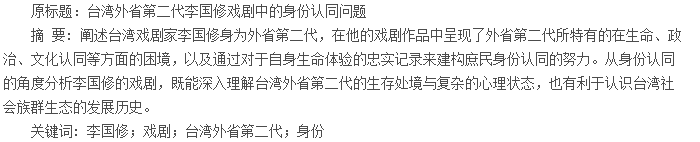
当代台湾著名戏剧家李国修(1955-2013),是台湾外省第二代人。他的戏剧创作始于 1986 年自己创立的屏风表演班,其后与台湾本土意识开始高涨和发展的过程基本同步。李国修在 20 多年的时间总共完成了 30 多部原创戏剧,其中大部分都是集编导演于一身。据"屏风表演班"官网统计,至今,屏风表演班已进行了 1800 多次演出,观众人数累积逾 150 万人次。这对一名台湾戏剧人来说,可谓是深受欢迎,相当成功。
然而,相比其社会影响力,学术界的反应是很平淡的。在国内学术界,目前来看,仅有三篇学术论文,分别为 2004 年台湾静宜大学陈铭鸿的硕士论文 《"拒绝漂流"---李国修剧作主题之研究》、2010 年台湾成功大学蔡佳陵的硕士论文《两种不同的凝视---李国修与赖声川的认同建构书写》,2014 年第 4 期胡明华发表于 《台湾研究集刊》的《台湾外省第二代李国修戏剧中的创伤记忆与超越》,其余只有寥寥的访谈和介绍性文章。
这一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应该与李国修戏剧比较草根和庶民立场有关,也跟其严肃的意义往往被喜剧的形式所掩盖有关,但是,李国修在他的剧作中,凝结着他作为外省第二代在台湾 1980 年代末以来本土化浪潮中身份认同的焦虑及应对的努力。因此,李国修在其戏剧中体现的身份认同困境与自我建构的努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国修的戏剧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6-1990 年,基本上是自发地表达对台湾生活的观察、看法与态度,如"三人行不行"系列第一、二部,"'民国'备忘录"两部等。虽有《西出阳关》写到外省老兵,但身份认同并未成为该阶段关注的问题。第二阶段为 1991-2000 年,这一时期台湾本土化潮流语境使李国修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迫切,所以注重"谈私领域的归属与认同问题"[1]56,代表作有"三人行不行"系列之《OH!三岔口》《长期玩命》《空城状态》,以及《松紧地带》《救国株式会社》《京戏启示录》等;第三阶段为 2000 年之后,在从外部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后,在上一阶段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意识地建立新的自我庶民身份认同的努力,表现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存在,该阶段代表作有 《好色奇男子》《女儿红》《六义帮》等。
李国修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表达和思考,主要体现在 1991 年之后即第二三阶段的剧作中。这些剧作不仅详尽记录外省第二代普遍性的生命体验和身份认同特征,还深刻体现了台湾社会在族群生态和未来走向上的复杂情形。
一、外省第二代身份认同的困境
不同于台湾外省第一代和第三代,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外省第二代有着特殊的矛盾处境。在他们身上,父辈原乡认同的直接影响和自身在移入地的生命体验二者是割裂的。在 1990 年代之前,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还不明显。但此后随着台湾本土化潮流的发展,台湾外省第二代不得不直面身份认同问题,并且陷入到两难的困境。为此,他们一般都倾向于双重认同,既有来自父辈情感和学校教育的中国人认同,又有来自生命体验和本土化浪潮压力的台湾人认同。据有关调查显示,1990 年以来,台湾外省人的身份认同在"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项上比例最高。
这体现的更多是外省第二代的倾向。单纯的统计数据无法反映其后面外省第二代的具体而微的复杂心态,更难以把握其后潜藏着的问题和启示。而李国修 1990年以来的剧作,以外省人第二代的视角关注台湾社会,寄寓着自己在身份认同困境中的体验和思考,给人 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李国修 2003 年时回顾说,在 1990 年代初"开始寻找到一个中心点,就是我对于这片土地的归属与认同,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延续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持续的,我的作品一直在谈同一个主题,叫做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问题。"[1]132应该说,李国修的对自身认同困境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他 1990 年代的剧作中,代表作如 《救国株式会社 》《 松紧地带 》(1991),《 京戏启示录 》(1996),以及"三人行不行"系列之《OH!三岔口》(1993)、《长期玩命》(1997)和《空城状态》(1999)等,也包含《女儿红》(2006)等。依据认同理论提供的角度,从生命、政治、文化层面来分析上述作品,可以看到李国修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纠结、撕裂感和夹缝中的困境。
首先,在个体生命体验层面,李国修有着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双重认同,以及夹缝焦虑。在身份认同理论中,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认同多寄托在地域空间上。相对于时间的无形无质,空间地标更为具体明确,所以生命的记忆往往跟空间连结得更紧密。在李国修生命中,山东莱阳和台北中华商场就是他生命的两个重要地标。
李国修的父母原籍山东莱阳,父亲是做京剧手工戏靴的师傅。1949 年,父亲携带家眷,跟随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辗转来到台湾,父亲念念不忘莱阳的风土事物,母亲更因不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患上了忧郁症,自我封闭在家十余年,郁郁而终。在父母的深刻影响下,李国修能说一口流利的莱阳话,并多次在舞台演出时使用。半自传体剧作《京戏启示录》和《女儿红》是李国修追寻自己生命之根的故事,在两剧中李国修都扮演满口莱阳腔的父亲。"我每次在台上透过角色的口中演出说山东话时,心里就会有种莫名的骄傲---我用我的母语讲我家乡的故事。"[2]33在《女儿红》中,母亲吟唱的"清蓝蓝的河呀,曲曲又弯弯,绿盈盈的草地望不着边……谁不说俺家乡好,就像那长青树呀,高高入云端",也是山东莱阳的歌谣,其他如父亲对莱阳梨的怀念,都化为强烈的原乡情结深刻地烙印在李国修的情感记忆中。毕竟这些来自血脉的牵连都是无法割舍的。
另一方面,李国修生于台北,长于台北,中华商场也是他生命的起航母港。中华商场不仅留有他童年至青年的成长记忆,而且是他的戏剧启蒙地。他的很多戏剧作品与中华商场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李国修也自述过,"像《六义帮》便取材我和中华商场一群玩伴结盟的故事,而《女儿红》也来自我母亲那多年来在商场阁楼上的乡愁。"[3]从中华商场扩展开去,对于台湾,他也有深厚的情感。妻子王月是台湾本省人,一对儿女已经完全把台湾当做了家乡。
然而,在两岸开放探亲后,他找到机会回到莱阳寻根,才发现虽乡音依旧,但亲人无踪,物是人非。在一次访谈中他还有些愤然:"现在回到山东老家,莱阳县已经不见了,因为要换地名表示政权建立,莱阳县已经没有了,改成莱西县。他改得面目全非,让你回去找不到。而且我的老家那一群人,因为历史改变已经定居在河南了,因为历史情境、国共会战造成今天。他们已经不在原乡了,老家有血缘的族群都已经不在老家了。"[1]141本来在多年寻根梦破之时,应该反过来加深他的台湾认同。然而几乎就在同时,1990 年代不断发展的台湾本土意识,又将外省人划为可疑的外来者,质疑其是否"爱台湾".这种两边都属于又都不属于的身份认同困境一直伴随着李国修 1990 年后的戏剧创作。
其次,在政治认同层面,李国修有着非中国非台湾的特点,有着被遗弃的焦虑。由于少年时期所受的国民党反共教育,对大陆"文革"的负面印象,李国修并不认同大陆,这在他许多作品中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可以得到印证,如《松紧地带》中满口官腔的女书记形象、《OH!三岔口》中只谈政策不谈亲情的解放军钱定远形象以及 《长期玩命》中老邓回大陆探亲的遭遇等。
同时,李国修也并不认同国民党当局。他认为,国民党把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府"设在本应成为国耻纪念馆的日据时代总督府,就体现着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执政的"过客"心态,说明他们没有花心思来经营台湾。《救国株式会社》要表达的是李国修的看法:"总统府就是台湾最大的株式会社".《长期玩命》中他借人物之口说台湾"这个环境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政府都没有方向,你没有给他看这个国民党政府弄得歪搞七岔、整个社会乱得像烂泥巴。"[4]
而且随着 1990 年代台湾本土意识的发展,李国修这些占大多数的外省人以前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恩泽,却要为国民党当局背负压制、迫害本省人的污名,对其也有一种怨恨的心理。当然,李国修也无法认同秉持台独纲领的民进党。台独理念直接将外省第二代怀有着深厚感情的祖籍地划为外国,并且招来李国修深深厌恶的战争威胁。而且,本土色彩过于浓重的民进党对外省人的不信任也使外省第二代如李国修者敬而远之,例如在《三人行不行:OH!三岔口》中,郭母从垃圾堆里捡到一个李氏宗亲神主牌位,暗讽李登辉数典忘祖。
在李国修看来,大政治并不关心民众,反而操弄民众,因而对政治持不信任态度,远离政见是非,这在他的作品《三人行不行:OH!三岔口》《三人行不行:长期玩命》中都有所反映。
其三,在文化认同方面,李国修也处于难以抉择的认同困境。文化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李国修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看重。他从父辈那里承传了对戏剧的热爱,虽然没有条件从事父亲愿望中的京剧,但还是选择话剧而不是电视戏剧演员作为他的终生职业。他早期的实验剧作《三人行不行Ⅰ》和《没有我的戏》就是受相声艺术形式的启发,在 1989 年还专程到大陆拜马季为师学习相声,并为父亲热爱的京剧的衰落而叹息。
然而,台湾语境让他的文化认同充满困惑。台湾受五十年日本殖民的历史,加上李登辉等的"去中国化"活动,使"台湾人依旧在后殖民的阴影里挣扎,一方面想在美、日等文化强国的猛攻之下站稳脚步;一方面又碍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分裂,对中国文化难有共识。"[5]
文化认同最重要的标志是语言。在李国修的剧作中,国语、莱阳话、闽南话、日语、英语等众声喧哗是常见的景观,虽然这是台湾的历史和文化造成的现实情况的反映,但在客观上也为他在文化的传承造成了困惑。莱阳话毕竟没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国语是学校教育的正统语言,也是台湾社会通用语,承载着中华文化,但其地位在 1990 年代的台湾也受到质疑。闽南语在台湾本土意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对李国修和外省人来说掌握它却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的需要。
对语言的认同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认同,语言多元的情境也意味着固有传承的威胁。在《京》剧中他感叹 "遗憾这个时代的进步将渐渐遗忘更多传统的精神与价值。"[6]32李国修在戏剧中的众语喧哗现象,无论是现实的反映、还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或者是适用观众的考量,实际上反映着他在语言乃至文化的传承上的不稳定感。
总之,由于 1980 年代末抬头的台湾本土化运动、1990 年儿子的出生以及 1992 年中华商场这一记载着他重要生命记忆的空间被拆除,李国修对自身身份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因此,在 1990 年代的剧作中,李国修表达了他在台湾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无法找到适当的身份认同归属的困惑,并且发现自己的生命体验也被这些宏大话语所遮蔽。所以,在拒斥宏大话语的认同的同时,他也发现并开始了新的身份建构的努力。
二、自我庶民身份认同的重构
2003 年,李国修说:"我后来才慢慢找到自己真正的创作核心,原来我关注的重点不是对社会或政治现象的感慨,而是那一个个在我身边发生的'生命的故事',我认为这才是我身上背负着的创作使命。"[7]其实表达生命故事的过程从 1990年代已经开始,如 《松紧地带》《蝉》《京戏启示录》,这一努力在 2000 年继续下去,并且更加自觉和深入,如《北极之光》《女儿红》《好色奇男子》《六义帮》等完全疏离了政治和社会议题,彻底转向家庭和情感题材。他在表达生命故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建构起了自己的庶民身份。
他在 2003 年这样说过:"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只有一个外省人第二代李国修,他用外省人在这片土地的情感写作品,所以我的作品就是外省第二代的观点,它很微妙。我在这个观点中记录着庶民的记忆,我不是在记录大历史,我没有必要做史学家,我用戏剧的形式,透过戏剧的包装来阐述庶民记忆。"[1]138这段话含义丰富,有三个层次对理解他的身份建构非常重要。第一,李国修强调自己的剧作立足于外省第二代的特殊定位。这是他进行身份重构的根本原因。第二,"我在这个观点中记录着庶民的记忆,我不是在记录大历史".此处提到的"庶民记忆",正是他基于外省第二代的定位,并结合前文所述在身份认同上的困境,进行庶民身份重构的基础。他之所以要重构庶民身份,是因为发现"当我们翻阅历史,历史并没有记载我们的一生;当我们面对史实,史实总是偏离你的境遇与感受。于是,在历史中我们看不到大量凡人的记忆。"[8]
第三,"透过戏剧的包装来阐述庶民记忆",可见李国修戏剧创作的自觉性。他有意识地将自己"情感的归属与认同的定标,透过编剧的位置写出来。"[1]138李国修所建构的庶民身份的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庶民的生命记忆和历史。他否认了庶民记忆是替弱势群体发声,或者关心认同土地的方式,而明确指出它是"一种对生命的看法与态度"."我为的是我自己的成长而创作,成长中累积的经验及累积前人、长辈给我的思想而创作,我一直在创作生命的故事。"[1]140所以,当别人认为他以戏剧表达政治立场时,他很不满,因为时事在他那里只是庶民产生独特生命体验的背景。李国修以自己的生命进程为线索,构建出自我独特的庶民身份认同。下面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属于什么地方""我要到哪里去"这些基本的身份认同层面对他的庶民身份认同内容逐一阐述。
其一,"我是谁?"作为外省人移民,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于是,他把自己定位为庶民,从本真的生命体验中重新确认自我存在。例如,《六义帮》是以他儿时记忆为蓝图的文本。他之所以改编了林怀民同名小说《蝉》,原因在于其深深触动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生命体验:"我有一种想要回到过去的冲动,阅读《蝉》时,那些场景是我熟悉的,我几乎闻到了当时晨雾里空气的味道,我几乎听见了中华商场唱片行所传出来的音乐,我几乎感觉到庄世恒就住在我家隔壁……"[9]《松紧地带》的创作动机源于目睹妻子倍受痛楚地生下儿子的生命经验,寄托着自己面对新一代的现实感受,这是他"为自己写下忠于自己的历史。"[10]
此外,在纪念父母的半自传体戏剧《京戏启示录》《女儿红》也镌刻着自己的生命记忆。这些都共同塑造出一个独特的"我"的形象。
其二,"我从哪里来?"《西出阳关》《京戏启示录》《女儿红》 是李国修追念父辈的主要作品。他在《西出阳关》的序言《苦难不再来》中写道:"十年前过世的父亲与父执辈的那群亲戚们,在四十五年前随着战争颠沛流离地来到了台湾……对于从事戏剧创作的我而言,我仿佛替他们背负着一个遗憾。"[11]剧作通过描写随国民党来台老兵老齐生离死别的爱情和无奈的现实,写出了作为庶民的父辈的血泪记忆,其中还把李国修父母经历的海南岛大撤退,作为故事的重要背景。《京戏启示录》则在真实的舞台上,叙述着时代变迁下的生命流动,并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精神的传承。父亲的"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的话被他奉为一辈子的座右铭。而在《女儿红》中,母亲的莱阳、儿子的中华商场在母子亲情中成为同一生命链条的两个相连环节。
其三,"我属于什么地方?"李国修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从中华商场扩展开去,认为台湾是自己的原乡,"我父亲那一代叙述的原乡对我而言没有情感,所以我在这里建立我的原乡"[1]142,"这里成为我的原乡,因为这是我出生地。"[1]141他在《六义帮》中,将自己的童年故事与日据时代的台湾英雄廖添丁、安葬于台北的杜月笙连结在一起,其实表达着自己与大陆的关联和对台湾原乡的认同。
同样是爱台湾,他体现出的是基于庶民身份的生命感受,而不是政治利益。在关注政治时事的表象下,是他对与生命相连的土地的爱与关怀。在他看来,台湾这块土地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即使在这块土地上有多么的动荡不安,他都会奋斗、努力。他在剧作中写了很多移民形象如《长期玩命》中的 Peter 一家,基本上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
因为他们没有以生命去爱台湾,而是因为利益而逗留台湾,手持外国护照,随时准备作鸟兽散。"看戏或看人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感情、寻找自己的位子、寻找一份希望与爱……毕竟城再空,人永远不空!老百姓如你、我都有一份情,彼此抚慰,鼓舞地找到了在这个城市活下来的理由。"[12]《空城状态》 中的这句话正是他对台湾之爱只是源于朴素感情的表白。
在建立庶民身份之后,他更加关心的是家庭和情感的稳定,因为家庭才是庶民更重要的存身之地,是庶民最后的避风港。在他创作的家庭婚姻题材的戏剧中,表达了自我的希望和恐惧。《婚外信行为》《北极之光》《好色奇男子》 等写了婚外恋题材,来表达家庭稳定的意义,如 《婚外信行为》只是想说明,一切情爱关系中的"信"应该是信任、责任和承诺;《北极光》写了对专一执著的爱情的永恒追求;《好色奇男子》则写了小人物在战乱时局中的感伤而美好的情事;《昨夜星辰》对婚外情和分裂家庭的思考。总之,家是庶民最温暖的港湾,需好好经营。
其四,"我要到哪里去?"对于庶民来说,生命的传承是最重要的,而未来又是自己难以把握的。
在李国修的戏剧中,大量出现了"孕妇"形象,从1988 年《"民国"76 备忘录》中开始,后来在《松紧地带》《太平天国》,"屏风系列"都有出现。孕妇形象的意义之一就是他 "有意识地在凸显生命的传承","为什么会出现孕妇,是因为我向往下一代……舞台上出现孕妇这样的符号人物,主要是谈'传承',谈生命的延续。当然传承有几个要件,一个部分是生命延续,一个部分是思想传承,一个是信仰传承。我在故事里常常用小人物来谈我的渴望,……渴望面对下一代,家的稳定结构和生命的继续延续。"[1]136-137除此之外,孕妇形象在李国修剧中总是意味着一种对安定的需要和对主人公的压力,指向未来,其中往往充斥着一种对未来迷惘的感觉。这一迷惘同样也是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如《松紧地带》《太平天国》中的主人公面对孩子即将出生的事实,心中充满了对于未来的焦虑,而他们所焦虑的正是没有把握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定的未来,《太平天国》中的杨秀清甚至愿意让外星人带走自己的孩子,"因为不能让孩子在乱世里生活!最乱的时代,我们要做最好的选择!"[13]
《女儿红》中的修国同样面对妻子的生产而惴惴不安,他不得不通过对家族历史的寻根、在对历史的追索过程中寻求面对未来的勇气,而这些都是缘于对台湾现状和未来的迷惘。
三、李国修身份认同思考的意义
李国修在戏剧中呈现身份认同困境与建构庶民身份认同的努力具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
首先,不同于别的外省第二代作家,李国修在对台湾外省人生存状态的表现上,有着自己特殊的意义。在外省第二代作家中,朱天心、朱天文、张大春、龙应台、骆以军、张晓风等著名人物基本都是出身眷村,而且台湾很多演艺界人物都出身眷村如侯孝贤、李安、杨德昌、李立群和王伟忠等,以致很多人经常把眷村作家和外省第二代作家等同。然而,眷村外省人在整个外省人群体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根据台湾妇联会"1982 年之统计资料显示,若不包含违建,全台湾眷村共有 879 个,共有 98535 户。其中,若以每户平均 4.47 居住人口计,约共有 467316 外省人住民居住于眷村,约三成外省人居住于眷村。"[14]
虽然具体比例有争议,大致在三成左右应该是可信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外省人并不住在眷村,而是与其他台湾人杂处。
眷村外外省人虽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富贵阶层,但更多的还是李国修这样家庭的普通民众。但是,在台湾,这个人数不少的人群却成了沉默的群体,他们的遭遇和处境很少有人知道,幸运的是,他们有了李国修这样的代言人。李国修戏剧中所表现的外省人身份认同问题应该在这群人之中有着极大的代表性。如果对比看李国修的剧作和赖声川、王伟忠的《宝岛一村》就可看出其特殊性来。《宝岛一村》自 2008 年上演以来,在海峡两岸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它真切描写了眷村中两代人从 1949 到21 世纪初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到,眷村外省人的生活范围是相当封闭的,即使是第二代,也大多移民国外,虽然还保留着中华文化的记忆。外省人与本地人融合的艰辛过程和认同困境在其中基本是被回避的,而这对一部分走出眷村融入台湾社会的眷村二代和眷村外的外省第二代来说本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复杂的命题,在眷村作家中触及是比较少的。而这个缺憾的弥补恰恰正是李国修的价值所在,例如《松紧地带》中的外省第二代雷海青与《太平天国》中的杨秀清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困境,都躲进了中国历史中的太平盛世,但是发现那里仍然充满着战乱和不安定,逃亡的过程让他们更坚定了在台湾安身立命的意愿;到了 《三人行不行:三岔口》《三人行不行:长期玩命》,李国修扮演的角色从外省人形象化身为本省人郭父形象,在移民潮中执著地坚守着对于台湾这片土地的情感。这种转变表现了李国修深感外省人的身份无法带给他稳定的归属感,不得不以本土身份寻求归属的无奈与努力。
其次,李国修对身份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一以贯之的以戏剧视角看台湾的方式,使其剧作成为台湾社会的一面忠实而完整的镜子。李国修为自己的剧团"取名'屏风',是因为我认为戏和人生并无距离,摆上屏风,就能演戏,幕前戏子伶人的扮演,不过是屏风后真实人生的演绎。"[15]
他常在舞台上扮演跟自己人生经历有关的角色,也经常密切关注和反映台湾时事,如"'民国'备忘录"系列与《株式救国会社》。李国修生于台北长于台北,并且所居住的中华商场,五方杂处。他对台湾社会的熟悉程度,从其戏剧作品深受欢迎即可看出。同时,由于父辈的原乡情结影响以及 1990 年代以来外省人被本省人的质疑,也使李国修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审视自己与台湾的关系,因此对台湾的观察与认识又多了一份局外人的敏锐和客观。这两方面的结合,让李国修戏剧中的台湾影像既有着可称为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又有着内在把握上的深刻性,其中对台湾社会现象、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对台湾语言现象的表现等等都是有独特性的。例如"'民国'备忘录"系列对于台湾当代社会现象的年谱式记录;《三人行不行:三岔口》《三人行不行:长期玩命》中探讨的"移民热"问题以及台湾人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西出阳关》《我妹妹》《北极之光》《京戏启示录》《女儿红》 中对于大陆内地多种方言和谚语(上海话、四川话、山东莱阳话、北京话等) 的保留和呈现、《女儿红》《好色奇男子》《六义帮》对于台湾各地方言和俗语的呈现等都构成了台湾历史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李国修戏剧中体现的对身份认同困境的克服与重构的努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从台湾历史上看,它经历了多次的移民潮,最终形成现在的社会状况。当今所谓的"四大族群"就是较大移民潮批次的不同造成的,虽然移民大多是从福建、广东等地渡海而来。所以,李国修戏剧中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台湾历史的重要部分,呼应和折射着台湾移民史上的血泪记忆。从现实意义看,台湾当今"四大族群"之说,虽然只是一种族群想象,却割裂着台湾社会。李国修戏剧中所揭示的外省人在台湾社会的融入经验,说明各个族群固然在生活方式上有一定差异,但互相的认同和融合也是可能的,关键是要延续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鲜活生动的文化传承,李国修思想中的家谱意识和戏剧传承精神就是对此的最好证明。
家谱意识是李国修克服困境,延续生命链条的力量源泉。他在多部剧中都有类似于"从踏上台湾这片土地开始就是我们的家谱"的话,如"我们家只要从一九五誘年五月一号踩在基隆码头的第一步算起,到今天,就是家谱了。"[2]169这是李国修在自己的身份认同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斩钉截铁提出的宣言。家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一种载体,而李国修重建家谱的行为看似隔断家谱,却反而真正秉承了其精神内涵,展现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顽强求生存的强大意志和生命力。其实早在 1980 年代的"'民国'备忘录""三人行不行" 系列都可以说是李国修在一种无意识中写就的家谱背景,因为它们都是"期望藉此创造共同的记忆与表达对社会环境的关怀。"[16]
戏剧传承是李国修在陌生、不安定环境中所依托的精神支柱。他多次说活在台湾只求三件事:温饱、安定和传承。李国修选择戏剧为职业,父亲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原因。身为京戏手工靴匠人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在京剧舞台上唱戏,光宗耀祖,这在半自传《京戏启示录》中有表现。然而京剧衰落,李国修接触同类艺术的话剧并将之作为职业的十年后,蓦然发现"原来,作剧场的那股拼斗的傻劲,全是源自于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我感受到了那股传承的精神与压力。"[6]23李国修的大哥传承了父亲做京剧戏鞋的技能,而李国修则选择剧场作为对父亲"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的精神传承,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支撑着李国修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坷,赋予他的生命以信念的光辉。
李国修对于自身身份认同困境在生命体验、政治和文化上的呈现,自我庶民身份认同的自觉、立体性建构,都渗透着他个人的而又有普遍性的情感体验和思考结晶。他的剧作不仅反映了台湾外省人生存处境和状态的复杂性,更体现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奋斗精神和传承意识,这使他的作品"相当程度摆脱了战后台湾外省人文学常有的哀愁基调,相对展现出不同的意义格外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1] 陈铭鸿。"拒绝漂流"---李国修剧作主题之研究[D].台中: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4.
[2] 李国修。 女儿红[M]. 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3.
[3] 陈玉慧。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陈玉慧对谈李国修[J]. 印刻文学生活志,2013(3):158-163.
[4] 李国修。 三人行不行Ⅳ:长期玩命[M]. 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3:92.
[5] 李国修。 好色奇男子[M]. 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3:32.
[6] 李国修。 京戏启示录[M]. 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3.
[7] 炊烟。 李国修的十问十答[DB/OL].(2007-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