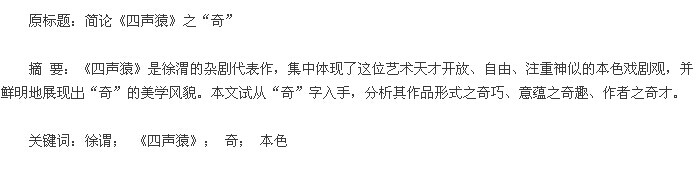
《四声猿》为明代徐渭所作杂剧,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 以下简称《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四个故事) .作为明代杂剧的代表剧目,《四声猿》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后世评论赞颂者繁多,如袁宏道云: “予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梅客生尝寄予书曰: ‘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王骥德云: “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四声猿》中的故事题材经过后世小说、戏曲、影视的多次重新演绎,已经为普通人所熟悉,积淀于我们的记忆之中,但作为明代杂剧的典范,被澂道人称为明曲第一的《四声猿》原本,到底具有怎样的艺术魅力,能让无数人击节称奇呢? 本文结合作品试从形式之奇巧、意蕴之奇趣、作者之奇才三个方面来做分析。
一、形式之奇巧
元杂剧与唐诗、宋词一样,成为一代文学之后终于走上格律化、体制化道路,其质量和艺术水准成为后世戏剧创作的圭臬。后世戏剧文学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至有明一代,形制更为自由、更具有生命力的明传奇得到发展和繁荣,开创了戏剧艺术的新局面。这两者都有庞大的体制和完整有序的结构,前后辉映,各领风骚,成为中国戏曲的两座高峰。
但在明传奇融合北曲声腔和元杂剧艺术样式的精华并逐渐文雅化、规格化、声腔化进而成为全国性大型戏曲样式之前,必有一个南北曲融合互补的阶段,徐渭正处于这个阶段。
首先,开放性和兼容性相宜的结构追求。元杂剧体制为四折一楔子。一个剧本由四折组成; 在音乐上,每折只使用一个宫调并且不能重复。而全剧只能由一人主唱,正末主唱的称为“末本”,正旦主唱的称为“旦本”.南戏则分“出”,但出数不做规定,音乐上也不限一个宫调,角色上不限一人主唱且歌唱形式多样,有独唱、对唱、合唱、轮唱等。到晚明时期,严格遵守元杂剧体制的已经很少见,徐渭更是秉承其一贯“不骫于法,亦不局于法”的艺术追求,吸收南北优长,据情剪裁。
《四声猿》不仅体制灵活,而且独创性地将四个题材和情节缺少关联的独剧合为一剧。每个独剧的篇幅也视剧情的需要而设置: 《狂鼓史》一折,《玉禅师》、《雌木兰》各两折,《女状元》五折。这不仅突破了元杂剧四折体制,连叙事文学的连贯性也打破,将故事贯穿的不再是情节,而是作者的主体精神,给人以奇异醒目之感。而且短小精悍,如《狂鼓史》只有一折,如宝剑锋利闪电敏捷,尤其便利于作家抒写怀抱、宣泄情感而不必考虑故事情节等叙事要素的束缚,更有利于集中的痛快的抒情。这种体制最接近被称为匕首的杂文,用于描画荒唐、嬉笑讽世、愤世嫉俗、感怀身世的文人化创作再合适不过。在明杂剧中,这种短小的讽世杂剧个性鲜明,成就突出,易为后世文人所接受。
其次,宫调使用的灵活。“从演唱体式上看,嘉靖以后的杂剧大都是南北合套或者纯用南杂剧,杂剧的纯北曲形式从北曲上看已经终结。”王骥德称徐文长杂剧“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四声猿》中,《玉禅师》约作于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年) ,其他三部作于万历三年( 1575 年)。《四声猿》正是这种融合时期的典范之作。王世贞《曲藻》中谈到北曲和南曲的区别:凡曲: 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 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宜粗,南气宜弱。
此吾论曲三昧语。对于注重表达自我主观情思的徐渭来说,自然是据情剪裁,不拘格套。《四声猿》便是北曲和南曲交融的典范。这一交融,使剧本呈现出生机蓬勃的精神风貌: 《狂鼓史》为北曲,一折; 《玉禅师》为南北联套,二折; 《雌木兰》为北曲,一折; 《女状元》为南北联套,五折。同时徐渭反对寻宫数调,认为南戏本是“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与”? 于是,表达祢衡怀才不遇备受压抑的不平之气和慷慨悲壮的情怀,便用“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辞情多而声情少……北气宜粗”的北曲,况且,“击鼓骂曹”这样的艺术创造,更要将击鼓和痛骂的动作以短促有力的音节展现出来方才痛快,至于效果,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语: “此千古快谈,吾不知其何以入妙,第觉纸上渊渊有金石声。”表达黄崇嘏意欲显示才调高妙的隐微心理,便用“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辞情少而声情多……南气宜弱”的南曲,细腻委婉。
二、意蕴之奇趣
《四声猿》从剧名含义、题材选择、体裁处理到整体风格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无不透露出作者的精心布置和托意深远,充满奇趣。
首先,名字奇特,动人情思。单就《四声猿》这一个名字,已经足以使人意远,将人带入悠长伤感的渔歌所营造的“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境界中。“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是《水经注》中记载的一首关于长江三峡的渔者歌谣。“猿啸之哀,三声已足使堕泪,而况益以四声也! 其托意可知矣”.于是作者之意,若要体会这第四声猿鸣之哀,也须观者亲临如三峡山水般清冷绝寂奇险境遇之后,再回首玩味。这第四声猿啸何尝不是感慨人世险恶,孤独行走,像首人生的挽歌。杜甫有《秋兴》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爱国忧民的深情满溢。《女状元》折数最多,托杜甫诗意也丰。开篇《女冠子》即取杜甫《佳人》诗比喻主人公的身世孤单,性情高洁,才华清俊。考取状元的题目,三首有两首化用杜甫的诗意。其中一首《北江儿水》:西邻穷败,恰遇着西邻穷败。老霜荆一股钗,那更兵荒连岁,少米无柴。况久相依不是才。幸篱枣熟霜斋,我栽的即你栽。尽取长竿阔袋,打扑频来,饣甫餐权代,我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这其中就有徐渭自己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意思。那么这第四声猿啸,何尝不是替天下寒士们发的。
其次,题材奇异,夺人耳目。《狂鼓史》写祢衡在阴司判官的要求下,将曹操一生劣迹补骂一番,曹操在判官铁鞭之下还要装足旧时模样,最后祢衡得上帝赏识,招为御前修文郎。剧中,判官“姓察名幽,字能平”,是一个“明白洒落的好判官”,且对文士极为尊敬,这补骂的痛快便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复仇手段的奇异,要到阴司后,代表正义一方的祢衡才能借助公正判官之力骂曹操一个盖棺定论,好生痛快。
而曹操到了此处完全是纸糊的老虎,供骂的对象,任摆布的小丑。是非要到梦境中才分明,现实的绝望和颠倒不言而喻。当年的曹操借刘表、黄祖之手杀了敢于骂他的祢衡,如今的严嵩假他人之手害死了敢于直陈时政的沈炼。《四声猿》剧中祢衡气概超群、才华横溢,26 岁英年而亡,只能以为鬼判、上帝修文书实现其价值。悲哉! 《狂鼓史》不仅是为好友沈炼鸣不平,而且抒发了自己那股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玉禅师》写修行二十多年的玉通和尚因为没有相迎新到府尹柳宣教而遭其报复,被官妓红莲使计破了色戒羞愧而死,立誓要投胎到柳宣教家为女,将来为娼做歹败坏他家门风,如愿后被师兄点化醒悟的故事。神权也好,政权也好,互相攻讦报复全利用一个色字。官府对不顺自己的总要打击报复甚至置之死地。佛门宣扬四大皆空却违背基本人性,且把形式的戒律看得太重,一经破坏立时便将世俗争斗尘世污秽填满胸臆甚至变本加厉。此剧将神权、政权的虚伪肆意玩弄。这也是与晚明个性解放、肯定人性正当欲望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雌木兰》、《女状元》写一对女子女扮男装,一文一武。文的高中状元,“词源直取瞿唐倒,文气全无脂粉俗”,管理民事大展“惠民束吏之才”,断三桩疑难案“理冤擿伏,可也如神”,文思有倚马之才,“撑着珍珠船一般,颗颗都是宝”,更兼“琴天籁,画活苔,棋吾败”.取她做状元的老师看中她的才华,立要招她为婿,她只好说破身份,终于又同老师的儿子即新任状元成婚。武的则为了国家急需军士,父亲老迈弟弟年幼,因此换男装替父从军,终于建立功勋,功成身退嫁给王郎。
首先,两部戏在题材处理上奇特在: 首开女子易装戏曲题材之端。自从《四声猿》推出黄崇嘏、花木兰一文一武两位杰出女性,不仅传奇作品全力响应,而且杂剧创作亦精心效仿,有清一代即有多部作品问世。王夫子《龙舟会》专写谢小娥易男装为仆,三年报仇雪恨的故事,无一例外体现出《四声猿》杂剧的精神浸染。
其次,在以喜写忧的结局处理。身为女子同样有治国安邦之才,且满腹才华,功业手到擒来。徐渭对她们进行热烈的赞美,于是两剧都提到的似叔援嫂溺难辞手的传统理由早已在二人才华的张扬和赞美声中淡出,读者感受到的分明是两位主人公的主动和自信,当才情得到展示后,主人公的行为之奇,才艺之绝统统归于正统,归于沉寂。表面看女貌郎才,皆大欢喜,可是,当夜空刚绽放过绚烂的烟花,人们的思想还会只看到平静的黑色吗? 世俗人看到的依旧是国人平素喜爱的大团圆,然而从艺术效果上看,却正如《红楼梦》中的《收尾》判词: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再绚烂的绽放也都是一个悲剧收场。
最后,本色观造成的奇妙的审美风格。所谓本色,指语言通俗晓畅且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徐渭《南词叙录》中反对以时文为南曲,反对将经、子之文匀入词曲创作中,甚至宾白也用文言的创造方式。“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因此,宁“俗而鄙之易晓”也要越通俗明畅越好,在于其素色本天然而已。而故意扭捏,婢作夫人,以入诗尚不可的经、子语入曲,徐渭直指这样的原因在于“直以才情少,未免凑补成篇”.艺术是为了丰富人类的情感,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真正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以情动人的,直接触动人心本色。要达到本色,有多种方法,徐渭选择抒情的写意。徐渭作为中国文人水墨画青藤画派的鼻祖,独创的泼墨水墨画法一直以笔走龙蛇、气韵生动之意震撼人的心灵,重视神韵多于技巧,比工笔易流于纤细柔弱更显气象之大。这种大写意的美学观必然渗透进戏剧观中。
三、作者之奇才
《四声猿》剧作之奇,归根还在于作者徐渭之奇,在于他才奇高而命运奇坎坷的反差与作品本身相互联系而让人对双方都产生了更深的理解和悲叹。如果说理解了作者的思想和经历,我们对作品本身也会有更深刻的感触。
首先,徐渭缺少家庭的归属感。徐渭出生百日丧父,由嫡母抚养。嫡母无子,虽然对徐渭疼爱有加,但是在徐渭十岁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徐家卖掉了包括徐渭的生母在内的一批仆人,无论有意与否都给童年的徐渭留下了心理阴影。
嫡母苗宜人与另外两个非她亲生的儿子不合,徐渭也受到家庭紧张关系的影响,自觉“骨肉煎逼,萁豆相燃,日夜旋顾,唯身与影”,而这个疼爱自己的人也在他 13 岁时离世。“病渐剧时,渭私磕头,不知血,请以身代,请医路。卜人语以谶语恶,不食三日。嫂怜之,好语之。稍粥”.在这种境况之下,徐渭缺少基本的亲情,童年时代的心理阴影必然对徐渭有影响,他独立以至于孤僻的个性以及最后精神的疯狂与童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其次,人生遭际的极度坎坷。少失怙恃,家道中落,青年丧偶,仕途无路,而诗书文画奇绝于世,徐渭的人生极度坎坷而传奇。在这所有困苦之中,仕途无望的打击尤为严重。
“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再试有司,辄以不合规寸摒斥于时”.在《女状元》中黄崇嘏女扮男装前去应考的动机也是如此,而且她对自己的才华极为自信,“管贝青取唾手功名”,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然而徐渭却终不得志。
徐渭的奇才还体现在他的军事才能上。从 37 岁到 42岁的 5 年间在总督胡宗宪府做幕客,是其一生得意之时,“一切疏记,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当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大权在握、威震东南,手下有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负责东南抗倭事宜,关系重大。这样一个人物对徐渭言听计从、礼遇有加,又是在徐渭最不得志半生潦倒的时候,对徐渭的意义可想而知。然而,这样一个人物却因为严嵩倒台而受牵连,终于死在狱中。
当世界是非颠倒,假作真时真亦假。惧怕也好,看透也好,徐渭“遂发狂,引巨锥剚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其后更加愤世嫉俗,佯狂愈甚,自称畸人,自为畸谱,自为墓志铭,“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世事颠倒,半明不灭。畅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 独有一般差似我,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积高千丈恨难消”.于是本色明畅的语言洪流,汪洋恣肆的情感大写意,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唱词宾白,让人强烈共鸣的艺术典型,真情流露的自喻性抒写,极具张力的主体精神,情感与艺术形象的有机结合,“不骫于法,亦不局于法”的艺术追求,徐渭的人格风貌和艺术精神,通过这个杂剧传递给后世同样块垒难消的读者、观众。《四声猿》的“奇”,也有观者感于徐渭本身行为才情之奇的因素,因为对于作品的解读,始终脱不开对于作者的人格和精神的解读和对话。
《四声猿》之奇,也就在于,才的绚烂华丽,性格的豪放不羁自由洒脱,构成一个理想的人格与精神的典范,而小人的诋毁甚而时代的压抑给“才”造成的重重障碍成为一个咏叹不尽的曲调。当徐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从人生、才华、遭际、创作上都给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个极端的范例,为天下文士吐气啸悲呐喊,后世文人怎能不在同声一哭中感到心灵的强烈共鸣,进而在艺术上和人格上进行模仿或赞誉呢。徐渭的《四声猿》便在这绝异的“奇”气中得到历史和精神的延续。
四、小 结
《四声猿》中,不管是《狂鼓史》借阴司痛骂,《玉禅师》借转世投胎复仇,还是《雌木兰》、《女状元》借易装实现才华,都是通过不真实的幻境才能实现作者的理想。与传统戏剧题材相比,主人公的落难原因也不是家道中落、小人挑拨、坏人当道,而是因为虚伪畸形的现实与主人公性格中对独立自由、真纯自然的天性的向往的尖锐对立造成的。因此传统戏剧中主人公的苦难容易被观众同情和理解,因为他们即便是受难也并不孤单并最终能通过战胜困难重新被纳入主流社会,获得重生; 但徐渭笔下的主人公所追求的理想和挣扎的方式在世俗看来都是怪而狂的,他们的苦闷只有通过狂来宣泄,“未须磨慧剑,且去饮狂泉”.本来畸形的是你,偏偏恶名的是我,《四声猿》的“奇”便因此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徐 渭。 四声猿歌代啸[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 骆玉明,贺圣遂。 徐文长评传[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5] 徐 渭。 徐渭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6] 杜 甫。 杜诗详注[M]. 仇兆鳌,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7] 杜桂萍。 论清代杂剧对徐渭四声猿的接受[J]. 文学评论,2007,( 3) : 102-107.
[8] 袁宏道。 袁中郎全集[M]. 台北: 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9]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10] 陶望龄。 歇庵集[M]. 台北: 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