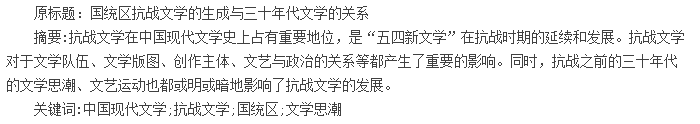
抗战文学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它不仅是指那些书写抗日题材的作品,而且包括抗战时期所有以人道、正义为主题的文学。中国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念上追求正义、和平与生存,拥有了一种世界的视角。中国的“抗战文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五四新文学”在抗战时期的一个发展,拥有“五四文学”的话语属性。抗战文学同样离不开此前的三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笔者主要以国统区抗战文学为例进行分析。
一
国统区抗战文学格局的初步建立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队伍迅速集结起来。不同的作家开始放弃先前的政治偏见,前两个十年因为属于不同艺术派别而反目的作家或因为不同的创作风格而相互敌视的作家们都站在了一起。文坛的分裂开始走向统一,尽管密切度还不是非常够,但是抗日都是共同的心声。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最早成立,此后还成立了象征全国文艺界大团结局面形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国统区抗战文学中最为鲜明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抗日救亡”成了激动人心的最响亮的口号,文学创作的组织化、实践化,与现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文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文艺工作者各自分工,担负不同的任务,在广州、宜昌、长沙、襄樊、昆明、贵阳、桂林、成都等地都活跃着文协的工作者。
他们深入敌后,转向内地,纷纷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文化工作团”、“作家战地访问团”等,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各种危险去收集第一手材料,并将制作的宣传材料和文艺作品发放到阵地和民间,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战,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这个时期最活跃的就是青年作家丘东平,“8.13”上海抗战一开始就奔赴前线投入战斗,写出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友军营长》《叶挺印象记》等,歌颂了中国官兵不畏牺牲、英勇抗战的爱国精神。
国统区抗战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向就是民族意识的空前强化。民族意识在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中曾有所体现,但是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描写现实和历史英雄人物。在五四时代,我们就缺乏一种启蒙英雄,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也是弥漫着各种的无助。但是在抗战文学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英雄,英雄的业绩又是鼓舞群体抗敌的强大动力。
很多小说都是充满着各种昂扬的题目,如《五十七条好汉》《烽火》《台庄一勇士》《江晓凤舍身诱敌》等,将对于敌人的愤慨化作了对英雄的渴望。但是也应该看到一些小说试图宣扬民族化的时候,不同的人对于民族意识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异的。有人主张强化民族意识就是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带有浓烈的封建色彩和专制意识。
国统区抗战文学中的审美心理也开始发生了嬗变,在以往的时候多元化的态势比较明显,有喜欢通俗文学的,有喜欢深沉的启蒙文学的,还有喜欢比较小资一点的闲适文学的读者。但是抗战之后,全中国都弥漫着一致赴敌、守土保乡的奋斗追求,沸腾着激越的爱国热情,也成为人们一致的审美心理。一些无关抗日的审美活动受到了抑制。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潮流中来,很多作家开始走进了民族抵抗战争的广阔天地,建构新的艺术美,积极寻找最为基础和本色的民间艺术素材,开始亲身实践那种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诉求。
在抗战前期的国统区,作家们基本上能够保证态度上的一致,即使有不同的艺术见解和看法,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论争和冲突。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急剧逆转,很多先前的矛盾开始展露出来。比如发生了“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提出,欢迎作者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由此导致对梁实秋的批判和梁实秋的“反批判”。此后还有火药味不是很浓的张天翼的“暴露与讽刺问题”。这场文艺界的论争,肯定了《华威先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规范了抗战题材,帮助作家们认清了抗战现实和文艺家的责任。整个抗战时期开展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想斗争,确保抗战的正确方向,也是文坛常见的现象。
在抗战时的国统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微妙,虽然国民党支持文艺运动,但是对于一些敏感问题还是管理的非常严格,就像鲁迅自己在杂文中写的那样,审查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国民党成立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采取各种方式堵塞作家“下乡、入伍”的道路,致使一些作家在进行抗日宣传的时候还要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臧克家的《春鸟》就表达了作家备受摧残压抑的思想情绪,唱出了呼唤自由解放的歌声。
二
严家炎先生在分析抗战文学的时候认为,抗战文学割不断与先前文学的关系,甚至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前些年,曾经流行过‘救亡压倒了启蒙’,但事实却雄辩地证明,连‘抗日’这个‘救亡’最热火朝天的时期,‘启蒙’都未曾被压倒(抗日初期还出现过专门的‘新启蒙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统区的抗战文学运动就是三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转向,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有着自己的主张和潮流,只是因为抗战的介入而发生了转变,但是根基上还是孕育于三十年代的文学的,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抗战文学的方方面面。
三十年代文学尽管是海派和京派的天下,但是其中有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那就是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和鲁迅、左联等都发生过不同层次的论争,其中不少发起人像陈铨、雷海宗等都有较高的修养,由于政府当局的支持,有为数不少的作品,这些都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像左翼作家群中的萧军和萧红创作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这些都是最早提供给了读者对于苦难民族的挣扎本相的个体观察。左联内部还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虽然只是政见上的不同,但是还是扩大了人们对于文学的社会功用认知。
三十年代文学为国统区的抗战文学提供了较为成熟的作家群。很多参加了“文协”的创作成员都是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从创作实践上看,抗战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四世同堂》《北京人》《寒夜》等都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创作的。
国统区抗战文学关注的“民族性”也是和三十年代作家关注的“阶级性”“人性”相关的,有暗合的地方。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左翼文学思潮分别要构建的就是文学的“人性”和“阶级性”。“人性”关注的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性,“阶级性”关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而这两者一直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但是在抗战爆发之后,这些不同的理念都被纳入到了民族性的范畴之下,两大文学思潮“相逢一笑泯恩仇”。抗战文学要求的民族独立意识可以看作是先前左翼温煦的阶级性的变种,是在抗日战争环境下的延续。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关注人性的思潮也逐渐演化成了对民族文化的剖析,对个性心理的探微等。
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左联思潮的对立还可以看作是精英文化和大众化的对立,大众化的趋势也是从左联开始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最早的“革命文学”中的普罗文学等。三十年代文学的大众化趋势深深地影响着抗战文学的书写,但是这个时候更多的是采用一种精英化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抗战文学作品都注重描写底层的小人物,改变了原先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抗战文学在形式、体裁上也开始接受以前左联作家比较擅长的报告文学等,可以说民族形式的文艺运动是非常受欢迎的。
总之,抗战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链条之一,是在早期五四文学和三十年代文学基础上的发展,是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的。我们发掘抗战文学与三十年代文学的关系,不仅是为抗战文学寻找合法性的依据,而且要充分理解它的多种内在机制。正如刘增杰分析的那样:“无论付出的代价何等沉重,抗战八年,终究是我们民族的闪光点,也是文学的闪光点。
人们只要不忘记因抗战的胜利,国家开始复兴,民族真正地挺起脊梁,就不会忘记为民族新生而牺牲自己、同时也发展自己的文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人们就不会再对文学提出美而求全、精而求妙的要求,对带有强烈功利性的救亡文学思潮席卷抗日文坛这一特有的文学现象,也将会充分理解。”
参考文献:
[1]严家炎.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J].河北学刊,2005(5).
[2]刘增杰.文学路向的两次调整:抗战文学的勃兴与分流[J].江海学刊,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