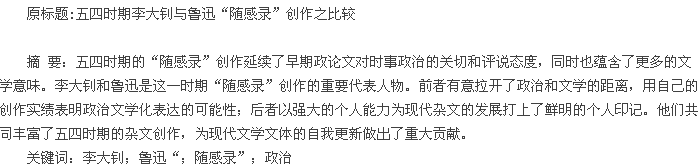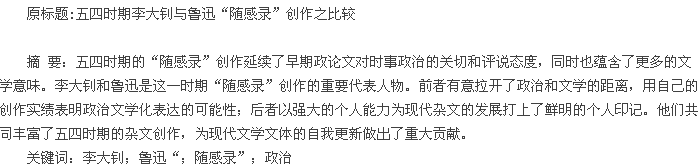
李大钊和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新青年》的旗帜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致力于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以及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虽然两人的文学理想和实践有所差别,但在时代的鼓动下却在现代杂文创作方面形成了共同阵线,不仅丰富了文学革命的成果,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文学复杂关系的不同观念。
一
杂文写作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体登上文坛并被确认,还要归功于《新青年》“随感录”栏目的设立。正是在这一栏目的引导下,作家们开始重视这种文体,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逐渐证明了这种先锋性文体的存在意义。杂文是以批评为主的文体,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媒介与所处时代有机联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它迅速渗入到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道德的乃至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能得到及时的社会反馈,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在这一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首推鲁迅。作为一个有明确自觉意识的杂文作者,他的杂文创作集中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给现代杂文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他的杂文创作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人物,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了解中国文化心理、民情民俗的一部活的历史。同时,他对杂文题材、手法的开拓,对现代汉语运用的自由无拘,以及超越常人的逆向思维,都对现代中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文学本体而言,他的杂文创作也为评论性文体的独立存在提供了强大的依据,为学术界提供了讨论与研究的热点。如果说,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现代小说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发掘有着不可替代的伟大贡献,那么他的杂文创作所具有的不可重复性,则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成为难以超越的巨擘。
与之形成有意味对比的是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的编委之一,在反帝反封建,呼吁民主自由,抨击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他与鲁迅别无二致。但李大钊出身北洋政法,对于政治、法律制度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作家。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时局,他更多的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去捕捉事件的意义,并以高度理性的方式进行论辩与反省。所以,他在五四时期发表的大量“随感录”式作品都带有政论文的色彩,即使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区分了文学创作和政论文写作,但依然不能完全稀释这种底色。与其他作家偏重道德、文化、精神层面的批评有所不同,他的批评更容易集中于制度的硬伤方面,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变革的热切期望。所以,当社会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被十月革命再次点燃时,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运动的洪流中去,终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成就了伟大的一生。比较两人在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创作,可以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文学的不同解释与追求。
鲁迅文学家身份的确定正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而他钟爱的杂文创作也是在这一时期起步的。他始终以冷静的态度向纵深挖掘中国文化的溃疡,探究在现实中如何去塑造“更好的国民性”,在“治病救人”的人生理想驱动下选择了文学道路。但现代中国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时局却使其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这并非作家的被动妥协,而恰恰是他们迎合时代、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政治风云动荡变幻的时代,各个领域的精英都会努力参与到这种变动中来,他们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自己的力量,彰显其个体价值。参与政治成为作家的责任之一,亦是他们写作的底色之一。作家们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沾染上的政治色彩和其文学底色相互作用,使得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呈现出诸多的发展可能。新文学的作家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这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谁吞噬谁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新自我的契机。“随感录”的出现就是一种证明,它是在现代媒介、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时局的多方博弈下催生出的新兴文体,是对政治的自由议论和对新文学积极建议两者的折中产物。借用陈平原的话来说,是“政治表达的文学化”。同时,对于一直热衷于社会活动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来说,五四时期投身文学建设也不是他们的一时兴起。作为知识精英,他们都敏感地意识到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的动力。近代以来的各种革命的相继失败让知识分子开始考虑社会变革的多样化途径,而回归知识分子本色,从实际问题出发着手改造思想,立足媒介舆论这一新阵地展开斗争,无疑成为一种脚踏实地的选择。他们革新了语言武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话语场,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切入社会的方式,更为现代知识分子开拓了公共空间,使得他们能够更方便与合理地进入到公众视野,拉近了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之间的距离,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
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李大钊等人从政论文创作中汲取经验,转而进行现代杂文的创作,淬炼了现代白话,增强了文学的现实意义,使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更为明晰。虽然在 20 世纪 20 年代,李大钊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李大钊和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实践,在五四时期达到了重合,又由于不同的职业选择而渐行渐远,但他们都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它们相伴而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色。
二
《新青年》从 1918 年 4 月 15 日第 4 卷第 4 期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以批评社会和时事为主。在它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各大有影响力的报刊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创作无疑最为突出,他成为撰写“随感录”的急先锋。而 1916 年终止学业回到祖国的李大钊,一方面在《言治》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杂志上继续议论、探讨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的“随感录”创作。尤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杂文,短小精悍,尖锐犀利,堪称精品。两个人的杂文创作无不围绕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社会时局的变动以及深层的思想文化问题)展开,虽各有侧重,风格迥异,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彼此相近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
就内容而言,两个人都猛烈抨击现行专制统治的暴行,批判腐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自觉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基点上,驳斥新旧势力的攻击。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以彻底的革新精神揭示了新文学的本质,“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虽然他并没有提出新文学的具体内容,但旗帜鲜明地展现出新文学的精神实质,廓清了那些意图披着新文学外衣贩卖封建主义价值的虚假文学作品,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展望了新文学的未来,告诫人们不可盲目乐观、故步自封,应认清目标,努力前行,不断为新文学运动培植土壤、加固根基。他的言论朴实,立场坚定,情感充沛,显示出一定的文学预见能力。而鲁迅则偏好以形象的譬喻和幽默的表达将对手的弊病呈现于读者眼前,让他们自己去进行判断和推理。同样是维护白话文,鲁迅仅一句“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就将那些文言文卫道士的言论驳斥一空,接下来他又以警句的形式给这些人下了判决:“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其言犀利如刀,处处切中要害,嬉笑怒骂中显现出强大的杀伤力。
在写作风格上,李大钊往往从大处着笔,提纲挈领,滔滔不绝,宏辩之风令人激赏,但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的是,他往往会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宕开笔墨,议论发挥,很少凭空虚构。在《新的!旧的!》一文中,作者提出新旧代谢乃是时代前进的动力的观点,他不无感慨地回想起前门马路上嘈杂无序、危机四伏的情形,暗合了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艰难现实,但作者并没有凭空拔高、大肆议论,反而相当平淡地提出,“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象那样拥挤了。即于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象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这种质朴的言论着眼于细小之处,平易近人,有相当的说服力,展现出作者注重实际、严谨踏实的个性。鲁迅也是一个善于从现实的蛛丝马迹发挥议论的作家,但他的议论往往剑走偏锋,文风峻急,剖根揭骨,寸铁杀人。
如《随感录四一》,从一封匿名信里一句方言“数麻石片”出发,痛斥了中国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劣根性,那些惯于诋毁别人的创造的卫道士们“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虽然行文风格各异,但他们关注社会的自觉性,反抗封建专制的坚决性都毫无二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热切地把希望寄予青年人,努力扶植新事物的成长,正如李大钊在《青春》中所希冀的那样“,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李、鲁二人,一稳健一老辣,一笃诚一激越,相映成趣,使杂文作家队伍更加多元化。
三
五四时期,李大钊并没有放弃过政论文的写作,他在《新生活》、《民彝》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探讨有关民生的政治体制、国家制度的文章,但从文章的总体数量和质量来看,“随感录”类文章依然处于其创作的主要地位,而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立也应该由这一时期的杂文来奠定。和鲁迅等文学革命健将一样,李大钊始终站在思想启蒙、救国救民的基点上发表议论,而且他的议论因为“随感录”的影响,文学趣味大大增强。在早年的着名政论文《风俗》与《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沉痛地指出,中国亡国之祸已然不远,但更可怕的是因道德极度堕落造成的“心死”,这种群体的道德破灭必然引发“亡群”的后果,而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意识到所负载的重任“,虽以不肖之陋,亦将赑屃其匹夫之任以从之。”在着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他为衰微病弱的中国开出了立宪政治、民主自由这一治国良方,并提出了具体的政体改革要求,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责任感“以之造福邦家,以之挽回劫运”。同时,他也就努力调和知识、道德、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有效地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种对政治现实的关注与解析并没有因为向文学倾斜而发生改变,但他却有意识地拉开了文学和政治的距离,不再以繁复的专业性分析为主,行文短小精悍,贴近生活,也灌注了更多的情感,显现出明确的文体意识。《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每篇不过三百字,有感于自杀现象频发,文中提出评判死的价值应从社会制度本身出发“,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何况那些为苦于不能实现理想而自杀的人“,对于他自己的生命,比那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通篇没有繁复的说教或是冗长的责难,言简意赅,颇有余味。
李大钊政治家的本色从来都不曾黯淡,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政治动向,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普通选举》寥寥百字,勾画出纷乱阴暗的中国政治现实,讽刺意味浓厚的论述中透露出无尽的愤懑之情。《光明与黑暗》凸显了劳动者的伟大,揭露了执政者的强盗本色。
十月革命爆发前后,他将启蒙意识与日益明晰的阶级意识和社会革命结合在了一起,尤其重视劳工阶级的重要性。《平民独裁政治》针对社会上对于俄国革命的无知与攻击,戳穿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从政论到“随感录”,李大钊的文风变化显着,这种改变固然是斗争策略的需求,也是他自觉地向文学家靠拢时,有意识在文体方面的自我规范。因此,李大钊的“随感录”创作成为一种目的明确的新文体成型过程,其文体诉求远强于同时代的政论作家,从而凸显出比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更卓越的文学见识。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创作道路也被自我窄化,仅在“随感录”文体的形式下探讨问题,缺少文学创作时应有的余裕宽松气质,而取向单一的弊病也使得他的文章缺乏直指心灵的方向和力度。这并非李大钊一个人的困境,鲁迅在谈到“随感录”创作的窘境时曾说“,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 倒不如不进去”。鲁迅一方面承认了“随感录”创作在艺术上确实存在不足,很可能是一种暂时的产物,但他也认定这种文体属于艺术的一支,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进行积极的创作。但对于他这样具有思想家素质的文学家来说,强大的个人能力会使其“随感录”作品焕发出不同凡响的魅力。他在《坟·题记》中谈到自己文章的价值时,毫不讳言自己乃是他人的眼中钉,“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强烈的自嘲精神与坦率决绝的创作心态使其能够自由地出入文学世界,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而鲁迅本人在这个艰难抉择中也深感出自生命本源的虚空,“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这种回避世人的心态在李大钊这样的作家身上是不会存在的。这并不能说明李大钊在思想境界上落后于鲁迅,李大钊始终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其文学目的并不在于对自身的精神突破,他的所有行为目的明确,毫不犹疑,皆指向外部世界。他不能也不会向内心发出过多诘难,他要忠于自己的社会使命。这也就预示着,李大钊的文学道路并不如他曾经的战友那样艰难以及长远。
五四时期的“随感录”是现代杂文的前身,虽然从文体、风格、写作手法方面呈现出现代杂文的诸多特性,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演变初期的不确定性和混杂性。尤其当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政治色彩浓厚的作家参与其中时,他们的特殊而彰显的身份往往会把学术界的目光引向其他方面,从而使得游离文学本质的评说和意识形态观点占据了文学史的主要地位。文学批评意识的萎缩和眼光的狭隘,使得学界对现代杂文的价值认定一直模糊不清,但这并不能抹杀杂文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大量的文学实践,尤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的创作,无一不在要求我们做出相应的评说,面对这种情况,有研究者提出“只有在批评本体的意义上才能克服散文或杂文文体的拘囿, 还鲁迅此类文学写作以恰当、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思想革命需要大量的系统的思想文化批评, 思想范畴的各种批判和改革, 落实在批评文体上要比落实在文学作品上更直接更方便也更有效”。五四时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不论重于批判,还是偏于建设,都在自觉剔除“导师”姿态和“学者”的尊号,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共舆论空间的建设中,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解放,强调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传播和流行,为新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陈平原“.妙手”如何“着文章”———为《新青年》创刊九十周年而作[J].同舟共进,2005(5).
[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9.
[3]鲁 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鲁 迅.鲁迅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