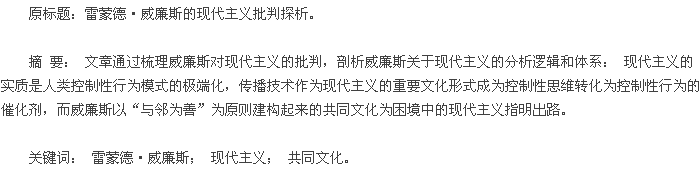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现代社会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发展的断层。作为英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威廉斯立足对现代主义与现代社会的批判,致力于建构“现代之后”社会的应有之貌。
一 现代主义是控制性行为模式的极端表现
威廉斯对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病进行反思和批判,本着“必须超越它,要从某种理论的角度来认识,看清正在发生什么,解释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还要有未来发展的方向感”[1]23的研究准则,借助传统中依然可资利用的资源来消解现代主义的困境,致力于对“现代之后”这一新时代的社会样貌的建构。
威廉斯对现代这一段有疑问的历史做了一个历史的质问。这一“历史的质问”撕毁了现代主义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创造力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进步外衣,暴露出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故步自封的现状和本质。创新是现代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但当创新不再是手段而演化为现代主义的目的和特质时,一味地突破边界与高度挑选最终将现代主义推向其终结点---失去创造性与创造力,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2]
这与英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本人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曾以英国为基地。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现代发展进程无疑可以作为现代主义研究的最完整样本,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以其先天的优势和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视角,对现代主义研究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威廉斯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将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揭示了现代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的内在逻辑所在。第一阶段是 16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中期。“现代”对应的是“中世纪和古代”,代表着对旧时代的创新和改进,是一种促进时代进步的力量。在发展程度上,这一阶段只是现代主义的起步阶段,但从精神实质上来讲,这一阶段的发展应当最符合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涵。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晚期尤其是在 1890 年至1940 年间。“现代”与“当代”形成对照,成为一个通往过去的名称,“现代主义”成为一场整体文化运动和社会发展阶段,进而更多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范畴。这一阶段,现代传播技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 19 世纪晚期,文化生产媒介如摄影、电影、收音机、电视、复制和记录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同时推动了各种文化派别的形成并使其进行竞争性地自我促进,在这种无止境的跨越过程中,创新成为现代性的正统表征和固有模式。作为现代主义先锋队的资产阶级,原本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被控制工人阶级的反抗所取代,陷入终极的衰退或颓废。至此,现代主义在其内部从政治上确定了“分水岭”.
“‘现代主义’被限制在这个高度挑选过的领域,以一种纯粹意识形态的行为拒绝其他一切。”[3]52于是,现代主义制造了自身的悖论: 它使自己成了终点站,历史在此停止了。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工业城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形式,“战后资本主义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把它付诸‘时髦的消费社会这种资本主义新形式’的‘似是而非的未来主义’的‘实践’之中。”[4]
在这种新形势下,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批判与颠覆,现代主义的批判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新常态。在威廉斯看来,后现代的颠覆性思维是现代主义自我否定的必然结果。“所留给我们的一切,就是成为后现代的人。”[3]49现代主义高度挑选、不断超越边界促进了历史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导致其致命的自我封闭,使得历史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死胡同。
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进程,其根源在于人类控制性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而现代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控制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极端表现。在威廉斯看来,工业和民主是现代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两大决定性力量,这两大力量也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关系时的重大成果,而这些重大成果的发展都是人类控制性行为模式的具体体现。
工业是人类控制自然的成果。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作为衡量自身能力的重要表征,正是人类对自然控制的思维和行为促成了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而这种控制的行为同样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物种灭绝、新疾病的产生等一系列地球灾难( 同时也是人类自身的灾难) .现如今,生态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对自然控制性行为方式的反思与批判。
民主是人类控制自身的结果。在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中,人类的历史同样充满了支配和控制的气氛,阶级、国家、法律都是这种气氛的产物。即便是标志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也经常透露着人类控制的习性。在现代主义思潮中,保守主义企图坚守旧的做法,社会主义试图创造人类新的生存方式,这些做法看起来无不是具有社会责任与美德的人们在为拯救人类做的崇高的事业,但其实质上都是人类控制性思维方式的精神重现。这种支配性、控制性思维方式在精神乃至行动上的表现,就是阻碍人类民主进程最大的障碍。我们最常听到的“赋予人民民主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支配性的语气,“民主权力”不是被给予的,而是民众本身就有的,应当是“发挥民众的民主权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不只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能力,一种建构在真正自由和对生命平等尊重的原则之上能力的。
控制性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决定论与反映论都是控制性思维方式在人们认识世界时的具体表现。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就是现代主义工业发展中控制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必然结果。威廉斯对此表达了明确的不满: “至于马克思,我们接受他所强调的历史、变革以及阶级与文化之间必然的密切关系,可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它的发生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个立场当中,一方面有对经济生活的极端化和抽象化,另一方面又涉及文化,我认为这既不符合其他人所体验的文化社会经验,也不符合人们想亲自体验的文化社会经验。”[1]39“经济决定论”对经济生活的极端化和抽象化,固然与机械反映论的认识方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唯经济决定论”的存在,他们被经济运行规律所左右,只能尽力理解并适应这一过程,成为被经济生活所控制和决定的客体,而非经济生活的主体。
于是,这种抽象的决定论成为历史的产物。威廉斯找到破解“经济决定论”的钥匙是“人所体验的文化社会经验”.威廉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承认文化生活本身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总是把文化活动还原为某种控制性的经济内容或者是由经济地位和状况决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表现”.而这种认识和理解具有其时代局限性。威廉斯用文化的整体性解读范式消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绝对化二分的做法,并用文化唯物主义的思维范式指出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愈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对现代主义的控制性思维方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为化解这种思维误区提供了出路。
二 传播技术是现代主义重要的文化形式。
传播技术已经深度参与进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使得现代人进入一种技术化的生存状态。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美国的经验研究还是德国的思辨研究,关于传播技术的解读无不属于控制性思维方式的阵营,他们都将传播技术视为抽离于社会而存在的抽象实体,处于决定或被决定的地位。
威廉斯对文化的整体生活方式的解读,将传播技术回归人类生活,定性为一种文化形式。以整体观的视角对作为现代生活的文化元素的媒介从产生到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存在状态进行深度解码。
首先,威廉斯在传播技术的产生中引入了“技术意向”的研究。传播学研究最常用的着名的“拉斯韦尔公式”,尽管相对全面地触及传播过程的五个环节: 谁,说什么,通过什么通道,向谁,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在威廉斯看来,这其中缺少了一个重要指标,即“为了什么意向”.他认为,少了对这一维度的考量,“拉斯韦尔公式”就将成为抽象的理论,而无法深入现实的传播本质。威廉斯指出,社会需要、社会目的、社会实践等因素共同构成“技术意向”成为技术在研发过程中的直接推动力,这种意向既是主观的存在,更隐藏着启动传播过程最本质的内在机制。“技术意向”的介入,使得对传播技术的研究步入一种历史的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