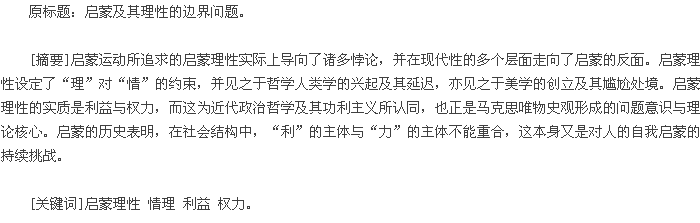
启蒙本与哲学同源,哲学本质的爱智、自明与“无知”精神正是启蒙精神。中国与西方哲学传统皆通向启蒙。启蒙运动显然彰显了启蒙精神,也开启了各种现代激进运动:诸如从苏格兰启蒙的经济激进主义到法国启蒙的政治激进主义再到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的激进性质不言而喻,以至于在浪漫主义及守成主义的思想资源中,启蒙本身成了一个问题,甚至于成了贬义词。黑格尔、霍尔德林、阿克顿以及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在不同程度及语境中拒斥或否定启蒙,自有其理据。但是,就现代性的状况看,我们既需要将启蒙与启蒙运动区分开来,反思启蒙与哲学的本己关系,又需要重新梳理作为现代历史的启蒙运动本身所敞开的现代性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揭示启蒙的内在矛盾,并勾画启蒙的限度及其边界。
一 启蒙及其自我悖反。
我们就从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说起。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在这一定义中,如下三个问题值得重视:(1) “不成熟状态”是指什么?康德说,不成熟状态是指“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这里,人的理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无力,在于缺乏行使理性的自主的决心和勇气;他人引导看上去也是走出不成熟状态的手段,但这种手段其实有可能构成听任于专断与权威,从而形成新的蒙昧。因此,自我引导便异常重要。(2)在什么意义上规定“不成熟状态”?对康德而言,不成熟状态看起来是人的本质性的缺乏。如果设定人的本质的成熟,便谈不上启蒙。因此,不成熟状态,并非认识论性质的,而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规定,是哲学上的本质规定。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乃人自以为成熟的状况,正是这种状况不断加重了人的本质性的无知无畏。(3)如何解除不成熟状态?在价值判断上,康德毕竟不满意于不成熟状态,而试图改变它,开出的药方是Sapereaude,即鼓起勇气运用人自己的理智。但问题在于,理性与感性、意志以及权能并不是那么协调一致。当康德把它们混同起来时,其间的矛盾也由此展开。康德的启蒙定义点明了启蒙运动的主题。这一定义,就其内容而言,当统领着诸如知性、科学、人本、自由、权力、宗教宽容以及无神论等一切现在称之为现代性的要素--其中,自由意志、知性及其运用至关重要。在康德那里,理性自有其运用能力,当然需要区分诸如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或者判断力以及历史理性等,但更要区分理性的不同运用。对此,福柯敏锐地指出,正是康德特别区分了理性的公共运用与私人运用[2].在康德那里,理性的私人运用是指在社会的特殊领域(即市民社会以及科层制)中,涉及诸如纳税、服役、神职及公务人员的活动,在这些领域,理性的运用听从于制度安排而不自由。而在人类公共的和普遍性的领域,理性运用则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乃理性化政治的内在要求。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从原则上将理性的公共运用与私人运用区分开来。这当然不是把纯粹理性与理性的公共运用以及把实践理性与理性的私人运用简单地等同起来,因为康德的纯粹理性并不直接扩展到政治事务,而实践理性倒是在其人类普遍的历史进程中得到阐明,但纯粹理性所具有的自明性给予理性的公共运用一种知性上的支撑,而理性之私人运用的那些特殊领域,必定属于实践哲学或现代哲学所讲的生活世界。问题的实质在于,康德对理性本身作出了区分,这一区分关涉到高度分化的现代性世界的不同理性类型,诸如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制度理性、工具理性、历史理性,构成了复杂现代性世界的合理化结构。
康德有关理性的区分是为了在德国传播一种法国版的启蒙思想及其政治理论。康德显然强调了理性在启蒙中的意义,并深化了理性主义。在康德那里,启蒙被看成理性之不断自我完善的事业。康德区分理性的目的不像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那样要限制理性,而恰恰是为了证明理性的强大。实际上,在康德有关启蒙的论述中,包括敢于明智、克服不成熟状态,都本质性地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及其提高。因此,包括那些异质于理性的意志、价值、利益、权力等,在康德那里都被看成理性的内在要素,而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更进一步发展了理性主义启蒙观。康德的启蒙定义中,除了当时的启蒙政治要求外,还蕴含着一种哲学的本质内涵。康德在人的本质的意义上看待“不成熟状态”.反过来讲,人的成熟状况并不在于人认定自己是成熟的,恰恰在于对自己不成熟状态的自我认识。这是贯通于中国与西方哲学的古老的智慧。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3].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w,且强调人的最本己的生存状态便是“复归于婴儿”[5].苏格拉底将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确定为哲学的第一箴言,明确地指出无知是哲学最根本的存在方式,是哲学与一般知识的最大区分。苏格拉底讲哲学起源于惊讶,所谓惊讶恰恰是对于自己无知状态的识别与自觉。正是基于这种生存论的设定,哲学要求确立起反省或反思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其实,所谓不成熟状态,常常是相对于另一种生活状态而言的,“不成熟”是与自以为“老成”实则僵化相比较而言的生存方式。人总是在一种比较状态中存在,甚至于包括对不成熟状态的评价,也是源于比较。柏拉图的“光的隐喻”,即指出了人在摆脱某种生活常态时的惶惑,在那里,启蒙过程其实蕴含着苦恼乃至于痛苦。“光的隐喻”本身就是启蒙俘论的隐喻。
启蒙的结果当然有好坏之分,对一种不符合人性的反常规的不成熟状态的克服,当然是合理的并且要求得到理解。特别是通过启蒙而实现的现代性对传统生活的改变,迄今为止仍然值得从其总体上加以肯定。但是,无论如何,传统有关不成熟状态的哲学见识中,包含着一种普遍主义的人性精神,这同样值得加以肯定。(1)它强调了人性的谦恭、人性的高贵,有时候是通过人的脆弱性显示出来的。(2)它存在着一种对生命、自然、传统以及神圣的敬畏。苏格拉底通过德尔斐神谕来传达哲学真理,孔子则通过周礼来进行教化,如此等等。(3)因为对无知的肯定,反过来为知确立了一种底质,知本身是有限的,人类求知的过程实际上是为了更深入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知识”在中西方传统中都是受限制的。但是,现代性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生存智慧的反讽。通过自我主体性的确立从而宣布对不成熟状态的一劳永逸的克服,被看成现代性唯一正确的方向。对于自然、上帝以及美德传统的“祛魅”被看成启蒙的唯一路向。卡西勒的判断是:“启蒙时代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对历史距离和历史隔阂缺乏理解,出于天真的过份自信,它拿它自己的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事件之绝对的、唯一有效的和可行的规范。”[6]而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启蒙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反面,理性走向了暴政。启蒙致力于运用理性,但理性也可以走向自身的反面,现代性的拓展带来了一系列启蒙的自我逆反现象。其一,启蒙是理性的事业,但由此导致的理性化却封堵了启蒙精神。启蒙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反思精神,其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服从于其他功用。但实际上,启蒙逻辑使理性走向了理性化,而理性化的实质则是形式合理性规定甚或抽掉实质合理性,其使目的从属于效用,使个体从属于结构,使理念从属于制度,使人性从属于物化,具体表现则是其自身建构且无所不在的组织化及其科层制。不断累积的科层化逐渐堵塞了启蒙精神的渗透,理性化从形式上嵌入了反思活动,但这种反思越来越成为某种规范性的程序,而不是批判性的或中立性的活动,理性化以自身的逻辑遮蔽了启蒙精神。其二,启蒙本来是反体系的,但其自身却成就了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开放乃启蒙的本质规定性,就其精神气质而言,启蒙是反体系的,康德哲学的悖论即表明这一点。纯粹理性可以无限穷尽现象界,并依此逻辑延及“自在之物”,但“自在之物”本质上不可知,与之相通的主体心内世界关联于实践理性。康德在区分不同“世界”时,也区分了不同的理性形式,如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或判断力以及历史理性。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方法的理性自身却逻辑化且本体论化,理性不再区分为多,而是统一于绝对理性及其绝对精神,并表达为哲学体系及其“一劳永逸”的完成,也完成了启蒙与理性主义的同构。
由此,理性主义哲学也达到其“终结”状态,并开启了现代哲学一波接一波的非理性主义及反理性主义,而现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及反理性主义,又都直指近代哲学的启蒙传统。其三,启蒙历来是知识分子的事业,但知识分子也需要自我启蒙。启蒙即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敦行教化,向来是社会的特殊阶层即知识分子的职任。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不仅在智识,而且在批判、责任以及奉献上总要高于普通人。但是,就实际的状况看,知识分子常常出现智识与责任、批判与建设的悖反现象。阶层的特殊性以及与世俗名利的结合常常导致知识分子群体自我认识能力的不足,并不断加剧其自我遮蔽,典型者即如时下被人垢病的“公知”现象。当然,最令人深思的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做到在运用理性时不把自己当成“例外者”,并且藉此推进社会的现代文明进程。其四,启蒙被看成是人道主义的事业,但却总要面对自然主义的质疑。启蒙运动乃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及其持续推进的结果,启蒙话语亦与人道主义、人类解放、主体性、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性话语同构。但与启蒙运动相偕并行的,还有一股强大的守成主义思潮,其思想主张并非一般的人道主义,而是经由人道主义所达及的自然主义及浪漫主义。就其偏向于守成主义与浪漫主义而言,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甚至是反启蒙的。对于尼采、海德格尔及施特劳斯而言,诉诸于自然主义而拒斥启蒙话语,更是成为高度的哲学自觉。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不仅导致其本人的哲学转向,而且构成了当代哲学深远的理论方向。就人类生态系统的实际状况而言,如何实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构想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将始终是严峻的历史课题。其五,启蒙被看成反封建神学的事业,但却要面对xuwuzhuyi问题。启蒙最初的目标,乃是反宗教神学,启蒙本身也是世俗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启蒙精神乃是本质的无神论,然而受资本主义裹挟的无神论,本质上却是夏洛克式的拜物教,是一种替代神圣意识的彻底的世俗意识。现代史进程中,有三大主张均致力于克服拜物教,也均是启蒙持续推进的结果:(1)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尤其是每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新的社会信仰及其制度建设,并通过激进实践及其社会化的人的建构活动,实现对资本主义及其拜物教的历史扬弃;(2)在宗教及其世俗化中寻找精神资源,不仅天主教传统被看成阻止拜物教侵蚀的稳定力量,而且在韦伯、桑巴特等的努力中,清教传统以及犹太教义也与资本主义精神关联起来,成为与拜物教区分开来的精神资源;(3)各种社会精神对主要依附于个人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拜物教的遏制,其中,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积聚起来的民族主义与国族精神,乃是遏制拜物教的典型资源。然而,伴随着上述三类思想主张的,依然是拜物教自身的膨胀,这就是彻底的xuwuzhuyi。19世纪80年代,尼采断言,欧洲全面遭遇xuwuzhuyi,然而,欧洲xuwuzhuyi本身就是启蒙思想的副产品。其六,启蒙被看成世界历史及普遍主义的事业,但显然需要面对非西方的多样性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迄今为止,如何将启蒙允诺的普遍主义及其人类话语,从其实际的西方中心主义实践中区分出来,依然十分艰难且不可能。就其历史境遇而言,启蒙带有欧洲的历史特征,其缘起时的动机,依然沿袭了应对东方帝国的历史逻辑,其盛时俨然与欧洲中心主义同构。对欧洲本身而言,启蒙是教化及文明的同义语,但对欧洲之外的世界,则意味着奴役与殖民,其实不再是启蒙逻辑。尽管打着普遍主义及其世界历史的旗号,但实际的道路还是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由此启蒙话语本身便成为虚假的意识形态。非西方世界最终是以反启蒙逻辑、尤其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并完成了非西方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
当然,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论证,仍须与西式民族国家区分开来,并从自身多样性的传统中阐释其独特性与合理性。其七,启蒙成就了一种宽容的传统,但启蒙同样也导向专制与集权。从宗教宽容到更普遍的人性宽容,乃是启蒙的本义。但是,现在看来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意图。宽容要求个体有相当丰富的涵容能力,但人性本身却是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在很多个体身上也不乏恶的因素;宽容其实要求以人的善良意志及其制度建构去包容各种价值,但恶却可能刺穿善良意志并陷社会于不公不义。一些政治哲学干脆以人性恶为前提,推导制度建设的必然性,但这实际上为监控与暴力提供了天然的合法性,并使宽容并非如此这般地可行。启蒙设定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进步逻辑,其中传统被看成不宽容的,而现代被认定是宽容的。但明眼人不难看出,现代性及其政治实践所导致的后果同样怵目惊心,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现象,依然是现代社会的常见现象。宽容要求人格独立,然而现代社会的各种聚焦与动员与现代性诸种条件混合,实际上却巩固了各种类型的附魅与奴役。从某种程度上说,宽容实际上怂恿了诸种专制与集权。启蒙在成就宽容传统的同时,也怂恿了现代性的专制与集权。这里绝非要否定宽容本身,而是提醒不应该赋予宽容过多的想象。启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恰恰自启蒙运动以来,启蒙与自身产生了脖谬,并展现出现代性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