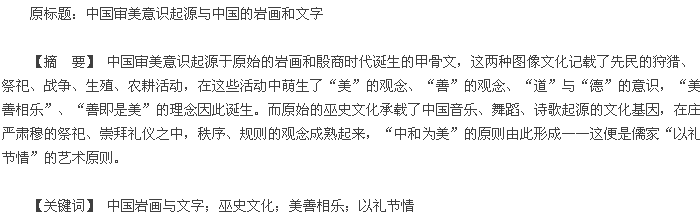
陈兆复先生认为,“史前的岩画是一种原始的语言,一种文字前的文字。”〔1〕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都与绘画相关,是表意的象形文字。腓尼基人根据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创造出字母,从此西方的文字脱离了绘画象形的表意方向,朝着抽象的拼音文字方向发展。中国文字却一直保留了绘画的象形、表意的特点,并将表意的图形和表音的特点结合起来,组成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在中国的文字里,像电影一样,经常可以看到生动的自然、社会、日常生活的蒙太奇画面闪回,这些形象的图画里传达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审美观念、人生理想,中国文字是图像叙事与审美体验的融合,自然、人生的感受,甚至观念都溶化于视觉图像之中。
中国岩画与中国的绘画艺术人类很早就有用坚固的材料将自己的生活活动纪录下来的冲动。石头是在金属冶炼术出现之前最坚固的物质,具有长期保存对象的作用,因此,世界艺术很早就与岩石发生了联系,突出的例子就是岩画。据统计和测定,全世界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分布着岩画,最早的岩画岩产生于距今四、五万年以前。
中国岩画分布广泛,分为南北两系。北方岩画更为古老,据专家推测,北方的岩画大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南方的岩画大概产生于战国时代。岩画的内容与南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概括起来有游牧、狩猎、战争、生殖、祭祀、舞蹈,其中的图形有各种动物、穹窿、毡车轮、车辆、日月星辰、天神、帝祗等等方面,这些内容包括了远古祖先的物质生产活动、神灵意识、巫术、宗教观念、偶像崇拜、本能欲望,它们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并绵延数千年直到今天。
中国岩画分为两种制作方式,北方的刻制和南方的涂绘,刻制包括磨制、敲凿、线刻;涂绘主要是用红色的赤铁矿粉混合牛血作原料进行绘制。
北方的刻制岩画成为后来的雕塑艺术的先驱,南方的涂绘则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祖先”。中国岩画是人类童年时代二维空间思维的展示,侧重表现对象的平面、正面形象,岩画的风格朴拙、粗犷、简约,充满童稚的幻想,不注重细节的真实,如很少描摹人和动物详细的五官,而是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如人的动作、体态、情感,动物的角、耳和尾巴,传达出对象的主要标识以及精神意趣,后来中国绘画艺术“以少胜多”、“以小见大”、“繁简得当”、“传神写意”、“虚实相生”的特点在岩画中开始萌生。南方的岩画喜欢用红色去表现对象,红色是太阳的色彩也是生命(血液的色彩)存在的依据,它传达出激情、欲望、温暖、光明、希望、朝气蓬勃的多重寓意,中国文化对红色和绿色(大自然植物)的一贯的挚爱也是后来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和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观念根源,只是后来儒家和道家对藏而不露的“含蓄”、“内敛”、“低调”的强调,红色这种张扬、跳跃、激情的色彩才被压抑在人们心底,只有当节日来临,红色才被广泛、大胆地使用,装点和渲染节日的喜庆气氛。
岩画对色彩和线条的自由运用给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以深刻的启迪。当然,岩画还没有从巫术和宗教的观念里分离出来,在远古,岩画更多地包含了利用“交感巫术”,以幻想的方式对客观对象的征服和占有(如模仿集体狩猎的场面)以及敬畏天地、山川、祖先神灵的方式。因此,南方的岩画经常出现在高山、河流、峡谷的悬崖峭壁上,附近往往是空旷的场地供人们举行庄严、肃穆、神秘的仪式,以此献媚神灵,企求护佑,带来福祉,反映的是祖先“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和观念。在这样的神圣、恐惧的场面中,形成了审美意识里对象伟大,自身渺小,敬畏自然的“崇高”感。而先秦时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和震慑观念实际山也来源于人类在岩画时代积淀的神灵、巫术、宗教观念。在蒙昧时代,神灵即是一种具有震慑力量的权力,并被统治阶级利用于政治目的。
虽然前人没有从学理上和逻辑上提出“美学”的概念,但中国的审美意识的缘起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就知道将兽骨和海边的贝壳串连起来,制作成项链来装饰、美化自己,山顶洞人就开始用红色的赤铁矿粉来表达生命和灵魂的观念。而艺术创作的历史也是悠久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八千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的骨笛,新石器时代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彩陶盆上联袂舞蹈的形象,传说中黄帝时期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乐,禹时期的《大夏》,商代的《桑林》、《大濩》、《万舞》,周代的《大武》,乐器钟鼓、琴瑟、石磬、铜铃、编庸、鎛、埙的很早使用,这些艺术的实践和产品催化了中国人对“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认识,形成了中国先民对色彩的美感以及不同色彩对心理产生的不同反应的理性认识,他们已经意识到到节奏、比例、对称、运动、韵律、线条的“曲直”带来的不同美感,同时,艺术与人的快乐的需求在原始的舞蹈和音乐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它经历了祈神、贿神、娱神、娱人的复杂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由蒙昧时代走向理性的时代,艺术的形式美与内容美的关系(后来孔子提出了“文质彬彬”以及中国文化后来对美的“秀外慧中”标准)得以充分认识。中国关于艺术的美的评价广泛存在于对书画、戏曲、音乐、诗文的品评之中。在岩画里反映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艺术与巫术、宗教、神灵之间的关系。甲骨文更是在岩画的基础上的理性发展,将中国以图像记载华夏先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以图像作为叙事方式的历史推向了新的阶段,在甲骨文里,反映的是美与图腾崇拜、美与宗教、美与善(道德功利)、美与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
甲骨文中的审美意识和观念商代晚期,河南安阳产生了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了“美”这个字,“美”与羌族相关,其他如“善”、“羞”也都是羌族文化影响的结果。“美”上面为“羊”,下面为“大”,“大”在甲骨文中是站在地面上“人”的形象。从这个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农业文明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开端,商代也以农耕文化为主,如甲骨文已经出现“耒”,即用木头制作的耕地的最早的犁头,也出现了禾、黍、粟、稷、稻、粱、菽等农作物的名称。
甲骨文“男”由“田”和最早的“耒”(像木制的犁)组成,表示男人是在田里从事耕田的人,但商代依然存在游牧文化和保存了关于游牧生活的记忆。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商代,采摘业与畜牧业已退居次要地位,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但畜牧业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美”的字形构造透露出它来自于古代的以羊为图腾祖先的部落——“羌”人。实际上,“美”与甲骨文的“羌”字“同形同构同义”。“羌”上面是“羊”下面也是“人”的意思。着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就认为,“羌”意指戴着羊角装饰的人的形象,与“美”相同。“美”和“羌”的“同形同构同义”反映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起源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羌族的直接关系,也体现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
关于华夏民族与羌族的血缘宗族联系,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一些专家也认为,远古时代作为牧羊部落的羌族一部分进入中原,成为华夏民族的主干部分。“羊”和“猪”是原始先民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到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以后最早驯养的动物。据考古资料,陶塑羊在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就出现了,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里也可见陶羊。从古代文献中我们得知,华夏始祖黄帝和炎帝为同母所生,《国语·晋语》最早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东汉许慎在解释“姜”和“姬”字时曰:“神农居姜水以为姓,从女,羊声。”“黄帝居姬水以为姓,从女,姬(姬去掉女字旁)声。”〔3〕东汉贾逵在《周语》中指出:“共工氏姜姓”。《山海经·海内经》也追溯了共工的家族谱系:“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由此可见共工属于炎帝的后代。宋代《太平御览》里更有直接了当的“神农氏姜姓”的说法。“姜”在古代与“羌”通,前者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意识的反映,而“羌”和后来的“美”则带有父系社会的特征了。所以,章炳麟在《检论·序种姓》中说:“羌者,姜也。”
甲骨文中与“美”同义的是另一个字“每”,其下的“母”代表婀娜多姿的年轻女性,上面的部分是女性华丽的头饰。王献唐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几个“每”字,“皆像羽毛斜插女首,乃古代饰品。”〔4〕同时,指出在原始时代,男女都有以鸟的羽毛作为头饰的习惯,但甲骨文男女之美的“美”字有所区别:“毛羽饰加于女首为每,加于男首则为美。”〔4〕因此可以说甲骨文“姜”、“每”是相通的,都是指女性的美。事实上,虽然商朝已经进入父系社会,但女性的美,在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关于美的描述大多是针对女性的。到周朝依然如此,如《诗经·关雎》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在告诉女性美(外在和内在的美)的魅力。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女部》里,关于女性的美的字就有:媚、媄、媛、好、 、姣、嫙、妩、媌、 、娟、妭、姝等。《说文解字》曰:“媄,色好也,从女从美,美亦声。”〔5〕关于夏朝的历史,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里说道:“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史记·夏本纪》又说:“夏禹,名曰文命。”杨雄的《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三国时期蜀国史学家谯周在《蜀本纪》里曰:
“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广柔包括今汶川、理县、茂县、北川。石纽,今汶川县),宋代《太平御览》里引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因此,国内学术界的多数专家认为,根据文献史料和神话传说,北川禹穴是大禹的出生地。着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也曾指出:
“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6〕到了商朝,羌人集聚的部落成为了商王朝的“方国”,是经常被征伐的小国。虽然《诗经》“玄鸟生商”的图腾故事说明,商代的人不再认为自己是“羊”的后代,而是“玄鸟”所生,羌族也早已臣服于商王了(如《诗经·商颂》中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但甲骨文中的“美”、“羞”字和周代金文中的“善”字与羌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却反映了羌人的生活和文化对后世不可磨灭的影响。周人在追述祖先后稷的历史时就认为,后稷是姜姓的女人姜嫄感应上帝的脚印怀孕后诞下的后代。“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诗经·生民》)综上所述,都在证明后来的羌族就是炎帝的后代,整个中国早期的文化都与羌族有关,羌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事实上的源头。
商代甲骨文里还没有“善”字,金文中有了“譱”,后来简写为“善”,“譱”表示对烹煮后的羊肉味道的连连赞美,即“美味”的意思。《说文》曰:“譱,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意。”〔7〕“善”的原始含义是指羊肉吃在嘴里有很舒服的感觉,因此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美的赞叹,它既是审美的评判,也是对事物的功利性评价,这种味觉的美感后来演化为对人的行为的道德评判。而与羊的外形相连的“义”在甲骨文里已经出现,本意为用刀具屠宰牛羊以祭祀,表示场面气氛的庄严肃穆。后来许慎将“义”解读为人的外表:“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8〕所以,“美”、“善”、“义”都有美好的意思,与羊带来的视觉的美感有关,而“美”和“善”又与羊肉的味觉的美相连,“美”和“义”又可直接指事物的崇高、威严、伟美的外表。甲骨文与味觉感受直接相关的是“羞”字。徐中舒等人认为:
“羞,从羊,从又,罗振玉释羞,谓为持羊进献之像。(《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按罗说可从。”〔9〕罗振玉的解释源于许慎,《说文解字》曰:“羞,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从丑,丑亦声。”〔10〕“羞”在甲骨文中为上下结构,上边为“羊”,下边为“又”,“又”在甲骨文里指“手”,两者组合起来的意思,即用手握着羊肉。寓意把美味的羊肉进献于鬼神,代表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后来“羞”加上食旁,变为“美味”的意思,如“珍馐”。在汉字里另一个与羊的味道之美的字是“鲜”,甲骨文还不见“鲜”字,“鲜”在金文里是上下结构,上面为“羊”,下面为“鱼”。羊为声符,鱼为义符。原来是指一种鱼,《说文》曰:“鲜,鱼名。出貉国。从鱼,羴省声。”〔11〕虽然本义为一种鱼,但不可否认,上面加上“羊”,肯定与羊肉给人的味觉美记忆有关,于是后来汉语就用“鲜美”来比喻食物的味道之美。在甲骨文中直接表示味觉的字为“甘”和“旨”,“甘,从一在口中,像口中含物之形,与《说文》篆文同。《说文》:
‘甘,美也。从口含一。’”〔12〕“旨”在古代也是味美可口的意思,“旨,从人从口,陈梦家以所从人为尸(殷墟卜辞综述三六六页)口或作甘,盖从甘之字古文多从口。《说文》:‘旨,美也。从甘,匕声。”〔13〕由此可以看出,“甘”和“旨”在商代同义,都指食物带来的美味的感觉。而甲骨文还没有“味”这个字,只有“未”,“未”指树木的枝叶繁茂。直到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才有了“味”的对应于味觉的解释。“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凡未之属,皆从未。”〔14〕许慎是用夏天枝繁叶茂的浓荫来形容食物的美味给人带来的强烈感官刺激,留下的沉甸甸的难忘记忆。
“美”与“善”的联系,表明中国原初的审美意识里既看重事物的外在“形式美”:即外表必须好看,同时在外表好看之外,更强调事物的内在品质,后来就演变为功利性的“道德”维度的考量。
“德”在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而“道”在金文中才见到,春秋时期“道德”已经成为儒家文献中广泛流行的词语,并作为帝王政治统治伦理的“合法性”根基,以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统治者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规范、法则。《说文》中“德”写作“悳”和“德”,《说文》曰:“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15〕许慎说:“德,升也。”〔16〕“悳”在这里专指一种后天的内心修养,这种修养将惠泽于人,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凝聚,德,不仅是自我灵魂的净化升华,而且有德的人也必将濡染影响周围的人,提高人群的精神素质。
“道”在金文里由三个字组成,“首”和“又”两个字在“行”的中间,“首”在上,“又”在下,“行”指街道,“又”指手,“首”指人的头部,组合起来意思是:人走在街道上,手在头前指引方向,引导前行。
“道德”后来的连用则指在精神上“正道直行”,道德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修炼达成的,即儒家强调的:无论天子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在儒家看来,这样的人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堪称万世师表,思想楷模,即儒家的“内圣”,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管理好家庭和有资格治理天下,即儒家的“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上面的甲骨文和金文里“美”、“善”、“鲜”、“羞”、“旨”、“甘”、“味”的含义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所指的美感与视觉和味觉的舒适感是分不开的。中国美学包含味觉的感受,可以说是从商周时代开始的,商代的农牧业发展,带来了丰沛的粮食和肉类产品,催生了酿酒、酿醋业的产生,人们不再纯粹为温饱而进食,而是不断地追求味觉的美感、快感。商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形成了“民以食为天,国以器为重”的时代观念,在夏代陶器制作的基础上更重视青铜器的铸造。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里就可以看出这一历史面貌,商纣王对奢侈的感官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达到了极致:
“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7〕而后来的告子也说:“食色,性也。”“味”成为中国美感源头是代表了中国文化是以生命体验为主的文化,《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从直接的生存到审美的超越是中国哲学和美学发展的道路。商代以后,春秋时期提出了“五味”,“味一无果”的观点,老子有“味无味”的哲学命题,后来以味觉的美感来评价艺术的原则更是代代相传,于是,魏晋时代有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余味曲包”,唐代有司空图的“味外之旨”对含蓄美的界定,窦蒙论书法艺术的美则有“百般滋味曰妙”,“五味皆足曰秾”的评说。
除了视觉和味觉的美感以外,中国的审美意识还与古代发达的音乐文化有关。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8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就有了用兽骨制作的长笛,在甲骨文里也出现了“磬”和“鼓”,统称音乐的“乐”已经出现在甲骨文中,写作“乐”。
“乐,从丝,从木,罗振玉云:‘此字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增订殷墟考释中》)”〔18〕许慎则认为“乐”为音乐的总称:“乐,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19〕他甚至将音乐的诞生追溯到了神话传说时代,如他对“琴”、“瑟”的解释:“琴,禁也。神农所作。象形。”“瑟,庖牺所作弦乐也。”〔20〕音乐的“声乐”部分在古代无法记录保存,我们只能通过文字记载的对应乐器和考古的实物证据来了解音乐的起源、发展。在我们看来,音乐、舞蹈、绘画是早于文字和文学的。前面已经说明,原始的岩画已经早于文字出现,岩画里有舞蹈的场面,应该说音乐在当时存在,只是声音保存困难,无法给后人留下足够的证据,但是从仰韶文化彩陶盆上手牵手的舞蹈画面里,我们已经知道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三人操牛尾,投足歌八阕”的载歌载舞景象了。而我们从传说中黄帝时代的《咸池》,颛顼时代的《承云》,帝喾时代的《唐歌》,以及《诗经》里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记载里,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乐”的源远流长。
“美”字在很大程度上萌生于图腾巫术,与巫术直接相关的字在甲骨文里是“巫”和“舞”,甲骨文的“巫”是两块玉十字交叉的形状,代表巫以玉祭神的意思。《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21〕在古代岩画里,其中最重要的场面就是舞蹈,可以说舞蹈是最能体现人的生命欢悦的一种形式。不但人高兴时会手舞足蹈,甚至很多动物也会用舞姿来表现喜悦或者以此献媚、吸引异性,如雄性孔雀的开屏舞蹈等,因此在汉语成语中才有“欢呼雀跃”的说法。在我们看来,原始巫舞主要是以迷狂、恍惚状态下的舞姿故意制造一种神秘、恐怖的鬼神附体的气氛,从而给人“代神立言”、“通天通神”的假象,而并不是以获得快乐为主要特征的。朱志荣先生认为:“原始的舞蹈主要是闲暇时刻的娱乐和狂欢,其中就有‘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等。”〔22〕朱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其实最早这种生命的欢悦是与图腾信仰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最早的舞蹈还是出于巫术、宗教的目的,并不是酒足饭饱后的游戏冲动。朱先生所举的“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实际上都是一种图腾崇拜的仪式场面。《吕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在这里,我们看到原始的音乐舞蹈与人的功利目的、日常生活、图腾信仰之间的联系,先民通过载歌载舞的形式来表达感恩、祈福、敬祖、求生的愿望。葛天氏当然是古代部族首领兼巫师的统治者,它进一步说明在原始时代神权和政权是一体的,甚至神权控制着政权。古代的巫觋都承担“以舞通神”的职责,以此祈求神灵保佑诸事顺利。巫师在做法事时会出现口念咒语,手舞足蹈,亦歌亦舞的状态,可以说,音乐和舞蹈实际上都起源于原始的巫文化,“舞”是既“娱神”也“娱人”的迷狂状态。甲骨文的“舞”是象形字,像两手操牛尾等舞具翩翩起舞的形象,本意为乐舞。故《说文》有:“舞,乐也。用足相背。从舛,无声。”〔23〕当然,不可否认,随着人的理智的成长,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摆脱了神灵的控制,后来舞蹈里“娱乐”的需要在不断增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甲骨文里“娱”和“乐”都出现了,“娱”写着“吴”,上为“口”,下为歪头婀娜跳舞的人形“大”,“表示边舞边唱,会歌舞娱乐之意。是‘娱’的初文”〔24〕“娱”、“舞”、“乐”都有表示人兴奋、快乐的意义,但其最终起源应该归结为“巫”这个歌舞源头的巫祝文化。美国美学家托马斯·门罗认为,原始歌舞常常被原始人用来保证巫术的成功,祈求下雨就泼水,祈求打雷就击鼓,祈求捕获野兽就扮演受伤的野兽等等。正如国内学者所说:“舞蹈是与音乐同源的。甲骨文‘舞’字像两人执牛尾舞,远古时代的诗、歌、舞是浑然一体、相互结合的。‘投足’是一种舞的姿态。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正是舞蹈和音乐结合的说明。”〔25〕如,商代就有天旱时祈雨的“雩舞”。史书记载,商汤克夏以后遭遇大旱,五年谷物无收,于是商汤以身祷于桑林,祈求天降甘霖,于是,天乃大雨,拯救了万民。(即文献记载的《桑林》之舞)王国维先生当年也曾认为,歌舞都肇始于原始时代的巫文化:
“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26〕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指出:“舞的确是巫的专长,在甲骨文中‘无’(舞)本来就是巫,也是一种舞蹈的姿态。”〔27〕“和”:儒家美学的最高境界起源于视觉、味觉、听觉的中国审美意识不但强调美的对象对于感官的刺激,而且强调感官的美是一种“适中”的美,因此在先秦时期提出了“和”的观念,它强调的是多元、差异的事物形成的对立统一的和谐美。关于味觉的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28〕晏婴认为,所谓“和”像烹制羹汤一样,是在食材中加入多种调料,通过精细加工、烹煮后使各种味道协调适中,取得无法言说的美味效果。君子长期食用这样的羹汤,就会温和敦厚,不走极端。“和”甲骨文写作“龢”,从龠禾声。《说文解字》曰:“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29〕“龠”是商代的一种三孔竹管乐器,类似后来的排箫,因此,龠为口吹排箫的意思。《说文解字》曰:“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仑,仑,理也。”〔30〕许慎认为,龠的声音之所以美,好听,就在于它的三孔发出不同的声音,并相互调和,符合听觉感官对“多样”、“差异”、变化、“和谐”的审美诉求。春秋时期的晏子以声音比附味道,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急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齐心,心平德和。”〔31〕在晏婴这里,声音的美与味觉的美的原理是相通的,是“多样统一”的结果。“和”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规则,是中国儒家所创的“礼乐文明”的最高准则,“和”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天地的意志,也是老百姓应该自觉遵从的规则。《左传》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地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是故为礼以奉之。”季札观周乐,当歌至《豳》时,季札感叹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乐乎?”〔32〕季札的观点为后来孔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为美的艺术原则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在《国语》中,单穆公对音乐的美和视觉的形象美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具体解释,认为这种美不应该对人产生负面影响,以至于妨碍五官对美的感受:“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33〕伶州鸠则把音乐的中庸、平和之美与政治联系起来论述其重要性:“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34〕在伶州鸠看来,音乐的“平和”之美,不但会带来政治的稳定,而且会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神人皆和的景象:“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和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35〕“于是乎气无滞音,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36〕史伯也提出“和”是物的多样性的表现,每一个事物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特殊性,才可能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同”意味事物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史伯认为,由相同特点的事物组成的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生命力的,单调、衰弱的世界,也就无美可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37〕战国时期的《乐记》将“和”上升为天地的规则,指出音乐是这种“和”的具体体现,宇宙自然遵从了这一“多样统一”的“和”的原则,才可能各司其职、合情合理、秩序井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38〕“乐”之“和”,产生于中国先民对自然神、图腾和祖先的祭祀文化,即在祭祀天地山川、动植物图腾、鬼神、祖先的仪式中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式、规矩、秩序,这就是规范我们行为几千年的“礼”。甲骨文的“礼”写作“豊”,像礼器“豆”中盛满了祭品“玉”,表示祭祀之意。《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39〕也就说,“礼”为祈求祖先神灵保佑、赐福的一种祭祀仪式。总之,儒家美学虽然主张艺术是情感的表现,但同时儒家强调这种表现必须是有节制的,符合“中和”原则,即“以礼节情”的原则,而不是任意的、狂野的、无拘无束的宣泄。
【参考文献】
〔1〕 陈兆复.古代岩画[M].文物出版社,2002.3.
〔2〕 朱志荣.商代审美意识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2.14.
〔3〕〔5〕〔7〕〔8〕〔10〕〔11〕〔14〕〔15〕〔16〕〔19〕〔20〕〔21〕〔23〕〔29〕〔30〕〔39〕 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63.258,260,213,78,58,267,310,244,311,217,43,124,267,100,113,48,48,7.
〔4〕 王献唐.释每美[M].中国文字·第35册,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70.3934.
〔6〕 徐中舒.我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J].四川大学学报,1980,(1).
〔9〕〔12〕〔13〕〔18〕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Z].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1584,497,512,650,〔17〕 司马迁.史记[M].岳麓书社,1988.18.
〔22〕〔25〕 朱志荣.商代审美意识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2.39,39.
〔24〕 谷衍奎主编.汉字源流字典[Z].华夏出版社,2003.272.
〔26〕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
〔27〕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63.
〔28〕〔31〕〔32〕〔33〕〔34〕〔35〕〔36〕〔37〕〔38〕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中华书局,1980.4,4,3,7,7,8,7,8-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