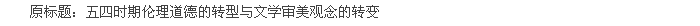
在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中,五四运动堪称首次波及中国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的变革为先前所未曾有。由于中国社会历来以伦理道德立言甚至立国,因而这一转折显得重大而深刻。从封建性质的伦理本位到近代性质的公共社会关系,从文以载道的依附审美到刻画现实生活图景的为人生的艺术,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直至今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改造的任务仍旧艰巨,而文学艺术的自觉创造也还任重道远。因此,对五四时期伦理道德如何转型与文学审美观念怎样转变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阐释和理论探讨的意义,更具有具体的实践参考意义。
一、从伦理本位、善美统一到真理至上
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伦理道德,两汉以来,更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到文学审美上,使文学随即呈现出独有的重伦理、崇道德特征。在伦理本位的影响下,审美活动高度重视善与美的统一,片面地强调善决定美,从而确立了善的绝对统治地位。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占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而这里的善主要是指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所推举的善。又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严格甚至绝对的统摄力量的存在,中国古代至近代的审美观念的发展便无不受到强烈的制约,审美观念既依附于伦理道德,与之难舍难分,又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掺杂其间。
在文学意识朦胧、文体区别不显的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只将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礼乐文章视为美,并把艺术作为道德的一种修饰而推广。自此以降,善对美的统摄地位便一发不可收。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曾一度出现自觉的审美追求高涨的时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重美轻善的倾向,但这一时期非常短暂。到了唐朝,善与美的关系又回归到善决定美的轨道上。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大张旗鼓地倡导“文以载道”,便是典型的例子。当然,此时的“道”既包括伦理层面上人与人关系的“道”,也包括在道德精神陶冶下作家所形成的高尚品格与道德情操。宋明时期,理学兴盛,善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至此文学美已降低到依附善而存在,甚至文学离开了道德便“文之不文”了。
到了晚清、民国初期,门户被迫开放,来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社会观念及学术思想不断涌入中国,善与美的联系才有些松动,但“伦理本位”的观念依然坚固,伦理道德依旧被视为立国之本、修身之道。在善与美的关系上,仍以善为重,以美为轻,文学的功用在人们的观念中虽有所扩大,却只限于单纯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来提倡。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彻底颠覆了“伦理本位”的观念。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不认为伦理生活是个人生活的首要内容,而且也不承认传统伦理道德是人格塑造的理想标准,他们甚至有意淡化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或刻意揭发伦理道德的虚假荒谬。在摆脱“伦理本位”观念束缚的同时,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在文学审美方面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认为文学是伦理道德的工具,需要为伦理道德服务,并被伦理道德所决定。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是自由的,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在西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尊崇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崇尚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真实,将真提升到了文学审美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明确地指出:“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
五四时期,文学界发生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潮头。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情感态度方面,还是在创作手法方面都对文学提出了追求真实的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他们主张文学应该暴露人生的真相,写出哲学、科学意义上的人情事理。胡适极为赞赏易卜生那种旨在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的“写实主义”;(2)傅斯年则向新剧本的编者强调:“务必使得看的人还觉得戏里的动作言语以外,有一番真切道理做个主宰。”(3)在文学的情感方面,倡导者们主张,文学中的情感应该纯真、质朴。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论诗通信》中,富有情感地写道:“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4)钱玄同在文学革命发起后不久便宣称:戏剧、小说若无“‘高尚思想’与‘真挚精神’者,便无价值之可言”。(5)在文学创作方法方面,倡导者们同样主张依据科学知识,遵循自然法则而创作。周作人提出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如实模写,始为得之”;(6)胡适则在诗歌创作上推崇“自然的音节”,所谓“自然的音节”就是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音节,胡适将这样的音节称作“诗的最好音节”。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也曾注意到真与美的关系,但由于传统文人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对情感与理性认识的不同,遂导致了传统与现代“真”的内涵不尽相同。传统文学审美中所谓的真主要是指意象的真实或玄理的真实。
意象的真实主要指意象能够逼真地形容出作者内心的情意或性情;玄理的真实则指文人饱满地表现出宇宙的生气(本体和生命),做到“气质具盛”。这两种真实都不同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具有实证基础的科学真实。
二、反纲常倡新伦 变情感为理性
中国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统治阶级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之说始于汉代,是由汉儒推出的一套伦理道德规范,但这一思想的根源还须追溯到先秦时代儒家所代表的伦理道德理念。先秦时代的儒家代表孔子、孟子、荀子以血缘亲情为根本来构建伦理关系,他们首先强调父母与子女间存在着一种父母有恩在先的债务性的情感关系,然后遵照情感平等的原则,子女就理应后天尽孝来报答父母的恩情。这种理念推演开来,便有了臣应该对君忠诚、妻应该对夫顺从的教条。所以,先秦时代的儒家虽没有讲过“三纲”,但他们的道德理念已为“三纲”学说奠定了基础。
情感在伦理道德的构建中充当着核心性的手段与载体的作用。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审美中,情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李泽厚认为,“中国美学在艺术上特别强调情感的表现”,中国古代,以乐为中心的艺术“充分地发展了艺术表现情感的功能”。
与乐相联系的诗,“也绝大部分是抒情诗。……突出地展示了中国艺术重视情感表现的特征”。(8)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却是一个理性精神彰显并不断高涨的时期。此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一面热切地介绍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一面揭橥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将其贯彻在思想、文学等各个领域。这一时期宣传科学精神最积极、影响最大的是胡适。胡适在积极宣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与方法的同时,也身体力行,审慎地践行着科学精神。他在留美期间及回国初期写了一系列研究古文词义语法的论文,这些论文严格遵照着科学的实证方法,不仅比前人更令人信服,也为当时的文学研究界输入了一股新鲜的风气。
理性精神的显达,削弱了情感的主观作用,也使文学审美由强调“情感”的表现转变成重视“理性”的思考。
其实,中国传统文学在注重抒情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理性的节制,只不过传统思想通常将人的情感机械地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发的、无节制的、非理性的情感,这部分情感主要是缘于官能的生理反应,传统思想将这一部分情感视为兽性的、低劣的、可鄙视的,是理当排斥的;另一部分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认可的理性的、可节制的情感,这一部分情感是传统文学表现的对象。
在传统文学中节制情感的理性又有两种。一种是指伦理道德义理的理性。伦理道德义理中的理性虽然也带有归纳、推理、分析、判断等理性特征,但这种义理的理性是将理性包含在情感中,实质是一种对义理的爱慕之情或用这种爱慕之情去节制非义理的情欲,归根结底是一种情理。与此相反,五四时期提倡的理性则是西方式的理性。西方的理性与感性相对,是一种排除了主观情感、严格遵照事物的原理与现象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展开的思维方式,此种理性更强调抽象、分析和创新。另一种包含在传统文学中的理性是玄学性的理性。玄学是深受老子、庄子影响的一门传统哲学。这种哲学主要是以宇宙本体、生命体验作为观照的对象,思考者常将所悟会的宇宙观融于人生观中。由于这种哲学思辨的特征是缺乏规定性、具体性和理论性的,因而主要依靠直观来感悟、把握,这种宇宙观就是一种遐想式的认识论,是一种脱离尘世、远离现实人生的玄虚说教,因此显得十分幽深缥缈、神秘莫测。与此相反,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理性精神则是一种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对现实人生加以客观认识的思维方式,这种理性不仅不会远离现实人生,反而会成为现实人生的指导。
在科学精神的鼓舞下,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纷纷推崇理性思考在文学中的作用。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大力倡导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因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9)深受胡适影响的傅斯年在文学革命时期也发表了一些崇尚理性的文章。在《文学革新申议》中他指出:“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0);在《怎样做白话文》中他说:“这理想上的白话文是甚么?我答道:(一)‘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二)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三)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11)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当时的“戏评界”缺乏“精密的思想力”,随后他又批评那种没有客观标准,只凭个人好恶而评剧的“党见”的不良之风。欧阳予倩在《予之戏剧改良观》中也提出“正当之剧评者”“必根据剧本,必根据人情事理以立论。剧评家必有社会心理学,论理学,美学,剧本学之智识。”(12)由此可见,五四时期启蒙作家和启蒙学者的思维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西方的科学思想和逻辑思维,他们的主张虽未深及社会底层,却鼓荡出了新世界观的潮涌,给新文化和新文学提供了锋利的思想武器。
三、推倒“和”字立新标 直面“自由”以为美
传统伦理道德以“和”为贵,将和谐作为道德的最高理想。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只有人与人之间保持亲睦和谐,社会群体方能统一,国家才会形成强大的力量以抵御外界的威胁,维持长治久安,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要。可以说,人际关系间的和谐被儒家视为保障社会安定乃至人自身生存的利器,正如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3),《中庸》也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4)为了求得和谐的局面,儒家一方面要求人人安守于自己所处的等级地位,并根据自己的身份尽到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儒家也特别强调,个人的言行举止应恪守伦理道德准则,严格践行中庸之道。儒家理想地认为,人们的言行若能恰到好处地达到伦理道德的要求,处事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会协调,天下就会和平安宁。应该承认,以“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对于调节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也为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间保持友好和睦的关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毕竟产生于科学精神并不显达的古代社会,科学思想的缺乏,必定会造成以“和”为贵思想的诸多不足。
五四时期,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启蒙知识分子们迫切呼吁个性解放、人格独立。陈独秀甚至认为东西民族伦理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前者以“个人为本位”,后者以“家族为本位”,“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15)众声喧哗中,人们不再将传统的道德规则视为天经地义,也不再将和谐作为道德的最高理想。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呼声取而代之成为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在个性解放精神的鼓舞下,五四时期的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崇尚一种“个人本位主义”的道德规则。“个人本位主义”的道德规则是在承认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个体与个体间的差异,强调自我人格独立的权利与价值,倡导相互尊重并保持个体的自由、独立。个体解放、人格独立的精神辐射到文学审美上,也使得启蒙知识分子们不再以“中和”为美的重要元素,而是直面“自由”,立“自由”为审美的新标准。
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理想也使得传统审美将“中和”作为美的一个重要元素。所谓“中”就是折中、调和之意,“中和”之美强调审美过程中,主体的情感应保持适度、平和,要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6)只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才是审美的至高境界。“中和”之美渗透到文学审美领域,助长了传统文学高度重视表现拘谨之下的形式美。中国古诗向来重视形式的规范化、程式化,倾向声律的匀称、格式的整齐,特别是唐代开始的律诗、绝句,更是在字数、句式、格律、音韵上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中和”之美的影响;在内容方面,“中和”之美也助长了传统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大团圆、善恶果报的表现倾向。中国传统小说、戏剧在设计故事情节中,非常注意平衡故事中的各种力量,想方设法化解各方矛盾,力求安排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以“中和”之美的模式来满足欣赏者的心理期待。
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在文学上以个性的自由伸张为新标准,视参差、错落、独创为美的重要元素。在新诗方面,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提倡打破诗体、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17)在戏剧改良方面,胡适厌恶带有团圆式的传统小说、戏剧,指出这样的小说、戏剧是一种“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是“说谎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澈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胡适认为“悲剧观念”才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绝妙圣药”。(18)傅斯年也在《论编制剧本》中批评中国戏剧中通行的大团圆式的结尾,说它容易将观剧者前面所获得的感想和情绪“一笔勾销”,“最好的戏剧,是没结果,其次是不快的结果。这样不特动人感情,还可以引人批评的兴味。……人物愈平常,文章愈不平庸哩。”(19)这些见诸新文学领袖们笔端的意见虽然不无瑕疵,但总体上却将中国传统的回避现实、戕害个性的迂腐哲学观念推倒在地,取而代之以清新、真实、充满变革精神的哲学观和审美观,同时又以强烈的文化自省意识和大胆尝试的创作努力为国人的思想启蒙做出了表率。
结 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去今已近百年,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审美文化的面貌虽仍透露出几千年传统的影响余波,但毕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回顾近百年来的演变轨迹,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不仅是极深刻的,而且也是极珍贵的,值得我们认真审思和批判。因为其一,这百年来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审美生活是充满曲折和付出巨大代价的,这不见硝烟、悄无声息的精神鏖战是蕴藏着巨大的认识资源的;因为其二,这些思想和艺术领域的遗产———无论是成功抑或失败———是对未来中国的道德建设和艺术创造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伦理文明遗产和丰赡的文学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传扬,但也有着早已不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陈腐丑陋的伦理道德积弊和阻遏文学艺术蓬勃生长的痼疾,这些都是我们乃至我们之后的几代人非经巨大的努力奋斗而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伦理革命和审美解放是一个古老民族经由近代启蒙而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再犹疑踟蹰,临畏途而退避。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已然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唯有奋力开拓进取,才会不负五四运动的启蒙先驱所开创的事业,贡献力量于伟大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