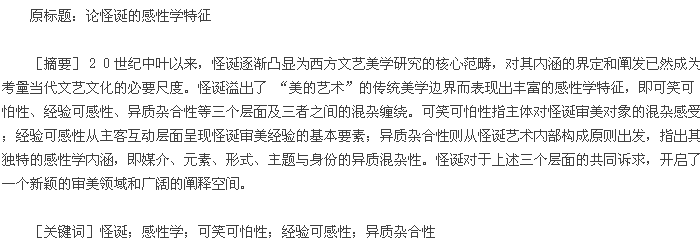
“怪诞” (grotesque)广泛存在于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之中,是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和后现代文化的骎骎日进,怪诞逐渐凸显为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受到了持续的关注和阐发。在文艺作品中,“怪诞人物形象不仅显着地出现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原始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词汇中,也在立体主义和某些抽象派那儿占据着重要的角色”,在美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人们往往把包括波德莱尔、罗斯金、尼采、弗洛伊德、巴塔耶、巴赫金、克里斯蒂瓦等有着深远影响的着名思想家纳入怪诞研究的传统。
①怪诞理论研究者斯泰格指出,无论怪诞曾在艺术与文学的讨论中充当多么卑微的角色,如今,它已经大致上获得了自己尊贵的地位。
②即便如此,包括文学、绘画、雕塑、电影和摄影等在内的当代艺术领域所呈现的怪诞特性,依然无法通过怪诞术语的词源学考证而揭示出来。
③而且,怪诞也不能被锁定在对特定意义、形式、历史阶段或具体政治功能的描绘上。甚至有学者认为, “任何通过定义方式来锚定怪诞含义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
④这源于怪诞术语所描述的对象的广泛性和怪诞定义的开放性。探讨怪诞的审美特性,不仅对理解怪诞艺术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新媒体、新生物技术和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科技、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种族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开拓出了创造性阐释的空间。
我们用 “怪诞的感性学特征”置换 “怪诞的审美特性”,意在回归 “aesthetics”的原初内涵,即“研究感性知识的学科”。
⑤因为,无论将怪诞视为“滑稽的和令人厌恶的扭曲”、“不一致、荒诞”,还是 “人类与动物互相交织形成的装饰图案”、“扭曲到滑稽的人物或设计”,⑥其丰富内涵都是传统 “美学” (关于 “美的艺术”的研究)所无法涵盖的。
同时,强调怪诞的感性学特征,也意在将对怪诞的审美思考 “沉降”到怪诞自身 “身体-物质”的低级但更根本的层面上。具体说来,本文旨在从三个层面探讨怪诞的感性学特征:首先,简要梳理西方怪诞研究对它的经典定义,指出这些定义的共性在于从 “审美效果”或 “审美感受”角度展开论证,认为怪诞是 “可怕的”与 “可笑的”相混杂,这涉及的是怪诞的主观感受层面,可概括为 “可笑可怕性”;其次,针对西方界定怪诞的上述倾向提出怪诞的可感性 (sensibility)问题,我们称之为 “经验可感性”,具体分析影响主体对怪诞艺术感知的基本要素;最后,指出怪诞的核心特征在于其 “异质杂合性”或混杂性 (hybridity),怪诞艺术在媒介、元素、主题、形式和身份等五个层面上具有混杂性特征,而这五种 “混杂性”的进一步 “混杂”,开启了一个新颖的审美领域。 “作为一种复杂而带综合性质的艺术手法和审美途径,怪诞可以说是连接诸种感性学范畴———悲剧、喜剧、滑稽、丑与荒诞等———的元范畴”,⑦也是对人类本质的思考过程中暂时 “无法摆脱的”范畴。⑧
一、可笑可怕性
许多学者认为怪诞属于 “不可范畴化”的范畴,因为它所指称的那种 “把所有东西都混为一体”的怪物是无法命名的,我们的思维里也找不出可以与之对应的范畴。
⑨然而,作为西方文艺研究中的一个术语,怪诞通常被界定为 “以夸张和变形的方式展示人体形象”,?其典型特征在于 “奇异的变形”(bizarre distortions),尤其是对人体特征进行夸张的、反常的刻画和描述。
具体说来,怪诞可以指称一种特殊的绘画风格,一种包含着 “某些创作观点……内容、结构以及观看者产生的影响……的美学范畴”,一种兼有 “装饰功能和护符功能”的 “装饰图案”,?“民间诙谐文化”的物质-身体形象体系,?美国当代文化生活的 “文学与视觉”表征模式,甚至是复数的 (grotesquerie)、朝向晚期资本主义的 “全球性怪诞”。
尽管这些界定各不相同,但有三点却是一致的:(1) “怪诞意味着对立项之间的混合”;(2)两个对立项分别为 “可笑的” (ludicrous)与 “可怕的”(fearful);(3)上述界定皆从审美效应角度展开,对于怪诞审美特性的探讨来说,这种被比厄斯利称作 “情感性定义”的方法是 “无法避免的”。
就第 (1)和第 (2)点来说,诚如海耶斯所言,20世纪的文艺研究者 通常继 承 了罗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的看法:“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怪诞之作都由两种成分组成:一是滑稽可笑的事物,二是令人心生恐惧的事物。”
对 “可怕”与“可笑”两种因素的强调可以说贯穿在包括雨果、戈蒂埃、波德莱尔、霍夫曼、凯泽尔、巴赫金、汤姆森、斯泰格、詹尼斯、哈普汉姆、芬格斯坦、科鲁斯、古德温、马斯葛来福、罗森、西斯瑞·罗尼、爱德华兹和格兰伦特等几乎每一个涉足 “怪诞”美学的学者。虽然凯泽尔因为受到浪漫主义怪诞观的 影 响 而 “过 分”突 出 “可 怕” 一 项 的 权重,但他仍然承认 “笑在怪诞的滑稽和讽刺的边缘发生”。
另外,由于巴赫金在 “怪诞现实主义”、“怪诞身体形象”和 “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之间建立了 “等式”,所以,巴赫金式的怪诞是一种全民性、节庆性和乌托邦式的 “狂欢”,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 “狂欢”是 “双重性的”,是 “对崇高的东西的降格和贬谪。……意味着靠拢人体下身的生活,靠拢肚子和生殖器官的生活,……靠拢交媾、受胎、怀孕、分娩、消化、排泄这类行为。”
而这些行为,在克里斯蒂瓦那里则被解读为 “卑贱”这一可以归为 “可怕”的身体经验和情感感受。
芬格斯坦在其着名的论文 《界定怪诞概念》 (1984)一文中指出,怪诞中的一些元素就其自身来说可能是 “美的”,但置于整个概念和主题之下却显出怪诞来。例如在亨利·弗斯理的 《梦魇》 (1781)一画中, “梦中的女人有着漂亮的脸蛋,体型优美,她的腿、头发和胳膊都比例得当”,但总体上却不妨碍画作传递出的 “恐惧与欲望、可怕的与美丽的、梦与现实之间复杂的混合”。
这提醒我们注意,怪诞中 “可怕的”与 “可笑的”通常与 “有吸引力的”以及 “令人排斥的”相互联系。
就第 (3)点来说,“可笑的”和 “可怕的”这样 “情感性的”界定,在美学史上一度遭到学者的质疑。
两者作为形容词,表达的是一种感受,不能充当 “客观描述”的功能。正因为这样,即便凯泽尔声称怪诞是一个 “有关某些创作观点 (如:像梦一样)、内容、结构以及观看者产生的影响 (维兰特的 ‘笑,厌恶和惊愕')的美学范畴”,但细读其 《美人和野兽》,却看不到对怪诞的所谓 “结构”分析。同样,在欧美怪诞研究界影响巨大的汤姆森,也认为 “怪诞本身肯定有着自己所独具的某种模式,有着自己所独具的某种结构”,但他论证该观点的方式却是大段引用经典文本中的怪诞细节描写 (尤其是人物形象描写)。当然,他把怪诞看作 “作品和效应中的对立因素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一冲突与表现在怪诞中的那种反常物自身的矛盾性质是一种并存的关系”,这一定义把我们引向可能构成某种分析原则的 “反讽”结构。即便如此,其整个的怪诞定义都建立在 “可怕的”与“可笑的”相互对立的主观感受范畴之上。
显然,上述的界定是从审美感受的混杂性来定义怪诞的感性学特征的。正是 “可怕的”与 “可笑的”、“具有吸引力的”与 “令人排斥的”这样互相矛盾的感受性词汇杂合而成的感受,使得怪诞的特征凸显出来。这种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它预设人们可以知觉到怪诞这种以混杂性感受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或者,它假定怪诞可以被人们知觉为审美对象,而这恰恰是 “成问题的”。将 “对象”知觉为“审美对象”,并非研究怪诞审美特性的自明的基础,而恰恰是其需要论证的前提。在审美经验中,尤其是在对 “怪诞艺术”的审美经验中,存在着一些 “极端的”、 “非美学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对怪诞艺术特性的 “盲视”。只有首先被知觉为审美对象,才有可能去探讨其具体的审美特性。
这就引出了朗西埃所谓的 “可感性”问题。
二、经验可感性
可感性或 “可感性经验的重构”,是朗西埃对“美学”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美学”既不是通常所言的 “艺术理论”,也不是使得 “艺术将其效果体现在感官上”的理论,而是一种 “鉴定并反映在艺术上的具体的体制 (regime)”。
而 “可感性的经验是感知与感知之间、提供可感性材料的力量与对此进行理解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关系。”简单说来,它涉及人们 “做的方式、看的方式、说的方式和想的方式等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体制或形构与 “伦理形构”或 “伦理原则”之间的 “对立或者转换”关系中,朗西埃所谓的 “美学”特性得以确立:“人们所能感知的和他们能理解的,是他们所作所为的严格表达;他们的所作所为由他们是什么所决定;他们是什么由他们的位置 (place)所决定,反过来,他们的位置又为他们是什么所决定。他们所在的位置与其内化的实践原则 (ethos)彼此契合。”
什么是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人们能够知觉到什么?什么能够被知觉为审美对象?这在朗西埃看来不仅是美学内部的事情,而且更多地牵涉到了非美学的因素。这一点在怪诞研究史中并非没有学者提及。
从最初维特鲁威和贺拉斯对那种把 “属于不同的族类”的事物 “交配在一起”的绘画风格的批评和排斥中,可以看出,在古罗马时期的批评家和艺术立法者眼中,后世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加以合法化的grotesque艺术根本就不是艺术,更不用说成为审美的对象了。无论是多么 “怪诞”的事物,若未成为审美对象,也就无从产生怪诞的审美体验。“对于一个步行回家的巴黎人来说,圣母院外的怪兽状滴水嘴 (gargoyle)就像他脚上的拖鞋一样让他感到舒服而没有任何的怪诞之感。”
这其实触及到了怪诞的可感性问题:怪诞艺术能否为人们所感知,进而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这是怪诞艺术之所以怪诞的基本前提。
朗西埃借用布尔迪厄 “趣味的区隔”和 “内化的实践原则”来解释 “欣赏和知识、需求和欲望等级之间的不一致”。
?
依据布尔迪厄的观点,主导阶层组成了一个 “自治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结构通过 “对其成员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分配”而得到界定。这种结构对应着特定的生活方式,通过惯习的中介影响着阶层内部成员包括美学 (或趣味)在内的一切实践的选择。
因此,“每个阶级都有其为内化的实践原则所决定的趣味”。这一点,具体到对怪诞的可感性的影响体现在四个层面。
首先,这种实践性原则被内化为某种美学规范,这种规范以无意识的方式主导着人们 (尤其是研究者)对怪诞艺术呈现的审美特性的接受或排斥。正是在古典美学 “一致性”原则的指导之下,维特鲁威和贺拉斯才对那种 “人头半身像”、“兽头半身像”等等把不同物种 “交配”在一起的画作表示不满,斥之为 “病人的梦魇”。
同样,在德国古典美学将 “aesthetics”置换为对 “美的艺术”的研究的美学气候下,雨果不得不从上古以来的资料出发,为自己的 《克伦威尔》以及其他作品中“滑稽丑怪”的形象正名。
巴赫金也指出,人们无法理解拉伯雷笔下的怪诞形象的真正意义,原因在于 “他的众多形象不符合自16世纪末迄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性标准和规范”,或者是粗暴地将其进行 “现代化”处理, “按照近代诙谐文学的精神来解释民间诙谐,或者把它说成是纯粹否定性的讽刺诙谐 (因此拉伯雷被称为纯讽刺作家),或者把它说成是纯消遣性的、无所用心的诙谐,没有任何世界观性质的深度和力度”。
其次,朗西埃和布尔迪厄的这种实践性原则体现在普通人身上,则是 “手臂活动和凝视活动之间的分离”。从柏拉图到康德和黑格尔,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的古典美学都建立在这种分离的基础之上,人们所做的或能做的不是其所欲求的,所看到的或所能看到的不是其所拥有的或能拥有的。马克思将其称作 “人的本质的异化”,对其展开了批判。
朗西埃在黑格尔的美学中发掘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称之为 “无所事事”。对于为有钱阶层铺地板的木匠而言,“只要铺地板的工作没有做完”,房间的布置、窗外的花园以及周外的一切美景都会使他“将手中的活计停一会,任由自己的想象向着广阔的风景翱翔”。
木匠没有把自己 “手上”的活计当作是财产、知识、欲望或科学,所以,他 “眼中”所见和 “手上”所做的事情之间就构成了 “审美”的关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 “眼睛”和 “手臂”的分离,工人就不可能在 “无所事事”中把对象知觉为审美对象。在怪诞的审美实践中,普通人与怪诞艺术的关系甚至根本不是 “眼睛”和 “手臂”相分离这样的关系,而更有可能是阿瑟·丹托提出的问题:“凭什么杜尚拿来的小便池是艺术品,他人拿来的小便池就不是?”
原本极其怪诞的事物,一旦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那么,即便是存在“手臂活动和凝视活动之间的分离”,人们也不可能把它知觉为审美对象。所以,我们可以把影响怪诞可感性的第二个因素称作 “怪诞艺术的生活化”。
再次,时空差异性也是影响怪诞可感性的主要因素。空间方面的差异,影响的是不同文化语境中怪诞艺术的可感性,时间方面的差异则表明社会历史变迁对怪诞的可感性造成了无法化约的影响。
“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既可怕又可笑的石雕怪物,在中世纪人眼里可能只是可怕 (也许只是可笑),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我们不一样。”
正因为这样,怪诞形象往往存在于充满异域色彩和考古色彩的游记和冒险小说中。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保证具有上述特征的某一文类中的怪诞形象具有可感性,美杜莎、蛇怪、帕伽索斯、半人半马兽、狮身鹰首兽、潘、哈比、古埃及的兽首神、亚述的人首动物身的神以及中国的龙,它们曾经 “既可怕又危险”,属于经典的怪诞形象,现代科技,尤其是电影业、动画制作业、生物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得这些原本依靠线条、画笔、颜料、文字 “虚构”的半人半物的神话形象以极其真实的影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以至于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怪诞即“畸形就是正常”。
例如,“赛博格”或 “电子人”、“半机械人” (cyborg),就是 “机器和有机组织的混杂”。在哈维拉看来,它并不是什么 “怪物”,而 “既是虚构的物种又是现实的物种”,因为 “在二十世纪末期,赛博格既是改变女性经历的虚构,又是 [女性]活生生的经历。”
科幻电影和小说的“常备剧目就是一群异常的物种:怪物、电子人和外星人”,因为后现代语境之下,“科学已经能够探索并综合以前未曾见过的空前数量的事物”,怪诞于是 “变成了某种正常”。
最后,影响怪诞艺术可感性的还有个体心理的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原本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术语,指的是 “自我对其感知为危险的内在刺激的反应”。
弗洛伊德认为, “自我”形成伊始,就充当着追求 “唯乐原则”的 “本我”与恪守 “现实原则”的外在世界之间的调解者。为了满足本我的需求,自我想方设法使本我避免危险、焦虑和令人不安的事情。
面对贝克特的小说 《瓦特》中 “林奇这个古怪的家庭”中的怪诞人物形象,读者会产生“既可笑又可怕、可恶”的 “分裂”性感受,这种矛盾感受 “涉及文饰作用和防御机制,它启示我们,怪诞 (假定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很难被人们所接受的东西,人们总是力图逃避怪诞引起的不安。”
詹尼斯认为艺术 “总是可怕的与可笑的品质的混杂”,其中 “可笑的” (或幽默的)因素就是怪诞 “战胜焦虑和恐惧”的一种方法。斯泰格则强调怪诞就是 “以滑稽的方式来平息神秘的 与 可 怕 的 事 物 ”。
他 在 此 处 没 有 使 用“grotesque”一词,用 的 是 弗 洛 伊 德Unheimlich的英译词Uncanny。在弗洛伊德看来,神秘的和可怕的感觉 (Unheimlich) “源于某种熟悉但却受到压抑的东西。”这种感觉往往和童年时代的经历相关, “当受到压抑的幼时情节因某种印象而复苏,或者,当已被克服的原始信仰似乎又得到了证实时,我们便会体验到神秘而恐惧的情感。”克服这种情感需要读者对文本进行合理化处理,即意识到小说中所有可怕的事物都不过是作家 “不按一般语言规则行文的自由和特权” “欺骗”我们罢了。
此处,弗洛伊德的洞见给怪诞研究以启发:怪诞的审美感受可能并非来自于审美对象,而很可能来自读者自身熟悉的东西。如此说来,怪诞感的引发就不在于怪诞对象被知觉为怪诞与否,而在于主体自身怪诞与否。
正是实践性原则被内化为美学规范、怪诞艺术的生活化、时空差异以及个体心理防御机制的运作等四个方面,影响了我们能否把某种对象知觉为审美对象,进而区分这种艺术到底是 “可怕的与可笑的混杂”的怪诞艺术还是非怪诞艺术。
三、异质杂合性
审美主体能否把一个一般对象知觉为审美对象,这既涉及可感性,同时也必然要求怪诞自身具有某种独特的感性学特征,缘之而与美的、崇高的、悲剧的、喜剧的、滑稽的以及荒诞的艺术相区分。
西方学者除了把可感性问题作为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之外,还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怪诞的混杂性特征。凯泽尔将施莱格尔的怪诞观总结为:怪诞是由 “形式和内容之间互相抵触的对照、不同种属的因素不稳定的结合、以及荒谬的爆炸性力量这些东西构成。它既可笑又可怕。”
爱德华兹和格兰伦特更是在其新作 《怪诞》中,直接用混杂性来界定怪诞:“视觉文化和文学中的怪诞,通常包含了类人的形式和动物性的特征相互混杂的形式。”
在怪诞最初描述的那些图案中, “人与非人、动物与植物这样完全异质 的东西之间 奇异 地 混 合 在 了 一 块(mixture,combination)”,而混杂的本意则是 “两个不同物种或种类的动物或植物产生的后代”。
可以说,怪诞与混杂性有着天然的契合。首先,两者在要素上都是异质异种的;其次,要素的关系都是“杂合”的;最后,它们都有自己完全异于组成要素的新 “物种”产生。只是研究者往往用两重性或二重性 (doubleness)来置换混杂性。即便我们暂时忽略霍米·巴巴赋予混杂性的颠覆性内涵,我们也很难说,马和驴杂交的产物骡子是马还是驴,或者说既是马也是驴,它属于一个全新的物种。同样,怪诞元素论中人与物的混杂形成的可能是全新的物种,这种物种在当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下成为了现实。怪诞反应论中滑稽与恐怖的混杂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而不是两者之间不同剂量的单纯混合。怪诞形式论中的反常和常规之间的博弈,则不仅仅等价于形式主义的 “陌生化”,它更指向一个权力的空间,或意义的整个分配网络。
据此,我们认为怪诞作为审美对象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其混杂性,主要体现在媒介、元素、主题、形式以及身份等五个层面。
媒介层次上的混杂,主要指怪诞艺术从造型艺术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成的视觉媒介和文字媒介之间 的 混 杂, 尤 其 是 “视 觉 预 设” (visualassumptions)在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中的必然性存在。
从怪诞最初所指的对象来看,先是绘画,其次是雕塑和建筑,再逐渐扩展到文学。绘画的“并列性” (juxtaposition)、 “物性” (physicality)和 “可见性” (visibility)瑔瑢?对文学中怪诞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1)形象性的要求。(2)场景化处理。(3)空间形式 (spatial form)。前两个方面使得文学中的怪诞在表现对象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形象 (尤其是人物形象)刻画和场景的渲染上,后一个方面涉及的是空间的并列性对线性的时间性叙事的 “干扰”,使得怪诞的文学作品在表现“动作”的时候倾向于以并列的方式,而不是遵循传统的线性发展的叙事逻辑。 “空间形式”由约瑟夫·弗兰克在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提出。
他通过分析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中农产品展览的场景指出,“就场景的持续来说,叙述的时间流至少是被中止了: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些联系游离叙述过程之外而被并置着;该场景的全部意义由各个意义单位之间的反应联系所赋予。”
空间形式对叙事文学的影响使得怪诞在一系列形象的描摹和场景的铺排中表现出来,形成 “贝克特式的” “抽象的怪诞”。
绘画对怪诞存在的影响还在于,绘画表现的主题转变为文学表征的主题。例如,希罗尼穆师·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1450-1516年)所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1485-1505)中的 “恐怖、神秘、性、暴力、荒诞”等混杂形成的主题,在爱伦坡、斯蒂文森、王尔德、马克·吐温、雨果、霍夫曼和福楼拜等一批卓越的文学大师那里得到了回应。
元素的混杂。怪诞的特性往往通过那种非纯粹的、非自然的、无边界的自然事物或虚构事物来表现,它们充当怪诞艺术的元素或者素材。巴赫金多次强调,怪诞的人体形象 “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这种非现成的、开放的人体 (濒死的—生育的—待生的)与世界没有明确的边界:它与世界相混合,与动物相混合,与物质相混合。”
凯泽尔认为,尽管不同的怪诞之作 “充满了千差万别的含义”,但 “仍然有一些倾向于某种内容的特殊的形式和主题”。此处的 “特殊的形式和主题”,其实就是怪诞的元素或素材。这些元素可以归结为六类:(1)虚构的 “怪兽”。作为 “杂交”的 “可怕的动物”,它们存在于我们现今归之于神话或传说中的物种,这些物种在 《圣安东尼的诱惑》和 《圣经启示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不断被注入新的意义。(2)真实存在但却宜于表现怪诞的动物。
“蛇、猫头鹰、蟾蜍和蜘蛛等等,这些都是栖息在人不能涉足的地方的、爬行的和夜间活动的动物”,这些动物真实存在,甚至平凡无奇,但是也会让我们 “体验到完全陌生的奇特感和恐怖恶兆的暗示”。
此外,还有害虫和蝙蝠。尤其是后者, “这个幽灵一般的动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极不自然的器官合并”,以及奇怪的行为习惯,让人感觉它是吸血动物,或者是 “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3)植物世界里的怪诞元素。植物世界一方面通过 “原始丛林”,那种 “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差别”被抹除的、 “藤蔓纷乱地缠绕在一起”的景象来传递怪诞,另一方面,人类技术 (如显微镜)对自然界的揭示也会把其中隐秘的怪诞的东西呈现出来。(4)物的怪诞。现代科技的发展催生了 “技术”怪诞, “有机成分和机械成分的混合”取代了传统怪诞里的 “尖利物”,“其中的机械象魔鬼一样具有破坏力,它们的力量远远地超出了它们的制造者。” (5)人的外表的异化。主要指 “赋予机械物生命和剥夺人的生命”形成的怪诞形象。其实质在于人与物之间边界的混杂:物体和人体杂合或物体具有了人的属性;另一方面,人变成了物,其生命的属性或精神的属性被未知的力量抽空,使得 “人变成傀儡、活动木偶和机械人,脸凝固成了面具”。这一点在前文论及的哈拉维的 “赛博格”理论里体现得较为明显,同时也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 “面具”意象、 “木偶”母题联系紧密,在当代文学,尤其是科幻作品和恐怖惊悚小说里成为屡试不爽的题材。(6)人内在的精神错乱。凯泽尔认为 “在精神错乱的人身上,人性本身似乎带上了不祥的色彩,仿佛有一种非人的力量,一个异己的、残酷的鬼怪占据了人的心灵”。
需要补充的是,内在的精神错乱必须表征为某种可见的行为或是语言,其不仅是异己力量与本己力量的混杂,更涉及非怪诞的、理性的话语与怪诞的、发疯的话语之间的混杂。例如,鲁迅 《狂人日记》即是此类怪诞元素混杂的例证。
形式的混杂。怪诞的艺术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往往会杂合各种艺术门类、各种文学流派的表现手法,在形式上给人造成陌生的冲击之感或文类的混杂之感。在文学传统内部,怪诞不属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但它存在于所有这些时期/流派中,同时也借所有这些流派或思潮的创作手法来表现自身。怪诞也不仅仅存在于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中,它更多地是各种文体形式的一种奇怪杂糅。用科鲁斯的话说,后现代的怪诞小说 “把先前看作是不相容的东西并置在一起”, “吸收包括街谈巷闻和黑话在内的话语、文本信息、聊天室和电子邮件混杂的新形式,以及信息技术的符号和语言等”。
主题的混杂。一些学者认为怪诞艺术作品传递的主题是负面的、黑暗的,通过 “不相容领域的互相混合;静力规律的废除;本体丧失;对 ’自然‘形状的扭曲;种属差异不复存在;对人格的破坏和历史秩序的破碎”来造成 “异化的世界”,传递出“毋宁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还不如说是对生活的恐惧”;也有学者认为 “一切现存事物的相对性在怪诞风格中总是欢快的,怪诞总是充满着更替的欢乐,哪怕这种欢快和快乐已减弱到最低限度 (如在浪漫主义中)”;?或者如切斯特顿把怪诞看作 “一种以新的眼光不加歪曲地表现世界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 “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重新认识(现实)世界,尽管这种眼光可能是怪异的、令人不安的,但却是清新的,真实可靠的”;甚至认为怪诞表现的其实是艺术家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得艺术家 “同时是自己又是别人”,“他们知道某人是滑稽的,知道他在不知道自己本性的条件下才是滑稽的;同样,根据相反的法则,艺术家只有在具有了两重性并且了解他的两重本性的所有现象的条件下才是艺术家。”
这充分体现出了怪诞作为一种艺术手法、风格、审美表现形态或美学范畴的巨大生命力,它表现的主题是混杂的, “从两头的癞蛤蟆到终极真理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怪诞艺术的表征对象。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怪诞表现的主题的混杂性可能不是指向双重的或二元的东西,而是霍米·巴巴意义上的 “混杂性”,其重要性 “并不在于可以 [据此]追溯到 [混杂产生的]第三项得以出现的原先的两项,而在于 [混杂性作为]第三空间,使得其他可能性的出现成为可能”,混杂产生的是 “不同的、全新的,也是难以辨识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意义和表征相协调的新领域。”
身份的混杂。怪诞艺术没有足够的同一性把自己整编为某一美学范畴或某一文类形式 (如悲剧、喜剧),在艺术的流变中,它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家族相似”。它与许多其他可以范畴化的美学范畴相联系,同时也相互区别。汤姆森对怪诞与荒诞(absurd)、怪异 (bizarre)、死亡恐怖 (macabre)、漫 画 (caricature)、 滑 稽 模 仿 (parody)、 讽 刺(satire)、反讽 (irony)、滑稽 (comic)等容易与之混淆的范畴进行区分。在布鲁姆看来,怪诞和崇高同样可以给人以 “震惊”之感,差别就在于怪诞有着 “洞穴的”、“地底下”的、 “幽灵出没”的源头,进而与崇高的 “超然性的震惊”区别开来。
于是,怪诞又和弗洛伊德式的 “神秘的与可怕的”(uncanny)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怪诞产生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它是 “最熟悉的陌生人”或 “最陌生的熟人”,是在可感性与不可感性之间边缘的一种存在物。在美学史上,它带给人们的是 “难以理解的形象”,“作为美学的孤儿,它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徘徊”。
除了上述五个层面的混杂性之外,风格的混杂、感受的混杂或许也应该包括在内。但是,怪诞作为风格、怪诞中可笑性与可怕性的混杂这样经典的定义,正是由于媒介、元素、形式、主题与身份的混杂糅合。这五个层面更倾向于对怪诞作为一个审美对象的客体性分析,一定程度上与风格的批评、传统印象式的批评相区别。小结怪诞艺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其 “陌生性”、“新奇性”给人的感官以巨大的冲击。后来无论是将Grotesque看作是特指16世纪发掘于意大利的古罗马装饰图案的专门词汇,还是对这种图案的模仿和在文学领域的拓展所形成的一种风格,甚至把怪诞看作是一种有着自身独特结构的美学范畴,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或是一种动荡社会现实的表征,其核心内涵都可以概括为 “可怕性与可笑性的混杂”。但是,这种西方学者定义怪诞的总体趋向忽略了怪诞的可感性问题,它事先假定怪诞可以直接进入审美主体的感受或知觉,而事实上对怪诞的感性学特征进行探究的第一步就是要追问其可感性问题。实践性原则被内化为美学规范、怪诞成为人们生活中习见的事物 (甚至生活本身即是怪诞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差异以及个体心理防御机制的运作等四个方面,以无意识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对于怪诞艺术的感受。在它们的运作之下,我们甚至根本无法将某一特定时刻或语境下原本极其怪诞的事物知觉为审美对象。怪诞的感性学特征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怪诞艺术本体的混杂性问题。怪诞艺术由于起源于绘画而渗透于各类艺术,因而具有媒介的混杂性,这种混杂性与元素、形式和主题的混杂性相杂合,使得怪诞艺术的同一性遭到破坏,造成了其身份的混杂性。但是,怪诞艺术本身的这种混杂性及其对人们审美感知的可感性的挑战,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颖的审美领域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现实与表征、意义与阐释、召魅与祛魅、美女与野兽难以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代社会生活和文艺文化的典型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