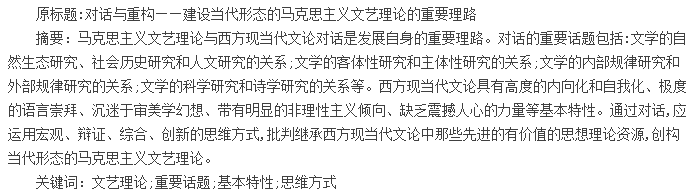
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理念的创新密切相关。原创是最可宝贵的,但原创是非常艰难的。学术理念的创新往往都是通过学术对话来实现的。我这里所说的对话,主要是指传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对话。这种学术对话是发展和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路。
一、对话的重要话题
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语境中,充满了西方话语。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同步进行的。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论呈现出强势状态,拥有话语的主导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往往受到西方现当代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本土化的阻遏,实际上是在西方现当代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本土化的夹缝中艰难进行的,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鉴于此,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必须正确对待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思想理论资源,通过学术对话,承接西方现当代文论之所长,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之中,重构新质态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一)文学的自然生态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关系
首先谈文学的自然生态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关系。由于自然生态的危机,这个问题越来越得到学界重视。围绕自然与人的关系,同时或交替出现两种对立的理念,即“自然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强调自然是人类的一部分,主张自然服务于人类,是造福人类的物质资源。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学科组提出了提升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即把自然科学社会化和人文化,并将自然科学视为一种实质上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理念客观上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如果极端运作,又可能会加剧人类掠取自然资源的竞赛,从而引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加重自然生态的危机。“自然中心论”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关系。我们注意到,西方一些生态主义者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对维护自然生态是有益的,但如果过度强调,又可能遏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两种理念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片面性。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应当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而应当友好互惠,和谐相处。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哺育和反哺的关系,是共存和互养的关系。我们既要善待人类,也要善待自然环境,促进和建构两者关系的良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通过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的评论,主张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从封建宗法式农耕社会向民主制市民社会的转型。同时,他们又提醒人们注意,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付出沉痛的代价。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颇有预见地揭示出建构人类和自然和谐关系的前景。经过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互走向,彼此靠拢:即人道主义走向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趋于人道主义,使两者得以双重实现,逐步达到完美和谐的理想境界。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基础,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方文论中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创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学理论。
其次,谈谈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对文学的人文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拥有深刻系统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学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系的阐释缜密而精当。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显得薄弱些。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人学思想仍然具有许多深刻的框架式表述。如关于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自然属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客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理论,关于人性的共同性和人性的差别性的关系理论,关于人的自由、异化和解放的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人学理论理应得到更具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发展。
西方文论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文主义的理论思想资源。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传统的人道主义到现当代各式各样的新人本主义,如归属于“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主要派别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人本主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狄尔泰的“解释学”的人本主义,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的人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人本主义,都从不同层面对文学与人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开掘,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维度大有助益。这中间也出现过一些非常极端的主张,如福山宣告“历史终结论”,德里达声称“人的终结论”和福柯鼓吹“人的死亡论”,尼采宣扬“上帝已死”、“理性的人已死”,罗兰·巴尔特主张“作者已死”等等。对这些“深刻的片面”的真理,应当进行科学的鉴别和剖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常注重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但并不是只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忽视文学与人的关系,不是只强调文学的社会理性和历史精神,拒斥文学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而是主张文学的历史精神和文学的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反对脱离人文精神片面地强调历史精神,或脱离历史精神孤立地强调人文精神。在与人文精神的联系中倡导历史精神,或在与历史精神的联系中提升人文精神,都是应当支持和鼓励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和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论述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实质上也应当是从社会历史的视域阐发文学与人的关系;论述文学与人的关系,实质上也应当是从人的视域解释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因为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人是社会历史的人。历史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的记录而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人的进步和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没有社会转型和历史的发展,就不会有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会给人带来利益和福祉;没有人的观念和素质的提升,就没有人的变革意识,也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两者是互动共进的。
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和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因而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擅长于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学者和钟情于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的学者,理应相互尊重。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和谐的,当社会历史的发展给人们带来自由、幸福和解放时,这样的社会历史对人来说,是温暖亲切的;当社会历史捉弄人、压抑人、给人造成痛苦和灾难时,这样的社会历史对人来说,是冷酷无情的。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往往是不相协调的。实际上,处于完全均衡状态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不存在的,总会有所倾斜和偏重,这是正常的。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发生人与历史的矛盾,人被历史的强势的制度、体制、物质力量和文化氛围所压抑,甚至受捉弄,遭践踏。
人与社会历史的矛盾,实质上是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尤其表现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在占有和再占有、分配和再分配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的矛盾,表现为不同群体在权力、财富和利益方面的占有和再占有、分配和再分配方面的矛盾,往往引发出社会历史结构中具有压倒优势的集团和个人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因此,人与社会历史的矛盾可以表现、还原、转化为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间的矛盾。只有解决不同人群之间在占有和分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畸形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社会历史的矛盾。
那些激愤地指控人与社会历史的矛盾的言论,只能流为一种美好而无效的空谈。
(二)文学的客体性研究和主体性研究的关系
文学与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以及文学与人的关系反映到文学自身,集中表现为文学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根本性和母源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较强调对文学的客体性研究。但并不是只主张客体性,不要主体性,而是主张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完美融合,反对单方面地强调客体性和孤立地夸大主体性。西方现当代文论,个别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消解人和文学的主体性,宣扬“人已终结”和“主体已死”,还有一位美国学者帕森斯·哈丁倡导突出政治基因的“强客观性”,最近又涌现出一种彰显客体性的“物质性批评”。
除此而外,大多数学者,特别是以强调人文主义为旨意的理论家都是宣扬人和文学的主体性的。著名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把人的主体性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海德格尔的“此在”和萨特的“先于本质”的“存在”被赋予极强的排斥客体性的封闭的孤立自足性。萨特竟然宣称: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外,并无其他世界。脱离主体性的“强客体”和消解客体性的“强主体”,都是不妥当的。
笔者认为,在文学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存在和组合结构上,往往表现为几种形态:和谐统一的融合形态,表现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合理适度的倾斜形态,或向客体性倾斜,表现为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或向主体性倾斜,表现为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如把客体性推向极端,则表现为以直观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为基础的自然主义,如把主体性推向极端,则表现为以唯心主义为依托的意志主义。我们应当提倡和谐统一的融合形态,支持和鼓励合理适度的倾斜形态,同时也要吸收偏执失衡的极端形态所蕴含的那些具有正价值和合理性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蕴藏着“深刻片面的真理”,以尖锐的挑战姿态和冲击力量,给人们以警醒和启迪。如极端张扬主体性的意志主义,特别是尼采的意志主义,从哲学和诗学的结合上宣示超人的“权力意志”和张狂的“酒神精神”,曾迷醉鲁迅一代文人。把客体性推向极端的自然主义,尽管有点模拟和拘泥于生活,但自然主义艺术流派的首创者左拉的一些小说很有特点,充满着生活的质感,洋溢着淳朴的真情。又比如自然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米勒的《拾穗者》等画作描绘勤劳善良的农民的劳动和生活,温润和激荡着浓郁的田园牧歌式的世俗风情。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奇特的精神之花。
与研究文学的客体性和主体性问题紧密相关,存在着一个怎样理解对文学的反映论研究和价值论研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重视对文学的反映论研究的,但并不是只主张反映论,不要价值论,而是认为应当把反映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直观的、被动的反映论,主张能动的、积极的反映论。科学的反映论永远是行之有效的价值论的基础。人们的价值诉求是认知活动的驱动力。脱离价值论的反映论是空洞的,撇开反映论的价值论是盲目的,至少会使价值诉求、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失去明确的方向感和目标感,从而局限人们价值目标的圆满实现。人们活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有合规律性,才能达到合目的性;为了实现合目的性,必须追求合规律性。我们应当把人的认知活动和人的价值活动视为追求和实现人的预期目标的同一个过程和同一件事情。因此,用反映论去价值论,或用价值论去反映论,会使反映论和价值论受到同样程度的伤害。
(三)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研究的关系
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包括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不承认文学有内部规律是不妥当的。事物有外因和内因,矛盾分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是完全必要的。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索绪尔等都从语言学视阈对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进行了探索。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较注重文学的外部规律。确实存在着一个怎样正确理解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关系问题。
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中,并通过这些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建构和发展。探讨规律,叩问对象富有真理性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都是完全必要的。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是相互依存和竞相发展的。一位文艺理论界的前辈曾把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比喻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的关系,十分贴切。地球是围绕着公转的轨道自转的,又是通过自转实现公转的。如果只自转不公转,地球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如果地球不自转,就无法实现地球的公转,如果地球的自转脱离公转的轨道,人类唯一的绿色星球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
与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紧密相关,还存在一个文学的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的关系问题。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派,对作品的语言形式符号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诸如关于“陌生化”的理论、关于“文学性”的理论、关于“骨架和机理一体化的”理论、关于“诗学”的理论、关于“结构—解构功能”的理论,都富于启发性。但一些学人倡导的“文本本体论”和“形式本体论”几乎完全消融和隐去了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外部对象和创作主体的密切联系。
一些研究者作为对“内容决定论”的反拨,开始从“内容决定论”走向“形式决定论”。对形式研究的日趋深入,产生了一些诸如“内容是完成了的形式”,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等有代表性的观点。实际上,“内容决定论”和“形式决定论”都是不完整的。从与内容的联系中,强化形式研究,或从与形式的联系中,优化内容研究,都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尽管形式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形式和内容共存于一个机理相关的共同体中,把两者断然分开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内容是形式的内容”,这些传统的经典性的理论表述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忽视和脱离形式强调内容是不妥当的。
西方现当代文论一味地遮蔽、隐匿、消解、掏空内容,倡导所谓“纯形式”、“炫形式”和“玩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在当代形式研究取得新成果的语境中,重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新关系。
(四)文学的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关系
文学是既具有思性,又具有诗性的;是既具有思想,又具有情感的。在文学艺术中,无诗性的思性和无思性的诗性、无情感的思想和无思想的情感,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别林斯基和普列汉诺夫都主张文学中的思想和感情的融合和统一。基于文学中存在着的思性或思想,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基于文学中存在着的诗性和感情,对文学进行诗学研究,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因此,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和对文学进行诗学研究都应当得到同样的尊重。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对提高文学的思想性、说服力、亲和力、感染力和艺术魅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当代的西方文论和诗学,附着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带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如福柯的“知识权力说”、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的凸显文本“权力结构”的“文化政治学”、詹姆逊对文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强调、伊格尔顿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都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富有浓郁的意识形态性质,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政治化的诗学理论。我们过去比较轻视对文学的诗学研究,以致造成作品的冷漠感和概念化的倾向。
现在,当代中国和西方已经开始形成诗学研究的热潮。诚然,这种趋向带有明显的反拨传统的反映论和现实主义的意味。实际上,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和对文学的科学研究都是必要的。不脱离文学的诗性和感情,侧重于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或尊重文学的思性和思想,对文学进行诗学研究,都是应当得到支持和鼓励的。用文学的思性和思想去文学的诗性和感情,或用文学的诗性和感情去文学的思性和思想;用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去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或用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去对文学的科学研究都是不妥当的。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较重视对文学的科学研究,但对文学的诗学研究也应当得到同样的重视。我们应当维护两者的和谐,使两者互补共进,竞相发展,把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和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有机统一起来。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可以充分体现文学的科学精神,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可以充分体现文学的人文精神。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实质上是突出表现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
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如表现为自然基础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而是属于人文哲学、人的精神哲学和部分语言哲学的范畴。尽管人文哲学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的思想内涵还是一个尚待解析的问题,但其基本的精神意向应当是追求公平、正义和真理,揭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那种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社会理性和价值诉求。与这种人文哲学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相联系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坚持真理、公平和正义的民主自由精神,与时代相协调的和谐精神,与历史发展规律相适应的人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为强烈的奋发进取的变革精神。
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既悖立又互补,两者相辅相成,竞相发展。任何用科学精神反对人文精神或以人文精神抑制科学精神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明智的学者们把两者比喻为孪生兄弟、姊妹花、双翼鸟、并蒂莲,把科学精神比喻为发动机,把人文精神比喻为方向盘。现代学者应当让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花绽放得更加丰富多彩,万紫千红。
综上而论,我们应当巩固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强项,吸纳西方现当代文论的优势,以补充、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那些空疏、模糊、弱势和缺失的部分,使其发生结构性和新质性的变革。我们应当把握上述两大学理中所蕴含的那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思想文化资源,通过两者的富有成效的对话,重构和发展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二、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基本特性
西方现当代文论有魅力,也有局限。而这种魅力与局限又往往是互为一体,杂然并存的。从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总体精神中,可以概括出一些基本特性。
(一)高度的内向化和自我化
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的人生哲学表达了处于异化状态下的人生体验。这种描述是高度内向化和自我化的。他们对所处历史条件下的人生境遇和人生感受,如“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人即是地狱”,人们感到孤独、烦恼、操劳、畏惧、迷惘、困惑、恶心、沉沦,乃至悲观失望,这些人生体验是十分真挚痛切的。这些心理症候实际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所酿成的心理创伤。
一些存在主义者好比精神病态的心理医生,他们对这些精神病态心理的体验和描述,颇能为处于生存逆境中命运多舛的人们感同身受。一些存在主义者觉察到世界的非人化的陌生和冷漠,提出使自身成为“此在”或“亲在”的祈盼。他们以高度内向化的自我意志和主观欲望作为“先于本质”的“自我存在”,一切从自我出发,提出一套“个人自由”、“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拯救自我”的方案,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可能实现的主观幻想。但他们为了追求个体自由,欲想摆脱心理痛苦的愿望,对启发文艺真切地表现人的生态和心态,重视文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处理好文艺中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都是颇有助益的。
同时要看到,这种封闭性十足、排他性极强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冷漠现实,贬抑群体,脱离大众,对以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确立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二)极度的语言崇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西方现当代文论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取得了深层次、全方位的进展。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这些语言理论的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
19世纪中叶后,语言哲学崛起,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成为一种有主导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想。西方现当代文论家多半都是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的书斋学者和擅长语言研究的专家里手。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具有变革意识的左翼人文知识分子,想通过文本语言和语言文本的研究介入社会现实,以引发社会变革,但多半都停留在语言层面。有的语言学家极端地夸大了语言的作用,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不是人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人。这种表述显然是把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关系搞颠倒了。从第一性的意义上说,是人塑造语言;只有在第二性的意义上才能确认和肯定语言的反作用,即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学语境中,人也要接受语言的陶冶和塑造。还有的学者主张采用语言的阐释学革命,即通过发动语言结构变革去推动和实现社会结构变革。语言朝人文主义的转向被称为语言阐释学的“哥白尼革命”,这种意图是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语言幻想。
首先,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把人隐匿和遮蔽在孤立自足的封闭的语言结构中。一些解构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主张打破僵硬的语言结构,倡导“冲破语言的牢笼”是有道理的。诚然,还有的语言学家意识到语言功能的局限性。如从逻辑实证主义者转为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并不承认语言是外部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又曾经追求语言与对象的同构性,后来又强调语言按照人的约定俗成的规则运作的游戏性,从而夸大了语言的相对性和随意性。可能是由于维特根斯坦懦弱的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态度,他觉察到因主体和对象双方都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差异性和流变性,语言不可能非常清晰、准确地说明和解释事物,往往陷入无能为力和捉襟见肘的困境。面对语言功能的软弱无力,对那些特别陌生的神秘的事物,主张只能“保持沉默”。尽管如此,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把语言从客观对象的对应物转换为对象的主体性构成符号,变成表现人的生存方式和主观意向的工具,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向度、新的内容和新的视域。承接和吸纳这些新的语言观念,对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语言学,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权力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由于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的叙述学理论艰深晦涩、诡秘玄奥,往往陶醉于无法使常人意会的语言游戏。语言学家们应当考虑运用简明易懂的表达方式,以便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只有通过西方语言理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真正实现西方语言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才能真正化到大众的心里,融入普通作家和评论家的实践中。语言革命或许在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心理,发出精神呼吁,调动世俗舆论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认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绝对的语言文本主义,想通过解构和重塑语言文本来解构和重塑历史,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这种愿望大体上相当于“词句革命论”的奢望,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词句革命论”时尖锐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
语言批判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正确理解和评价语言变革的作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三)沉迷于审美学幻想
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西方现当代的文论家和美学家都想把审美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倡导审美,对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是颇有助益的。审美是令人感到温暖和慰藉的精神灵丹。对人的心灵世界具有安抚、滋润、补偿、调解、激荡、救赎的作用。有贴近现实的审美理论,也有耽于幻想的审美理论。总的感觉是,西方现当代的文论和美学与现实生活大有隔膜,多半痴迷和沉溺于审美幻想。
如果说,席勒的《美育书简》还表现出通过审美教育改造和培育人生的美和美的人生的现实感,那么到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到各式各样的“审美乌托邦”、“审美救赎”,再到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都带有浓郁的幻想色彩。“白日梦”中的人生故事可能非常美丽迷人,但醒来后,穷苦的人们仍然要在痛苦和灾难中煎熬;“乌托邦”是美的,但这种“美”毕竟是“乌托邦”的;从根本上说,“审美”对人是无法实现“救赎”功能的;没有巨额的金钱和财富,想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诗意地栖居”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所追求的本来是荷尔德林所倡导的“诗意地栖居”也存在着虚假和伪善的一面。令人惊异和痛惜的是,为了充当法西斯帝国哲学王,他竟然在法西斯的营垒中“栖居”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审美理想”、“诗意地栖居”是人们憧憬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
笔者主张把具有现实根据、能够通过实践可以实现的审美理想和没有现实根据、不能通过实践实现的审美幻想加以区分,使审美理想多一点实际,少一点空洞的幻想。让现实更理想些,让理想更现实些,不要过于痴迷和崇拜审美幻想。从根本上说,纯审美理论是无助于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恩格斯曾经批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倍克的一些“飘浮在云雾中的”诗,只歌颂“朦胧的幻想”,并嘲讽“他的诗歌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止血用的三包沸腾散’”。
(四)非理性主义倾向
非理性主义是现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特征和思想灵魂。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贯穿于人文、主体、心理、生理、审美、内部规律、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之中。非理性主义无疑是具有两面性的。非理性主义在人文、主体、心理、意识和语言形式符号领域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相当显赫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作为人类的思想文化资源,必须得到尊重、承接和吸取,以丰富和补充传统的学术格局中所空疏和缺失的部分。非理性元素是人类的生理机能和意识思想结构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失去了历史的先进性和合理性的、过时的、僵化的旧理性的反叛、消解和颠覆,对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思想结构和思想体制的冲击和破坏,对旧权威的亵渎和颠覆,对大一统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和搅扰,从这些意义上说,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我们一方面要肯定非理性研究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一切去科学化、非科学化、反科学化的研究理路,应当科学地评价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是非功过。对一切无节制地反对主流、反对中心、反对权咸、反对稳定、反对统一性和整体性,主张平面化、边缘化、碎片化、无深度、去价值的观念,理应采取有鉴别、有选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的理性态度。
一切反对认知理性、道德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论说只能使一个民族陷入被动和愚昧的状态。非理性意识,作为人类思想结构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非理性渗透的纯理性,也不存在脱净理性元素的单纯孤立的非理性。我们在批判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时,不要把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也一并抛弃了;我们在破除旧理性主义时,也要克服和防止把正确的、有价值的理性一股脑扔掉了。这种“弃水泼婴”的幼稚病是昏昧的表现。旧理性过时了,非理性太时兴了,有的学者提出新理性的概念加以回应。这种新理性应当理解和阐释为实践理性。如果新理性只是停留在舆论、语言和幻想层面,会局限、缩小乃至损害它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实践实现了新理性,只有变成现实生活的物化形态的实践理性,才是新理性的理想境界。
(五)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由于不同程度地脱离现实生活、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使西方现当代文论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书斋中的左翼人文知识分子本身并没有力量。知识要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力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群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才是有力量的,不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力量的。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对推动建立文艺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拥有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才是有力量的。
从整体上看,西方现当代文论和文学是缺乏力量的。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从表面上看是有力量的。这种哲学亵渎上帝、冒犯权威、反叛传统。这种思想的表述方式如狂飙烈火,似有摧枯拉朽般的磅礴气势。尼采以批判家的雄伟,傲视一切。但由于全然拒斥理性,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显得底气不足,似有虚脱和内荏之憾。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对遮蔽社会问题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压抑人的、表现出某些悲剧元素和负面作用的“启蒙理性”的批判,对导致人的异化、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依附资本意志、被文化工业和商业社会所同化、一定程度上被主流意识蒙蔽、误导和改塑的大众意识、实际上带有“反文化”性质的“文化批判”,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化批判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批判企图从文化层面介入政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批判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对阐释意识形态、工业理性、文化生产如何按照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但这种文化批判理论也是有局限的。它只敏锐地看到了工具理性的非人性的一面,如可能造成对人的欲望、个性、灵韵、浪漫情怀、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的压抑,但并没有论述工具理性肯定人,如提高人的智慧、技能和力量,健全自身、征服和善待自然、捍卫真理和维护正义的一面。存在主义比较关注“实践”的功能,表现出改变人的生态的意向,但忽视群体的力量,这种学说所张扬的孤独的悲观绝望的个体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
由于受到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侵害,人们一度变得怯懦了。反映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缺乏力量的,如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描写人在社会重压下变成了大甲虫那样的软体动物,有的作品表现处于异化状态下的人由于承受痛苦和灾难的折磨心灵上受到重创所造成的病态和畸形。这些荒诞的和处于异化状态下的“单面的”或“偏型的”弱势的小人物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却是没有刚气和血性的。现代派的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在国家机器、战争机器、工业机器和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辗压下,人生步履维艰,命运坎坷不幸。他们本身十分软弱,卡夫卡被他的研究者们称为“弱的天才”,绝不可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理念和作品。
我们有时只能在一些科幻影视作品中看到少许孔武有力的超常的巨人形象。即便是那些带有批判意念的理念和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多半也都停留在舆论、幻想、语言层面,或迷信于道德说教、精神呼吁、审美救赎,甚至新感性革命、文化批判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坐而论道”或“纸上谈兵”的性质,一切精神批判都无法超越和取代实践批判,只能靠塑造“新人形象”,培育出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通过变革现状的物质批判去加以解决。因为只有“新人形象”才能从正面充分体现出全新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才能作为“有实践力量的人”变革现实,改变旧环境,创造新世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只有服务并推动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才是有力量的。
三、对话的思维方式
学术思想的对话实质上也是思维方式的对话。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作为客观对象的对应物,需要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切合客观对象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
以新人本主义为主潮的西方现当代文论,都随心所欲地夸大主体心理、精神和意志的作用,包括海德格尔和萨特宣扬的“存在论”,都带有浓郁的主观成分。一些本来很有价值的思想,都这样那样地脱离了客观世界,消解和遮蔽与现实生活的深层关联。对这些带有主观随意性的文学模式、理念、思想和学说理应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析,通过对话和改制,将其置放在坚实的客观世界的基础之上,赋予这些文论思想以可靠的现实性生活的根基和源泉,从而加强和提升这些文论思想的科学性。
对西方现当代文论中的一些所谓“深刻的片面的真理”应当进行辩证的解析。西方的文论史上,一种文艺理念崛起后,不久便被另一种文艺理念所取代,像走马灯那样,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三五年。一点论、片面性、绝对化、走极端、具有浓厚的“自恋情结”和强烈的排他性。
同时或交替地出现两种不可兼容、相互对立的观点。如客体性和主体性相互排斥,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彼此消解,有的宣扬“历史终结论”,有的则主张“人的终结论”。有人强调语言的可通约性,有人则认为语言具有不可通约性。所谓物极必反,一种理念讲过头了,又要回过头来重新言说,以至于不断出现学术研究的轮回现象和钟摆现象。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现当代文论家,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西马文论者,由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要的驱动,又峰回路转,明显地表现出从他们所心仪的人文主体性学理向历史客体性学理回归的走向和趋势。
西方现当代文论,无论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具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不少消解社会理性、追求生理欲望、玩弄语言游戏、炫演“娱乐至死”的精神意向,都不同程度地陷入非理性主义的偏执。因此,运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对各种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进行鉴别和解析,在肯定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的同时,创造富有时代精神和实践精神的新理性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我们应当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改制和整合西方文论。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全局性和总体性的理论创新,必须对西方现当代文论进行重组和整合。文学艺术和任何事物一样,实质上都是一个包括多层面各种复杂元素的有机集合体,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跨学科的全景式整体性探索和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我们注意到,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努力改变迷信“深刻的片面的真理”的局限性。美国哲学家奎因力倡“整体主义”的学术研究。科学史家库恩主张打破学科壁垒,提出一种“范式理论”,强调对学科进行“系统结构研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社会知识学的“强纲领”,特别是一些人类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许多论述,都有意识地对文学进行各种形态的跨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表现出西方现当代文论从局部的微观分析研究追求向全面性、总体性的宏观综合研究转型的发展势头。
文艺学既然是科学,便应当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平等的、有选择的学术对话,梳理和整合各种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文艺理论资源。对待人类的一切思想文化遗产和理论资源,既要有开放、包容、拿来的心态,同时又要有鉴别、批判、改造的精神。既要尊重和吸纳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有益的学术成果,又要破除对西方现当代文论的盲目迷信和极端崇拜。
在文化交流、交锋和交融中,我们应当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取长补短,优化组合的原则,经过批判继承,把西方现当代文论中那些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融入和重构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
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那样的胸襟、智慧、胆识和勇气,像对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样来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学术成果。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黑格尔,而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了辩证法,抛弃了唯心主义;同样,马克思也没有完全否定费尔巴哈,而是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了唯物主义,抛弃了唯物主义机械性,从而开创了崭新的哲学体系和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具有分析、鉴别、整合、改制、重塑人类的一切文化思想资源的卓越能力。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待一切有科学价值的文化思想理论资源,重构、创造和发展当代形态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参考文献: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3][4][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