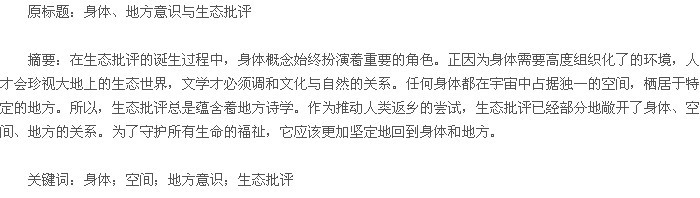
在西方生态批评兴起的过程中,地方意识始终是一种建设性因素。作为“偿还人对自然债务的尝试”,萌芽期的生态批评就关注荒野、处女地、河流、山脉、沙漠、边疆、城市。到了较成熟阶段,它的代表性人物力图使地方(place)成为新的批评范畴。进入21世纪以后,地方已升格为其“不可或缺”的概念。当生态批评家们如此演绎地方概念时,另一个范畴不时闪现,这就是身体(body)。它犹如幽灵出没于相关文本中,驱使人们重视所有可供有机体栖居的地方。虽然身体概念的重要性尚未获得生态批评家的普遍承认,但以下事实却确凿无疑:如果人没有物质性的身体,那么,他就无需依赖生态体系,不必非得珍视大地上的世界。只有当人肯定身体性存在时,生态体系(包括特殊的地方)的意义才能获得显现的机缘。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揭示身体、地方、生态概念的内在关联。
一、身体意义与地方意识的共同凸显:生态批评诞生的逻辑理路
从古希腊开始,柏拉图就率先将文学定义为“对人类行动的模仿”。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演绎,这个定义在西方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很少有批评家对此提出异议。然而,究竟是谁在行动?是灵魂,还是身体?在西方人提出的已有答案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显然具有代表性:“……灵魂由于属性随附而作运动,在其所寓的躯体之内,虽此躯体之运动实有赖灵魂为之做主,但说灵魂之为运动的命意,必限于躯体之内;别于这一命意之外,而说灵魂能在空间运动,这就绝无可能”。在与身体结合以后,灵魂已经“寓于内”,无法直接参与外部的空间运动(spatial movement),只能以指挥身体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欲。与“寓于内”的灵魂不同,身体总已经“裸于外”,既占据空间,又在空间中延展;被他物所推动,也能推动他物。它至少是外部行动的直接承担者,模仿行动意味着模仿身体。
在美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米克(Joseph W.Meeker)于行文之初就提到了上述定义。他对其基本前设并无异议,只是强调自己更重视喜剧性的模仿模式,因为后者具有生态学意味。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所有机体(organism)都是活动的承担者,文学应该模仿广义的行动(如animal behavior)。主角是机体,场所是整个生态体系。尽管米克未在此文中提及身体,但他对机体的重视却推动了身体的出场:落实到动物层面,机体已经发展为高度组织化了的身体,重视机体意味着重视身体和环绕它的世界。作为研究机体“如何在家中生存的科学”,生态学诞生之初就反对身心二分法,其创始人海克尔(Ernst Haeckel)曾明确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灵魂,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我把心理学看成是自然科 学和 生理 性的一 个分支。……所有灵魂生活的现象,毫无例外地都和躯体的生命实体中的、也就原生质中的物质过程分不开的”。如果灵魂不过是生理性活动的结果,那么,人就只能是思想的身体。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我整个地是身体,再无其他;灵魂不过是身体某一部分的名称”。
从“人是身体”这个命题出发,我们最终会抵达这样的结论:人与其他生命都是机体(身体是机体的一种),生态世界乃是机体结缘而成的共同体;机体需要栖居于某处,总已经把空间(space)改造为地方(place),组建属于自己的家;珍视生命意味着尊重机体在家中居住的权利。由此可见,在重身理念和生态思想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关联:如果生命就其本性而言是非物质性的灵魂,那么,人就无需珍视机体及其栖居之所,相反,摧毁大地上的生态体系很有可能是帮助它们转世的善行。柏拉图曾把从事哲学定义为“练习死亡”(灵魂演绎告别身体和大地的可能路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其专着《生态批评》中,杰拉德(Greg Garrard)也揭示了“泛灵论的困境”(thetrouble with animism):由于视动物为不死的灵魂,印第安人相信毁灭水牛的肉身并不会使其数量减少,因而会较大规模地猎杀它们;有时,为了防止逃走的动物暴露自己现在的行踪,他们会杀死所有可以控制的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尊敬首要地献给动物的灵性主宰(spiritual master)而非机体本身。要真正珍视有机生命,人就必须回到自己所是的身体。与传说中的灵魂不同,身体依赖大地上的生命支撑体系。后者为身体提供了诞生的机缘,养育它,为之提供长眠之所。没有大地上的生态体系,就没有身体。身体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生态世界的恩典。当他/她思想时,生态世界也在默默地提供营养和其他必要的条件。
在《从 超 越 到 废 弃》一 文 中,弗 洛 姆 (HaroldFromm)曾以反讽的口气表述自己重视身体-生态的立场:“思想可能没有重量,不占据空间,但它只能作为意识之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一部分存在,而后者离不开食物、空气、水”。
如果地球上的生命系统停止运转,大脑就无法思想,所有灵魂的故事都会终结,因此,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人太看重身体,相反,它植根于灵魂的神话中:精神实体可以不吃、不喝、不呼吸空气,却可以支配大地上的一切,仿佛意志的发动机(theengine of will)就可以孕育万有。这是一种忘本行为:人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的根扎在大地上,身体则似乎成了可以废弃的附属物。于是,致命的威胁出现了:养育人类的环境可能停止养育。
为了不再“自断其根”,我们就必须回到自己的生物学存在———吃、喝、思想、行动的身体,明白自己的根只能扎在大地上。对“根”(root)的承认必然牵连出地方意识:“根”总已经“扎”在特定的生态体系中。身体是永远的此在(Dasein),注定属于特定的境遇(situation)。身体的这种境遇性(situatedness)使人不断将自己所到之处建设为故乡,把空间“转变为地方”———空间广袤、中立、淡漠,地方则“能够被见到、被听到、被闻到、被想象、被爱、被恨、被敬畏”。如此被定义的地方是家,是身体被供养的生态体系。人在其中生长、栖居、长眠。它可能呈现为赏心悦目的风景,但仅仅从审美角度肯定地方显然失之肤浅。正因为如此,部 分 生 态 批 评 家 反 思 风 景 美 学 (landscapeaesthetics),倡导内在关联意识(consciousness ofinter-relatedness):在生态体系中,我们不是到此一游的观光者,相反,人置身于其中,被绵延数亿年的有机体系列所孕育和供养;它是家,是栖居之所;作为家中的成员,居住者属于特定的地方,是“地方 的 一 部 分,正 如 鱼 之 于 水”(Neil Ever-nden)。归根结底,地方意识是一种在家意识。生态之家里不仅居住着人,还存在无数其他生命。为了与家庭成员的复杂性相称,文学批评应该升华为协调所有机体关系的家事裁决(housejudge)。在论文《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中,霍瓦斯(William Howarth)曾如是说:“生态批评这个词所包含的生态学含义比人们通常所了解得更多,除非他们知道生态学在历史上曾经突破了怎样的铜墙铁壁。
Eco和Critic来自希腊文Oikos和Kritis。在联起来使用时,它们意指‘家事裁决’(house judge),这可能令形形色色的户外写作者吃惊”。具体来说,从事生态批评意味着:一个人从赞美自然的角度出发,审度写作———描绘文化对自然影响的写作———的功绩和缺点,叱责掠夺自然者,通过政治行动修正他们对自然的伤害。守护生态世界的基本秩序,让其成员各安其位,这是家事裁决的基本原则。它从每个机体出发,展开为地方性的话语实践,力图使边沿(border)、分界线(boundaries)、先锋(frontiers)、地平线(horizon)、边缘(margin)等隐喻具有生态学上的所指。随着这种家事裁决的兴起,“生物区域”(bioregion)、地方依附、具身化(embodiment)等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生态批评文本中。
从根本上说,对身体的遗忘和生态危机互为因果:遗忘身体就必然遗忘养育有机物的生态体系,反之亦然。生态批评只能诞生于珍视身体、栖居地、空间的语境中。它对于上述三者的关系认识得越充分,就会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来处和归途。
二、对身心二分法的超越与地方性的显现:生态批评发展的一个内在理路
在第六个沉思中,笛卡尔(Descartes)曾强调:身体“具有广延性而不思想”,“我”则是思想而无广延之物,因而绝对有别于前者。思想着的东西才是“我”,“我”可以离开身体而存在;在与“我”结合时,身体总是被它领导、推动、支撑。为了解释“我”支配身体的具体机制,他专门撰写了论文《灵魂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soul),假设灵魂通过松果腺对身体施加影响:“身体机器被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所构造,以使松果腺能被灵魂以各式 各 样 的 方 式 推 动,并 将 环 绕 它 的 精 气(spirits)推向心脏的孔隙,后者再将之传到筋肉神经,使肌肉神经推动四肢”。思想实体支配广延性存在,灵魂统摄、推动、利用肉身。由于自然属于广延性存在的集合,因此,它也由于贬抑身体的逻辑而降格。由此可见,压迫身体直接意味着控制非人自然,以灵魂的名义进行空间扩张。
于是,地方成为灵魂施威的场所,而非我们居住于其中的家园。只要身体的意义不被承认,自然、地方、生态体系的价值就必然被继续忽略。要恢复生态世 界 的 本 有 秩 序,就 必 须 解 构 身 心 二 元论。只有超越了灵魂宰制身体的神话,身体和环绕身体的存在(空间、地方、自然)才能显现出自己本有的价值和尊严。
毫无疑问,生态批评诞生于超越二分法的行动中。自米克撰写《喜剧模式》起,它就指责西方盛行的二元论“割裂身心、分隔男女、将人从自然中强行剥离出来”。在为《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所写的序言中,劳伦斯·库柏(laurence Coupe)强调:“超越二元论,超越对精神和物质、主体与客体、思想者与物的区别,才有‘认识’自然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二元论显现为一系列等级图式(如文化/自然、精神/身体、男人/女人、理性/情绪、文明/原始),但它却可以最终归纳为两个系列:
1.身体和类似身体的事物:自然(广延性的物质存在)、女人(比男人更加肉身化)、情绪(更多地受制于肉身的生理因素)、原始(属于未经文明化的肉身,如“落后种族”)。
2.接近精神的存在:文化(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男人(比女人擅长心智操作)、理性(高级的心智活动)、文明(心智高度发展的结果)。
凡被判定为接近身体者(自然、女人、原始部族、动物),就会被低估、贬抑、排斥、压迫。正因为洞察到了这个逻辑,《后殖民生态批评》(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一 书 的 作 者 格 莱 翰 · 胡 根(Graham Huggan)和海伦·提芬(Helen Tiffin)才指出:通过分裂身心,西方人发明了物种主义(speciessist)、种族主义(racist)、性别偏见(gen-der bias)。也就是说,身心二分法不是诸多二分法中的一种,而是其原型。保留它就不可能真正超越次生的二分法。譬如,由于在生殖中的角色(孕育后代),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加肉身化,更接近自然”。再如,少数部族和劳动者也倾向于直接依赖身体,属于身心二分法中低级的一方。于是,女性、自然、身体被界定为待征服的空间性存在。只要身体的意义依旧被遮蔽,自然、女性、动物、少数部族和属于他们的地方体系就无法真正受到守护。即使在梭罗等人的自然写作中,这个逻辑依然在起作用。“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将身体当做纯洁与危险斗争的场所”,莱格勒(Gretcher Legler)指出,“他强调要与风景建立关系,一个人就必须超越他的身体。他的写作反映了他对自然混乱的不屑,对自己身体需求和欲望———包括饥饿、渴、疲劳、孤独———的厌恶。
‘自然是难以克服的’,在《最高法则》中他写道,‘但她必须被克服’”。在讲述自然的故事时,梭罗建构了“超越物质性的未被肉身化的身体”,因而实际上“以隐身的方式工作”。由于身体退到了幕后,属于物质系列的存在(女性、自然、地方性生态体系)就难以真正获得珍视。恰如生态批评家杰拉德指出的那样,梭罗并不认同身体性存在,而是对其心存畏惧:“我敬畏我的身体,这个与我联结在一起的物质变得如此陌生。我不害怕精灵和鬼怪,因为我是它们之一。或许我的身体怕它们。我所 怕 的 那 些 身 体,我 颤 抖 着 与 它 们 相遇”。他将自己等同于精灵和鬼怪等精神性存在,并因此对身体和所有物质性存在心存畏惧。
在他的言辞中,分裂身心的二元论逻辑依然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莱格勒(Gretcher Legler)等人对他的批评证据确凿:身心二分法妨碍了梭罗进一步走向生态学场域。事实上,正是分裂身心的二元论逻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生活允许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脱离自然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的乡土联系。身体被看作一架生物机器,自然也被看作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 观 念 则 成 了 世 界 主 义 者 眼 中 未 开 化 之物”。要克服梭罗所代表的局限,就必须彻底克服身心二分法。从根本上讲,生态学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对身心二分法的克服:从海克尔开始,人就被领受为会思想的机体,一元论便开始显示其强大的阐释力。事实上,当生态批评家强调机体概念时,身心二元论就会暴露其“专横和可疑的逻辑”:经过漫长的进化,部分机体已经具有感觉、思想、行动的能力,精神不过是肉身的活动[8]119。作为生命的唯一主体,肉身只能生存于“家”中,居住在特定的地方,建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身体取代“我思”之后,空间、地方、世界的意义也会随之敞开:“‘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名言。这是个让我感到非常不适的程式(formula)。它意味着 无 思 想 的 生 命 属 于 第 二 等 级。 相 对 于 思(thinking),我更主张完整性(fullness)、具身化(embodiedness)、存 在 感 (sensation of be-ing)———不是对你自己作为幽灵般的推理机器的意识,相反,是这样的体验———作为拥有手足的身体在空间中伸展,活在世界中”。要克服灵魂的神话,就必须“让身体显现出来”。当身体重新显现出来以后,人们就有可能克服此生的二分法,回到身体栖居的生物学空间(bioregion)。
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之前,人都没有在身体场域中赢得胜利的任何严肃的可能性”。
事实上,身体的厄运在20世纪仍未终结:受制于信仰、传统、思维惯性形成的综合力量,人们仍倾向于忽略身体的主体性。在业已成为文字的生态批评中,身体也常常以隐蔽的方式起作用,几个重要的相关文集都未于索引中提及它。于是,身体、地方、生态之间的关联时隐时现。
三、回到身体和地方:生态批评的未来使命
如果精神不过是身体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逐渐摒弃“与灵魂相关的观念群”,更加坚定地回到身体。身体是实在者,任何实在者都在宇宙中占据着独一的位置,都是永远的此在(Da-sein)。作为机体,他始终隶属于特定的生态体系,注定“在世界中”而非像灵魂那样随时准备远走高飞。对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说得更加清楚明白:“身体在一个世界里出生、成长和死亡。如果自我不是没有肉体,它就不会没有世界,而它的世界总是由无生命的东西和活的东西构成”。身体与地方的关系绝非偶然的联结,相反,这些关系就是他自身,就是他的个性、身份、“本质”,因此,珍视身体意味着关心他生长和栖居的地方。对此,着名生态主义理论家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说得非常清楚:“所谓‘身体’,我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所谓‘自然’,我指的不是科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地方’,我指的是生物区域,是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由身体出发,我们必然走向地方哲学和生态文化。只有回到身体和地方,生态批评才能真正显现出其生态性。
任何机体都需要自己的家,肉身也不例外。
随着身体意识的增殖,栖居也成为重要的范畴。
在论文《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中,霍瓦斯(Wil-liam Howarth)强调“生态学研究物种与其栖居地(habitats)的关系”。栖居地既展开为小的生物区域(bioregion),又属于整个生态世界:“环境思想中存在两种主要的‘居住’理念,一个是地方性的,一个是国际性的。我们‘全球化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这个口号同时显示了生态思想与它对现实政治的实际影响的对比,也展示了调和两种观念的企图”。为了阐释“地方哲学”,生态批评家杰拉德提到了“深生态学的先驱”海德格尔。事实上,海德格尔的栖居思想已经暗含了一种身体哲学:“你和我存在的路径,我们人类在大地上的方式,就是居住。成为人意味着成为大地上的短暂者。这意味着居住。当人居住时,他才存在,这正是古词Buan所说的意思。它还同时意味着珍惜和保护,留存和关心,尤其是指耕种土地,栽培葡萄”。这个栖居在大地上的有死者只能是身体。倘若人不是需要吃、喝、呼吸的身体,他就没有必要非得栖居于大地上,更无须“耕种土地,种植葡萄”。我们人类之所以注定“住在大地上”,是因为后者是身体的家园。身体是有死者,有死者才需要栖居于大地上。终有一死的肉身生性脆弱,随时需要遮护之所。在寻找和建造遮护之所的过程中,地方显现出来:“此类事物的制造就是筑居。它的本性在于与这些事物的本性契合。它们是调配空间的所在。通过建造这样的所在,建筑成为空间的建立和结合,把作为spati-um和extension的空间带入到建筑的物之结构中”。不过,海德格尔所说的地方性还未完全克服 形 而 上 学 的 遗 痕:每 个 建 筑 都 是 四 元(earth,sky,mortals,divinities)的统一,建筑则是四元的显现之所。于是,他所指的地方最终普遍化和抽象化了,不是有机体的家园,而是四元游戏的场域。它们不是具体的地方,而是所谓的地方本身。产生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海德格尔对待身体的暧昧态度:他所说的栖居均为身体的活动,但后者在其文本中却始终处于隐蔽状态;在提及神性时,身体则被挤压到无意识的疆域———假如神不死,那么,它就绝不会是肉身,因此,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岂不仍要君临于身体和地方之上?
我们莫非还要服从来自天空的神秘召唤?对于这些问题,杰拉德进行了初步的反思,认识到了其中的部分症结:“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居住绝不仅仅意味着生活在某处,而是人向存在开放,被存在征用”。设置大写的存在(Being),强调它征用人的合法性,最终使海德格尔背离了地方理念。
这乃 是 海 德 格 尔 成 为 纳 粹 主 义 者 的 深 层 缘由。值得警惕的是,此类迷途情节随时会在生态批评界重演:“存在地方性的生态体系,但所有地方性的生态体系都从属于全球生态体系,属于一个无物可以被排除在外的体系。这使环境主义成为后殖民多元主义和‘全球化’关系的关键性的实验场。在某些方面,环境主义无疑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敌意和对多元主义、反讽、小叙事的强调相冲突”。一旦回到脱离具体地方性的宏大叙事,生态批评家就难以避免类似错误。
要走出海德格尔式的迷途,就必须更坚定地回到身体。离开了身体的本体论和生物学特征,地方概念就无法真正为自己奠基,生态世界便难以展露其本真面相。
人是身体。身体不能随便栖居于某个地方,只能生活在特定的生态体系中:“只有在适合它的家中,当且仅当与环绕和养育它的所有生物联合起来时,有机体才有意义和价值”。这些特定的地方就是家园,生态批评家所说的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归根结底就 是 地 方 诗 学(the poetics of Place)。珍惜家园就是珍惜它养育有机体的能力,保护生物就是保护他们所是的机体,关爱他们栖居的地方。为了所有生命的福祉,未来的生态批评应该更坚定地敞开身体(机体)与地方的本 体论关系,推动人类踏上返乡之旅。
参考文献:
[1]Glotfelty,C.,Fromm,H.The Ecocriticism Read-er[M].Athens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Georgia Press,1996.
[2]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M].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与其他[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M].解雅乔,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5]Nietzsche.Thus Spake Zarathustra[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 limited,1997.
[6]Garrard,G.Ecocriticism[M].London &NewYork:Routledge,2012.
[7]Descartes.Key Philosophical Writin s g[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7.
[8]Coupe,L.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2000.
[9]Huggah,G.,Tiffin,H.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10]Kerridge,R.,Sammells,N.Writing the Envi-ronment: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M].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 Ltd,1995.
[11]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