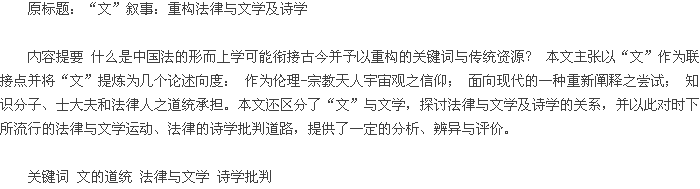
一、人文学与法律: 法的形而上学之另一种视角?
法律与文学,究竟有没有解决一个法理学的内部问题---即法之形而上学( 意识形态的) 及中国时代的道统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人文主义①的思想进路。而当代着名的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先生,曾将人文理解为文②,本文以此作为思想基础,来阐发中国面对现代法治文明和本然传统的整合道路上,如何对待和处理传统形而上学道统的问题。
从批判法学或批判理论③角度看法律,现代的形式法④在多个向度上具有中西语境之危机。从中国语境看,形式法,在道德层面和价值层面并不具有传统礼法的一种道的正当性,而只是停留在形式理性、技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弱的道德上---这无疑可以从中国“文”的叙事予以审查之。
从西方语境观之,也有以法律与文学这样的进路,来看待法的精神世界与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⑤当然,国内也有研究法律与文学的学者,从跨学科之角度以及从反对现代市场和资本逻辑下的形式化法之批判角度,提出了对于现代形式化法的激进批判。⑥而本文则希冀从文、文学之中西进路而予以批判意义上的法治危机之审查---对这样两种进路之别,笔者亦会作出区别并交代。而在这种进路下,笔者将区分两种精神源头: 法学与诗学或诗歌与法律和文学之间的不同。最主要的观点是想将中国式的文叙事区别于诗学与文学,而与中国法的形而上学精神构建进行融通与对话。
二、中国传统“文”叙事的现今法则意义
( 一) 文,作为伦理-宗教天人宇宙观之信仰
中国古代对于文和神之间,特别是对于“神”有着非常有意思之理解( 有别于希伯莱圣经传统) .这种神或非神,亦神亦非神的状态,使得中华文化,非常亲缘于佛教,而非基督宗教。
文,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概念,但是它和有神论的神不同。对于文这个叙事,需要先界定“文”.而对于文之含义,文之道,史载可谓汗牛充栋。比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 论语·子罕) ; 又斯文之超越感: “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荀子·天论) ……文与自然、文字和神明,是什么关系? 宋代大儒张载所提出的气论说,非常启发众生---而中国式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理性神之间究竟有无对峙与对话? 或许亦是需要作一判断的。
( 二) 文的重要人格意象是君子或曰士大夫
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并非“世俗”人文主义( “secular”humanism) ; 他提出儒家的“宗教性”---因为若没有对于儒家宗教性( Confucian religiousness) 之理解,我们对于君子的理解就会是空洞浅薄的,就会误解儒家的“政”以及儒家的形而上学会是空无的。而笔者以为,文的载体---表面上看是文章、是书,但真正的还是人格或曰学问或“道”.在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 传统是文人) 也遭受到普适善本体的一种考验和心灵自我主义的探1的人---就担当道义了吗? 我们在圣经里面发现,谦卑粗鄙而没有受到人文教育的耶稣和那些老百姓门徒们,可以占据圣经的精英谱系---这不由让我们对于精致的书法和文教,究竟是否具有善的检验标准和责任的担当能力,产生了由衷怀疑。今天,人们普遍以艺术将这些文教边缘化了,实际上的确,它们最大的敌人和挑战不是科技,而真正是中国之文道遭受到普适主义真与善⑦的最真实之挑战。中国的这些文教作品,看来似乎也无法以普适救赎的气场而发挥往日之功效了。
( 三) “文”: 面向现代的一种重新阐释之尝试
今天的文之“道”---又是什么? 文与普适性之张力是什么? 笔者以为,中国式之文叙事下的正道,有天命观作为观照与验证,所以和普适主义之间---始终葆有一种张力。
本文简要归纳、提炼“文”之含义:
( 1) 文,需要在与礼的关系、节奏中去界定和阐发---即文的时间性与伦理性。
( 2) 文,象征最基本的道德文章或是君子教化。
( 3) 文,代表正统的道德传统和文化传承。
( 4) 文,象征着学习的状态、为人为学之状态。
?上述这样一些章句之例举,表达“文”的繁复但一贯之意象。文,其乃一种中国之“道”之意象。
而这个文,其实真乃是区别于文学的( 中和西的文学) ---有时候,从狭义来看,可以意指中国文学的一些表现( 当将中国文学的某些追求作为道统一部分看时) ; 但从广义看,文,应被阐发为一种中国精神或美感意识、道德规仪和行为的风度。
( 四) 文的道统: 知识分子、士大夫和法律人的路向
而将“文”的传统,理解为知识分子的传统与特点---是否合适? 包括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新儒家杜维明先生的《道·学·政》,都使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语词---但事实上这与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包括萨义德( Edward Said) 等之描述---比如《知识分子论》中对于知识分子之精彩描绘与定性完全之不同。
而文教的提出,乃是国内近年来不断加强之通识教育的一个精神实质。而笔者以为,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乃是有分野的。道与文的分离乃知识分子的一种要求---知识分子的道是一种忠诚于知识系统及其伦理的道,而非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人生道德取向的正道观。当然,在中国,读书人与官阶制度密不可分,专事考据书画的文人,应是作退隐不得志之状态。士,代表着精英主义的理想。
在士,官僚与学者的角色兼有之; 对士阶层来说,文就是道,就是经典典籍与传统。
比如在唐代,礼曾是文之重要准据,若说文是属人的,那么礼就代表天地之正当性,文显而礼乃潜藏之精神,文既特殊又有历史感而礼则是普遍又持续的,文是文学化的而礼是伦理化的。?但 知 识 分 子 之 精 神 实 质 乃 是 独 立 与 批评---更极端地说,知识分子往往会充当永恒的批评者而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都不为过之。
法治不区分君子大人小人,而统一以道德与理性,其似乎并不能在精神上作出某种理想化之建构与向上之指引。士精神---能否成为被专家( Specialist) 所领悟的精神、且成为专家精神之补充? 我们知道: 纯的知识生产者成为今天的专家;而中国古代的教师,却并非知识之生产者,充其量只是传播者( 述而不作) .天地君亲师,师者之地位,似可从亲友之角度相提并论之---此乃从人格风范角度,依然并非是出自于对专家型知识之尊重而言的。王国维先生对于知识分子和学术是什么认识得很清楚---他尝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来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笔者以为,孔夫子《论语》所讲到的士大夫人格,似可以补充近代专业人士灵魂人格叙事匮乏之问题。而士之正当合法性,并非若欧洲比如英国式贵族来源于血统或世袭,乃靠读书、写文章、依靠负担士之责任那样一种道义伦理。士的身份共识或通识,来自于“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其实就是中国精英阶层之信仰,也是中国先前等级社会中的民众之理想主义之旨归与信仰。
笔者同时以为,对于传统伦理精神和人生观的孝道,不能作狭义化、西方化和近代化之理解,而要作贯穿传统的天命和命运的理解,作一种形而上学之理解。我们会由此可知,知识分子,必然以反传统反伦理之面目出现---即那些具有极致知识分子精神的知识人---而非各种形式的现代式救世之“士”或现代士大夫。法学者、法学家,尤其是中国的,其实还是以一种士精神在感动昭然于世间。在今天,笔者以为,绝佳之状态,或许会是“知识分子-士大夫-文人”之合一或三位一体之新的精英精神?
真正的诗人,也或许会不经意间充当了立法者之角色。而中国诗人中的顾城和海子,被认为是具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诗精神的。将诗歌纳入法律的某些讨论,也真正从法律人和法律世界的高度( 礼法、法则、宪法) 来理解了海子( 这与一些诗人回忆反思海子不同) .诗人与知识分子是同类---就好比悲剧是诗的王者; 且知识分子与诗之间往往是同质的一种精神。诗人恰是知识分子群中的极致者、献身者、“王者”.王国维先生亦尝认为: “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也,而非一时一地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
诗的革命精神,来自于诗总以求真( 真理) 为自己之精神使命,所以,诗与传统守成与习俗之间,总是一种紧张与敌对之关系---可以说,诗乃最无辜也最激烈反传统之“罪魁”.诗里面其实包含革命的力量。因为诗乃是对于时间之一种质疑和反抗,对于历史和现实之一种质疑与反抗。
而现代性语境中法律人之超验批判: 比如批判经济功利主义的努斯鲍姆之诗性正义观,现代性语境中的法律人( 理性、功利与经济人模式) 之探讨,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观,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语境下之法律人思维,中西、古今之间的法律人对照---这些个论域与命题,都与本文之总体思索路向与情绪如出一类; 或曰之: 诗之忧( 对于形上的追问和对于现代性的批判) 的可能性。
三、法律与文学对话法的诗学批判?
法美学是什么? 吴经熊先生在他的 The Artof Law、舒国滢先生在《在法律的边缘》中,都曾提出过美学和艺术之于法律的意义。
而美学,笔者以为是一种理性哲学,其有别于作为批判传统之诗学---故而笔者以为,法美学有别于法律诗学( 法诗学) .看上去理性的法律与反理性之诗歌,像一个双面人/或曰悖论---难道法律诗学之提出,或本就乃一个悖论?
( 一) 有关法律与文学的内在张力
比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更早的,符合文化和广义“文”意义上的文学的,是法律文化学、法律的文化解释、法律与文化理论,比如梁治平先生的研究风格等,谢晖老师的诗歌创作与民间法关怀,苏力老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研究也是一种现当代社会文化研究,许章润老师之历史文化理路的汉语法学思维等。文学在中国,和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 在中国,文学的意义集中在艺术领域,而不作为政道出现; 而笔者以为,文学隶属于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法律。
而一般理解上的法律与文学思潮,如果一定要严格以狭窄的近代之视角看,乃是起源于美国的一场针对于法经济学之思潮。
国内学者苏力教授最为系统、影响力大地予以引入。而法律与文学研究,主要包涵这样一些向度与内容或曰理解法律与文学作为学科范畴和知识谱系的四种模式或范型---“文学中的法律( in) 、作为文学的法律( as) 、通过文学的法律( through) 、有关文学的法律( of) ”.法律与文学---是否应以主流的波斯纳式的法经济学视角和理性功利主义视角而事实上忽视了努 斯 鲍 姆 ( Martha Nussbaum) 、怀 特 ( J. B.White) 以及其他法学者的更多人文主义宽容背景之研究叙事? 法律与文学本身是具有张力的( 或者某种程度之不兼容) ,它从对于法经济学的批判而来; 正是因为法律与文学的这种张力,使这种方法充满批判的可能力度,比如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批判,再比如对于法律经济学、实用主义的计算思路、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等,法律与文学的视角都构成了一种属于对极观点的对观。
而什么又是诗性正义? 我们知道,努斯鲍姆进一步在确立文学人移情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诗性正义”.她认为,缺乏移情能力的经济人不能具体和同情地对待个人,或者说抹杀了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种思想易于导致模式化的群体印象以及在司法过程中同情和怜悯的缺失,并因此引发群体仇恨以及群体压迫。
而什么是我们今天的哲学? 实用主义的计算,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 正如苏力教授在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之代译序“孪生兄弟不同命运”中,提到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与法律的文学想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才是笔者所要着墨予以阐述之的。国内学者刘星显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理想型之间的对峙,提出文学人及其反经济人之特质。“如果包括圣徒、反社会者、神秘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符合经济人定义的话,那么这个定义就是毫无价值的……”,“令法律人文学者困惑的是,法律经济学者摒弃了在决定社会成本之中的价值因素。除去经济成本的考虑之外,法律经济学家几乎没给价值任何存在的空间,因为价值不可能以严格的量化方式予以计算。由于相关联的价值不能被量化,他们计算的第一步便是用一种假设来达到排除价值的完美状态,在该假设之中每一个人都对满意度有相同的要求。”
苏力教授所引进的对于波斯纳法官一系列思想着述之译介之中---波斯纳其所理解之法律与文学---是不是会内在充满来自法律人之偏见与局限? 比如,法律与文学的共性在于修辞---究竟够不够? 而大力引进波斯纳法律与文学理论的苏力教授其在运用文学工具和视角上也是美国化的现代视角,比如: 苏力教授的《法律与文学: 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分析工具都颇有“西方的眼光”和“西方的思维”.无疑从波斯纳《法律与文学》的精神气质与语式,我们可以读到波斯纳实是以民主社会之基色、基底论调来论证西方的法律与文学的社会现象---其既与诗学不同也与前现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浪漫派不同---这些其本身都是一种从西方中心主义论出发的而在全球化语境下被接受为一个普适学科和知识真理的事物。而苏力教授孜孜不倦地翻译波斯纳的文集,在《法律与文学》中也交代了自己本土语境之例外,即他山之石之叙事---却也依然没有给出一个什么是中国之法律与文学叙事的内容与方针,而可贵的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以西学译介来简单以为要推行这样的法律文化或法律与文学---然而一边批判西方自由民主一边恢复中国文化叙事如果只是停留在建国几十年的政治文明基础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包括文化先天不足的时代原因所导致的人的哲学观和宇宙观的断源性,共同之文化传统、具有神性精神的传统文化之被贬值---若以这样的社会现象出发要产生并谈论法律与文学,会不会都可能是无根之源? 当然,笔者以为,哪怕那些以传统文化为爱好者,亦不一定在智识和学术思考力上必然可以承担反思中西语境之重任。真精神之产生、真反思之产生,是一种对于传统的真正反思与整合的长时段的一种努力---因吾等仍处于全球文化沙漠化的总局之中,对于中国这样现代后发型国家而言,提出批判现代和上启传统的文化批评的声音,更为不易,不为人众、甚至知识分子群与学界、专业圈子所能理解之的。
当然若从波斯纳的美国式民主思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维出发,必然会看到美国式的法律与文学关系之尽头---没有法律与经济学这么管用和盛行。前者没有一个中心的、突出的纲领,实证性和规范性都没有,“虚假的起点、夸张的解释、肤浅的争论、轻率的概括和表面的感悟。”
另也有研究指出了这一点,“……波斯纳始终没有忽视法律与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法律在小说中完全是补助性的,小说主要想说明的并不是法律,因此,必须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小说对人类处境的关怀区分开,他告诫世人: 最好不要将成文法理解为文学作品,而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命令。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正构成了这一运动向外扩展的界限。”
不过苏力教授也提出了自己虽然不是基于传统人文主义、但依然是在将文和文学作技术化处理的思路上肯定文的意义之于法律技艺训练之正面意义: “对于法律家来说,这种能力并不非常重要,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判断和权衡。但是,对于文字的敏感,对于细节之意义的把握,仍然是法律家必备的能力之一。事实上,英美法先例制度中的区分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的就是对细节的把握,对细节之意义的阐明; 至于英美式判决书之写作,更要求对文字的驾驭。至少,具备这种能力不是一件坏事; 中国人说,艺多不压身.……说不定,中国也会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尽管可能还不会形成一个运动.而且,我也正在努力。”
( 二) 法诗学: 法的诗学批判?
法律与文学,如果说是一种晚近的法律后现代的思潮; 那么,法律与诗学---几乎没有被提及过,又意味着什么呢?
法律与诗学( 广义上的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包涵了诗) ,是不是也构成了一组悖论而不能使诗学安置于法叙事之内? 正如法律与革命,作为稳定性的法律和作为反稳定性的革命之间能相容---那么法与诗,能否也成为秩序的一个内在对位性,诗成为法度的一个张力? 它是对于法的颠覆、革命还是精神之浇灌? 而从广义文学的角度看,诗学其实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文学是一种批判的话,那么诗学更是一种极端的背叛---比如悲剧,对于现实和正当性的嘲讽。
法诗学的构成和维度,又有哪些呢? 如果说批判是诗歌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其他的维度,笔者以为可以表现为独立、否定( 比如自我放逐,否定既成的各种利益的世俗理解) 、反对( 激烈的表现为颠覆) 以及建构( 诗歌的立法) .同时,法律与文学和批判法学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广义的批判法学当然必须包含文学( 包括具有文学精神的哲学) 这种最具有批判性和先锋性的工具与进路,而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之美国批判法学之运动和后现代化的反基础和反本质的颠覆正统的思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具有法诗学精神( 即具有批判精神) 的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是一种法律与诗学或法诗学研究。而法诗学---从某种程度上,笔者认为,是可以与批判法学划上等号的,或前瞻性地绕过西方的法律现代性和法治中心论的普适论话语,更深层地观察到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对于民族性之原初思维模式之取消---从而与批判精神一样,分享着一个新的反思的解构,即基于传统或当下的批判建构或曰创造性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