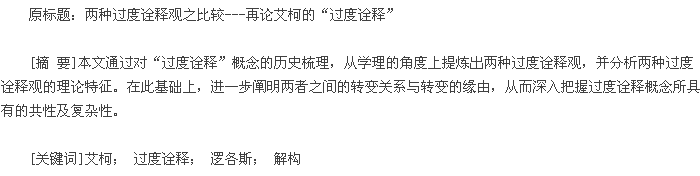
1990 年,安贝托·艾柯主持丹纳讲座,选择“过度诠释”作为演讲主题,旨在在目前有关意义的本质以及诠释之可能性与有限性这个不断深入的国际性大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讨论中,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此后,学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与应用,发表了一系列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对过度诠释的概念缺乏一致的判断,并没能深入把握概念的产生背景与历史渊源,只是在一味地应用艾柯关于过度诠释的看法,使得在过度诠释的研究中常常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如果沿波讨源,对过度诠释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我们就会得知过度诠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其本身的复杂性不足以被一个观点、一个理论掩盖。
一、两种过度诠释观
现有的学术研究资料表明,在1900 年英文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中首次出现了“过度诠释”这个词。作者在文中说: “要使初学者明白即使他把握了梦的全部诠释即具有独创性与内在一致性,并且顾及梦的每一部分,他的工作依然没有结束,这是一件困难的事。
因为同一个梦还有其他的诠释,如过度诠释'.的确,我们不容易有这样的概念,即无数活动的潜意识挣扎着寻求被表达的机会; 而且也不容易体会到梦的运作常常把握着一些能涵盖多种意义的表达,就像神仙故事中的小裁缝一拳打死七个.读者常常倾向于抱怨我在诠释过程中使用了一些不必要的技巧,不过实际的经验将使他们知道得更多。”[1]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诠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读者往往认为自己已经对梦作出了比较好的诠释,而实质上还有其他诠释存在,这些诠释就是过度诠释。可见弗洛伊德的“过度诠释”与艾柯的“过度诠释”完全不同,因为弗洛伊德的用法不含有任何负面的效果。弗洛伊德还把过度诠释的存在与梦自身运作联系在一起。梦作为一种潜在的、含混的表达,混合了大量的无意识幻想,所以它具有了多元意义的可能。读者在面对梦时就不能忽视过度诠释的存在。过度诠释的概念使得弗洛伊德表现了没有什么正确或错误的诠释与现实的概念意义相关,没有一个单一的意义体现在脑中,并且能够被正确地诠释出来。
意义一直都是部分地被实现,只有当考虑潜意识中的内在联系时才给予正确或错误的诠释这样的判断。可见弗洛伊德关于过度诠释的概念使诠释活动成为开放的、动态的,并且与多元意义相关联。
弗洛伊德对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看法实质上是诠释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诠释是多元的,因为诠释的对象---梦本身就是含混的,并没有一个单一意义等待人们给予正确的诠释。弗洛伊德在1912 年写的论文《性无能---情欲生活里最广泛的一种堕落》里说: “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实乃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于文化,没有能力求得全盘的满足,它那不得满足的部分,乃大量升华,缔造文明中最庄严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类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其欲乐,又有什么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转用在其它地方呢? 他会只顾着快乐的满足,而永无进步。”[2]
在这里,弗洛伊德把性欲看作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把人的各种复杂思想、感情和愿望与人的本能欲望联系在了一起。按照他的说法,文学是对人无意识领域所产生的生命冲动的一种补偿,对于文学的诠释自然而然要联系到纷繁复杂的无意识领域。如此,他对于过度诠释的看法便从心理学领域转到文学领域。对文学作品的诠释与对梦的诠释具有一致的心理学基础,因此弗洛伊德关于过度诠释的看法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他利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进行分析,认为作品中体现了无意识领域里普遍存在的杀父恋母情结。虽然这种分析忽视了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但他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所隐藏的大量的无意识幻想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文学艺术产生的心理根源,成功实践了他的过度诠释观念。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诠释并不仅仅停留在把作品中每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弄明白,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发掘,而这种深度发掘需要过度诠释来指引。
由弗洛伊德我们得知,过度诠释这个概念在使用之初并没有负面的效果,而是代表着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深度追求与多元化诠释。对于艾柯的过度诠释,斯特凡·柯里尼( Stefan Collini) 评价道: “艾柯对当代批评思潮的某些极端的观念深表怀疑和忧虑,尤其是受德里达激发、自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美国批评家们所采用的那一套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主要与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的着作有关---对他而言,这种批评方法无异于给予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艾柯认为这是对无限衍义这一观念拙劣而荒谬的挪用。正是因为此,他在讲题中,试图探讨对诠释的范围进行限定的方法,并希望借此能将某些诠释确认为过度诠释。”[3]
二、两种过度诠释观之转变及缘由
从弗洛伊德到艾柯,过度诠释经历的从深度意义向消极意义的转换,与文学诠释领域关于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讨论、后现代思潮中所产生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有着直接的关系。
“诠释”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用于不同的人类活动。文学诠释只是诠释活动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一活动与历史诠释、宗教诠释、法律诠释等人文学科相互交织在一起,既具有自身独特性,又具有普遍性。诠释学自身所包含的多维度特征,使文学诠释活动中长期存在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相持。一元论者认为对于给定的文本只有一个正确的诠释。波尔·范德维德( Pol Vandevelde) 曾经说: “一元论者声称发现作者的创作心理与恢复作者写作时的生活经验,如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所代表的浪漫主义诠释学那样是对文本正确的诠释。……另一种类型的一元论者如赫施( E. D. Hirsch) 就认为文学唯一正确的诠释就是通过作者的文本发现作者的意图。”[4]
多元论者认为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如何对待文本。例如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就曾被作为地志学的重要着作,也被作为精神分析的读本,女性主义批评家则认为该部作品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偏见。这些诠释都与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相关,在自身的理论范围内既实现了对文本的深度剖析,又实现了诠释的多元。在支持多元论的理论家中,伽达默尔的观点尤为突出,他认为“文本的真实意义是由处于历史环境中的诠释者与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文本的意义超越了作者。这是为什么理解不仅仅是复制活动而是生产活动的原因。”[5]“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就是不同的。”[5]
我们的理解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意识不同,我们的意识是植根于历史的,理解活动依赖于构建在历史之上的包括意识在内的视域。对于文本的诠释,诠释者的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出发点,还作为一种可能的实践,被诠释者带入诠释活动中,帮助诠释者回答“文本说了什么”的问题。伽达默尔说诠释是生产性的,意思是诠释行为发生在文本与诠释者的相互对话中,这种对话是有逻辑的对话、有逻辑的问答,诠释的生产性起自这种问答逻辑。但他并没有给这种问答以一定的边界,反而认为这种问答在历史的延续中一直存在下去。同时他也没有给出诠释有效性的标准。正因为缺乏诠释的有效性,他遭致了其他学者的不满,其他学者认为他的诠释理论有滑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个危险,他引用了“传统”这个概念。“文学的所在并不是对某个疏异了的存在的无生气的延续,这种延续是以共时性形态展现在某个以后时代的体验现实中的,文学更是一种精神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因此,它把消失的历史带到了每一个现时之中。”[6]
他的意思是说传统调节着文学诠释,读者的诠释依循了传统就具有合理性,反之则不具有合理性。但他还是忽视了传统作为规范的不恰当性,因为传统本身是可变的、描述性的。如果把客观演变的规律性强加给传统,传统自身就失去了生命力。这样看来,传统也不能解决伽达默尔滑入相对主义的危险。我们依据他的理论便会得出一个结论: 文学诠释向未来无限开放,文学意义没有确定性。在这样的理论影响下,英美文论界与法国文论界都不约而同地废除了作者头上的光环,以作者之死( the death of author) 换来了“解构主义、女性批评、文化研究等理论的涌现,并且声称重新阅读、解构、散播,这些理路术语成为时代风尚,热烈地参与到文学诠释当中。”[7]
在这些理论中,当属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最为盛行,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在哲学上的怀疑论思想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广泛接受。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与命名人,像他的前辈们如尼采( Nie-tzsche) 、海德格尔( Heidegger) 等德国哲学家那样对基本的哲学概念如知识、真理、永恒发出疑问,也如弗洛伊德一样违反传统关于个体意识是一个自身的统一与连贯性的概念。德里达在他的三本书中表达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三本书都出版于 1967 年,《论文字学》( Of Grammatology) 、《声音与现象》( Speech and Phenome-na) 、《书写与差异》( Writing and Difference) .随后的时间里,德里达对三本书中所提到的观点进行重新论述与扩充,并应用于理论实践。我们在这里无法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论述,只能挑选出一些对文学诠释比较有影响的观点。威廉·雷( William Ray) 认为,“德里达的学术研究最终的目标就是解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以及关于假定意义作为一个自我同一的整体。……这样的传统与态度,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8]
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他消解了诸理论赖以存在的各种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 在场与不在场、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理智与情感、本质与现象、语音与文字、中心与边缘等等。意义在这样的消解中无从确定,如德里达所言,“假如意义的意义( 指一般意义上的意义而非意谓功能) 意味着无限的暗示,假如能指向能指的转移是无法界定的,假如它的力量是某种纯粹的暧昧性,这种暧昧性不给所指意义留下任何缓冲和歇息可能而将其纳入它自己的经济学当中使之再次意谓并不断延异,这难道是一种偶然吗?”[9]
意义缺乏有效的限制,无休无止地在能指和所指间游荡,这种反传统的姿态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意义的确定性多么遥不可及; 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不断地对文本进行诠释,确定更多可能的意义。说到底这就是意义的游戏,意义在自我差异中走向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中所说的“嫁接”活动。卡勒认为,“嫁接,它既能说明我们迄至此地讨论的指意活动的过程,又提供了深入德里达本人文字结构的方法”.[10]
这样的解构主义思想在美国文学批评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形成了以耶鲁学派( the Yale school of criti-cism) 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阵营。也有些学者用耶鲁“四人帮”来称呼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四位批评家: 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杰弗里·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 、希利斯·米勒( Hillis Miller)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德里达于 1979 年与四人联手出版《解构与批评》(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一书,使耶鲁学派成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口舌。M·H·艾布拉姆斯( M·H·Abrams) 与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 Geoffrey Galt Harpham) 主编的《文学术语汇编》(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中对解构主义这一词条作如下描述: “解构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种,致力于阅读理论与阅读实践,主张颠覆和摧毁关于语言系统作为决定文学作品意义的基础,以及语言系统自身所建立的边界、一致性或统一性。典型的解构主义阅读就是展现文本自身各种矛盾力量的冲突,驱散结构的确定性,使文本意义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无法兼容的序列中去。”[11]
从词条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对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理论的一种颠覆,结构主义在语言中寻找秩序与意义的确定性,解构主义则在语言中发现混乱与意义的不确定性。解构主义把文本看作对意义的一种颠覆,否认通过文本可以获得意义的最终诠释。解构主义实践者赞颂文本的自我解构,认为文本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使得阅读成为一场永远无法停止的语言游戏。解构主义否定了形式主义关于文本具有最终意义的承诺,认为文本永远在变化之中,只能提供暂时的意义。所有的文本都向诠释者完全开放,符号与意义之间只是任意地联系在一起,意义只能指向众多无法确定的其他意义中的一个,因此文本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解构主义批评摧毁了文学诠释中的作者论、结构论,更重要的是它否定了意义先验性与确定性,提倡意义的暂存性与多边性。以德·曼与布鲁姆的理论实践为例。德·曼是把解构主义理论应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中最具革新意义的批评家之一,他提出了独特的修辞学阅读理论,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也因此在文学阅读方面深化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
他认为“一个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和否定它自己的修辞方式的权利”[12],这就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批评性阅读的多种可能性。芭芭拉·约翰逊( Barbara Johnson) 作为德·曼的学生,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解构主义阅读的目标与方法: “对于一个文本的解构,不能通过任意的怀疑与颠覆进行下去,必须要从文本中细致地探索出相互冲突的意义,如果什么都被解构式所毁灭,那就不是一个文本,只是一种明确的赋意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而已。解构式阅读是一种从文本自身出发阅读与分析文本的批评性差异。”[13]
在这样的方法指引下,解构式阅读会走向意义的不确定性。布鲁姆也是美国当代着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吸收了德里达“延异”( deffer-ance) 的概念与德·曼的解构思路,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和创造意义,所以阅读总是一种误读。这里的误读不是通常所说的误解,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创作性的背离。读者通过有意识地背叛前人的作品以及前人的阅读,使用一些修辞手段,在阅读过程中创作出新的意思。正如布鲁姆所说:
“只有强势误读和弱势误读,就像只有强劲诗歌和差劲诗歌一样,但是根本就没有理解正确的阅读,因为阅读一个文本必须阅读整个文本体系,而且意思总是游离于文本之间。”[14]
从他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意义是居无定所的,没有正误之分,并在不断的误读中消逝或呈现。
解构式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从一开始对它进行批评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对解构主义的批评主要认为它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缺乏严肃性,严重威胁了文学研究的稳定性,并且促进了哲学上的xuwuzhuyi。在最近几年里,它过度的理论化发展与蓄意使文本晦涩难懂导致理论渐渐压制了批评实践。而它的批评实践也像它的理论一样,缺乏对批评结果的重视,导致批评活动漫无目的、任意漂移。回到艾柯关于过度诠释的看法,我们就会得知为什么艾柯所提出的过度诠释具有负面影响了。
过度诠释概念从对文学作品的深度追求与多元化的诠释( 积极的) 到读者的任意发挥与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消解( 消极的) 穿越了整个 20 世纪文学诠释理论,其中既有文学诠释理论自身关于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也有解构主义思想对文学诠释的理论观照。对于过度诠释这个概念来说,这些理论有一个共性,就是对文学作品的诠释超出了文学自身,使用了大量非文学的理论工具对文学进行过分精致的诠释。在这一点上,笔者和耶鲁大学的教授保罗·弗莱有一定的共识。他认为过度诠释首先是读者根据一定理论对文学作品非常精细的诠释; 其次,过度诠释代表着一种诠释的叠加,新的诠释叠加在旧的诠释之上。其实两者可以合并起来理解,因为有新的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进行诠释,产生不同的诠释结果,诠释结果之间由于自身的理论视域不同又产生了对作品诠释的叠加效果。这样,过度诠释不仅带来了文学诠释活动的繁荣,也刺激了理论的多元。
但如果把它推得太远,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来说是一种考验。在理论的过度诠释中,它往往会失去自身。
伽达默尔曾说: “美学必须被并入诠释学中”[15].他的观点可以作为过度诠释的一个脚注,但这个观点极易遭到批判。匈牙利学者彼特·斯丛狄( Peter Szonde) 在《文学诠释学导论》一书中就认为“文学诠释学必须以作品的审美因素作为诠释的前提。”[16]
通过以上论述得知,过度诠释的概念并不是单一的,在具体的文学诠释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过度诠释观,并且两者受到自身以及外在因素影响而发生转变。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个概念,避免以讹传讹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M]. A. A. Brill Translate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3: 523.
[2]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275.
[3]Stefan Collini.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8
[4]Pol Vandevelde. The task of the interpretation---text,meaning,and negotiation[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Press,2005: 3.
[5]Hans -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M]. 2nd ed. Joel Weinsheimer & Donald G. Marshall Translator,New York: Con-tinuum,1998: 296,297.
[6]赫施。 解释的有效性[M]. 王才勇,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1: 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