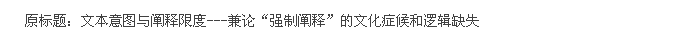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西方文论思潮的大量涌入,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面对西方文论“独霸天下的姿态”,中国学者虽一开始就有从“跟着说”“接着说”发展到“对着说”的良好愿望,但迄今为止,能与西方文论“对着说”的中国文论体系尚未浮出水面。
为此,张江提出了“强制阐释”概念,借以“重审整个当代西方文论”,为如何重释“西方文论”、如何建构中国话语做出了有益的理论尝试。
所谓“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此论一出,使得“阐释”及其相关话题,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纵观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史,“阐释”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且不说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文论和阐释学理论,即便是接受美学诸家,也绝不敢小觑文本及其阐释问题。例如,伊瑟尔的《虚构与想象》一开篇就涉及文学阐释问题:文学需要解释,因为作者以语言营造的文本,只有通过可供参照的认知结构才能把握其意义。
如今,解释文本的方法和技巧已变得如此精巧而复杂,以致五花八门的解释学说和文本理论本身也变成了“细读”(scrutiny,即详尽的研究)的对象。……尽管各类批评或解释方法角度不同、目的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文本的密切关注。
(2)在伊瑟尔看来,文学文本具有一个完善的阐释系统,这个系统的独特性使文学文本具有独特的意义。文学文本具有交往性、应用性、可鉴赏性,有关文本的意义阐发、结构分析、价值确认,甚至以突出其语义模糊性来发掘其潜在的审美意义,所有这些,对于文本解释者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接受美学的核心成员,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中,明显地表现出了“回归文本”的倾向,他重申了传统文论的一些基本常识,例如,他把文本看作是诗人生活的写照或反映社会的镜子。而追寻“意义踪迹”的方法所关注的,正如许多方法论所暗示的那样,是寻求一种解释文本的思路,解释者通过对暗含结构的解读来发现文本的奥秘。
这种转向,对我们从学术史的视角理解“强制阐释”的必然性及其局限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走向综合性与总体性的文本阐释
我们知道,从 20 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到二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文本分析的精细化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文本这块“生肉”已经被煮烂煮透了.经过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的切分与解剖,再到 60 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拆拼与翻搅,文学文本已经变成了一锅热气腾腾的“肉羹”.对 60 年代以后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说,剖析文本的创新空间已经日渐逼仄,他们大约也只有在文本之外的“佐料”等方面翻点花样了.60 年代之后,国际政治冷战气氛日趋缓解,欧洲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倾向也渐有抬头之势,加之信息技术崛起极大地拓宽了思想交流的渠道,文本之外的社会意义也随之凸显出来……总之,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向接受,可谓水到渠成,于是,接受美学,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正是接受美学把阐释学中的读者之维推向了极端.但作为接受美学的主将,伊瑟尔从接受美学向文学人类学的转变,重新思考“文本意图及其阐释限度”,或许是我们阐释当下流行的“强制阐释”之源流与本质的一个别有意味的切入口。
伊瑟尔的《虚构与想象》有一个副标题---“文学人类学疆界”.不言而喻,这个“疆界”与本文所谓的“限度”多有相通之处。在该书的译后记中,笔者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20 世纪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五花八门的理论与学说,彼此渗透,互相辩驳。它们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追“新”逐“后”,东起西落。……但是,在理论风云变幻无定的近百年中,比较而言,大体上有这样的三种类型仍旧引人注目:一、主要以作者为中心的“表现主义”理论,如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二、主要以作品为中心的“形式主义”理论,如以雅格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兰塞姆等人热衷的“新批评”,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倡导的“结构主义”;三、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美学”等,主要代表有英伽登的“阅读现象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以及姚斯、伊瑟尔倡导的接受美学。
我们注意到,不同国籍的好几代美学家和文论家,在近百年的时间内,顺着从“作者”到“作品”再到“读者”的顺序,各自建构并发展着自己的理论体系,这里是否隐含着学术发展史的某种必然规律?令人感叹的是,历史老人竟是如此条理分明的逻辑学家!我们不能肯定理论研究关注的中心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循环”,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种综合性、总体性研究早就显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例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批评、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探讨和整体性把握,他们都注意到了传统文论将作家、作品和读者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在这一方面,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自觉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伊瑟尔的转向,就是顺应文学研究的综合化和总体化发展趋势的一个生动例证。
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的思路表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已近穷途末路.这是西方文论近百年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和历史教训.作者、文本和读者都是文学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顾此失彼的阐释或独照一隅的研究都是不可取的。刘勰说:“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专注整体中一域,而又不忘一域所在的整体,这种综合性与总体性的文本研究,或许对规避“强制阐释”、戒除各种强作解人的“挪用”“转用”“借用”都是一味喝破痴迷、回归现实的清醒剂。
二、“强制阐释”的历史根源与文化症候
从学术史的视角看,“阐释学”虽然是一个现代哲学概念,但对阐释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事实上,“阐释学”(hermeneutics)义即“赫尔墨斯之学”,其词根就来自古希腊语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是神的信使,他变化无常,模棱两可,所传达的神意玄秘含糊,具有难以理解、难以言说的神秘性,这一点从“神秘主义”(hermetism)一词与“阐释学”的同根同源亦可见一斑。希腊罗马人都相信赫尔墨斯是雄辩家的偶像,同时也是骗子和窃贼的保护神,让人看不清、猜不透。“这位既给人宣示神谕,其言又殊不可解的神话人物,最能象征理解和阐释的种种问题和困难。”
(3)因此,将研究阐释问题、克服理解困难的科学命名为“赫尔墨斯之学”,可谓恰如其分、切中肯綮!众所周知,阐释学是在对《圣经》的词语“诠释”和神学“解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阐释学仍旧具有隐约可见的宗教文化特有的神秘色彩.张江《强制阐释论》指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作者还对强制阐释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该文视野宏阔,取材宏富,气势宏大,于兹不妄作评介.笔者发现,“强制阐释”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这种现象却很普遍.就西方文论而言,其根源早就隐伏在西方文化的“二希”源头之中.古希腊逻各斯主义“一线到底”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希伯来宗教文化“一以贯之”的一神教精神,都以基因的形式渗透在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西方文化的“二希”源头,或许可以看作我们理解“强制阐释”的历史根源及其文化症候的基本前提.例如,弗洛伊德强调力比多,则万物皆是性意识的象征;德里达强调文本,则说“文本之外无一物”;新批评强调作品的中心地位,便一刀斩断作品与作者的联系;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主体性,则将接受看成一种超越作者和文本的纯粹个人体验,凡此种种,“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无不与“强制阐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注意到,即便是被阐释了数千年的希腊神话,在今天的出版物里仍然充满了目的不同、方法各异的“强制阐释”.譬如说,谢利曼挖掘的特洛伊财宝、伊文斯发现的阿伽门农面具、苏格拉底最后的遗言等等,都明显存在着罔顾事实的“以今释古”现象。谢利曼戴在索菲亚身上的那些头饰,一再被煞有介事地说成是海伦的首饰;而所谓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实际上与那位身份可疑的迈锡尼王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对苏格拉底遗言的“误读”更可以说是“强制阐释”生动的例证。苏格拉底说:“克力同,别忘了替我偿还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一只鸡。”意思是说,他一死,所有病痛一笔勾销,既然百病痊愈,那就该照习俗给医神献祭一只鸡。但不少中国人把苏格拉底的“视死如归”阐释为“信守诺言”,而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也被想象成苏格拉底的邻居。这种“明知故犯”的“别解”相当普遍,古今中外,概莫能免。譬如说,中外史书常常煞有介事地把帝王们描述成“神之子”,更不用说《圣经》等宗教书籍了。尤其是文学创作中虚构与想象的特权、陌生化、典型化、“箭垛效应”等等,都为强制阐释提供了纵马驰骋的空间.至于今天微信、微博上的众多明星八卦和历史戏说,在评说明星言行和阐释历史事件时,罔顾事实、混淆是非的情形,则更是把强制阐释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强制阐释,说到底是一种话语权利的“滥用”.
公元 646 年,欧麦尔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他解释说,如果这些希腊人的着作与安拉的经典一致,它们就是多余的;如果不一致,那么就是有害的;总之,阐释的话语权掌握在哈里发手里.
有趣的是此前罗马人曾两次焚馆(恺撒,公元前 47 年;狄奥多西,公元 391 年),但都没有欧麦尔焚馆事件那么富有争议,这或许是因为欧麦尔的“强制阐释”比焚馆事件本身更加耐人寻味吧?与此形成有趣之对照的例子是,1420 年,北京故宫竣工,但永乐皇帝在新殿御朝不足百日,前三殿遭雷击悉数被毁.
一时间“朝论沸扬”“台谏交口”,以致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皆未敢重修大殿,由此不难想见时人对“三殿灾”的阐释让皇族承受了多么沉重的心理压力!
当避雷针技术传入中国后,当年那些“朝论”“台谏”,不攻自破,沦为笑谈!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马克思的话:“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
(4)我们感兴趣的是,当人类生活在一个主要靠想象力理解世界的时代,阐释者的话语权有时甚至会凌驾于皇权之上。事实上,负责处理人神关系的祭司或巫师对“神谕”或“神迹”的解释,是“代神立言”,往往比国王的法律更权威。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持续了数千年,时至今日,求神问卦者也并未绝迹。帝王们热衷造神,意在树立权威、以愚黔首,这与教皇鼓吹“无知乃虔诚之母”如出一辙。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强制阐释也有其超越解释学的合理性。如汉朝儒生奉命对《诗经》进行“强制阐释”,开辟了中国诗学的政教之路,诗经变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有力武器。这样的例子也一样举不胜举。
尽管现实生活中歪曲事实理所不容,但文学艺术的“强制阐释”却势所难禁。探究这个悖论的症结,除了借鉴“趣味无争辩”“衍义无疆界”等陈规旧训外,或许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从接受心理上讲,强制阐释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预期。譬如,即使明知秦始皇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但人们还是津津乐道于此类野史.还是恺撒说得透彻:“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第二,文学艺术并不以求真为务,它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对美的创造.莱辛有句名言:“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凡是为造型艺术所追求的其他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必须让路给美.”(5)第三,从阐释的艺术效果看,“正如大多数知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样的诠释在某些情况下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平淡寡味.切斯特尔顿对此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一种批评要么什么也别说,要么必须使作者暴跳如雷.”
(6)总之,强制阐释,更痛快,更有趣,更能一鸣惊人!但就阐释的必要性和目的性而言,“强制”恰好站在了“阐释”的对立面.
三、文本的意图及其阐释的限度
《汉书·韩安国传》:“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同理,任何强词夺理的阐释,必有理屈词穷的时候。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艾柯曾树立了众多批评的靶子,如:“对文本唯一可信的解读是误读”“本文只一个开放的宇宙,在本文中诠释者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真正的读者是那些懂得文本的秘密就是无的人”“波麦的文本有如野餐会,作者带去语言,而由读者带去意义。……”(7)遗憾的是,艾柯的批评根本没有针对“阐释的无限性”提出有力的批评证据。当然,他反对过度阐释的态度倒是毫不含糊。艾柯批评说,即便情况真如波麦之诗,“作者所带去的词语也是一个令人棘手的、装满五花八门材料的大包袱,读者不可能将其置之不顾”(8).
艾柯的意思是,文本的阐释终归有个限度。在艾柯看来,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奥古斯都之后能安享近200 年太平(Pax Romana)(9),那是因为它拥有稳固的边疆,这与游牧蛮族的居无定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本之所以成其文本,就如同帝国之所以成其为帝国一样,它们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所谓“水停以鉴,火静而朗”,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强制阐释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无视边界的存在,甚至以打破疆界为时尚.艾柯说:“我所研究的实际上是本文权利与诠释者权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有个印象是,在最近几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些过火了.”
(10)艾柯指出,传统阐释学唯一目的就是要寻找作者本来的意图,而后现代阐释学认为,阐释者的作用仅仅是“将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罗蒂语).为了在两种极端阐释理念之间寻找一种折中的阐释方式,艾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文本方面,为此,他祭出了“文本意图”的旗帜.当然,艾柯强调回归“文本意图”,并不是重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老调,我们不妨将其视为“走向综合性与总体性文本阐释”的一种尝试.从一定意义上说,强制阐释常常与“文本误读”互为因果.尽管“误读”的原因千奇百怪,但无外乎主观“故意”或客观“无心”两种.以韩非子的着名寓言“郢书燕说”为例: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
对于秉笔者来说,误写“举烛”二字显然是“无心而为”,但对于燕国丞相的“强制阐释”而言,就很难说是“无意之举”了。有趣的是,丞相的误读带来了燕国大治的结果,这种充满正能量的“误读”应该说是值得庆幸的。所以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感叹说:“郢书燕说,未必无益。”(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四)。当然,韩非子的本意或许是讽刺当时学者望文生义的浮躁治学态度。
其实,今天的学术界,“郢书燕说”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刘心武把“红学”讲成了“秦学”就是“强制阐释”的活标本。笔者曾写打油诗《戏拟刘心武揭秘“红楼”》:“郢书燕说小说招,信口开河戏说曹;梦中说梦侃秦学,祸枣灾梨知多少?”
(11)但有人替刘心武辩护,其理由是任何人都有阐释的权利,只要能自圆其说,于曹氏其人其书,又有何碍何损?按照弗莱的批评理论,刘心武只不过是把曹雪芹想说而又不能够直说的东西替他说出来而已。斯威夫特说:“渊博的批评家目光何其犀利,读荷马能见出荷马不懂的东西.”(As learned com-mentaters view, I Homer more than Homerknew)这话原意本是讽刺,但对于今天的批评家来说,听上去反倒更像是一种恭维.阐释者站在“今之视昔”的角度,阐释出“荷马所不知道的东西”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即便是“海伦的首饰”和“阿伽门农的面具”或“秦可卿的皇族身世”这类充满想象力的强制阐释,其“文本意图与阐释限度”也是一望而知的.说到底,文本自有文本的意图,阐释自有阐释的限度.譬如说,郢书燕说中将“举烛”释为“尚明”固然是“误读”,但也主要是文本“意图”之误在先,臣子向燕王的“强制阐释”在后.无论如何,读信人不可能将“举烛”强制阐释为前文所述的“焚馆”或“毁殿”,因为阐释者无法迈过逻辑这道门槛,更不用说历史事实这道铁门槛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本的意图往往对阐释的限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谓“1”无非是因“阐释的循环”而造成的一种错觉而已.当然,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往往使相关文本的边界模糊不清,毕竟,文本帝国只有其虚拟的疆界。要避免强制阐释,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白居易说“: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其三》。)由此可见,历史和事实是最伟大的阐释者.要避免强制阐释,张江所说的“辨识历史,把握实证,寻求共识”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注释:
(1)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 年第 6 期。以下有关“强制阐释论”的引文皆出于此。
(2)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 页。
(3)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 173 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13 页。
(5)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 16 页。
(6)(7)(8)(10)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张北根译,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135 页,第 47-48 页,第 28 页,第28-29 页。
(9)Pax Romana 特指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但译者将其误译人名:帕斯·罗马纳。同上,第 33 页。
(11)拙着《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5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