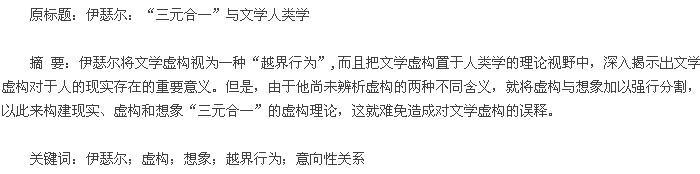
伊瑟尔的《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是对文学虚构问题做出全面、深入思考的重要着作,是他在接受理论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
随着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以其令人注目的方式取代文学独立性和审美性,文学所承担的文化功能势必愈益复杂,随意性不断增大,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因此受到质疑。正是针对这一现状,伊瑟尔试图从人类学角度重新阐释人之所以不能缺少文学的根本原因。他抓住文学虚构这一核心问题,不仅深入讨论了文学活动中现实、虚构和想象的关系,从文学史、哲学史角度梳理了有关虚构和想象理论的流变,并且致力于探讨文学虚构的人类学依据。因此可以说,这部着作标志着伊瑟尔文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他不再仅就文学而谈论文学,而是将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从人类基本特性出发重新考察文学。
一
正如萨特所指出的,人的理想的存在,是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的存在,伊瑟尔对此作了自己的发挥。他认为,人总是既想了解自己已有的自我存在,又向往着未来,希冀突破自我,重塑自我。人既“向心”又“离心”地生存着。正是基于人的这一本性,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人所不可或缺的活动领域,因为文学为人提供了种种与现实相关联又不为现实所限制的生存方式,也为人提供了“人的自解”的不同形式:文学体现着人类自我呈现的冲动,它将这种冲动展开在人的眼前,促使人去思考“人究竟是什么”;同时,又通过虚构和想象来展现人的可塑性,让人可以去亲身体验和发现“人应该是什么”和“人可能成为什么”.唯有作为虚构文本的文学,让人的历史保持着极其活跃的开放状态,为人的生存开辟了无限可能性。文学的虚构性蕴含着人之为人的深刻根源。这种虚构意识是现实世界的入侵者,它避开人的认知能力,公然漠视事物的本质,撕裂和拓展了这个供它参照的世界,构成了一种跨越现实与虚构之疆界的行为。文学虚构的“越界行为”既创造了一个文学虚构世界,又同时关联着现实与虚构这两个世界。因此,在伊瑟尔的理论中,文学虚构不再与现实相对立,而是成为跨越和贯通虚构与现实两个世界的越界行为。
为此,伊瑟尔指出了关于虚构与现实间的关系之“常识”的谬误:其一,人们历来把文学视为“虚构之物”,并将此作为“不言而喻的知识”;其二,一旦文学是虚构文本,它就割断了自己与已知现实的关联,那么就势必成为谁都无法理解的“天书”.这两点都是常识,却又相互抵牾,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间存在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正建基于传统认识论将现实与虚构二者相对立的旧观念。与此相对,伊瑟尔提出自己对文学的独特见解:即以现实、虚构和想象“三元合一”来取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并将这种三元合一的关系作为文学文本存在的基础。
在伊瑟尔看来,文学文本是现实与虚构的“混合物”,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互通互融的特性远胜于相互对立的特性。一方面,文本中弥散着大量具有确定意义的词语,它们来自社会,来自某些非文本所能承载的现实。可是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却并不是为了追求现实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现实一旦被转化为文本,它就必然成了一种与众多其他事物密切相关的符号。因此,文本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它们所描摹的原型。”[1]15这种对现实原型的超越正是文学的虚构化行为。
在以往文论中,虚构与想象是相互纠结、难以区分的概念,伊瑟尔则试图将两者区别开来。
在他看来,虚构是一种有意识的运行模式,是受主体引导和控制的行为;而想象则是自发的,并不是一种自为的潜能,它必须依靠其他因素才能发挥作用,犹如任性的鬼魅,想象常常一闪而过,来去无踪,没有定型,它是自我意志在瞬间的显现。因此,虚构化行为激发了想象变化多端的潜能,并赋予想象一种明晰的格式塔(gestalt),为想象对现实的越界提供了依据、导向和框架。
在文学活动中,虚构与想象是交相作用、水乳交融的。由于虚构化行为的引领,现实才得以升腾为想象,虚构拆毁现实的栅栏,同时将纵横恣肆的想象的野马圈入形式的围栏,虚构化行为充当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纽带;而想象则以其多姿多彩的形象为文学提供了审美维度。“在这一过程中,虚构将已知世界编码(transcode),把未知世界变成想象之物,而由想象与现实这两者重新组合的世界,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1]16虚构和想象相互融合,共同实施了多重越界,构成了现实、虚构和想象的三元合一。
伊瑟尔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和具有田园风格的作品为例,来具体阐释文学虚构的越界行为。田园体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它重现了乡间世界;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另一个田园世界,以使现实中无法寻找的事物成为可能。这两个世界有着双重指涉,因此,虚构的田园诗的世界同时与理想化的状态及历史的世界相关。虚构使得原本互相排斥的事物和平共处。“在历史的世界和艺术的世界边界的跨越过程中,田园罗曼司提供了一幅既非置于艺术世界也非置于历史世界的文学虚构的生动图画。”
[1]66人们只要戴上田园诗主角“牧羊人”的面具,就可以从一个世界自由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同时,又将面具揭示为虚构的假象,以便虚构的伪装允许他随心所欲地闯入任何禁地,违反种种现实禁令。面具让人获得了双重性,他既是自身,又作为牧羊人来表演,并因此成为“他人”.面具以伪装遮蔽了人的真实面目,却又以变化的角色揭示出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人借助面具超越自身,面具则让人居于自身之外而发现了自己,并真正拥有了自己。
二
伊瑟尔阐释文学虚构的方式最基本的特点在于:他不是将文学虚构视为“现实”或“真实”的对立面来做静态的概念界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虚构化行为”来看待。既然是“行为”,其边界就势必时时变化、流动不居,就不可以给它做简单的界定,而应该转而对其功能做出描述。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伊瑟尔把文学虚构的功能区分为选择、融合和自解。
文学作品是作者依从其倾向性对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系统等多重因素做出选择的结果。
只要文本中的参照物是既定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就可以被看作是现实本身。而选择却是一种越界行为,因为一旦对象被选择和挪用,它就从原来所属的现实语境中超脱出来,失去了它在原有体系中的本相和功能,成为“另一个”文学世界的构成部分。选择改造了现实参照物,打破了它们的既定秩序,以“另一种”文学世界的秩序重组了它们。尽管被选择对象本身并非虚构之物,却已经超脱原有现实的疆界而进入文学虚构之境了。对于所构建的文学虚构世界来说,那些在选择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因素虽然是不在场的,却由于和所选择的因素原本密切相关,也会随之进入人的感知领域,这就形成一个考察虚构化行为的“大背景”.“那些看上去明白无误的缺席者,在文本中也如同始终在场一样。”
[1]18-19他如文化习俗、文学典故和惯例的选择也如此。一方面它们与原文本相关联而保持着最基本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纳入到新的文本,在新的结构系统和语境中获得了新意义。因此,文学的多重选择造就了多重越界,并因此形成多种系统的相互交织。文学文本注定着自身极其复杂的“互文性”,它既因为多重越界而成为一个独特的虚构文本,又与社会、历史、文化和其他文本构成了相互参照关系。“选择,作为一种虚构化行为,揭示了文本的意向性。它将一种跨文本的真实性引入文本之中,将不同系统之中各种被选择的因素带入共同的语境,而这一语境把被选择过程淘汰的因素作为背景,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双向互释的过程;在场者依靠缺席者显示其存在;而缺席者则要通过在场者显示其自身。”
[1]19正是这种“双向互释”既区分又瓦解着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以及其他各种文本之间的边界,构成多重越界行为。因此,我们既不能把文学文本的意向等同于对现实世界的追问,也不能将其视为虚幻的想象,它是一种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过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
虚构化行为的另一个功能是融合,它使各种被选择的不同因素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是选择功能重要的互补方式。
在谈到文学语言时,巴赫金指出: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融合的现象。这些语体、杂语和各种声音来自种种不同社会领域、阶层和民族,各自带有自己的意向并牵连着原有的语境,它们在小说中构成了不同语境、不同观点、不同视野、不同情感色彩、不同社会语言间的交互作用,或相互支持、映衬或相互抵牾、冲突,无论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必须深入对方的视野,在他人的疆界里、在统觉的背景上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或对话语做出理解。小说作品既要广泛接纳多语型、多声部、多体式,甚至常常是不同民族语言的成分,以不同的格调彰显各种世界观的、派别的、社会诸方面的特定评价,又必须让种种杂语服从于“最高的修辞整体”,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作品世界。“作品作为统一整体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人物的言语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在现实的言语交际条件下独立存在的情形:在与其他言语、与作者言语的对比中,它获得了附加意义,在它那直接指物的因素上增加了新的、作者的声音(嘲讽、愤怒等等),就像周围语境的影子落在它的身上……在一部完整作品的统一体中,一个言语受其他言语框定,这一事实本身就赋予了言语以附加的因素使它凝聚为言语的形象,为它确立了不同于该领域实际生存条件的新边界。”[2]
如此,文学文本既有自己所属的世界,有自己的统一性、整体性,又充满了各种对话和潜对话,是各式言语相融合的“汇合地”.巴赫金所说的“最高修辞整体”主要是从言语类型和特征角度,来阐述文学究竟如何将杂语融合为作品整体的,伊瑟尔则扩大了融合功能的范围,不仅包括不同文本、不同系统的话语和语词间的融合,而且还涉及不同的社会现象、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文学典故,等等。那些被选择的因素在融合过程中重新建立了新秩序,并获得文学世界的“真实感”,一种迥异于经验世界的“真实性”,或如古德曼所说的“源于虚构的真实”[3]106.至于被排除在外的因素虽然未能进入文本,却因原本与所选因素相关联,又构成被彰显因素的背景,建立起“形-影”关系。“在场者通过缺席者而显示其存在。但是,当融合不得不通过被排斥因素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时,虚构化行为就必然会造成在场与缺席相互依存的局面。反过来,文本中已被确定的关系又会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活泛起来。”
[1]22融合功能致使各种矛盾因素共同关联着文本这个统一体,它们既相互揭示又相互遮蔽,从而赋予文学文本极其丰富的互文性,也因此构成了种种不同性质的越界行为,导致意义的不稳定性。
选择和融合这两种行为都涉及文学与社会系统间的越界,同时也都涉及对参照系统的跨文本越界。越界行为穿越了虚构与现实,以及文本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它们间的边界,模糊了文学作品的边界。为使虚构化行为进行到底,使文学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世界,就需要另一种功能,这就是虚构性自解。
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中包含着大量标示其虚构特征的信号,这些信号并不等同于语言信号,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和读者共享的某些标识。譬如文学类型、流行故事,等等,它们都具有一种使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的虚构功能。文学虚构的自解功能既要求作者遵循这些文化共识来完成文学文本的建构,设立某些标识,又引导读者将其作为虚构文本来解读。文学的自解功能有效实施着文学文本的自我显现和自我解释。从某种角度看,这种作者和读者间达成的共识,犹如乔纳森·卡勒所说的“程式”.一方面,程式是作者从文学传统中获得的某种文学观念和能力,并成为作者进行创作的内省意识;另一方面,也是读者所具有的阅读能力,读者按照他在文学经验中建立的一系列形式规则,把文本视为非现实的虚构之物,由此展开再创造,这些程式既是他实施再创造的条件,又是对创造的限制。正是由于存在文学程式,才能有效引导文学阅读活动,以使读者“把某一文本当作文学来阅读就是当作虚构文字来阅读”[4].在伊瑟尔的文学虚构理论中,虚构文本的自解即对文学文本虚构性的彰显;对于读者而言,则引导阅读态度的转变,它要求读者改变接受心态,以区别于阅读非文学文本时的态度。虚构的自解功能引起读者对一个非真实世界的热情,并使读者的自我真实性在想象中得以展开。文本在读者的经验面前实现了再次越界。
当读者把文学作为虚构世界来看待,文本中隐含着的大量依稀可辨的“现实”也被伪装起来,“现实”的世界于是被悬置,读者的“本真态度”也被悬置了。只有通过这种悬置,读者的想象才获得自由,真正的文学欣赏才可能顺利进行。“就这种超越现实的意向而言,虚构文本的实际功能,不过是给现实描绘一种模糊的轮廓,颇有画饼充饥的意味。因为,虚构对其实用而言,它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即文本的真实并不等于现实的真实。文本的真实是一种假象的真实。
文本的真实性是一种假象的真实性,因为它的功能就是赋予对象以想象的空间。”[1]27文学虚构离不开自解功能,正是它揭示了文本的虚构性,并赋予作者和读者超越现实的权力,亲身体验种种生存可能性。
三
在考察虚构理论的历史演变时,伊瑟尔指出:随着知识确定性观念的衰落和对虚构问题研究的深入,虚构在哲学中的地位开始攀升,它从一种只有负面价值的欺骗形式变身为认识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正如克默德所指出,人类通过提供虚设的开端和结尾来建立“和谐的虚构”,以此寻求现实的意义。或者如古德曼所说,世界是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是被人为构造的,存在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世界,而没有一个所谓实在的世界。因此伊瑟尔认为,虚构有着实用主义的本性,它取决于我们对待它的态度,总是随着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语境以游移不定的方式展示自身,产生出虚构的不同形态,其边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虚构的具体应用所证实的只是虚构的功能而非本质,它不可能获得一个不变的身份。为此,伊瑟尔着重针对弗兰西斯·培根、耶利米·边沁、汉斯·费英格和纳尔逊·古德曼诸学者关于虚构理论的阐释,将“虚构”置于哲学话语体系中进行分析梳理。
培根揭示了作为“再现”的具体形式的“四类假象”,并致力于以“虚构的设计”,即实验和操作来克服虚假的再现。与培根不同,边沁并非意图消除虚构,而是批判虚构在法律领域的特殊使用,他认为法律实践掩盖和压制了对其虚构特性的意识。实际上,虚构作为一种“模态”,它构建了“虚构的实体”,人只有通过虚构的实体赋予真实对象以形式,才能了解对象并将它当做一个真实的存在来谈论。在边沁的理论中,虚构已不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成为一个观念与真实间的“调停的模式”.如果说,在边沁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对虚构的肯定倾向,而这种肯定还仅限于弥合认识论视野中暴露出来的鸿沟,那么,对费英格而言,虚构说明了感觉与现实间的根本分裂,并且唯有虚构能突出这个分裂。根据观念地位的变化,费英格勾画了感觉与现象之间差异性的图式:即信条、假设和虚构。在信条中,人们否认实际存在的虚构,强调观念与现实相符合,以使差异得以填平;在假设中,则指明了观念与现实的不一致性,以至于观念变成了一个需要在反复试验过程中被修正的假设;在虚构中,差异性被认可,区分的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假设总是寻求解释自己所创造的秩序,并通过争取广泛的赞同获得正当性;虚构则借助于想象开始筹划产生某些非现实的“事物”,虚构是“有意识的虚妄观念”[5]15.在对虚构做出分析的基础上,费英格阐述了“仿佛”哲学。“仿佛”造成了不同物之间的认同,它承认差异性,承认自己不是存在物,却又是假定的连接的结构,并为洞见带来可能。“仿佛”揭示了虚构的双重性,以自身的差异性标明虚构同时是假的和实用的:假的是对真实和有效性的否定,强调根本差异依然存在;实用性则表明,虚构作为感觉设计的形式来说,假的外观变成了一个变化的“指涉框架”.费英格的理论仍然建立在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古德曼则抛弃了这一认识论框架。在古德曼的理论中,世界本身就是“人为”地以多种方式,诸如哲学、艺术、科学、知觉的方式,或者是用不同的符号形式所构造的,是“多元世界”.存在着多个由不同符号构建起来的“真实的世界”.在由此形成的多个世界“译本”之下,并不存在所谓实在的世界,它们不可以被还原为一个唯一的基础。
①“无数的世界借助于符号的使用从虚无中被构造出来”[3]1.没有一个被构建起来的世界样式将被视为唯一的真理,所谓真理只能是“适合性”和可接受性。从世界本身是被人为构造的角度来看,“真实性”其实来自“虚构的真实”.在上述理论中,虚构的意义,以及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虚构与现实不再相互对立,而且虚构已经成为构建人的世界的必要手段和必然途径。伊瑟尔从这些理论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其中,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费英格的“仿佛”哲学。因为连词“仿佛”关联着既有事物与不可能的事物,揭示了虚构文本与所反映的世界之间关系的双重性:一方面,文本为反映世界,就必须加以生动的描绘,以使文本世界“仿佛”是真实的;另一方面,文本世界又注定只能是貌似真实,它自己否决了自身的真实性,强化了文本的虚构性。“仿佛”语式结构激发了想象,并为想象提供了自由驰骋的空间。这恰恰可以被伊瑟尔用来阐释文学虚构的越界行为。至于“想象”在哲学话语系统中也同样经历了变化。在柯勒律治那里,想象是一种源于主体的能力,并被划分为“幻想”“第二级想象力”“原发性想象力”三个层次;在萨特的阐释中,想象是一种创造精神性意象的行为,它在意识、潜意识的作用下展现自身;卡斯特里阿蒂斯则认为,想象只能通过心理和社会历史来体现,想象取代神话成为制度的基础,它既建构社会,同时赋予社会自我改革以可能性。总之,想象并非一种自我激活的力量,它必须借助外力,如主体、意识、社会历史才能得以展现。但是,主体或意识或社会历史的实用要求,都将想象引导到一个十分具体的方向上去。与此不同,虚构则以一种不确定的灵活方式激活并推动想象。虚构和想象相互交融,造就了错杂交织的越界行为,开辟出变化多样的游戏空间。
“人类的表演多种多样,唯独不能拥有自我'.只有文学才能反映的这样一种分裂并非人所共知。因为人类不能成其自身并不一定非要拥有自我.事实上,成其自身与拥有自我二者的鸿沟不可逾越,文学的作用就是发现探索二者的空间距离。”[1]379文学文本表演构成了游戏本身。无论作者或读者都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表演着,作为文学世界中的一个角色,一个“他者”表演着。他融入想象的环境,融入自己产生的独特幻象和行为,并且相信自己已经暂时忘记和摆脱了自己的个性,成为自身之外的某个人。文本游戏让人突破被日常习惯所模铸的固化的自我,走出种种藩篱,扮演着多种多样的角色,以此重新寻找被禁锢的那部分自我,探索人的未知领域,进而开发出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无限可能性。
四
伊瑟尔以其精细、系统的分析,阐述了文学虚构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把虚构与现实相割裂、相对立的二元观,将虚构视为一种行为,以“越界”来统摄现实、虚构和想象,建构起“三元合一”的理论观点,而且把文学虚构置于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中,深入揭示出文学虚构对于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正如汪正龙所指出:“伊瑟尔所说的文本表演与文本游戏是在对现实的越界中实现的。它融合了经验世界的元素,又对之加以超拔和间离;既是人类经验的展开,又是人类的自我塑造与反思。可以说,它在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同时,又反对了后者在文学虚构问题上的意义xuwuzhuyi。”[6]
原先那种在认识论框架中对虚构做出理论界定的方法被抛弃了,代之以人类学视野,在具体语境中对文学的虚构化行为做出详尽的功能描述,这就使得文学虚构问题研究得到极大推进,并为文学活动找到了人类学依据。
人较之于其他任何生命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不仅是他自身,而且总是不断超越自身,正如普勒斯纳所说,“人离心地生活着”[7].文学恰恰以其虚构化行为为人打开自由的活动空间,让人既置身其内,又超然于外,为人摆脱现实束缚、真正赢得创造性和超越日常的自我提供了可能。“由于文学虚构,超出自身之外和之上总是保留了已经被超越的东西,以这种双重化方式,我们作为有差别的人对我们自己在场,但是作为多种角色的综合,人类依然不懂得他们自己,因此文学虚构代表了与人类使自己成为什么和理解什么有关的某种东西……虚构指明了人类不可能对自身在场,它需要通过没有允许我们与自己所创造之物相一致的梦境,行使创造性权利的条件。我们所达到的是对这个基本特性的构想,即虚构使人类成为自身。”
[1]106文学虚构即人的自我越界。伊瑟尔从人的基本特性出发来阐释文学虚构,也就抓住了文学活动对于人类存在最为核心的价值。
但是,伊瑟尔虽然为文学虚构理论做出重要贡献,而其理论却存在局限。文学虚构固然如伊瑟尔所说,是越界行为,可是越界行为却并非必然是“文学的”虚构。越界并非文学虚构的专利。
正如伊瑟尔所列举的培根、边沁、费英格、古德曼诸学者所指出,人类认识活动同样无法摆脱虚构和越界。并且文学虚构也不仅仅是一种更自由、更富于想象性的行为,与认识活动中的虚构因素相比较,并非只是一种量的变化,两者间其实存在质的差异。我们赞同伊瑟尔把虚构视为一种越界行为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造性洞见,但是,不同意伊瑟尔把虚构的越界行为建立在“选择”“融合”的基础上,而是认为,文学虚构的越界行为源于意向性关系的转换。
意向性关系的转换既将文学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区分,又仍然使二者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虚构行为与认识活动中的虚构因素区别开来了,文学虚构中的越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越界。
尽管认识活动包含着虚构因素,这毕竟是一种对象性活动,总是指向“现实”或那个被构建且被指认为现实的“世界”,它处于“现实关系”之中。文学活动则不然,它并非对象性活动,而是另行建构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仅仅属于人自身而不属于现实的另一个“世界”.在此活动中,人与文学世界相互生成、相互亲近、相互融合,于是,世界也就不再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它同时成为人自身。无论这个被构建的世界是否与真实世界相类似、相接近,它都让人处在另一个生存维度上,处在非现实的“虚拟意向关系”之中。因此,文学虚构的越界行为并非伊瑟尔所谓通过选择和融合由现实进入虚构,而是直接由现实关系转向非现实关系,由对象性关系转向非对象性关系,越界行为的关键在于意向性关系的转换。关系转换促成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化,正因如此,文学虚构才是一种自由自主的活动,才有着远为阔大的空间。
在文学活动中,人充分调动并展开了自己的想象,既是虚构化行为的参与者,亲身参与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又生存于这个虚构世界之中,和这一世界相融合。因此,文学活动中的虚构和越界有别于认识活动中的虚构和越界,前者处在一种非对象性关系,也即“主体间性”关系之中;后者则仍然处于对象性关系,即主客体关系,两者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意向性结构,并因此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文学虚构的越界行为是以意向性关系的转换为前提的,它建立了一种非现实关系和非对象性关系。意向性关系的转换才是越界行为的根本,正是意向性关系的转换才导致越界行为的发生,才决定着文学活动中的虚构和越界不同于认识活动中的虚构和越界。伊瑟尔的虚构理论恰恰未能对这个根本差异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强调。
固然,在阐述文学虚构行为的功能之一“自解”时,伊瑟尔指出了文学文本存在着引导读者改变接受态度、以非现实态度对待文本的自我解释作用。可是,在其理论框架中,自解却只是与选择、融合并列的三个功能之一,并且它主要是一种自我解释功能,针对阅读接受活动发挥作用。
这就大为贬低了自解的重要性,不能有效阐明文学活动整体,也不能阐明文学虚构化行为的根本特性。我们则把意向性转换视为文学活动的前提。
无论文学创作或阅读,文学活动及其虚构化行为的特殊性就在于:文学活动改变了日常现实态度而采取了非现实态度,建立了一种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这是一种迥异于其他对象性关系的新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象”已不再是对象,不再是“它”而转化为与我相对待、相融合的“你”,转化为另一个主体。在文学活动中,非现实关系与非对象性关系是互为因果、表里一致的。意向性关系的转换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是由于这种转化,一种新关系的建立,让作者或读者从现实关系中摆脱出来,从现实世界越界而进入虚构化行为,进入另一个虚构世界的创造过程,由此,想象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人也才有可能在越界中向无限开放,并最终自由地成为“我自己”.伊瑟尔正确地批判了将虚构与现实相对立的二元论,并提出虚构是一种越界行为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但是,恰恰忘记最为重要的一点:虚构的越界行为首先是人的自我越界,并且这种越界根源于人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式,改变了看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和方式,改变了意向性关系。意向性关系的转换是文学活动及其虚构化行为的关键,其他诸如选择、融合等行为都在这个前提下开展。因而,选择就不是一种对现实素材的机械择取,融合也不是一种拼凑,而是在新的非现实、非对象性关系中,在双重主体性关系中,敞开人的心扉,勃发人的创造力,以使种种内心经验(这些经验原本就关联着人的现实活动,具有现实性)得以充分发掘和涌现,与此同时,在创作意向、心态和情感的主导下,又自然而然地对各种经验加以筛选和融合,就如克罗齐所说:“每个表现品都是一个整一的表现品。心灵的活动就是融化杂多印象于一个有机整体的那种作用。”[8]
关系转换决定了文学虚构行为的独特品格,也决定了文学活动的独特性。
伊瑟尔虚构理论的失误,其根源在于没有对虚构的两种含义做出辨析的前提下,就把虚构与想象强行割裂开来。尽管伊瑟尔小心翼翼地想要区分虚构和想象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恰恰在他梳理种种不同含义的虚构和想象的过程中,反而使虚构、想象的意义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夹杂不清,这势必无法为虚构和想象设定界限。正如金惠敏对伊瑟尔的访谈中所指出,在伊瑟尔的理论构架中,虚构与想象仍然纠缠在一起,不能形成一个相互区分的清晰图像。
我们认为,伊瑟尔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尽管历来人们对虚构有各种不同解说,但是,从言语行为角度看,虚构具有两种不同含义:其一,指话语所“指谓”的是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对象;其二,指话语“构建”另一个虚构世界的行为。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虚构,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言语行为,有着不同的功能。伊瑟尔没有对此做出区分,因而也就无法对文学虚构做出相对明确的阐释,更无法阐明虚构与想象的关系。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它并非必须具备前一种意义的虚构,因为文学艺术作品的描述既可以没有确定的、真实的现实对象,如海妖塞壬、屈原笔下的云中君、东君等,又可以有真实的指谓,如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文学艺术虚构主要指后一种意义的虚构:建构一个虚构世界。就在人运用语言符号构建一个话语世界之际,必然会如约翰·塞尔所说暂时悬置“纵向原则”,中止语言符号指涉现实对象的功能,让人沉醉于建构活动以及这个人为建构的语言符号世界。他和现实世界暂时分离了,并置身于这个正在被建构的人造世界之内,处在非现实关系之中。正是文学话语建构虚构世界的行为,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构建起非现实、非对象性关系。不管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世界相近似,只要它的指涉功能被暂时中止,人就处在“另一个”世界,一个非现实的虚构世界。此际,这个被建构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有多大关联已经无关紧要了。而这种构建另一个世界的虚构行为,同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想象。从这一点来看,虚构与想象是难以区分的,它们讲的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描述的角度不同:
虚构侧重于话语的建构行为,而想象侧重于人的心理功能,两者又融合一体。一旦把想象与虚构强行剥离,同时也就窒息了活泼生动的话语建构行为,使话语萎缩成干瘪的表述和指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判别指涉是否具有现实对象,由此做出真实或虚构的判断。这就是说,话语指涉意义上的虚构是和想象分离的。虚构与想象的关系历来解说不清,伊瑟尔想要区分它们也终归于失败,其原因就在于:虚构本身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在前一种意义(指谓)上,虚构与想象是相互分裂的;而对于后一种意义(建构)来说,虚构与想象则为一体,只是人们一直来尚未对虚构的含义做出明确阐述,这就必然导致种种误解和误释。建构行为虽然是文学语言最重要、最具特征的行为,却并没有因此剥夺指涉行为,在文学活动中建构行为和指涉行为总是交替进行的,同时构成意向性关系的转换以及现实与虚构之间不断的越界。
尽管伊瑟尔对文学虚构的阐述十分细致,且提供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见解,但由于他未能辨析两种不同含义的虚构,未能澄清文学虚构的真正意义,而将虚构与想象硬性分割开来,以此来构建现实、虚构和想象“三元合一”的虚构理论;同时把态度和关系的转换贬低为文学虚构化行为中和“选择”“融合”并列的一个“功能”,甚至只视为文学阅读活动的一个功能,而不是作为文学活动的根本特征和文学虚构化行为的“前提”来看待,也就不能最终阐明文学虚构问题。
参考文献
[1] 沃尔夫冈·伊瑟尔。 虚构与想象: 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 汪正龙,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2] 巴赫金。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C]. // 钱中文。 巴赫金全集: 第 4 卷。 潘月琴,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283.
[3] 纳尔逊·古德曼。 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M]. 姬志闯,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 乔纳森·卡勒。 结构主义诗学[M]. 盛宁,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193.
[5] Vaihinger H.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A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Religious Fictions [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2: xlii.
[6] 汪正龙。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文学虚构理论及其意义[J].文学评论, 2005, (5): 28-34.
[7] 米夏埃尔·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M]. 张乐天,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193.
[8] 克罗齐。 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 朱光潜, 韩邦凯, 罗芃, 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