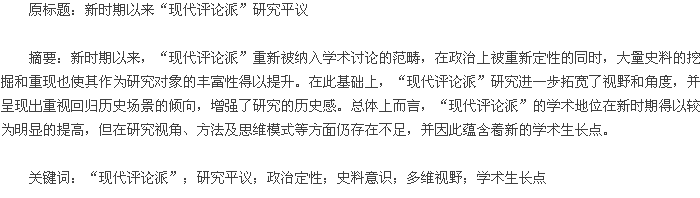
“现代评论派”得名于同人刊物《现代评论》,是“五四”退潮之后较早出现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派别,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中有着重要影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学术研究的政治化倾向,“现代评论派”在学界研究中长期处于被遮蔽、压抑的位置,即便出现相关的书写中也往往被贴上“段祺瑞章士钊的走狗”、“一小撮买办阶级的无耻奴才”等类似的反动政治标签,直到新时期到来,“现代评论派”才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并获得了学理高度的观照。总体来看,新时期以来的“现代评论派”研究大致以1990年代初期前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既在研究视角和维度上呈现出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又形成了颇有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与衍变风貌,从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现代评论派”研究的历史脉络,而已有研究在视角、方法及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将成为“现代评论派”后续研究的着力之处。
一、重评:政治“松绑”与史料挖掘
新时期初期,“现代评论派”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出现了一系列“重评”文章,这些文章突破意识形态的禁锢,爬梳原始资料,重新评估其历史功过,极大地扭转了以往欠缺公允、乖违史实的批评倾向,开创了“现代评论派”研究的新局面。
1.政治上的重新定性。新时期“现代评论派”研究打开局面的首要工作是对其进行政治上的重新定性。重评文章放弃了对“现代评论派”简单否定的粗暴做法,开始采取审慎的分析态度,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历史评价。陈金淦的《关于“现 代 评 论 派”》(《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丛刊》,1980.3)一文认为,对于“现代评论派”“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给以正确的历史评价,切忌简单化的否定一切和打倒一切。”陈先初的《重评现代评论派》(《近代史研究》,1989.4)一文认为,“在现代评论派成员和《现代评论》的撰稿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不能划入反动阵营,”并进而对其作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集团”的阶级属性界定。甘竞存的《我们应 当 怎 样 评 价 陈 源》(《云 南 师 范 大 学 学报》,1986.4)则最早对“现代评论派”主将陈源的阶级性质进行了重新判断,认为陈源“并非帝国主义的走狗或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志浩的《评鲁迅与陈源的论争》(《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8.4)也侧重于对陈源进行重新评价,认为“整个来看,陈源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走狗,他是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现实斗争中属于中间势力而向右倾斜”。总体上来看,“重评”文章排除了“左”的干扰和历史的成见,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中来展开具体讨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但也显示了较为单一的政治视角,仍然拘囿于阶级论的评价范畴,未能突破政治定性的阐释框架,这自然是由于前一个历史阶段的“现代评论派”研究本身就是纯粹政治性的,政治成见构成了对于“现代评论派”的极大遮蔽,因此移除这种成见成为了“现代评论派”研究走向深入和拓展的前提性条件。
当然,对于“现代评论派”在政治上的“松绑”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如前面提及的陈金淦的《关于“现代评论派”》一文在对“现代评论派”同人进行成分划分时,就依然认为胡适、陈西滢属于“具有较多的买办性或封建性,在一些问题上立场观点反动的人”,并最终“转化成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这种判断的生成实际上是由“拨乱反正”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
如果说“拨乱”是展开对“文革”历史时期的批判的话,那么“反正”则是要重新接续“文革”前的价值判断和观念体系,因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 潮 和 学 术 作 风 在 新 时 期 依 然 产 生 了 影响。
①同时,思想僵化的状态虽然已经破冰,但突破思想的禁锢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然有学者就《现代评论》是否为反动刊物而展开讨论。又如重评文章在涉及到“现代评论派”与鲁迅的论战时,一种普遍性的逻辑前提依然是几乎不妨害鲁迅的绝对权威和崇高地位,吴三元的《试评〈西滢闲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4)就依然断定“当年鲁迅对于陈西滢的批判沉重而准确”,对于鲁迅并不全面的评价则以“由于战斗的急迫,形势多变,鲁迅无暇顾及这一工作”来进行实际上说服力不足的开脱;而林志浩的《评鲁迅与陈源的论争》在着重对陈源言论的两面性进行分析的同时,却又将鲁迅的论争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予以合理化解释,从而放弃了真正意义上的辩证分析。即便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之后、甚至远至新世纪以来的部分着作中,论战中的鲁迅形象也是近乎完美无缺的,而对“现代评论派”的基本态度则是批判的,②这种研究局面和倾向尚有待进一步的扭转。
2.史料的挖掘与重现。由于史料的挖掘和重现本身就构成对于1950—1970年代极度简化“现代评论派”历史叙述的一种反拨和解构,因此是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联系在一起的。史料的不断补充和修正,也使得“现代评论派”的真实面目得以多层次地逐渐显现,作为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得以提升。在这方面,陈漱渝的《关于“现代评论派”的一些情况》(《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0.3)和 《“现代评论派”史料 拾 零》(《鲁 迅 研 究 动态》,1989.9),黄裔的《追本溯源:重探现代评论派》(《中国文学研究》,1991.4),以及马光裕整理的“现代评论派”同人钱端升、陈翰笙、沈从文谈《现代评论》的系列文章,都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效用,提供了研究的重要文献成果。但即使是作为亲历者的“现代评论派”成员关于史事的记述也不尽相同,甚至出现相互抵牾之处。如有关“现代评论派”的创办与国民党的关系的记述,钱端升谈到“《现代评论》与国民党有关系。皮宗石对我讲过,开始办《现代评论》,是汪精卫拿出来的一笔 钱。”
陈 翰 笙 记 述 为 “国 民 党 拿 了 一 笔钱,”但“主要策划筹办这一刊物的除石瑛之外,主要是另一右派政客胡汉民。”
沈从文则只提及“《现代评论》当时即和国民党有些关系,我并不明确具体情形。”而陈西滢则认为是“汪精卫主张在北方办一个刊物,由段(祺瑞)拿出一千银元 作 开 办 费 用。 这 笔 款 是 李 石 曾 先 生 转到。”
这种回忆性记述的浮现所带来的差异性,以及研究者掌握相关史料的有限性,也导致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例如对胡适与《现代评论》关系的考证和定位,陈金淦编撰的《胡适研究资料》与吴福辉的论文《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及历史命运———胡适与〈现代评论〉、〈新月〉派》(《文艺争鸣》,1992.3)均将胡适记述为《现代评论》“主要撰稿人”,石原皋认为“胡适在一九二四年就创办《现代评论》”,白吉庵则指出胡适“早年编辑《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和《独立评论》……”类似的史料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争议,说明了史料本身的难以穷尽和史料研究本身尚有开阔的上升空间,因此,“现代评论派”研究中史料挖掘与整理这一维度一直延伸至今。
由姜文、姜淑红编写的《民国思想文丛:现代评论派 新月人权派》是有关“现代评论派”史料整理的最新成果,主要收录了“现代评论派”和“新月人权派”基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性文章与专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原始资料。在“重评”文章逐渐剥除其政治外衣之后,伴随着史料的不断丰富,“现代评论派”研究也体现出学术上的连续性,走向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入。
二、深化:拓宽研究向度与回归历史情境
1990年代初中期以来,大陆学界的“现代评论派”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颇有收获。一方面是在研究视野与角度上更为开阔,观照的对象上更为具体、丰富,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了回归历史情境的趋向和走向“细化”的特征。
1.研究视野与角度的拓展。这一阶段出现了“现代评论派”研究的首部专着,即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该着作将“现代评论派”放置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背景中,从宏观文化角度阐释了该派复杂的思想体系,揭示了该派作为欧美派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派别的文化模式,并对其文化贡献与历史局限进行了评价,显示了开阔的视野和透辟的逻辑分析能力。稍有欠缺之处在于对作为“现代评论派”主要思想文化资源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论述过于笼统,未能对其自身的复杂变迁作出梳理;同时对“现代评论派”为实现文化理想而作出的学理性探讨和实践性努力未作区别,因而在评价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总的说来,“是一部值得学术界关注的着作”。而就学术论文而言,对单个“现代评论派”同人的研究也纷纷出现。孔庆东的《试论丁西林剧作的唯美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2)一文,从艺术技巧、审美趣味、戏剧观念、戏剧风格等方面论述了丁西林剧作的唯美倾向,文章从文本出发又归于文本,并对比前人观点进行充分论述,显示了作者进行“内部研究”的不俗实力和评论功底。郭汾阳的《“北新书屋”与并非“现代派”的陈翰笙》(《鲁迅研究月刊》,1999.7)一文,试图说明陈翰笙虽然是《现代评论》的写家和编辑,但却与欧美派教授绅士有别;同时强调陈翰笙作为“第三国际”通讯员的身份及其进步性,并最终作出“陈翰笙并非‘现代派’”的结论,文章有着大量细致的史料钩沉,文风踏实,但结论似乎尚可商榷。陈学勇《论凌叔华小说创作》(《中国文化研究》,2000.1)一文概览了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全貌,对其予以了极高的文学史地位;文中援引了有关凌叔华作品的大量评论,勾勒出了凌叔华研究史的线索。此外,其他“现代评论派”同人诸如王世杰、陶孟和、杨振声、张奚若等,也开始得到发掘和较为客观的评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有关“现代评论派”同人的研究中,对于鲁迅最主要的论敌———陈源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较为突出,研究者开始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观照,陈源的文化思想、文化人格、文学创作及其成就、翻译思想、戏剧理论等都得到了较为学理性的阐释。范玉吉的《被窒息的空间———以陈西滢为个案分析20年代中国言论空间开创的尝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2)与《陈西滢文化心态初探》(《江南大学学报》,2003.2)、王树槐的《陈西滢“三似说”的符号学意义》(《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1)、王嵩的《陈西滢:意态从容,“闲话”天下》(《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以及丁晓萍的《现代戏剧理论创建期的独特贡献———陈西滢的戏剧观》(《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1.6)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也共同彰显了陈源的知识分子身份和思想文化启蒙立场,阶级性在整体上 被 放 逐,也 由 此 实 现 了 研 究 的 时 代 性跨越。
此外,借助于新理论和新视角,“现代评论派”研究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毕晓芬的《〈现代评 论〉及 其 文 学 现 代 性 问 题》(《东 方 论坛》,2006.5)一文,将《现代评论》视为同人阐释自己价值观念和争夺公共领域话语权的媒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其文学的现代性品格。易蓉的《〈现代评论〉“公共性”的表达和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2)一文,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现代评论》作为现代公共媒介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阐释,认为其公共性不仅在于言说着知识分子多元的公共关怀,而且用话语形式展开了政治实践,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沈毅的《〈现代评论〉与新诗传播》(《现代传播》,2012.4)以及《〈现代评论〉与科学传播》(《中国出版》,2012.4)两篇文章则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对《现代评论》周刊的新诗传播与科学传播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议,认为《现代评论》对于繁荣新诗乃至推动文化发展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而其科学传播则存在过于专业化、学科分布不平衡、轰动性小等不足之处。范玉吉的《从一本杂志的态度看民国时期的编辑思想———以〈现代评论〉为例》(《编辑之友》,2009.12)一文,分析了《现代评论》“开放”、“独立”、“研究”以及“尚实”的四种编辑态度,但文章对民国时期的编辑思想却并未作出延伸式分析,因此缺乏纵深性和立体感。颜浩的《〈现代评论〉的两个专栏:“时事短评”与“闲话”》(《北京社会科学》,2003.3)一文,认为“时事短评”与“闲话”这两个重要栏目的设置,保证了杂志的办刊宗旨在技术层面上得以顺利实现,并形成了严谨有序的编辑风格,对现代期刊的发展有着借鉴意义。总体上而言,运用新理论和新视角进行“现代评论派”研究的成果还比较有限,这一向度的评论空间尚有待开掘。
2.回归历史情境的趋向。在拓宽研究视野与角度之时,“现代评论派”研究还重视历史场景的回归与再现,增强了研究的历史感。阎晶明的着作《鲁迅与陈西滢》以七章的篇幅较为全面、客观地追述并评议了1920年代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几个回合的论战,该着作在详尽的历史叙述基础上叙议结合,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交代论战的原由及经过,立论扎实而充分。就单篇论文而言,桑兵的《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5)、钱理群的《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鲁迅研究月刊》,2002.11)、傅 国 涌 的 《〈语 丝〉与 〈现 代 评论〉———以“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为例》(《文艺争鸣 》,2003.4)、黄乃江的《从〈现代评论〉的两度“变风”看“现代评论”派》(《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5.
1)、陈于武的《从教育风潮看教育自由———以〈现代评论〉的相关讨论为中心》、卢毅的《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晋阳学刊》,2007.
2)、黄亦君、李晓兰的《〈现代评论〉与善后会议》(《社会科学论坛》,2009.4)等文章,也都将研究对象放置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细密考察和钩沉现象、事件的来龙去脉,注重在原初的历史事实之中作出谨慎判断,并观照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些文章在“主体性”反思的知识气候中,避免了以先入为主的立场粗暴地进入历史的趋向,也搁置了“主体论”的文艺学阐释所持的价值尺度,而是在历史场景之中去观照对象发生、发展的多重制约因素,力求做到“论从史出”,这种作风在整体上提升了研究的学理性和客观性。
这种研究倾向在新近出版的另一本“现代评论派”研究专着《现代评论派与192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作者从近代史研究的角度对“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观在国内政治、外交、民众运动等方面的体现,以及该派的历史困境等进行了论述,详细爬梳了善后会议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其时中国内政外交的历史风貌,史料运用扎实、缜密,避免了行文的凌空蹈虚,从而使研究中的“史学”本义得到了彰显。同时,上述文章及着作在选题上还显示出“细化”的特征。研究者普遍放弃了宏观的立论和抽象化的叙述方式,而是从“个案”着手,在历史细节中追寻现象的原初风貌。这种研究态势重分解而轻归纳,并由此缺失了一种把握大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但又以其缜密、严谨的推导纠正了多年来忽视微观考析的倾向。
三、有待提升与开掘的不足之处
毫无疑问,新时期以来的“现代评论派”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升了“现代评论派”的学术地位和其作为研究对象的丰富性,拓宽了研究视野和角度,并呈现出回归历史场景的倾向和“细化”特征。但总体上而言,学界对“现代评论派”的研究仍然是不足的,在比较的视野之下,这种不足就更为明显。就流派研究比较而言,“现代评论派”研究大大逊色于“学衡派”研究,后者在“五四”思想史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多有相近之处,并且在新时期到来之前的历史叙述中同样备受冷落、遮蔽和批判,但随着反思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国学热”的兴起,“学衡派”受到了极大关注,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和焦点,相比之下,“现代评论派”的研究则显得稀落、零散。而同作为“胡适派”文人群体的组成部分,“现代评论派”研究在整体上也不如《努力周报》同人研究与“新月派”研究,甚至“现代评论派”同人被分化而散见于二者之中,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就期刊研究比较而言,“现代评论派”最为主要的舆论平台《现代评论》周刊的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
实际上,为了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新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加强了文献的发掘和整理,由于受到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布迪厄场域理论等的影响,对现代报纸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的发掘和研究尤有力度,形成了近年来期刊研究蔚然成风的大势,《小说月报》/《新青年》/《晨报副刊》/《语丝》/《现代》/《论语》等报刊杂志都较为彰显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梯队,相比之下,“比较地着重于文艺”的《现代评论》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阐释。因此,在整体上,新时期以来的“现代评论派”研究不仅并未构成劲势,甚至并未获得与其文化史价值与地位相匹配的研究态势,这就促使“现代评论派”研究需要在诸多方面更新研究观念、拓宽研究思路、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准、最终推动研究走向深入。
具体而言,首先是“现代评论派”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由于“现代评论派”长期以来被定性为“鲁迅论敌”,这一身份定位实际上造成了对于“现代评论派”的遮蔽,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鲁迅研究。如在有关“现代评论派”与鲁迅论战的研究中,姜振昌、王连仲的《杂文家的窘迫和失重———重评“现代评论”派》(《东岳论丛》,1997.5),阎晶明的《无所顾忌的作家与教授———我看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鲁迅研究月刊》,1999.7),以及徐文海、李淑敏的《“呸!”来“呸!”去的“学者文人”———鲁迅与陈西滢的几个回合争斗》(《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2)等文章,虽然已进行了颇为辩证的分析,充分注意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论战的个人性与文化性,使得“现代评论派”不再是一个备受唾弃的研究对象,但基于鲁迅在当代中国所获得的极为显赫的文化位置,研究文章在整体上依然存在从鲁迅单方面取证和论证的倾向,该派与鲁迅之间的论战,往往被解读为鲁迅战斗性的重要佐证材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评论派”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
其次,在研究视野上需进一步均衡、全面、清晰。已有研究对“现代评论派”与鲁迅的论战挖掘颇为有力,这也反映出鲁迅研究在当代中国学界所具有的极高人气;但对“现代评论派”的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思潮的梳理和研究则较为欠缺,单篇论文尚且未有这一选题的研究成果,而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与孔祥宇的《现代评论派与192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两部专着对于“现代评论派”所接纳和移植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都停留于简略交代和泛泛而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流变、不同传统路向、价值要素以及本土化过程都未能真正厘清和进行充分的论述。此外,已有研究对历时四年、共九卷209期的《现代评论》杂志的观照总体上也较为薄弱,政论性和文艺性文本受到较多关注,而“现代评论派”有关经济、历史、科学、教育、法律等方面的文本尚未被充分开掘,并且诸多研究文章停留于描述性地呈现刊物对某一专题的探讨,而缺乏系统性的价值判断,在文本开掘上还留有较大的评论空间,尤其是《现代评论》进行过着力宣传并隆重推出的四期增刊与诸种“现代丛书”,尚未在整体上纳入“现代评论派”研究领域并得到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观照。同时,一些研究在“《努力周报》同人群体”、“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等群体的厘定上仍未明晰,如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 代 中 国 自 由 主 义》和 沈 卫 威 的 《自 由 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都将“现代评论派”归为胡适所引领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但实际上前者更多地是将诸多“现代评论派”成员纳入《努力周报》同人行列,而后者则将其收列于“新月派”旗下,忽略了“现代评论派”独立存在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从而造成了对于该派极大的遮蔽。再次,应改变在研究框架和格局上普遍较为狭小的局面。
研究文章在着力于具体探讨“现代评论派”思想言论的某一侧面之时,往往缺少相应的理论框架和对于研究对象背后的思想文化生态等的纵深性透视,论述在整体上较为浅显,立体感不足,而在整体上也极少将“现代评论派”纳入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乃至整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因而也就忽略了对其思想史地位、价值功能以及缺失的判断与论述。同时,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僵化或偏颇的研究思维模式。某些论述受到“左”的模式时期既有权威性观点的支配,对“现代评论派”仍持严厉批判和轻视的偏颇态度,使研究丧失了真正在学理层面进行阐释的意义,这一倾向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着作的写作中尤其明显,因此应进一步突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学术民主的氛围中提升“现代评论派”研究的学理性与学术品格。此外,应进一步运用新视角和新理论对“现代评论派”及《现代评论》文本的丰富内涵进行发掘和展示,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具备立体感和层次感的研究态势。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正和改善研究观念、视野、思维及方法等方面的不足与偏颇,将促成“现代评论派”的研究不断拓展评论空间并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
参考文献:
[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M]//翟秋白选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424.
[2]李新,等.中 国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 通 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64.
[3]马光裕.钱端升谈《现代评论》周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2):295-296.
[4]马光裕.陈翰笙谈《现代评论》周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2):293-294.
[5]陈漱渝.“现代评论派”的一些情况[J].鲁迅研究动态,1980(9):51-54.
[6]马光裕.沈从文谈《现代评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4):261.
[7]陈金淦.胡适研究资料[Z].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