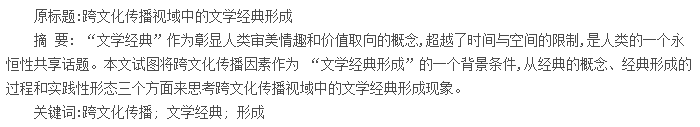
关于 “文学经典形成”这个问题的讨论,西方学术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展开,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关系到人类自身价值的永恒性话题,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本文试图将跨文化传播因素作为 “文学经典形成”的一个背景条件,思考在和同质文化语境比较更为复杂的异质文化即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文学经典形成现象。
雷蒙·威廉姆斯在 《传播》一书中对传播给予了一个定义: “我们所指的传播是什么呢?
这个词语在英语中最早的意义能够被总结为人与人之间思想、信息和态度的传递。在这本书中,我所指的传播是思想、信息和态度被传递和接受的机构和形式。传播是指传送和接受的过程,社会是传播的一种形式,通过社会经历被描述、分享、修改和保存。我们已经适应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描述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据经验,这种对传播的强调断言,人和社会并不是局限于能力、财产以及生产之间的关系中的。他们在对经验进行描述、学习、劝说以及交换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
传播将社会中的个体放置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中,提供人们分享各自经历、感受、话语和思索的机会。一般来说,文化传播分为文化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文化内传播是由两个处于同种文化背景的交流双方做出的行为,一般是探讨和描绘单种文化的类型和特色。而跨文化传播则是指交流的双方分别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信息传播过程中需要突破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主要关注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跨文化传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总是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在文化协调过程中,传播主体会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缺乏安全感。
“跨文化”,在抽象意义上而言,借用霍尔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在信息对象基础上的编码和解码的主体性行为,大部分是在人类主观性意图的指导下进行的具体实施和操作,它的复杂性缘起于不同文化中人类行为和认知的不同构建。具有现代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建立在哲学视域上,将文化视为个体或群体的具体表征,将跨文化交流的不同的动态概念、传播行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和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
一、跨文化传播视域中文学经典的概念
经典是什么? 它是一个想象性的概念,却又为何具有魔力? 它决定了哪些作品得到永久性保存,而绝大多数的作品会逐渐被历史所遗忘。经典的言下之意是权威吗? 是否这个名词的使用意味着被选中的是神圣化,而未被选中的则是边缘化? 这里的选择是由谁做出的? 是我们一贯所认为的杰出人士或是资历深厚者商讨制定的结果,还是领导人类精神事业方面的圣者的职责? 文学的经典性状态是如何获得的,即经典化过程应该如何描述? 它是缘于文本内在的自我构建,还是取决于文本对未来作品的影响? 一般认为,经典的概念属于神秘时代的秩序,是需要适当的保存和欣赏的,旨在保存传统,继承文化血脉。布鲁姆对经典的起源以及那些做出决定的特权力量是这样阐述的: “经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词汇,如今已成了为生存而互相争斗的文本之间的选择,不管你认为这个选择是由谁做出: 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或如我主张的是由那些自认为被某些古代名家所选中的后起作者。”
“文学经典”这个术语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发生了很多语义演变,本文的讨论是建立在其现代性涵义的基础上,即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 “文学经典是指获得批评家、学者和教师的一致认同,并被广泛承认为 ‘主要’的,其作品被经常赞誉为文学 ‘杰作’的作者,以及经典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一定时期内被不断地复印出版,被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频繁地讨论,很可能被收入 (文学) 选集和纳入大学课程教学大纲之中,并被冠以‘世界杰作’、‘主要的英国作家’、‘伟大的美国作家’这样的称誉和名号。”
哈罗德·布鲁姆在 《西方正典》一书中说:“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莎士比亚赐予我们的不仅是对认知的表现,更多的还是认知的能力。莎士比亚与其同辈对手的差异既是种类也是程度的差异,这一双重差异决定了经典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你可以无止境地梦想以种族中心和性别的考虑来取代审美标准,你的社会目的也许确实令人赞赏,但正如尼采恒久地证明的,只有强力才能与强力般配。”
经典作为表征一个民族美学理念、审美情趣以及思维模式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个民族区域的所有人群的情感意志、美感体验,随着历史长河的流转构成了由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荣格提出的心理学现象,即集体无意识。这是一种由于历史积淀而作用于人类心理深处、达成普遍共识的人类本能和体验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经典作品为自己的民族本真性的保存和升华提供了最好的支持。“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如果在职业、生活习惯、理想和年龄各方面都各不相同的人们对于一部作品都异口同声地说好,这许多不同的人的意见一致,就有力地证明他们所赞赏的那篇作品确实是好的”。
这是朗吉罗斯在 《论崇高》中对经典作品的定义。本雅明为文学经典赋予一道美丽的光环,正如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边休憩着一边凝视地平线上的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或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那就是这座山脉或这根树枝的光晕在散发”,这道光环虽然近在咫尺,却又是独一无二,文学经典所具有的自身价值和永久性是在时间维度中经久不息的,而且在一个文明社会的文化秩序中必定存在一些值得膜拜的经典作品树立权威,引导人们的统一价值观。陶东风在《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一文中指出,经典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是被视为与权力元素相脱节的, “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 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并且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否定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颠覆了传统的纯艺术性和美学属性,认为: “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就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同时也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可以说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就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由于经典是传统文化的凝聚,所以,通过对经典命运的追踪,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文化传统的历史遭际。”
经典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作为一种串联知识性的工具,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学习机制和策略,不仅节省了阅读者对知识感应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挖掘了他们对知识吸收的潜能。同时经典由于是筛选过的精华,提供了一种捷径,使人们以较为轻松的方式与核心准则面对面相接触。在文学世界的更新换代中,新作品会推陈出新,而纵横在新作品和旧作品之间的动态选择过程并不是一个全封闭的个体,它也是期待着普通读者的私人化参与,尤其现在社会网络等大众传播技术十分发达,为其创造了有利的空间。也许对于每一位爱好文学作品的读者,无论他是业余爱好者或者是专业文学工作者,每个人心中都会珍藏一些对自己影响深远、印象深刻的作品,这些文本激发了我们的灵感,我们也许对其中的篇章和语句始终疑惑不解,但是却对其永生难忘,这就是属于每个读者的私人经典,它的存在是个体性的行为,但却意味深长。
二、跨文化传播视域中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
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起始于对所保存的文本的筛选,如果文本有幸被挑选中,而最终得以保存和流传,这就标志了其文学文本再生产历程的实现。对文本的选择就是对价值的选择。在一个具体化的价值的世界,美学价值和我们所熟知的其它各种价值一样,面对读者,自身价值的直接消费者,并不是采用一种想象性的虚拟方式,而是以一种能够被真实感受的方式。基洛利将文学经典的形成视为文学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过程,认为经典化分析以及其他文化表征设置了一个真正的具有建设性的框架,经典化判断是体制所设置的,强调学校作为传播经典的一个场所,所发挥的复制社会秩序的作用。“经典形成的历史是属于文学生产的历史,因此是作为生产的一个条件; 同样的,文学生产是经典形成历史再生产的一个条件。因此,文学文本的生产不能被简化为一个具体而唯一的社会功能,甚至都不能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功能”。
“再生产”顾名思义,是除去文本原作者创作生产外的二次或者三次生产,它延续了文本在来世的生命,为其成为经典、进入复活状态提供了途径,同时这种文学文本的再生产为文本价值的升华奠定了基础。
“经典”这一称号仅仅存在于作品的身后时代,即当作者离开作品与世长辞以后。经典性这个词语是和死亡相关的,因为作者只有在生命终结后才有可能被追封为圣者。而相应地对于那些仍然活跃在现代话语语境中的经典文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比喻为一种神符,逝去的作者赋予它特权,旨在帮助其发挥圣者的作用,为生者或现代的读者贡献力量。经典的形成离不开一个持续性的筛选过程,哪些应该被放弃,哪些值得继续,都需要一个经受得住考验的准则。存在历史的长短是经典作品自我积累和沉淀的条件,它的魔力在于能够超越时间和时代的鸿沟。
人们习惯说继承经典,表明经典一定是受人尊敬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从文化历史学来考虑,我们其实也会因为一些很充分的理由去挪用或者改写经典。文学作品、艺术品以及其它一切关乎审美的物质都是相对而言具有持久性的符号,很无奈地说,有时候经典并不是可靠的标签,因为那些被贴上经典标签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有时仅仅是因为各种各样外在的因素,与它们内在的圣洁感和卓越性无关。这样人们就明白经典的形成有时候被无端地强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致使人们潜意识认为有资格成为经典的作品都必须是完美无暇的。
瓦尔特·本雅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人物之一,将意识形态策略融合进入艺术审美鉴赏理论的建构之中,认为文学批评不应该局限于文学的文本形式,而应该将读者或作家的个人审美体验扩展为一个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私人性和公共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等方面都妥协稳定的状态,他是 20 世纪影响最为深远、号召力最强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本雅明认为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自身所承载的意义是可以脱离作者的本意而得到无限衍生的。当读者在一定的传播过程中获得了作品,就似乎接过了一个接力棒,担任起了阐释性阅读的任务,颠覆了传统的纯粹消费者和被动的接受者的角色,而转变为积极的合作者和参与者。在他自身的这种阅读过程中,他不仅令自身获取作品意义,同时也将自身的思维融入其中,填补作品中的意义空白,使原作品的生命力扩充,获得更加蓬勃的生机。本雅明将这样一种艺术作品传播过程称为复制的过程,他认为所有艺术作品都是具备这一特性的,“然而,即使最完美的复制,也不能欠缺一个基本元素: 时间性和空间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这一艺术作品的特殊存在,决定了它有自身的历史,是穿越时间的存在物。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的流逝使艺术品在其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也包含了艺术品可能所处的不同占有关系的变化。前一种变化的痕迹只能由化学或者物理方式的分析去发掘,而这种分析在复制品中又是无法实现的; 至于后一种变化的痕迹则是个传统问题,对其追踪又必须以原作的状况为其出发点”。
因此经典作品的宝贵价值当然并不是单独存在于它作为一篇作品的个体,而是通过传播这个辅助性工具而得以扩散性表达,当很多作品排列整齐,等待经典化过程的筛选时,我们的注意力不仅要落在这些作品上,也要聚焦在作品和作品之间、作品和读者之间、读者和作者之间以及阅读空间时间性和原作时间和空间性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具备这一前提条件就很难将作品自身独特性和其与生俱来的传统性组织肌理完美结合,展现出其原真性的价值。传统的观点告诉我们,经典作品一定是具有超群的文化价值,具有很明显的纪念意义,而在实际情况中,很可能一些经典作品自身并不制造令人难忘的价值,它的意义仅仅是在于它作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一分子贡献出了力量,这种真实的社会过程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价值的再生产。
对于跨文化传播视域中文学经典的形成,我们还需要关注经典文本的具体流变过程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 “误读”或者 “水土不服”现象。根据基洛利的理论,经典和非经典之间的区别可以总结为包含和排斥的区分,同时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一组二元对立。哪些是适合被包含,而哪些需要被排斥,这是由社会性实践发挥作用的,这种实践必须要公正、令人信服才能达成共识而形成社会性一般准则。经典作品中所彰显的“表征”目的以及非经典作品所传达的信息,都需要通过实践性行为来给予反应和展现。同时经典和非经典之间也存在一种纯粹的关系概念,非经典虽然被边缘化,但也是读者阅读背景中的一部分,隐含着另一个文本生产和接受的封闭体。
这里的包含和排斥的对象都是社会性指示物,被种族、性别、阶层或者国家状态所定义,所有的作者创作状态和文本的具体表达都可以在经典形成过程中得到表征。在经典化过程中,非经典范畴的确立似乎十分被动,它是被批评实践排斥而逐渐形成的一些被放在边缘化位置的作品。有时候通过阅读这些非经典作品的声音,可以发现社会群体别样的表征,而这往往发生在主流写作领域被不公正的力量操纵时。这样一来,这些被忽视和边缘化的所谓的非经典作品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身份恢复,也就是说它们似乎在以一种无声的力量表示抗议,或者说这些被贴上非经典符号的实际经典作品在一个先入为主的经典性之外的特权地方得到重新配置,获得了自由。
经典作品在跨文化环境中的相互 “不兼容”主要表现为经典的传播受阻现象,而最突出的一点是表现在语言上,运用一种语言去表达最初是用另一种语言进行阐述的文字,其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 这需要译者付出什么样的主观思维? 译者在此期间抱以什么样的目的呢? 译文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有没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意义缺失和磨损,或者将这种损失减少到零? 这个转换过程的背景就是源文以及它所处的环境,任何一篇源文一定是深深地镶嵌在一个复杂的语言学、文本学和文化意识形态学的背景之下,利用它所处环境中的自然关系来实现自身所表达的意义以及文本交流的意图和跨语际阐释的效果。这是一个将文本从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然环境中剥离开来,重新移植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并且接受新语境对其创造的过程。源文起初一直是生活在一个动态和谐、均衡稳定的语言文化氛围之中,一旦脱离了本身的环境,文本意义会本能性地破碎,译者就是这一干扰行为的操作者,他们很勇敢地将源文文本连根拔起,小心翼翼地试图将其敏感的意义移植到目标语境中。也许这句论述能够帮助人们亲身体会到为什么那些蹩脚或者不负责任的翻译作品读起来或者听起来那么的虚伪造作和不自然,这一方面生动地证明了翻译过程的难度,同时也提醒从事这一行的译者肩上所担负的重任。
以下选取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黄兆杰 (Siu - kit Wong) 、E. R.修斯 (E. R.Hughes) 以及罗易丝·富塞克 (Lois Fusek) 对曹丕 《典论·论文》中一些经典语句的四种译文进行比较赏析,体味译者们逐字逐句细细斟酌,每一个英语对等词慢慢推敲,成功地承担起了作为译者的神圣职责,将译文视为与源文同等地位的一种生命形式,虽然没有 “前世”,但是却具有无限的 “来生”。
例: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宇文所安: People are good at [or fond of]making themselves known; but since literature(wen) is not of one form (t'i) alone,few can begood at everything. Thus each person disparages thatin which he is weak by the criterion of those thingsin which he is strong.黄兆杰: The truth is that it is easy for us to seethe particular merits in ourselves and that,while lit-erature encompasses a variety of styles,few writersare equally accomplished in all of them; as a result,what is one's own forte often becomes grounds onwhich one levels attacks on fellow - writers gifted inother ways.E. R. 修斯: Men in their own eyes are good[at writing],But since literature does not consist ofone style only,there are very few who are good allround. The result is that every man,because of thatin which he excels,despises that in which he comesshort.③罗易丝·富塞克: Everyone prides himself onhis own strong points and deprecates the skills inwhich he is deficient. This is because,on the onehand,men are generally fond of showing off,andalso because few are good at all forms of literature,since literature is not a single ent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们都喜欢表现自己,但是文章并不仅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所有体裁都擅长,所以各个人总是用自己的长处去轻视别人的短处。这里的 “见”是通假字,同 “现”。就第一句而言,黄、修斯都是直接误读源文产生误译,而富塞克译文中的 “show off”表明炫耀和卖弄,是个感情色彩强烈的贬义词,在这里的采用是与源文句意造成偏差。另外对于 “体”的翻译,富塞克的译文也是误译,没有正确解释“体”作为体裁,即写作形式的本意。宇文的译文将 “善”的两种合理的解释都译出,将源文意义准确表达。对于后半句,我们看到这四篇译文分歧的重点在后一个 “善”字的理解上,宇文所安和富塞克都译出了 “擅长”的意味,而修斯误译为 “善”的形容词意思即 “好”,而黄直接将 “善”理解为引申义 “熟练的或者多才多艺的”,这些都是由于误解和误读而造成。其他的译者在译文形式上都是采用了遵从源文句序,唯独富塞克采用了颠倒式的句序,流畅度和句式工整度稍有欠缺。
三、跨文化传播视域中文学经典形成的实践性形态
可以说,文学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与文学经典化过程紧密相连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美学价值观和文化资本的构建手段,经典的形成前提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它的价值归因于自身在客观历史进程中所肩负的传统性任务,即执行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化保存,而这种文化保存方式公共领域作品流通以及文学传播过程中,是在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的,而跨文化文学传播的终极目标理应是依据几个重要的实践性形态完成异域文化语境中的经典化形象重构。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具体经典形成的实践性形态因子包括翻译文本、文学选集、文学史、文学参考书、学术界的评论研究和出版等文本再生产方式。
(一) 文学选集及其衍生物
和博物馆的管理者挑选放置在馆内供参观者欣赏的展品一样,选集的编者们也要精心筛选出那些被认为具有文化重要性或者销售价值的选集成员。而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选取过程中,编者们针对自己所关心的某一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使所持有的选集成为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供读者从中吸取精华。“选集的编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单一型的,也有组合型的: 即旨在一个给定的领域呈现出编者认为是最好或者最具有特色的文本 (或者其它印刷物) ,或者是他们所判定的对于一个给定读者群而言最有用的信息。选集对文本的处理工作类似于博物馆对艺术品以及其它具有文化重要性物品: 保存和展览它们,并且通过选择和安排这些展览品,突出对一个给定领域的理解,使关系和价值显现,或者是培养品味。简言之,选集试图为文化(一个分支) 提供结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即是以物质的形式贮存在国家仓库,同时也是对这个邀请做出回应的个人的活性文化”。
作为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传承和展现的一种方式,文学选集是具有实用性的,从体积上来说,一本文学选集涵盖了一段历史或者一个国家的文学精髓,但是却不像文学丛书那样从数量上给读者 (尤其是普通读者) 带来一种阅读压力。另外,一个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和一部选集之间具有显著区别,即前者是展示实实在在的艺术品,有视觉和手工制品,艺术在原则上是被整个世界所欣赏的,能够穿越国界和跨越文化区分。而后者的组成成分是文本,尤其是当涉及到不同国家和语言时,它是需要翻译,进行语言上的转化,才能为其他语言团体的成员们的理解提供可能性。
旨在从微观角度予以考虑,本文想要借用中国文论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案例。中国文论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思想根源来自于传统哲学、美学、宗教学等,自古以来以和谐、中庸为核心内涵,强调真情实感的表达、推崇以虚表实,主观先于客观、感性优于理性。它的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三个历史进程,“第一部分是1886 年到 19 世纪末期,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缺乏足够的认识与了解,对中国文化充满向往与猜忌,其中传教士、商人与外交官三种身份群体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第二部分是从 20 世纪初到20 世纪 40 年代末,此时国际汉学的中心还是在欧洲。第三部分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此时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是美国”。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的跨文化传播贡献出了很多重量级选集作品,代表性的是 《印第安纳传统中国文学指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 《中国文学: 古代和古典》 《诺顿中国文学选集: 初始至 1911 年》 《中国文学论文选》《翻译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话题: 概览和书目》《简明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 《早期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艺术理论》等。对于经典作品的判定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人类的文明遗产,使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精心呵护下继续颐养天年,而且是为文学研究创造一个理想化的模式,即文学世界需要提供一个结构典范、思想深厚的创作标准。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些采用选集形式的中国文论的美国研究著作就可以被视为一项准则,它们在世界汉学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而且主要关注的兴趣点、侧重点以及论述形式都各显特色,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中国文论在美国传播以及经典化形成的主力军,经常在美国汉学界的重镇之地大学课堂上被选定为教科书而得以广泛传播。中国文论在这些选集中所受到的重视和阐释在一个侧面上确立了其经典的形象,在传播的过程中搭建了一座桥梁。除此之外,这些选集为汉学工作者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辅助性作用,它们所彰显的卓越的学术性价值、严谨的学术方法、精准的学术信息、高深的学术思维势必影响和指导着汉学研究事业循序渐进式的发展和演进。
(二) 跨文化传播的中介———翻译
研究一种文学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中的传播需要考查处在不同标准的文化表征,即这种文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融入其中,被异域的接受者面对,并且给予回应。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跨文化中介就是翻译。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跨文化现象,涉及到将叙述和文本进行转换,从一种表述形式转为另一种,将文本从一个历史性背景传送到另一个背景之下,将意义从一个文化空间转移到另一个文化空间。翻译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运动,人们更多的将翻译理解为经验性的语言机动,但是会在新的背景下去重建物质的和文本的过去,这也是翻译的另一种形态。在从一个领域或条件转换到另一个领域或条件的过程中,源文的事件背景和理想一定会重新改装; 翻译的结果是使源文在本质上并不再是源文,而是一个身份已经重新定义的新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译文和源文之间无法划等号的客观事实寻找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 “借口”。
同时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应用文本或者语言的过程,而且是一种解码或暗示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发生在文本、语言和文化之中的。从本质上说,哪里有语言,哪里就有翻译。所有这些文本同时也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完善,即哪里有文学,哪里就有翻译,在这里列举美国学术界出现的代表性中国文论英语译本,一般来说这些译文中有的是全文翻译的,有的仅是部分段落的选译,有的以译著的形式出现,有的出现在博士论文或者专论的部分章节中。它们是 《文心雕龙》译本 (共有五个不同版本) ,作者分别是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宇文所安 (部分选译) 和 E. R.修斯 (部分选译) 。 《典论·论文》全文译本(共有 5 个版本) ,作者分别是 E. R. 修斯、缪文杰、富塞克、宇文所安和黄兆杰。《文赋》全文译本 (共有 5 个版本) ,作者分别是陈世骧、方志彤、康达维、E. R. 修斯和黄世杰。美国汉学界的这些中国文论英译作品虽然主要限定对象是英语世界中汉语及文学研究者、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学生以及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并不包括身处在中国自身语境中的本土研究者,但是当这些本土学者比照阅读这些译作时,犹如在给自己照镜子,译文和源文之间无法避免的语义偏差、理解空白以及语境隔阂往往能够从侧面打开一扇窗口,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既定思维和阐释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和遗漏。如果仅仅将翻译视为一项传播工具或者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桥梁,那么任何能够准确如实、忠实通顺、不制造晦涩语义和茫然疑问的译作都应该广为散播和积极鼓励。在中国文论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任何对于中国文论作品的翻译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为不同层面的读者提供了帮助。鉴于中国文论作品本身极强的专业性和学术难度,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受众范围较为局限,数量也颇为缩减。以上所提及的翻译作品,几乎所有的译者都是相关文论小方向的专家学者,他们身处美国汉学界的语境,继承了其严谨苛刻的学风和译品,译文中注释、注疏、典故来源、格式和体例等丝毫不得含糊,这些较佳的译作不仅可以帮助美国读者阅读,而且反过来可以帮助中国学者补充其对之前原文理解和思考的不足,取得双向交流的佳绩。
(三) 学术研究的积淀
文学评论的本义是对文学作品的阐述、评价和研究。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评论是建立在文学理论基础上的综合性审视,文学理论中抽象和哲学性的讨论将文学评论方法和方式进行深层次展现。文学评论一直以来被视为是文学作品的补充性活动,帮助读者更好地融合、进入超越文字的文学思想境界。然而,文学评论的角色绝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性定位,它是一种独立的思想形式,是文学作品公共身份得以认同的精神渠道。正如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其体裁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等,当它们步入读者的视域,最初作者在文本中传达的源身份将会被广大读者结合自身经历和认知氛围而进行更改,于是作品的公共身份超越了源身份,在作品的再生产过程中得以彰显。而评论者这一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他们一定要秉持着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分析对象,传统的观点甚至要求他们避免自身情绪的波动,以及愤怒、悲伤、大喜、阴郁等极端情绪的冲击。
他们必须在阐释作品意义和传达自身思想之间找到平衡点,使自己的文学评论论据确凿并且具有启发意义。通过对他人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成功的评论者借此推广和展现了自己价值观和独特的批评视角和理念。总而言之,文学评论即广义上的评价过程,其宗旨是超越最简单形式的美学判断,本质上是一个自我声张、自我展现以及自我解释的过程。美国汉学界展开对中国文论的研究和阐释,最常用的一种学术方法便是将西方思想和概念,尤其是现有的西方文学理论思维植入跨语境的诠释之中,由于中国文论本身叙述的模糊性和表意的深刻性,西方研究者采用这一方法有助于西方读者迅速将思维模式交替变换于中西方语境之中,借助自身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西方文学理论,在跨文化的对照物身上寻找类似、对应或者相悖的思想热点,通过一系列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以及穿插研究手段,帮助西方读者消除文化隔阂,溶解相应的陌生感,这些研究结果必定会挖掘出一些类似点、不同点以及适合于相互转换的连接点。代表性的评论作品有: 吉布斯·唐纳德·亚瑟的 《〈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思想》、邵耀成的 《刘勰: 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赵和平的 《〈文心雕龙〉: 一篇早期的中国修辞学论文》、刘若愚的 《中国文学理论》《语言—矛盾—诗学: 一个中国观点》 《跨语际批评者》和王靖献的 《金圣叹》等。通过对这些代表性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总结四种美国学者最常用的评论路径: (1) 依托一个最基本的西方文学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模式通常在文本分析方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易于将中国文论视为研究对象放置于这一背景理论构架中进行比照和归类性分析。他们认为通过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对中国文论的分析,可以帮助美国读者更加容易地理解中国文论思想,理论性地将处于两种文化背景之下的思想观点进行比较性观察。叶嘉莹也曾指出中西方诗论在理论模式和立论根源方面的不同之处,强调了双方各自独有的优势特点,以及双方以互补共进为前提的合作共生。
(2) 对中国文论中的一些重要术语抱以特殊的兴趣,通常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对每个术语在其所处的语境下的特殊意义进行阐述。这种“以西释中”的比较研究方法,将中国文论家在作品和文字中传达的理论主题和问题意识进行二次叙述,凸显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学思想之间的磨合和抵触之处,引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借助于自身比较熟悉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背景达到跨文化的思想共识和理论契合。 (3) 将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或者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放置在一个平等共存的平台进行比较性研究,持有更加公允的态度面对两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中构建的理论源泉。这一思索源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中国式思维模式以 “天人合一”为本,天、地、人、自然万物以及物质世界都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而对于西方思维模式而言,二元对立的理性分析思维倾向于将一切物质存在或者情感思维都放置在一分为二的系统性思维背景之下,对其规律和准则展开思索。 (4) 针对一些重要的中国文论作品展开概览性的研究、全面性的介绍和解释这些作品的意义、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历史环境、作者的文学批评观和基本文学术语的概念等,通过严谨的叙述态度,对文论原文仔细钻研,以西方学术界的视野为美国以及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和进一步接受创造了坚实基础和便捷的渠道。
四、结语
本文所谈的跨文化传播视域是指一种文化植入另一种文化的融合行为,此过程的构建主体是源文化本身的特性以及目标文化为其所提供的环境,在这其中必定存在一个排斥、冲突、磨擦和融合的四步曲,在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中最有趣的应该是思考源文化在目标文化中所寻找和最终确定的位置,也就是跨文化传播过程所获得的结果,表征在具体性的实践性形态因子之中。既然文本再生产实际已经成为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么在事实上一部作品在进入读者视野之前就早已经跨入了经典化的范畴,即首先是出版、翻译,随后是书评、学术评论文章,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在教科书、选集和百科全书中,而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参与性合作反过来也加强了作品的意义。翻译文化理论家勒菲弗尔将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翻译、编选、评论以及编辑过程都视为 “改写”的表达,改写作为一种操控形式,可以创造出另一个文本形象、文学体裁或者表达方式,从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这些多种多样的改写形式可以接触到很多层面的读者群,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为了理清这一经典形成过程,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整理其逻辑层次,首先我们要确定源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定义,源文化作为主体进入目标文化,目标文化作为客体吸收和接纳源文化,那么两种文化在政治背景以及经济力量这两个方面是否处于对等关系,还是力量悬殊? 两种文化在双向融会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尊重,或者是否维护了自身的个体性? 遇到文化重合性时,两者一定是平稳交流,而当摩擦发生,两者又是如何磨合,“改写”与 “挪用”在具体实践性形态因子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经历了磨合的阵痛后,源文化中哪些价值理念被实践证明具有思想形态上的独特性而被拒之门外,哪些又被认为是适宜转换的,有能力跨越文化可接受性的界限,从而导致了经典性地位确立的契合与迥异? 总之,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绝不是作品依赖自身这份财产而进行单调的传播的个体性行为,而是以自身为中心,以网状轨迹辐射开来,与其他作品产生关联、互相映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