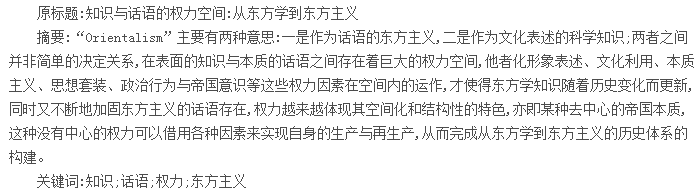
Orientalism(东方学,又译“东方主义”)是阿拉伯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的成名作,也是后殖民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一套“Orientalism”话语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影响,从而成为讨论殖民时代以后全球状况的关键词。萨义德在该书绪言中将“Orientalism”定义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一门学科,对东方进行学术研究,名为东方学。
萨义德对这一学科的历史、演变、特性和流布进行自己特有的思考与阐述。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它建立在“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关于东方的思维方式,并以此来“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性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
三是在前两种含义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限定,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时间上是 18 世纪晚期以来,西方(主要是英法美的东方学界)怎样表述东方(主要是指中东伊斯兰世界),以及这种表述与帝国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
西方的学科建制自近代始,受科学精神与实证主义的影响,这些学科的成立都以对对象领域的客观、公正、准确地研究为基础,进而形成该门学科完备的具有真理性与科学性的知识体系。
“Orientalism”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关于东方世界的准确表述,即便存在错误之处,也能根据东方的现实进行修改,以符合客观对象的真实状况,确保其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真理有效性。事实并非如此,萨义德创造性地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知识与安东尼奥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放置在西方对异文化的表述领域及其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上,敏锐地察觉到这门学科所隐藏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权力关系,以及背后的帝国运作机制,至此“Orientalism”三种含义纠结在一起而形成了福柯意义上的作为一种话语的东方主义。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东方学又是如何成为一种东方主义话语的?在两者之间的时空场域内,权力因素又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问题成为理解“Orientalism”的关键所在。
一、他者化与文化利用
一般而言,在各国各族的文化交流、碰撞以及对对方的文化表述中,总是伴随着文化想象,建构异文化的他者形象。他者形象是对异文化进行书写的必然结果。作为民族文化建构的产物,他者形象也是对自身文化存在与特性的确证。因此,他者在民族文化自身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说幼儿在镜中看到镜中的影像,开始促成“自我”的形成。
“人是通过认同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他的精神分析学,把人的“自我”认识视为按他者的看法建构而成。各国各民族文化在与异文化的对比与认同中,折射与建构自身的文化品格。
他者化属于文化表述中的问题,属于历史阐释的范畴。因此人们还可以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塑形。我们在进行阐释时就有“前理解”或“前见”。它是由文化传统、历史与经验意识等所建构起来的,并逐渐内化为阐释者的文化心理机构,发挥一种无意识的作用,因此对异文化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与“受限”,而阐释者当下的现实情境、情绪色彩与语言翻译中的偏离等都有可能导致对阐释对象的重新改写与主观塑形。
实际上,无论是自身文化的折射与建构,还是文化研究者的阐释局限,问题并不在于他者化能否加以避免,而是自身如何表述异文化,即自身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与运作程序中,采取什么方式和出于什么目的来建构他者形象。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北大讲演录(1989)中提出“文化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对异域文化的兴趣与表述是建立在文化类同基础上的文化利用,以此来达到对自身文化的批评、反省与改造的目的。即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异域文化。对于西方而言,描绘一个原始社会,表述异域文化是由于自身的需要,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不是为了异文化的现实,也不是为了不同文化在交流对话中相互促进。考察东方学的历史,这种出于自身需要,利用异域文化的事例随处可见,总括起来,它主要采用三种方式:
首先,赞美他者文化,批评自身的文化。西方出于自身目的,对他者形象有过诸多的赞美。
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所描绘的元代繁盛景象,就充分表达出对一个美好的社会乃至神话世界的赞美之情,这位商人描述了元代中国发达的工商业,其极尽欣赏的笔调与夸张的描述,使许多现代学者都质疑其旅行的真实性,何况其中根本没有叙述诸如汉字、茶叶、缠足、长城、筷子、中医、印刷等最基本的中国元素,但《马可·波罗游记》(Marco Polo and HisTravels,1298)却对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新的知识与广阔的视野促发了欧洲人文精神的启蒙与复兴,并使欧洲重新绘制地图,开辟新航路,而欧洲海外的殖民行径与帝国意识正是依赖于航海业的拓展。18 世纪,法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既传播欧洲的宗教文明,也将中国文化带回欧洲,伏尔泰(Voltaire)就盛赞中国儒家思想,以此来批评法国社会,宣扬其启蒙精神。他还将传入法国的古典戏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1755),并将其背景改放在成吉思汗时代的皇家宫廷内,元朝大军对欧洲国家的侵略与征服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记,在文学创作中仍不忘其警示作用。
再次,贬低他者文化,彰显自身的优势。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曾被后殖民理论家认为是表现西方殖民扩张意识的经典文本,而鲁滨逊也成为欧洲开拓海外事业的典型形象。
小说中鲁滨逊渴望航海,一心想到海外建立功业,他曾在巴西作过庄园主,不甘心又去非洲贩卖黑奴,失事后漂流到一座荒岛上,数次目睹“食人生番”的场景,在经营荒岛时救出一个当地的土人,便给他取名“星期五”。鲁滨逊非常讨厌土人的说话方式,便开始教其说文明的西方语言。总之,西方认为自己有权控制并经营任何海外荒岛,尽管岛上还住着当地人,但这些土人野蛮低下,只配作为被统治者的奴隶,因此欧洲人也有权给土人命名,传讲所谓的西方文明与语言方式,全然不顾土人已有的风俗习惯。
最后,删改他者文化,以备自身的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他者形象并不都是西方的发明创造,同时也有建立在东方文化与文本形象基础上的选择、剪裁、扩略与改造。如阿拉伯女作家汉娜·谢赫(Hananash Shaykh)的处女作《宰哈拉的故事》(The Story of Zahra,1995),在翻成英文,进入欧美文学界的时候,译者故意回避了作品中对西方妇女的批评与讽刺,而将它介绍成一部在“‘封闭的中东社会’里否定阿拉伯妇女之人类天性的小说”。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多次提到,西方作家经常直接或间接地从《古兰经》等阿拉伯文献中来定义东方人的形象。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1995)中说,《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曾经引发西方作家对东方世界的想象,成为他们想象东方的重要资料来源,是个 “转喻的宝藏”。西方作家,如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还有那个被萨义德称为“没有人比他更反动、更具有帝国主义思想”的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等都在其中吸取了大量的东方标本与符码,成为其作品描述东方的重要资料来源,然而它们与东方世界存在着多层隔膜:古老的,缺乏当下的;文本的,不是现实的;异域的,缺少体验的;静止的,没有变化的等等。而当时大量的探险寻宝等通俗小说更是受到《天方夜谭》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添油加醋”的描绘叙说曾经激起了西方狂热的冒险热情和到东方世界去发财致富的梦想,这些欲望、热情与梦想逐渐形成自 18 世纪末期正式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帝国扩张行为。
概括地说,西方是在地域区分、差异确定的基础上采用边沁主义的态度处置东方文化,进行文化塑形,创造出与自身对比的“镜像”——他者形象来代替真实的东方。真实的东方是复杂的、充满着历史变化的,而形象往往是固化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无论是对他者的贬低,还是对他者的赞赏,抑或是旧有形象的改造,都是西方自我权力在东方主义话语内的策略表现,一个叫“王”(Wang)的小说人物很能说明这点。
他是英国现代文学开拓者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 1914 年出版的小说《胜利》(Victory,1914)中所塑造出来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里,王的行为古怪与不可理解,性格不慷慨,很自私。虽然话语不多,但充满谎言,还张口就来。然而康拉德摒除西方的偏见,又将王拿来与他的主人海斯特(Heyst)等人进行对比,王敏锐、果断、具有同情心;海斯特则迟钝、毫无作为,而里卡多(Ricardo)却是真正的冷酷无情。康拉德迎合西方人的他者化心理,一方面把王描述成带有劣等民族文化的印记,另一方面又借用王的一些优秀品质来批评西方的文化心理与民族品格。对于他者形象,无论是称赞还是否定,都是西方自身的需要,解决的是西方自身的问题,或者批评自己的社会与文化,或者是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确证,或者是勾起殖民侵略的欲望,或者是对殖民侵略行为的合法性认证。但是,这些他者化的形象不管好坏与否,都有可能充满了对中国历史现实的隔膜、误读与扭曲,但是欧洲需要这些他者形象,需要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因此中国形象是欧洲人眼中的形象,文本中的形象,是可以随时加以利用的形象,不是中国的现实形象。
二、本质化与思想套装
在萨义德看来,出于自身需求而利用他者文化,以及西方对东方世界敌意基础上的文化表述,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因为东方世界也存在着各种对西方文化的利用与具有对抗意味的文化书写,这是历史事实。但萨义德发现东方学家有意识地建构伊斯兰世界负面、异端的形象,以至于西方世界长时间维持并加固一种刻板僵化的东方形象。从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os)《波斯人》(Persians,BC472)、德尔贝洛(Barthelemy D’Herbelot)《东方全书》(Bibliothèque orientale, 1697)与但丁(AlighieriDante)《神曲》(Divine Comedy,1308-1321),一直到现代东方学以及美国区域研究,东方学保持自己的一贯特性,将东方世界进行文化编码,并逐步使之本质化与系统化,这些编码的言说被视为关于东方世界的真正知识,被当作科学的真理在西方世界蔓延开来,东方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这些东方学家的编码工作。与其说这是一种学科化的知识处理,还不如说是一套话语的建构,它并没有真正的科学性与真理追求,反而是加固了早已存在的东方主义观念,强化了旧有的东方形象,披上了科学知识的外衣,但这套外衣却有着非凡的作用,它让欧洲人具备一套对付东方世界的有效方法,形成一种意识与思想的言说套装,可以完全无视东方世界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与内部差异的现实,而使这套关于东方世界的话语不断衍生,符合其自身权力生产与再生产需要。
由此,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文化表述所采用的思维与表述方式是永恒一致的:经验现实被文本意象完全替代,对东方世界的看法依赖于早已存在的东方主义观念及其文本言说,萨义德重点考察了英国曾经的首相、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James Balfour)对埃及的演讲论述,在详尽的分析后他发现,对贝尔福来说,埃及本身是否存在无关紧要,英国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埃及只是按照英国人的认识方式而存在的。而在大量的东方学文本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少量某某有名有姓的东方人,有的只有姓氏,如上述康拉德小说中的“王”;还有的将本国的姓氏与他者形象结合起来,如英国人笔下的“中国佬约翰”(JohnChinaman)是一个呆头呆脑、行为古怪,只配嘲讽的人;有的甚至与动物联系起来,如《胜利》中琼斯(Jones)蔑称王为“支那狗”;更为常用的则是那些无名氏,没有个体,只有群体的名称,他们被冠之以“赶骆驼的人”“支那人”“近东人”或“黑鬼”等称呼,它们成为了西方文化与知识体系中的通用术语。欧洲人对这些观念与术语代代相袭,互相征引,相互促进,形成了一股广阔深巨的言说东方的大潮,既席卷了欧洲的现实,也囊括了西方的历史。
对于没有去过东方世界的西方人而言,沿袭旧有东方学文本,并以此文化表述来看待东方,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很少有人怀着一种批评质疑的眼光去看待早已存在和熟悉的事物,就算有疑问,也没有足够的亲身体验加以证明,何况所有的东方学家对东方世界的描述基本上相差无几。但是对于那些去过东方世界的人,尤其是那些具有敏锐观察力与思辨力的学者作家,还有那些以客观研究与事实分析为主的科学家,他们对东方世界应该有自己独特看法,或者说其观点比较切合东方世界的真实状况,并极有可能挑衅之前一以贯之的东方主义观念与言说模式,然而残酷并带点讽刺的事实让萨义德大失所望。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GustaveFlauber)在东方之行中邂逅一个名叫库楚克·哈内姆(Kuchuk Hanem)的埃及舞女和交际花。库楚克的放荡与麻木给他以无尽的遐想。旅行结束后,他在信中说,“东方女人不过是一部机器,她可以跟一个又一个男人上床,不加选择”,成为了一群只知肆无忌惮地展示“它们的性的动物”。
不仅福楼拜如此,还有许多西方作家学者都“可以从一个具体的细节上升到普遍的概括,将一位 10 世纪的阿拉伯诗人的看法提升为埃及、伊拉克或阿拉伯这些东方人心性的普遍证据,古兰经中的一首诗就是足以证明穆斯林根深蒂固的纵欲本性”。
对于东方学家而言,个体经验很容易上升为普遍理论,单个印象被认为是整体形象,因为西方有权定义与塑形东方,给东方以某种身份,将它分门别类,并统一规划治理。
接下来萨义德还考察三位东方学家的文本,他们多少都有东方的经历与体验,但其著作却与东方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并且还是那套东方主义观念的变形版本。爱德华·雷恩(EdwardWilliam Lane)的《现代埃及风情录》(Accounts of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ons,1860)只是为了验证早已形成的东方主义观念而去搜集材料,毫无自己的个性体验,使自己全然屈服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规范。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根本不注意观察东方,只是按照东方主义的观念去任意想象东方,将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至高处。与雷恩屈从东方主义观念不同,他让东方主义观念屈从于强大的自我,他有权以东方主义观念作基础,然后依照自己的性子去任意涂抹东方世界。当然在东方学的历史上,完全没有东方学家质疑,甚至批评过东方主义的观念与言说模式,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东方学的发展史上有不少东方学家都曾经试图改变东方主义的话语规范,理查德·伯顿(RichardFrancis Burton)就是其中一位,他熟悉东方世界,会说数种东方语言,对东方文化了解、倾慕而去东方朝圣过,但萨义德经过分析后发现,这样一位对东方世界颇多知晓的东方学家,依然有着强烈的支配东方的意识,西方优于东方的观念,这种动机不自觉地契合那个时代兴盛起来的帝国主义话语,难逃东方主义权力逻辑。
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经将真理的遮蔽或消解溯源并归罪于修辞话语长期灵活的运用所导致的虚幻后果:“一组灵活变化的隐喻、转喻和拟人——简言之,一个人类关系的集合,这些关系以诗性的方式和修辞方式得到加强、转置和美饰;并且,在经过长期使用后,对某一民族而言似乎成了牢不可破的、经典的、不可或缺的东西:真理本质上只是幻象,不过人们经常忘记它的这一幻象本质。”
尼采用修辞学来质疑真理,说其不过是幻象,但人们却一直把它当作真理来看待,我们用他的观点来分析知识与话语之间的权力运作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东方就这样被一种“思想的现成套装”,一种加工既定文化模型的“修辞方式”与“修辞策略”囚禁起来,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双重压抑。简单地说就是没有自身的历史,真实的东方不存在,它只存在于由东方学话语掌控下的不断修辞化。人们以为随着东方世界的变化,东方学知识也会随着改变,从而显现出知识的历史真理性,实质上这不过是尼采意义上的修辞幻象。萨义德将这种行为概括为“东方化东方”,即一种对东方的“彻底的皈化”,它使东西方关系变成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一种阐释与被阐释的关系;一种西方既能随心所欲地赋予东方定义、身份、形式与地位的单向修辞过程,同时又将东方作为一种话语而不断加固的存在历程。更糟糕的是,它又与殖民贸易、军事侵略等霸权行为、殖民行径相辅相成、相互发明和共同促进,使得现代东方学逐渐积聚成一项“令人畏惧”的事业,文本化扩展到政治化,由对异域风情的描述表现合并到殖民化与帝国行径的政治军事活动之中。
三、政治化与帝国行径
如果仅是由于阐释的受限与自身文化确证的需要,文化书写采用一种边沁主义的态度来建构他者形象,那么这并不是后殖民的问题所在。
因为这是人类本身以及探索真理时所具有的局限性。问题在于他者形象与西方的霸权意识、殖民行径结合在一起,乃至于他者形象的塑造就是出于政治与霸权的需要。在权力运作与科学理性的双重作用下,文化霸权超越了一种简单的、居高临下的压服与禁止,而是形成了一套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具有超强的消解功能的话语规范。当然,文化霸权走到如此地步,首先归结为文化与政治的合谋与共犯。换言之,西方出于文化利用而建构的东方形象、对东方世界进行研究的东方学以及各种公共政策、社会机构在初始的时候并没有紧密相连,成为一个针对东方世界的庞大的规范系统。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前这些零零碎碎、不成篇章的权力因素逐渐靠拢,终于在某个时期融为一炉,由话语紧密相连,开始了自身秩序化、结构化与扩张化的征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现代东方学的建立。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讲述了现代东方学的创建状况。法国亚洲研究会于 1822 年成立,其目的已经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清晰地展现出来了。萨西(Silvestre de Sacy)担任了研究会的首任会长,开始对东方学进行有计划的现代建构。
然而早在 1799 年,他发表第一部著作《一般语法原理》(The Principle of General Grammar,1799)期间,就告诉他的学生,书是为你们而写的,因为它有用,你们需要它。这些话的用意在于即便是语言学这样跟政治实用不怎么沾边的学科,其研究也不在于它的创新程度,或者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是应该采取一种实际功用的态度把已经获取的零散知识进行剪裁、整理与归类,对已经做过、说过或写过的最有用的东西进行概括与修正,因此东方学的创建一开始便建立在实际功用的基础上,其力量支撑源自于西方的霸权意识与帝国行径,它与政府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是在政治规范中构建出来的。萨西在 1802 年参与了拿破仑委托法兰西学院对 1789 年以来法国科学艺术的发展进行总体截面式描述的专门小组。随后按照当时政府的要求,萨西删繁就简,精心编选了一套三卷本《阿拉伯文选》(The ArabiaAnthology,1806、1827)、一本阿拉伯语语法与一本论述阿拉伯语韵律和德鲁兹教派的专题著作等有关东方世界的文本,成为创建现代东方学最有效的途径。
不过,作为文化表述与科学研究的东方学与现实世界的公共政策、制度机构的结合并非始于现代时期,其实早在现代世俗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有关东方知识的文本进行增删外,基督教会也组织教徒对传教士描绘东方世界的文本进行修改。利玛窦(Matteo Ricci)于 1610 年在北京逝世,其所著的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记录及其研究手稿被教友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带到西方,辑成书出版时,金尼阁作了删改,去掉了利玛窦对中国的坦率批评,“利玛窦对晚明的某些阴暗面的揭露是十分坦率的,而对于教会来讲这并不合时宜”,当时的教会机构正在筹集更多的钱财以便把更多的使者送往中国,要想达到此目的,就得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美好的国度。传教士的活动记录及其著作可以按照利益要求进行任意的增删与篡改。
实际上,文化、政治与权力的联接和共谋在话语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而话语在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则是由法国思想家福柯赋予的。福柯在对各种人文科学进行解构后指出,真理不是在客观世界与经验领域发现总结后传播开来,反而是由人类的压抑经验领域的行为即一整套的话语建构起来的。人类所谓的具有真理性的一切知识都是由话语产生出来的,所有的真实都是话语的真实,话语是权力运作的条件与结果,“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也就是说,由话语构成的人文学科,成为一种对人与世界的规约,真理是话语的建构物,而且话语又生产出真理体制,为权力的运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形成知识管理技术,乃至知识政治。如果在福柯那里,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存在历史的争议外,那么在萨义德看来,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是很清晰的,在知识与话语的之间的时空内,文化利用、修辞学的运用和思想套装,以及权力机构与公共政策等不断地加固东方主义话语,并使东方学知识出现各种新变化,而这种变化不过是话语策略和修辞幻象而已。
在此,不应该忽略科学理性的规范作用。从萨西与拿破仑的关系就可以看出现代东方学创建的政治性,而东方学家所拥有的科学理性的武器,也是政客们最为看重的地方。东方学家将理性化原则强加在东方上,成为东方自身的原则。
东方不再遥远,不需要经验,也不再陌生。它就在东方学家的手边,就在西方人的理性范围内,就在东方学的文本之中,就在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之中。要使东方学成为一门学科,就需要运用科学理性的原则将以往东方学的真知灼见系统化,加固东方学的既成话语。萨义德认为,作为现代东方学的第二代,赫南较为成功地完成了此项工作。在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真理,并不是来源于对社会现实与自然世界的考察,并不在于追求与客观事实的符合,它由话语建构起来,让关于东方的知识获得一种科学的、清晰的表达。科学理性的作用有二:一是通过科学理性将有关东方世界的材料文本进行整理规范,形成东方世界的“科学宝库”,从这个“宝库”中所提取的形象、观点等都是科学的、真实的、不容怀疑的;二是科学理性与权力机构结合起来,实现东方学话语对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奠定知识的稳定结构,消除过分暴露的权力意识,使之作为科学规范与真理内容内化于人们的心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保持话语的扩张性与伸缩性,使任何违背话语规范的差异现象经过科学理性的作用都能融入其中。科学与政治的联姻,让话语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更远离了真实的东方世界,从而更具有宰制性,拥有一种“微观物理学”的权力效果。
四、结论:话语的本质——去中心的权力
不管是那些主张边沁主义的东方学家,还是认为必须依靠自身体验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作家,他们在对东方世界的表述与再现中,始终脱离东方的经验现实,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书房在不违背东方话语理性原则的情况下,来凭空想象东方,任意处置东方,形成学术理论、沙龙讨论稿、会议发言稿、小说、戏剧、游记、以及表现异域风情的杂志与旅游指南等各色各样的文本。“文本不是对事物的再现,不是对外在于它们的超验所指的指涉,而是以一种完美的表征方式仅对它自身进行表征,”这些文本不是对东方的再现,不是对知识真理的指涉,它们只是在自洽的东方话语中指涉自身,是脱离了所指的能指滑动体系,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完美圆圈”。于是,东方学家仅在类似实验室的封闭空间中就可以作出主观的专横判断:西方人有理性,爱好和平,文明,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优越,进步等;东方人则专制,欲望好色,落后野蛮,生活无规律,整日脏兮兮的,甚至连语言都是无机的、没有生命力的、完全僵化的,没有再生能力的。文化、权力与话语构成一个整体的结构模式,乃至欧洲人的言谈表述中就包含一种权力意识,对东方的每句书面语词或口头表达都成为欧洲霸权意识的具体体现: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与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只有在话语规范及其策略行为中,我们才能理解西方人心中时而赞美时而贬低的他者形象,才能理解福楼拜将一个埃及女人的放荡说成是所有的东方人都在展示“它们的性的动物”,也才能理解奥斯丁(Jane Austen)这样的优秀作家为何不可避免地将庄园的稳定秩序建立在对异域时空领域不经意的处置上。
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将权力观念、公共政策、政治运作、军事行动、文化机构和科学理性、形象表述等熔为一炉,成为其策略化的表现形式,使得 19 世纪晚期以来的东方学研究,包括美国的区域研究,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已逐渐不再是以某个帝国为基础或中心的帝国主义,科学理性、政府行为、文化制度、公共政策与市场经济等相互促动,共同构成一个去中心的帝国,这恰恰是东方主义作为话语的本质所在,即没有中心的权力,却能不断地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没有中心与边缘、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西方与其他地区之分的情况里,宰制者就是每个人,即有利于帝国霸权的文化习性,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帝国霸权的维护者。这就是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种族主义、地区主义,甚至最不显眼的部落或唯我主义不同的地方,它“能够界定现代全球历史,其本身还能够成为那段历史的普遍渴望和目的”,其东方主义式的霸权逻辑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得到扩散与加强,面对这一权力话语的逻辑与现实的困境,东方世界该如何摆脱与消除,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予以解决而显得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2] 拉康. 拉康选集·编者前言[M]. 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7.
[3] 林丰民. 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J]. 国外文学,2002(4):25-32.
[4]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5] 张兴成. 他者与文化身份书写:从东方主义到“东方人的东方主义”[J]. 东方丛刊,2001(1):14-25.
[6]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24.
[7] 赵稀方. 后殖民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8.
[8] 史景迁.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 廖世奇,彭小樵,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6-27.
[9] 福柯. 性经验史[M]. 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0.
[10]赛义德. 赛义德自选集[M]. 谢少波,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0.
[11]德里克. 后革命氛围[M]. 王宁,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