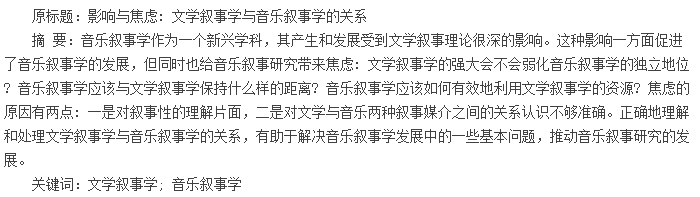
美国现代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罗姆(HaroldBloom) 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影响的焦虑》,其主旨是考察近现代英美重要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书中提出一种观点: 前辈诗人的影响会给新诗人造成焦虑,新诗人要通过克服焦虑实现自身定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前辈诗人是新诗人学习模仿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新诗人需要不断向前辈发起挑战才能开拓出属于自己的诗歌领地。布鲁姆在书中总结出新诗人克服“影响的焦虑”的六种“误读”方法。他认为“影响的焦虑”构成了诗歌发展的基本动力与模式。“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
“影响”与“焦虑”用来描绘当下文学叙事学与音乐叙事学的关系也比较贴切。文学叙事理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而音乐叙事学是最近几十年才诞生的新兴学科。音乐叙事学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文学叙事理论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带来了不少益处,但同时也让音乐叙事研究者感到“焦虑”: 音乐能否叙事,或音乐能否像文学那样叙事? 音乐叙事与文学叙事有多大差异? 该不该模仿文学叙事模式去建构音乐叙事模式? 这种模仿会不会削弱音乐叙事学的独立性? 文学叙事理论体系中哪些对音乐叙事学是有价值的? 在音乐叙事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如何处理音乐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的关系涉及到如何给音乐叙事学定位、如何界定音乐叙事的特性以及如何构建音乐叙事机制等关键性的问题。本文尝试梳理文学叙事学对音乐叙事学的复杂影响,剖析“焦虑”的症结,以助力音乐叙事学的发展。
一、文学叙事模式: 作为否定的“他者”
在音乐叙事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反对的声音。其中以纳蒂埃(Jean-Jacques Nattiez) 、阿巴特(Carolyn Abbate) 、基维(Peter Kivy) 为代表。他们认为: “音乐作品无法在最基本的文学意义上去叙述。”
其反对的关键方法就是以文学叙事模式来否定音乐叙事。
他们依据文学叙事的一些主要特征逐一对音乐叙事进行质疑: (1) 音乐作品缺少文学叙事的“过去时态”。叙事在时间性上表现为一个“现在”的讲述者叙述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文学可以很轻易做到,但音乐中却无法标识出过去时态。(2) 音乐作品没有文学叙事的“故事 - 话语”结构。“故事 - 话语”是叙事中相互独立的两个空间,故事层是故事中人物所活动的空间,话语层是讲述人“叙述”行为发生的空间。音乐作品很难显示这种双层空间结构。(3) 音乐作品没有文学叙事的“叙述者”。文学叙事中总有一个“讲述人”,他在向故事的听者“叙述”故事,音乐作品中缺少这样一个担负叙述行为的主体。(4) 音乐作品没有文学叙事的语义精确性。文学叙事中的人物、事件、情节、时间、地点、环境等信息的表达都是具体而确定的,而音乐作品无法在这些信息上达到语义上的精确。(5) 音乐作品缺乏对“因果关系”的标识。文学叙事的重要性质就是事件按照因果关系形成情节,而音乐作品很难表达明确的因果关系链条。(6) 音乐作品的重复性与文学叙事不兼容。音乐作品中从动机、乐句到乐段到乐章都在频繁地重复,这种重复是文学叙事所不能允许的。
对音乐叙事的质疑并不限于纳蒂埃等人,他们只是将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疑问进行了系统化的表达。很多人在听到“音乐叙事”时,都会下意识地发出这样的疑问: “音乐能讲故事吗?”这种疑问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背后有着未曾言明但十分确定的参照标准,即《荷马史诗》《格林童话》《战争与和平》等经典的文学叙事样本。文学叙事成了树立在音乐叙事对面的一个“他者”,一个“否定”的他者,它的无所不在构成了对音乐叙事强大的无形的否定力量。这让音乐叙事研究者感到很焦虑。
面对这些质疑之声,音乐叙事学者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自我辩解。对有的质疑予以断然否定。如针对“重复性质疑”,西顿(Douglass Seaton)认为文学叙事也存在重复,重复本身并不构成对叙事的否定。音乐与文学的重复有差异,并不能证明音乐不能叙事,音乐可以具有与文学相区别的叙事性。对有的质疑则是部分接受部分否定。
如针对“语义性”质疑,莫斯(Fred Maus) 承认音乐确实不能传达精确的信息,但并不认为这有损于音乐的叙事性质。
对另一些质疑采取其他曲折的方式进行辩护。如针对“因果性”质疑,音乐叙事学者承认音乐没有明确的因果线索,但他们提出一种补救的办法,如纽康(Anthony Newcomb) 指出: 音乐可以在听众的接受过程中通过想象来建构出因果关系。这些辩解中有一部分显得苍白无力,如关于时态的争论。萨姆尔斯(Robert Samuels) 认为音乐可以有“过去式”,他依据的是阿多诺对马勒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一个比喻,阿多诺曾把这一乐章形象地比喻为讲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故事……”萨姆尔斯据此就认为它是音乐“过去式”叙事的例证。
这种论证确实显得较为牵强。
音乐叙事学者的辩解虽然费尽周折,却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既没有消除对手的质疑,也没有解决自己的焦虑。这是由于他们的辩解存在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 除了个别学者(西顿) 之外,他们仍然以承认文学叙事模式的“优先地位”为前提,试图通过让音乐攀附于文学来证明音乐具有和文学一样的叙事性质。这种做法只能强化文学叙事模式的标准性地位,而弱化音乐叙事的合法性。
二、建构音乐叙事体系: 让文学走开?
批评者以文学叙事模式为标准来质疑音乐叙事学的合法性,给音乐叙事学者制造了不少麻烦。他们在极力辩解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是不是音乐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走得太近了? 因此,为了维护音乐叙事学的独立性与合法性,避免给反对者留下把柄,有学者提出应该远离文学叙事学来建构音乐叙事理论体系。如道格拉斯·西顿,他说: “当前关于音乐叙事讨论的一个主要弱点就是过于依赖于这一假定: 即叙事在本质上属于文学。”
西顿认为对文学叙事模式的过于倚重是导致音乐叙事问题丛生的根源,在他看来,“音乐中的叙事观念完全不必依赖于对文学的模仿,就像反过来文学不必依赖于音乐叙事一样”。他提出两个超越媒介限制的叙事因素: “情节(plot) ”与“声音(voice) ”。“情节”是通过“人物”(由旋律、节奏的统一性所确定) 和“动作的展开”(由稳定的和声音型、渐强的张力、高潮、解决和尾声确定) 实现。“声音”指叙事的人格,它由多种方式形成: 可以隐含在音乐的曲式内部,可以通过文字线索标示,可以围绕音乐的表演和聆听的一些行为以及对音乐的接受等方式实现。
另一位音乐叙事学者拜伦·阿蒙与西顿相似,也认为音乐与文学的类比“所带来的问题和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在文学叙事与音乐叙事的关系上,阿蒙区分两种情形: 一种是“衍生模式(de-scendant model) ”,一种是“平行模式 (sibling mod-el) ”。 前者“给予文学叙事以概念上的优先权”,把文学叙事与音乐叙事视作“父子”关系,音乐叙事由文学叙事派生出来,因而音乐只能按照文学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叙事。后者则把它们看作“兄弟”关系,作为兄弟,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渊源,也有差异。
根据后一种关系模式,要证明音乐的叙事性首要的是“确定普遍的本质的叙事要素,以及音乐使用这些要素的独特方式”。阿蒙根据里兹卡对神话叙事的解释,认为“叙事在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重估行为”。阿蒙认为这一定义是普遍的“超媒介的”(medium-independent) ,它适用于包括文学、音乐、神话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叙事。音乐叙事也是一种人类文化中的价值重估行为,这是与文学叙事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音乐的价值重估是通过一套独特的机制来实现的,在阿蒙看来这套机制就是他所提出的“神话原型模式”。
西顿和阿蒙试图通过隔离音乐叙事研究与文学叙事理论来解决让人焦虑的问题,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又无法完全做到。如西顿虽然极力避免使用“故事”“话语”这样文学色彩浓厚的术语,但他的“情节”“声音”仍然是从这两个范畴转化而来的。
阿蒙以“兄弟关系”来描绘音乐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是合理的,但实际行动中他也背离了自己的设定,他所提出的神话原型叙事理论实际上是模仿文学理论(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与里兹卡的《神话的符号》) 而提出的。所以尽管他们一再宣告音乐与文学相独立的立场,但仍然避免不了对文学叙事模式的模仿。口头宣称音乐独立,而实际行动中又悄悄地滑向文学,这种“言”与“行”的矛盾正是音乐叙事学者在处理音乐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关系上“焦虑”心态的表现: 既想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又不得不向文学叙事学寻求帮助。
三、谁更有价值: 普罗普还是布斯?
音乐叙事学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音乐如何叙事的核心问题,出现了多种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虽各有侧重、差异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受到文学叙事理论的影响,在它们的背后都隐约折射出某个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子。如纽康的“情节原型(plot archetype) ”模式,受到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和列维 - 斯特劳斯的神话叙事理论启发,认为音乐作品的表现内容可以提炼归纳为人类某些基本的“情节原型”。莫斯的“戏剧模式”受到经典叙事学的“情节语法”的影响,认为音乐的叙事就如同舞台表演的戏剧一样,是由音乐中的虚拟人格向观众表演的一系列具有整体结构的行动。阿蒙的“神话原型”理论则受到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和神话学家里兹卡(James JakóbLiszka) 的影响,认为音乐的叙事在于以音乐的形式阐释了“秩序”与“反叛”,“胜利”与“失败”等神话主题。科恩(E. T. Cone) 的“音乐人格”论,则受到另一位小说叙事学家布斯(Wayne Booth) 的影响。
他把布斯小说分析中的“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声音”等概念加以改造应用于音乐作品的分析中。拉比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 跨越文学与音乐研究两个领域。他提出的“音乐修辞叙事”模式是他关于文学修辞叙事理论的直接延伸。此外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 、劳伦斯·克拉默尔(Lawrence Kramer) 等人的音乐叙事著述同样受到文学叙事理论很深的影响。
虽然都是对文学叙事理论模式的借鉴,但各个模式之间却存在不小的差异。拉比诺维茨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对立的两个大类: “普罗普式的”与“布斯式的”。他认为音乐叙事学研究在运用叙事理论的方式上存在严重的缺点。“在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叙事分析是片面的: 他们是普罗普式的而非布斯式的,强调故事,而不是话语”。在拉比诺维茨看来,音乐叙事学把叙事视为“事件的序列”,关注“情节”和“行动者”,却“忽略了叙述行为本身”。他认为这种音乐叙事研究“并未充分利用叙事学理论”,而且与传统的音乐分析相比,也并不能提供更好的分析结果。“早在‘叙事转向’之前,音乐理论家就已经研发出精确的针对音乐媒介的技巧概念来分析音乐的布局谋篇规则和程式化阐释策略,他们实在不需要借用叙事学理论的分析手法来阐释音乐究竟如何使人产生期待、惊奇和结局等感觉的”。
拉比诺维茨的批评源于他所持的“修辞论”叙事观:不能把叙事首先看成一个形式对象,而应该是一个置于某个规约性框架内的修辞行为,即,叙事是通过某种方式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交流,它依据某些既定的规则,从某个人(或某一群人) 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更确切地说,对于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来说,叙事的最简单定义是: “某件事发生了。”而对于修辞叙事批评家而言,最简洁的叙事定义是: “某人———通过使用约定俗成的技巧———为了某种目的告诉另一个人某件事发生了。”
叙事首要的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交流而讲故事,而不仅仅是为了建构一个情节而讲故事。拉比诺维茨一直把自己与其他音乐叙事研究者置于两种对立的位置: 重故事或重话语,重情节或重修辞,普罗普式的或布斯式的。拉比诺维茨所揭示这种对立实际上有着更深层次的学理渊源。
在叙事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有两本奠基性的著作,一本是俄罗斯学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尽管这本书初版于 1928 年,但直到 20 世纪50、60 年代才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直接刺激了结构主义学者对叙事学的研究兴趣。普罗普把所有的民间故事切分为 31 个功能单元,不同单元的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的民间故事,这种化繁为简的神奇效果正是叙事学诞生初期的主要目标,即寻找所有故事共同的“叙事语法”。另一本是布斯 1961 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在这部著作中布斯关注的重点不是所有小说共同的故事结构,而是关注在一部具体作品中(隐含) 作者与叙述者如何通过叙事来影响读者,讨论叙事中处于不同层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普罗普的“语法传统”和布斯的“修辞传统”在后来的叙事学研究中都得到继承和发展,在80 年代以来,两者呈现相互交叉的趋势。从这两个传统来看,纽康、布斯、阿蒙属于典型的普罗普式研究,而拉比诺维茨则属于典型的布斯式研究,同时属于这一传统的还有著名的音乐学家爱德华·科恩。总体看来,在目前的音乐叙事研究中,语法模式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这两大传统在文学叙事研究中都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但它们移用到音乐中却可能会产生价值的分化。在拉比诺维茨看来,对音乐作品作普罗普式的情节语法分析并无多大价值,至少相对于已有的音乐分析术来说并不能提供更新的东西。拉比诺维茨认为修辞叙事的方法对于音乐分析价值更高。虽然这仅是拉比诺维茨的一家之言,却反映了音乐叙事学的一个现状: 面对庞大的文学叙事理论宝库,音乐研究者在借鉴时往往缺乏甄别,致使许多地方存在生吞活剥的痕迹,给反对者留下批评的可能。如何合理地借鉴文学叙事理论,如何将最有用的叙事学成果用到音乐研究中,这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症结: 叙事的性质与媒介
在对待文学叙事理论的态度上,音乐叙事学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心态: 它是音乐叙事学理想中的朋友、事实上的父亲和潜意识中的对手。在理想的状态中,文学叙事学最好是作为音乐叙事学的朋友,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在不需要的时候又可以保持距离。而在事实上,文学叙事学一直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在音乐叙事学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叙事学一直无私地向它提供灵感、理论和方法,大部分音乐叙事理论模式都是从文学叙事模式中衍生出来的。但是在潜意识中,文学叙事学又是音乐叙事学的“对手”,它威胁到音乐叙事学的独立性与合法性,是音乐叙事学需要摆脱的一个潜在的敌人。这种矛盾的心态正是文学叙事学给音乐叙事学造成“影响的焦虑”的表现症状。导致这种症状有两个深层次原因: 一是对“叙事性”的理解较片面,二是对文学与音乐两种叙事媒介的性质与关系认识不够深入。
“叙事性”(narrativity) 是对叙事性质的界定,在叙事学研究中,有关叙事性的讨论非常多,形成对叙事性的多侧面多角度的认识。但音乐叙事学所假定的叙事性却比较单一片面,基本上都遵循经典叙事学的“情节”中心叙事观: 叙事是叙述者向听者讲述的以时间和因果关系结合起来的事件系列。
这种叙事观历史悠久,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具有开端、中间和结尾的完整结构———中就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并在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布雷蒙的《叙事的逻辑》等经典叙事学著作中被反复强调。这种叙事观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基本上是从文学(尤其是小说) 中总结出来的,带有强烈的“文学中心主义”色彩; 第二,它具有排他性,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定义。如尚必武指出: “在经典叙事学阶段,出于建构‘普遍叙事语法’的需要,几乎所有有关叙事的定义都基于‘二元对立’的立场,希图由此划清‘叙事’与‘非叙事’之间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叙事性’被看作是叙事特有的‘属性’或‘区别性特征’,凡具有叙事性的就是叙事,否则就是非叙事。”
这种以文学为中心的排他性叙事观对研究文学作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促进了叙事学的发展。但随着叙事学逐渐走出文学的圈子,其局限性也随之显现。
音乐叙事学的发展一开始是直接受到这种叙事观的影响而诞生的,试图建立音乐中的“情节”机制,但情节论叙事观的文学中心主义和排他性又本能地与超文学的应用相矛盾。所以出现了批评者借这种叙事观来否定音乐叙事,也导致音乐叙事研究者在处理与文学叙事学的关系时不知所措。
拉比诺维茨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不良影响的纠正,不过他完全以一种叙事观(修辞论叙事) 来代替另一种(情节论叙事) 也不尽合理。对于音乐叙事性的理解不能限定于单一的视角,叙事学界对叙事性的讨论早已超出文学中心主义的藩篱,从多侧面多因素来界定叙事性,如叙事发生的语境、接受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叙事的媒介、文本的特征等等。“叙事性”已经不再作为一种排他性的标准,而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开放范畴。我们应该突破文学中心主义的叙事观,以广义的叙事性范畴为引导,充分考虑音乐作品生产、传播、接受的各个方面因素,来建构音乐的叙事性。
从广义的叙事观来看,对叙事性的界定不能离开叙事的媒介,导致音乐叙事学焦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对文学叙事媒介与音乐叙事媒介之间关系认识的不准确。其表现为两种并存的对立态度上:一种是过于看重音乐与文学之间的相似性,通过把文学叙事模式直接移植到音乐中来证明音乐的叙事性; 另一种是过于看重两者之间的差异,通过排斥文学叙事模式来寻求音乐叙事学的合法性。这种矛盾必然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音乐与文学作为叙事表现的两种媒介,它们之间既不是绝对的同一关系,也不是绝对的隔绝关系,而是一种“互文”关系。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是一个重要的文艺批评概念,它经过茱莉亚·克莉丝蒂娃、罗兰·巴特、德里达等著名学者的阐释,成为 20 世纪人文科学重要的理论范畴。互文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的关系,“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中的参与,是指一个文本与某一种文化多种语言或意指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那些表达了这种文化的诸多可能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文本”不单是指写在纸上的“文字文本”,而是指广义的“文化文本”,它将人类一切符号化的文化实践对象及其成果都视为文本,这些文本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指涉的关系。对于文本的接受者来说,要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不能像传统的解读方法那样,只着眼于单一文本本身的结构,而要放开视野,从与此文本发生互文性关系的大量其他文本中了解它的意义。
音乐与文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两种文化文本,它们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文性关系。首先音乐与文学本来就有着天然的关联。不管是中国的先秦时期还是古希腊,音乐与诗歌在诞生的时候都是浑然一体的。19 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更是把文学视作音乐创作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同时从音乐的接受来看,诉诸于文学的音乐解释也比比皆是。塔拉斯蒂说: “19 世纪后半期研究文学文本以作为意义之源,这已经成为音乐解释学的领域之一。”
音乐并非只是一串音符,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文本”。我们“听”音乐时绝非只听到音响,而是听到“和弦与话语的复杂综合体”。我们对音乐的聆听与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话语的影响。音乐与文学是总是处于互文性关系中。
音乐与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为我们解决音乐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的难题提供了合适的角度,它们之间既不是完全的同一关系(音乐叙事学通过模仿文学叙事学获得合法性) ,也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音乐叙事学通过独立于文学叙事学获得合法性)。
而是相互区别、相互交叉的关系。
五、结语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音乐叙事学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文学叙事理论很深的影响。但是由于音乐叙事学过于片面地强调一种叙事性认识,对音乐与文学关系理解僵化,导致对其自身的合法性和独立性认识出现危机,从而产生“影响的焦虑”。同时由于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采取了一些极端化的措施(把音乐与文学隔离,或是用一种叙事观来否定另一种叙事观的价值) 。音乐与文学的互文性关系决定了文学叙事学对音乐叙事学的影响将会持续,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音乐叙事研究者在面对这种影响时不再因立场选择而感到焦虑,而是开放我们对叙事性认识的视野,深入探讨音乐与文学两种媒介的叙事性关联,去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这种影响来发展音乐叙事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美)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徐文博,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