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30至40年代,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理论进行了接受与重构,形成了独特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这在批评界毁誉参半。在探索与论争中,公正与独立的内在精神品格在他的文学批评中愈加显现,其中公正是批评家对自我的约束,独立是批评家对自由的追求。这二重精神品格不仅使得李健吾文学批评成为了典范,更是影响了现当代印象式批评的发展。
关键词: 李健吾; 文学批评; 精神品格; 公正; 独立;
李健吾是一位非常独特的文学批评家,既不同于左翼批评家,也与京派文人有所区别。他独特的文学批评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难以复刻的瑰宝。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学界大多认为李健吾受法朗士、勒麦特、蒙田等人影响而创作了《咀华集》与《咀华二集》,并且认为他的文学批评既带有西方印象主义批评色彩,也与传统直观感悟批评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当下研究大多只注重把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进行横向比较,很少把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发展的角度上进行纵向梳理,因而总结国外因素的多,考察国内因素的少;分析内容特征的多,梳理构建过程的少。只有把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背景下,对比西方印象主义批评,才能突显出李健吾文学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界的独特价值。
一、接受与重构:批评公正性的构建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思想与理论,其中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等等。1922年,在陈小航《法朗士传》的介绍下,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开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视野之中。由于符合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趋势”,加上茅盾对文学思潮的引进、林语堂对王尔德文艺思想的译介、周作人与郭沫若等人对批评直觉的推崇与认同,印象主义批评自20年代流行开来。不少中国的批评家尝试着让“灵魂在杰作中冒险”,张扬自我的主体性。但因为中外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大多缺少理性判断,常常陷入对作品的谀颂或者谩骂的极端,以至于不少批评家对印象主义批评表示质疑。1926年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印象主义批评缺少理性精神的弊端,认为印象主义批评根本错误在于“以批评为创作,以品味为天才”。[1]238针对印象主义批评过分强调“自我”而缺少理性判断的弊端,郭沫若在《批评—欣赏—检察》中也曾谈到:“真正的批评家要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要泯却科学的态度与印象主义的畛域,他不是漫无目标的探险家,他也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的陶醉者。”[2]5可见当时印象主义批评在中国还未能克服“自我”的恣肆,创作出区别于“读后感”的印象主义批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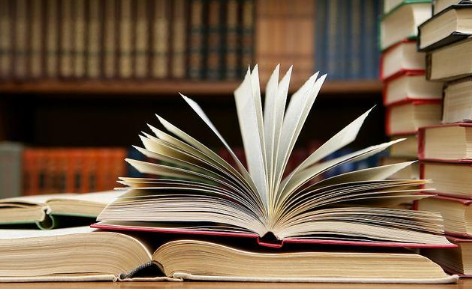
1931年李健吾前往法国留学,期间接触了不少西方重要的思想学说。受到法国印象主义批评余波的影响,李健吾对印象主义批评有过详细的考察。西方印象主义批评至少让李健吾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文学批评观念:
第一,李健吾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都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家独立创造的艺术活动”。王尔德、圣伯夫等人提倡文学批评是一种艺术再创造的活动,认为批评家应当得到与作者相等的创造地位。这让李健吾认识到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创造性的活动,是不必再窠臼于作者的,因此他分外看重批评家独立创造的权利。这一点在李健吾与巴金的争论中格外突显。初出茅庐的李健吾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甚至把巴金的自白当作是作者的宣战,并表示自己面对作家的自白也不会“不战自溃”,他反复强调文学批评是有尊严的艺术,是一种独立的艺术。
第二,李健吾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都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家自我表现的艺术活动”。法朗士认为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强调艺术主体的享乐主义。法朗士认为读者对艺术的理解存在着“人差”的现象,因此否认了“统一”的存在,也否认了艺术境界中标准的存在,认为“美学是绝没有一点实在的东西做根据的”。[3]26法朗士对“自我”的绝对强调和对“标准”的绝对否定,让李健吾在《自我和风格》中使用“变本加厉”来形容。但李健吾仍然十分认可批评的主观性与相对性。所以李健吾在提出“自我”的危险性后又补充———它(自我)有许多过失,但是它的功绩值得每一个批评家称颂。它确定了批评的独立性。它让我们接受了一个事实:批评是表现。[4]李健吾不仅认识到了“批评是一种自我表现”,还认为“自我表现”是批评家“独立创造”的重要条件,对于展现批评的尊严有着积极意义。
第三,李健吾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都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增富并提纯印象的艺术活动”。黄键曾经敏锐地指出,相比于法朗士,李健吾受勒麦特影响更大———如果说李健吾的批评观念与批评范式仍属于印象主义批评的范围的话,与其说它近于法朗士的印象主义,不如说更接近于勒麦特的印象主义。[5]205勒麦特基于“批评总是相对与变化”的观点,认为批评无法夸大为学说,所以更趋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增富并提纯人们由书籍接受的印象的艺术”。[3]41所以他认为批评是一种“印象的印象”。虽然在《自我和风格》中李健吾对此表示并不完全认可,但是勒麦特的观点让李健吾的批评观更加的中正,对他建构直觉与理性并存的批评观有着很大的影响。
这三个批评观念最终都指向一个内涵———文学批评是艺术活动。这一内涵几乎奠定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基调。尽管李健吾认为印象主义批评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他十分认可西方印象主义批评促使“文学批评成为艺术品”上的功绩。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对“自我”的强调也给李健吾文学批评带来了创造的热情与批评的活力。
不过从《咀华集》《咀华二集》的批评实践来看,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不仅做了淘洗与过滤,针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观随意性、批评家灵魂探险的单向性、脱离现实的人生态度等方面,他还进行了重构与超越。
李健吾虽然赞赏“自我”,但不拘泥于“自我”,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观随意性并不认同。1937年李健吾在《自我和风格》中以审慎的态度提出“妨害批评的就是自我”。1939年李健吾在《文学批评的标准》中更直接地指出以自我为标准的弊端———如果批评家随着时间、生理、心理等因素发生变化,那是不是“书本的好坏也天天不同”呢?这说明李健吾认识到了以自我为标准时,批评主体本身不可避免的个性、偏好与变化会损害批评的公正性。这是批评主体必然带有的限制性。所以李健吾认为文学批评不能仅仅是批评家散漫的主观印象,为了达到批评的公正需要以一种宽容、克制的批评姿态,保持一种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在“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公正关系。他宣称批评是自由的,批评家可以自由地表达,又清醒地认识到需要限制危险的“自我”。因而批评家应该要做的是“学着在限制之中自由”,使得直觉印象的批评不至于失了理性。比如在《咀华集》中评价《边城》时,将废名与沈从文的创作相较,就做到了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虽然李健吾更偏爱沈从文“对美的热情与崇拜”,但是对于废名,他努力限制自己的个性,十分中肯地把废名比作“修士”。李健吾认为废名追求的是一种属于少数读者的抽象化的超脱意境,所以他觉得废名的作品虽孤独,但孤洁。他克制了自己的喜爱,展现了批评家充分的包容与尊重。可见李健吾对部分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家极端的主观随意性有所纠正,引导印象主义批评在主观抒发之上形成更为公正的价值评估。
同时,由于看到了批评对象与批评主体的不可分割性,李健吾比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家更看重作者经验,强调文学批评不仅是西方印象主义批评所说的批评家的单向探险,更是两方心灵奇妙的相遇。李健吾在《答<鱼目集>作者》就曾认真地阐述了批评家(读者)读懂作者的不易,但是李健吾并不因此放弃与作家心灵相遇的可能性。在《叶紫的小说》中,李健吾通过考察叶紫“从血泊中爬过来”的人生,借此更加体会到了叶紫小说作为一株“烧焦的幼树”的悲壮与生命力。虽然李健吾偏爱“光影匀停”的作品,但是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李健吾对叶紫小说里压倒字句的热情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包容,更显理性精神。所以李健吾才认为法朗士名句“心灵在杰作里面的探险”的“探险”不如翻译成“奇遇”,因为批评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6]68文学批评并非如王尔德所说的“一人的灵魂记录”,批评家要在杰作中谦虚而谨慎地深入批评对象的心灵。
在现实人生态度上,李健吾也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家不同。李健吾是自觉把审美推向人生的批评家,他强调艺术自由,但也结合人生经验,对现实有所关照。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不是利己的一时快感,而是利他的艺术自由。李健吾追求着艺术化的人生,强调艺术与人生的交融。在《叶紫的小说》中李健吾不赞同茅盾作品里充满“指示”的态度,因为这是被热情填满的“现时”,而他欣赏鲁迅“暗示”的艺术,因为这些血与泪是兼具艺术自由与人生经验的,这才是属于艺术的“现实”。李健吾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强调的是文学艺术化地表现世界的力量。李健吾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一个站在天平中权衡艺术与现实的批评家,他怀揣艺术理想,但并不缺少现实精神。
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三个方面的匡正,形成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独特品质。他抓住了自由与限制、感性与理性、艺术与人生之间的缝隙,维持了文学批评一种“公正”的平衡。李健吾反复强调批评家对批评主体要努力做到“公正”,要实现自我的自由也要限制住狂妄的自我;批评家对批评对象要“公正”,可凭直觉印象展开批评,但也要以包容、理性之心考察作者经验,以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批评家对现实世界态度要“公正”,要艺术自由也要自觉地表现人生,发掘“人类幸福的明征”。因而李健吾说“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7]208李健吾虽然向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借来了一套鉴赏逻辑,但在具体实践中添上了独特的“公正”品格,从而让“自我”戴着镣铐跳舞,诞生了两部独特的文学批评集。当印象主义批评在中国整体上还只停留在“读后感”般随意抒发的阶段,李健吾察觉到“公正”的间隙,及时地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提供了一种印象主义批评范式,建构了属于李健吾“公正”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
二、赞誉与质疑:批评独立性的追求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由于颇有独特性,俨然不同于当时“学究式的文学批评”,也不能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等同,因此在批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中既有着一些赞誉之言,也有着不少鄙薄之声。经过了数次“笔墨官司”,李健吾文学批评中“独立”之品格也愈加突显。
以朱光潜为代表的部分京派文人对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颇为赞赏,他们都认为批评是独立的艺术,不是“现时”的政治工具。1947年朱光潜曾在《文学杂志》中赞许李健吾文学批评的艺术价值与功用———“书评成为艺术时,就是没有读过所评的书,还可以把书评当作一篇好文章读。书评成为文学批评时,所评的作品在它同类作品中的地位被确定,而同时这类作品所有的风格技巧种种问题也得到一种看法。刘西渭先生的《读<里门拾记>》庶几近之。”[8]549朱光潜对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是偏爱的,这不仅因为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风格符合京派文人对批评审美性的追求,更是京派文人建构自身话语时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呼唤。早在1937年《大公报·文艺》中“书评是心灵的探险么?”讨论栏目中,朱光潜就与李健吾同样表现出了对法朗士这句话的赞赏,尽管这一态度表现得很含蓄———朱光潜借法朗士之口,表达了“批评标准是相对的,批评是独立的艺术”的基本观点。这在30、4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范式迅速兴起的背景下显得格外不同。受“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愈发取代了艺术价值。当艺术审美让位于阶级关系,文学批评便成为了政治宣传与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也就形成了李健吾在《咀华集·跋》中提到的“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气息”的批评现象,李健吾甚至觉得那个时候的批评恨不得“把人凌迟处死”。[7]209因而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尤其强调文学批评家应该有高度自觉的批评意识,争取批评的独立性,而不能只是时代的留声机。以朱光潜、李健吾为代表的一批京派文人对批评独立性的追求,也是在革命政治话语中对艺术与美的坚守。
大部分作家对于李健吾的批评风格不置可否,但如果李健吾对作品的理解与作家自身有所不同时,他们也会跳出来守护自己作为作者的阐释权。这自然与李健吾对批评独立性的追求相悖。受印象主义批评观影响,李健吾坚定地认为批评家与作者都有自己理解作品的权利,批评家是独立的,不受限于作者的创作想法。1936年李健吾与卞之琳因为对《鱼目集》有不同的理解而争论不休,李健吾不愿就这样被作者剥夺自己理解作品的权利。于是他在卞之琳的自白之后迅速在《答<鱼目集>作者》中激烈地回应:“我的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吗?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9]178在批评独立的条件下,不存在批评家的理解“全错”。即使批评家与作家的想法不相同,李健吾也推崇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文学批评的对话。批评家是特殊的读者,作家与批评家应该互相尊重。因而朱光潜也在两人争论不休时,发表了《谈书评》。他公允地指出“书评是读者与作者的见解和趣味的较量”,所以“刘西渭先生有权力用他的特殊的看法去看《鱼目集》”。[10]426
不仅如此,李健吾还收到了一些来自左翼批评家的恶评。他们通过否定李健吾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对象,进而否定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面对质疑的声音,李健吾在批评对象上有所调整,但自始至终不变的是对批评独立性的追求。因为批评家并不是某种批评方法的实践工具,他是独立的。1937年4月,李健吾发表《自我和风格》,表达了对印象主义的欣赏与反思,并写下了着名的一句———还有比我更爱印象主义批评的?同年5月,欧阳文辅就发表了一篇《略评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印象主义的文艺批评》,直接把印象主义断定为“垂毙了的腐败的理论”,继而把李健吾定性为“旧社会的支持者”“腐败理论的宣教师”。[11]1453全文先认定李健吾的批评就是印象主义批评,然后给“印象主义”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否认李健吾的批评方法,继而提出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就是腐败理论下隔绝现实、离群独居的文艺批评。对于欧阳文辅想用“一条印象主义的绳索缢死刘西渭”的做法,李健吾感到分外不平。李健吾显然并不认同欧阳文辅直接给自己扣上的“印象主义”帽子。这并不是因为李健吾反对印象主义,而是这个“腐败”的帽子困住了批评者的独立和自由。在李健吾眼里,“他的主子是一切,并非某党某派,并非若干抽象原则,然而一切影响他的批评”。[12]185所以,他并不服膺于什么党派,也不是伺候东家的清客,他的主子也不是诸如“印象主义”等抽象原则。李健吾认为批评者是接受一切的,既“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也“尊重文学独特的个性”。所以他属于社会,但是依然是独立的。也许正因为李健吾并不想被印象主义这些称谓所缚,由李健吾亲自收集整理并于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文学评论选》中,《自我和风格》里的“还有比我更爱印象主义批评的?”一句被直接删除了。尽管这并没有影响学者们把这句着名的话当作李健吾的印象主义宣言,但这句话的删除至少说明了李健吾并不愿意被印象主义“缢死”。
批评家不仅独立于现时政治的要求,独立于作者的想法,同样独立于某种批评方法。李健吾反复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不服从于政治的引导权威,也不屈服于作者的创作权威,更不是某种批评方法的实践品。他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审美活动,是一项有尊严的事业,是一个可以自足生存的艺术品,具有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因而尽管欧阳文辅1947年看到了《咀华二集》再版,又写了一篇《论刘西渭的批评》,把李健吾常说的“公正”“人性”“综合”“比较”等关键词都给予了否定,并认为这些错误认识都得“怪他根据的印象主义的批评”。[13]11李健吾明面上没有再回应。因为欧阳文辅坚持把创作和批评都当作理论的实践品,显然这与李健吾的批评追求并不在同一个讨论空间。欧阳文辅把论证的重点放在了“李健吾用的印象主义理论是腐败的”,但李健吾无意与欧阳文辅争辩印象主义是否腐败。李健吾真正追求的自始至终都是印象主义批评方法背后的“批评独立”。在这些毁誉参半的评论声中,他坚持张扬批评家的主体性,维护文学批评的独立性,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以其独特品格在30、40年代批评界刮起了一阵别样的清风。
三、遗落与重拾:批评品格的传承
经过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的批评实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象主义批评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有了不小的影响。有趣的是,李健吾既是戏剧家,又是翻译家,还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批评家可以称得上只是李健吾的“副业”,而他却以其批评品格和文学才气为后辈留下了印象主义批评的传世之作。
抗战胜利后,借着《文汇报·世纪风》复刊,李健吾一鼓作气发表了四篇《咀华记余》。前两篇《咀华记余》通过抒发自己的批评感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追求,好为接下来大展身手做好铺垫。只可惜正在兴头上的李健吾,只发表了两篇《咀华记余》,谈了谈女作家的创作和抗战时期的名作后,就以一篇《与吉文书》草草收尾了。由于一切都有“阀”的存在,吉文认为李健吾所推荐的抗战名作大多难以出版。李健吾也未改对批评公正性与独立性的追求,对吉文的批评很快就给予了回应,并强调失去“政治的阀”或者“艺术的阀”都是文坛悲剧。而对于自己一贯的“印象主义批评风格”,李健吾也觉得并无不妥,篇幅所限,空空泛谈也是情理之中。因而尽管《咀华记余》未能延续,但是在这一短暂的重现中,依然能看出李健吾对自己批评风格的坚持,以及对批评独立性执着的追求。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已被左翼批评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因如此,李健吾所秉持的“公正”与“独立”之品格更显难能可贵。“公正”是李健吾对批评家自我的约束,是一种“律人先律己”的自觉;“独立”是李健吾在批评界强烈的诉求,是一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坚守。
20世纪50年代,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在批评界逐渐隐匿。这与印象主义批评本身的局限有很大的关系。尽管李健吾完成了对印象主义批评的重构,但是印象主义批评很依赖批评主体的自我发现与灵魂冒险。一方面,如果批评家缺乏足够的素养与灵气,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批评对象的独特性,漂浮的印象就难以沉淀为条例,难以与“读后感”区别开来。换言之,印象主义批评很依赖“天才”。另一方面,一旦言说环境发生变化,天才批评家也难以再次创作恣肆放旷的印象主义批评。
尽管印象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范式难以成为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也就此断流。学术界常认为李健吾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后继无人,这主要由于李健吾作为集大成者,后辈确实少有人能完全超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李健吾“公正”与“独立”的批评品格也一直在滋养着印象式批评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法热”催生了“李健吾热”,而李健吾所代表的印象主义批评也随之被重新发现。但是西方过分强调“自我”的印象主义批评常让批评家们感到苦恼。1988年王蒙就曾经谈到,尽管自己也喜欢印象式批评,但是总感到一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正是不满足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中理性精神的匮乏。所以王蒙觉得印象式批评应有品格高低之分:“感觉印象式批评最近被人称为批评的儿童态,是初级阶段的批评。我觉得这也未必准确。感觉印象式的批评仍有品格高低之分。”[14]562正因如此,王蒙、汪曾祺、毕飞宇等人都在尝试延续和发展直觉与理性兼容的印象式批评。尤其是王蒙,他除了保持着一种“中道”的原则,还加强了印象式批评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联系。比如王蒙1993年一篇引发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着名文章《躲避崇高》,就是一篇印象式批评。王蒙的这篇文学批评虽然结构略显松散、语言不算严谨,但是能从自我的阅读印象联系到“文学世俗化”的现象,可谓是做到了“从独有印象到形成条例”。所谓“高品格”的文学批评应该就是这样,少几分理论方法的禁锢,多几分评点的尺度。若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去考察,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及其精神品格在批评界其实也并未断流。
在当下坚硬的文学批评风格里,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能给读者带来一种艺术审美的柔软力量。感性认识虽然不一定能够建构知识体系,但至少证明了诗与艺术的合理性。文学批评对象———文学作品首先是艺术思维结晶,如果只是把文学作品作为机器一般地拆解,那么也容易在分解中丢失了艺术的整体美感,而李健吾作为一代坚守批评独立、艺术自由的知识分子,在直觉与理性的缝隙中,为批评界留下了一颗难得的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丁帆,刘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郭沫若.批评-欣赏-检察[J].创造周报,1923(25).
[3] 琉威松.近世文学批评[M].傅东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4] 刘西渭.自我和风格[N].大公报·文艺,1937-4-25(328).
[5]黄键.京派文学批评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6] 刘西渭.边城[C]//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7] 刘西渭.跋[C]//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8] 朱光潜.附录编辑后记(二)[C]//许振轩.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9] 刘西渭.答《鱼目集》作者[C]//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10] 朱光潜.谈书评[C]//许振轩.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1] 欧阳文辅.略评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印象主义的文艺批评[J].光明(上海1936),1937,2(6).
[12]李健吾.跋[C]//孙晶.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 欧阳文辅.论刘西渭的批评[J].文艺垦地,1947(创刊号).
[14] 王蒙.十年来的文学批评[C]//郭友亮,孙波.王蒙文集第8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