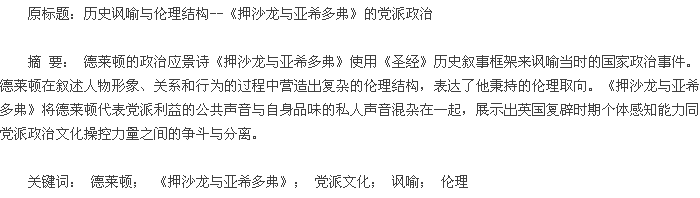
1. 引言
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 的政治讽刺诗《押沙龙与亚希多弗》( Absalom and Achitophel) 创作于一个血与火的年代①。此时英国正值王政复辟时期,经受着教派冲突和党派纷争等重重危机的袭扰。德莱顿特意选择在 1681 年 11 月 17 日发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此时英国政坛恰逢一个举国瞩目而又敏感的时刻: 一周以后,法庭将对沙夫茨伯里伯爵被控叛国罪一案开庭审判。由辉格党一手组建的陪审团最终设法为沙夫茨伯里伯爵洗脱了罪名,并于 1682 年 2 月将其从伦敦塔释放。《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未能真正直接影响判决结果,但它发表后立即风行英国,引导了大众舆论,掀起一股声讨沙夫茨伯里叛国罪的浪潮,帮助查理二世所在阵营有效打击了沙夫茨伯里集团的炽热气焰。
2. 当历史照进现实: 政治讽刺诗的锋芒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长达 1031 行,是一首用英雄双韵体写就的政治应景诗,具有讽喻( allegory) 特质与党派文化背景。这首长诗混杂了基督教神学叙事、历史人物与现实指涉,形成一个宏大的时空架构,这种诗歌构造形式为德莱顿提供了一个文化叙事框架,便于他在虚构与事实之间往复穿梭。《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是各种讽喻和影射的集合体,里面充满了众多对圣经的类比、对《失乐园》的引用、对古典传统的索引以及与真实历史事件情境的互动。德莱顿在诗歌中将讽刺手法与反讽技巧混合在一起,制造嬉笑怒骂的效果,这种将反讽运用于引经据典模式的叙事风格被鲁本·布饶尔称为“影射式反讽”( allusive irony) ( Brower 1952: 43) .德莱顿选择《圣经》典故作为讽喻框架,赋予其厚重的宗教意义与文化底蕴,恰如其分地在时事政治和历史典故之间找到极佳的类比效果和讽喻平衡点。他的这一举动和他当时的政治身份有极大关系。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是以党派宣传册的形式出现,此时德莱顿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头衔---桂冠诗人。作为王朝复辟时期文坛翘楚,德莱顿的笔力自然远胜格拉布街上的寻常文字掮客。德莱顿对自己诗作的党派政治色彩了然于心,在前言中就为自己的举动做出辩解。当时英国政坛争斗最激烈的莫过于围绕教派纷争展开的王位继承权大战: 查理二世没有合法子嗣,其弟詹姆斯觊觎王位,詹姆斯信奉罗马天主教,英国政坛的利益集团就推出蒙玛斯公爵以争夺王权。蒙玛斯公爵是查理二世与情妇露西·沃尔特所生的私生子,在民间声望很高,且颇得查理二世欢心,可能是潜在的王位继承人,然而查理二世却一直没有给予他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德莱顿的《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为其贴上一个文化标签---《圣经》中的着名逆子押沙龙。德莱顿深谙官场之道,不便或许也不想直接对其进行文字攻伐,于是就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支持蒙玛斯公爵争夺王位的股肱之臣沙夫茨伯里伯爵,称其为亚希多弗,即《圣经·撒母耳记》所载大卫王身边的奸佞小人。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里刻画了一个着名的“引诱”场景,戏仿《失乐园》里撒旦对夏娃所发表的巧舌如簧的演说。如此一来,德莱顿就在伦理维度与政治领域巧妙地为蒙玛斯公爵推卸掉了责任,将后者在伦理和政治上“堕落”的过失归咎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怂恿。
在这篇诗作里,德莱顿另辟蹊径通过假托与重构《圣经》历史人物的方式讽刺鞭挞现实生活中的政敌。通过这种方式,德莱顿利用了文化规约中价值取向的趋近力量,将需要讽刺的现实人物形象与《圣经》人物形象进行重叠,这种拼贴效果很好地利用了《圣经》文化叙事框架中的类型化价值取向。德莱顿将所处时代的现实人物与《圣经》历史人物进行类比,吸引读者注意力,融合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在两种时空的切换与融汇之间重塑形成极具张力的文学空间,展示出政治讽刺诗的锋芒。
3. 人物关系营造的伦理结构
人类文明史表明,自然选择是通过进化完成的,伦理选择是借助文学完成的( 尚必武 2014: 72) .《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以押沙龙和亚希多弗为中心展开叙述,构成较为复杂的伦理结构。伦理结构指“文本中以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线索建构的文本结构”,包括人物的关系、思维活动和行为规范之间的交织互动( 聂珍钊 2004:260-261) .德莱顿在《押沙龙与亚希多弗》的文本内部和历史语境之间营造了互相映照的伦理结构,通过巧妙的历史讽喻手法试图向读者还原当时蒙玛斯公爵反叛父亲查理二世这一事件的历史现场,用诗歌语言创造与再现了这一事件的伦理环境,意在使读者对诗中人物产生同情抑或憎恶之感。诗歌描写了几对父与子的人物形象,他对这些人物的不同态度显示出政治倾向是怎样渗透相同的文学文类而在伦理判断上创造差异的。诗中最重要的一对父子是大卫和押沙龙,对应的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分别是查理二世及其私生子蒙玛斯公爵。这一历史讽喻源于《旧约·撒母耳记( 下) 》第 13 至 18 章中大卫和押沙龙父子之间背叛与篡位的典故。虽然蒙玛斯公爵背叛了父亲查理二世,但是查理二世对这个儿子还是有怜爱之心。此时继承危机还未尘埃落定,他们二人有可能和解,也有可能彻底决裂。在这首以宣传册形式出现的诗歌中,如何处理这对父子关系是皇家御用文人德莱顿所面临的一道难题。蒙玛斯公爵悍然侵犯了伦理秩序,德莱顿需要为国王和公爵都找到托辞,利用文学话语舆论的力量帮他们摆脱伦理困境与政治危局。
查理二世在这场政治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责。但是德莱顿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得艺术地组织语言来缓解这个政治僵局,他“在本诗中多处采用的策略是正视严酷的现实,同时却又巧妙地将国王安然无恙地护佑在责难之外”( Zwicker & Hirst 1981: 52) .
党派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了德莱顿在写作时只能“戴着镣铐起舞”,在有限的腾挪空间里尽量展现出诗歌技巧与语言智慧。因此,德莱顿将所有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政治动荡与危机都形容为天命所在,是无法避免的灾祸,因为“生活从来都不全是永远都安宁”( 43 行)②; 国王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误被称为“迟来的复仇”( 940 行) ,在处理危机中的迟疑则被冠以“与生俱来的仁慈”( 939行) .德莱顿知道查理二世的这些弱点,但他所处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在评判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无法以全知叙述者的口吻对此发表过多的议论或影射。他所做的是在结尾处使国王讲了一通长达九十余行的独白。批评界倾向于认为查理二世授意德莱顿将自己在牛津所做的演说词放到《押沙龙与亚希多弗》的结尾部分。文学评论家弗兰克·艾利斯曾将本诗详细对照了查理二世的演说词,发现了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据此推出结论,认为德莱顿在写作《押沙龙与亚希多弗》时心里确实有查理二世演说词的影子( Ellis 1988: 396-397) .党派政治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穿插与引用领导人的话语说辞,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该文本的权威性,而且可以逢迎领导人的虚荣心,使其声名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流传。德莱顿的《押沙龙与亚希多弗》以暗示查理二世身份的典故开始,又以暗含查理二世演说内容的说辞结束,在谋篇布局上通盘考虑的也是为了解决他与私生子蒙玛斯公爵之间的危机。
蒙玛斯公爵( 押沙龙) 与查理二世( 大卫) 之间的人物关系是本诗的中心点。德莱顿时刻谨记自己皇室代言人的桂冠诗人身份,蒙玛斯公爵的反叛违反了两大伦理禁忌: 作为儿子,他悖逆了父亲; 作为臣子,他忤逆了国王。蒙玛斯公爵的反叛行为在行动上已经事实确凿,然而德莱顿在诗作中又不得不为他开脱。为了帮助蒙玛斯公爵推卸责任,德莱顿将蒙玛斯公爵所有在伦理与法律上的失范都归罪于沙夫茨伯里的怂恿和唆使。蒙玛斯公爵被描绘成一个纯洁和无辜的年轻人,他误入歧途是因为受到邪恶的沙夫茨伯里处心积虑的诱惑,他只是在向往伟大与光荣的野心驱使下走错了一步,他“毫无警觉地被引诱着离开了善的德行/被荣耀迷住了心窍,被赞美蒙蔽得得意忘形”( 311-312 行) .即便他在政治和道德上都犯了滔天大罪,还是应该得到自我救赎的机会。查理二世对犯了错的儿子是持这样的态度: “要是我的小参孙想要撼倒房柱/玉石俱焚,就让他自作自受断了生路。/可是,咳,要是他能活下来并痛改前非该有多好! /子女们犯的错做父母的一转眼便忘掉! ”( 955-958 行) 这些话与其说是查理二世自己的想法,倒不如说是德莱顿对蒙玛斯公爵的规劝与期盼。德莱顿相信亲情伦理的纽带能使他们一起安然化解这场政治危机,父子二人重归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