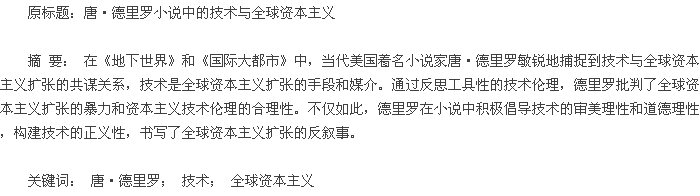
悉数当代美国文坛具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唐·德里罗( Don DeLillo) 无疑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自《白噪音》1985年获得国家图书奖以来,德里罗先后摘取了笔会/福克纳奖、耶路撒冷奖等着名文学奖项。2014年又因其在创作中做出的贡献,获得了诺曼·梅勒终身成就奖,成为继托尼·莫里森、奥罕·帕慕克等着名作家之后第六位摘取该殊荣的作家。有论者根据德里罗小说创作的特色提出,从《地下世界》算起,德里罗开始进入创作的后期阶段。该阶段充分体现出德里罗作为“美国后现代社会最机敏的病理分析家和最具批判性的讽刺作家和社会评论家”[1]的成就。这点从《地下世界》和《国际大都市》对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进行的深刻反思可以看出。这两部小说敏锐地捕捉到技术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共谋关系,技术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手段和媒介。通过反思工具性的技术伦理,德里罗批判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暴力和资本主义技术伦理的合理性。不仅如此,德里罗在小说中积极倡导技术的审美理性和道德理性,构建技术的正义性,书写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反叙事。
一、技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共谋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化、另一些经济大国中心的出现、尤其是东亚地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明显的求助资本主义等现象,把全球化带到了人们意识的最前沿,并且确保了将产生出全球性的不同表征的新的分析”.
阿里夫·德里克把资本主义新近发生的变化称为“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走出欧美等发达国家,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生产方式。这种漫延的步伐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断加快。由于对立性意识形态阻碍的削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重组全球政治经济模式方面的优势不断得到凸显和增强。阿里夫·德里克指出,这种生产方式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组织形式,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促进资本的国际化与全球性。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和赞同。其中,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肯定冷战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扩张的同时,强调了技术在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全球资本主义阶段具有三个非常明显的代表性特征: “科技优先的地位得到确立; 科学技术官僚的产生; 以及传统工业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过程”.技术是全球主义扩张的必要手段和传播工具。
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异常敏感的作家,德里罗在《地下世界》的结尾处专门辟出一节描述网络技术给人类认知方式带来的影响: “人类所有知识都被收集、链接、超级链接在一起,这个网站通向那个网站,这项事实指向那项事实,轻击键盘,敲响鼠标,一个密码---世界无边无界”.[4]825《地下世界》因此提出疑问说,“究竟是网络世界存在于世界还是世界存在网络之中?”[4]826人们通常所谓的“地球村”这个概念离不开信息技术给人类认知世界的模式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随着技术资源在世界各地流通和分配,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德里罗在散文《在未来的废墟中: 9·11之后对恐怖和丧失的思考》的开篇即感喟道: “在过去10年,资本市场统治了话语、塑造全球意识。跨国公司似乎比政府更具有活力与影响力。道琼斯指数的迅速上扬及互联网发展的速度感召我们永远生活在未来,生活在网络资本发出的乌托邦光芒中”.[5]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国别政治权力的约束,冲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地下世界》告诉读者,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消退,资本主义的技术力量迅速扩张,体现出惊人的跨国性,“生产线的速度在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生产线相互配合”.[4]785主人公尼克切身感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和信息化技术给他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他把自己的垃圾处理业务拓展到全球区域提供了条件。他开的汽车则是全球资本主义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物。他开的那辆雷克萨斯牌汽车是“在一个完全没有人影出现的工作区域中完成组装的。没有一滴人类的汗水。当然,方向盘上会有点湿润,那是把产品开出厂房的伙计们留下的。生产系统永远向前流动,每一个细节都采取自动化”. [4]63尼克的汽车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产物。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产品的生产和管理之中,改变了以往依靠熟练工人流水生产的模式。另一方面,《地下世界》第一章以汽车意象开篇帮助读者了解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显得既恰当又自然,因为汽车产业几乎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通常被研究者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兴起的标志性特征,而这两种生产方式都与汽车制造技术的革新和发展直接相关。在世界各地奔跑的汽车不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最好例证,而且是反映全球资本主义时期技术发展水平的代表。
或许正是基于汽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符号性意义,德里罗在《国际大都市》中直接以一辆智能化的汽车来展现技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使这部表面上以纽约生活为主题的小说超越了国界的限制。正如德里罗在一次采访中所强调的那样,这本小说“并不是一本美国小说,它讲述的是关于纽约与世界的事情”[6].初听起来,这种广阔视野与小说简单的故事脉络并不符合。因为该小说叙事线索简单,讲述了股市操盘手埃里克·帕克一早乘坐私家轿车穿过纽约市中心到童年成长的街区理发的行程。但是,埃里克途中遭遇反全球化游行队伍堵路、避让总统车队等事件,而且他自己还不时地下车与情人幽会,结果原本无需半个小时的行程竟然花费了一天。读者发现,随着小说叙述时间的延长,小说中的空间意象随之拓展。这里的空间意象不仅指埃里克看见的商店、走进的饭馆等物理空间,而且指通过安装在埃里克轿车中的电脑显示屏连接的外部虚拟空间。凭借自己支配的信息技术,埃里克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无处不在的电子信息设备让他在股市国际交易舞台上如鱼得水,就连他手腕上配带的手表内都设有微型照相机,以便他收集周围的信息。当然,最能体现埃里克对技术力量掌握的还是他那辆被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武装起来的轿车。这辆经过改造的轿车里既安装有微波和心脏调节器,又有收集世界各地股市信息的电子显示器,他凭借声音和手势就能够使所有技术系统为他服务。他可以随时发布命令,从银行贷款用以股市投资,或者侵入他人的信息系统,获取想要的秘密和情报。所以埃里克尽管年龄不过三旬,但是他对股市的影响遍及全球。因此,有论者提出,正如埃里克的公司“帕克资本”所寓意,他是“全球经济霸权的一个巨大象征”.[7]
技术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发动机和力量源泉。德里罗在撰文分析美国在全球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时,就特别突出了技术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他指出,“技术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是这个星球上的超级大国。我们设计的材料和方法让我们有可能把握住未来。我们不必要依靠上帝,也不必指望先知或其他出人意料的事情。我们就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我们制造神奇,制造改变我们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的系统和网络”.[5]
技术的力量被崇高化,是资本主义施展点金术的法宝。然而,对于一名被批评者称为“坏公民”的作家来说,德里罗不仅为读者描述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面貌,而且把“反对权力代表的事物、政府经常代表的事物、公司指令的事物”[8]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德里罗在为我们呈现技术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的同时,通过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技术伦理的工具性,讲述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暴力性质。
二、工具性技术伦理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暴力
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是一篇无辜的福音。从欧美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主义在向世界各地植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冲突。英国学者大卫·哈维在研究全球资本主义时,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性。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冷战结束之后全球资本失去对抗性力量束缚的结果,成为资产阶级集团在冷战之后谋取经济利益、推行政治权利的重要方式。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日常的生产、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和文化冲击、流入和流出不同的领土实体( 比如国家或地区性权力集团)的方式”
来确保自己在世界的霸权,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政治性同样蕴含在德里罗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描绘中。杰里·瓦尔萨瓦在评论《国际大都市》时,就把埃里克视为一名“无赖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形态的特征是置社会伦理准则于不顾,致力“追求特权和不公平的利润”.
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中的贪婪和狂妄自大成为德里罗小说揭露的焦点和批判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德里罗把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暴力与资本主义所推崇的功能化和工具性的技术伦理联系在一起。
早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陷入由工具理性编织的“牢笼”的过程。这种工具理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成为脱僵的野马,渗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和结构组织的各个缝隙,以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理性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信奉的技术伦理观。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分析,这种技术伦理观到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时期最终确立了主导地位。在后工业时代,原本与“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的“技术 - 经济领域”摆脱道德伦理和审美伦理的约束,成为资本主义运作的中心和主导。这一领域“与生产的组织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有关。它界定社会的职业和分层系统,涉及技术使用的工具目的。在现代社会中,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调节的模式是经济化。究其根本,经济化意味着在雇佣关系和资源使用中讲究效率、最少的支出、最多的回报、最大化、最优化以及其他类似的判断方式”.对资本主义来说,社会财富和经济利益的积累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以征服和控制为目标的工具性技术伦理观自然受到欢迎。
不过,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不仅把资本主义工具性技术伦理崇高化的过程归因于经济因素,而且揭示了冷战时期政治原因对这一进程的加速作用。在小说“序言”部分,德里罗把1951年10月3日举行的一场棒球赛和前苏联试爆第二颗原子弹并置在一起。在场的观众没想到,“这一天对于冷战的构建至关重要。因为美国从此有了足够强大的对手,以维系二战后美国认为美国主权正遭受攻击的妄想症”.
对前苏联军事实力的敌视与美国当时兴起的“红色恐慌”相互呼应,使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国内思想的主流。当时在球赛现场的中情局局长胡弗收到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情报后,立刻意识到苏联这次试验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巨大的影响。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推动下,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一方面秘密地增设军事基地和武器研发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方式让民众认同只有更先进的技术才能战胜敌人、才能确保国土安全的观点。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鼓励军事技术与工业生产和消费文化相结合。有一家销售除草剂的工厂推出名为“轰炸你的草坪”的活动,杜邦公司的宣传口号则为“为了更好的生活,通过化学生产更好的事物”.工具性的技术伦理成为美国政府组织生产和操纵人们思想的手段。①冷战结束之后,工具性的技术伦理并没有受到质疑。相反,它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向世界各地推进。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家,德里罗敏锐地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私与贪婪。工具性的技术伦理已经构成资本主义置他人权益不顾,为自己在全球谋取利益辩护的理念。在《地下世界》中,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暴力可以从资本主义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垃圾这一典型事例略见一斑。尼克在哈萨克斯坦看到有好几个人穿着上面印有为同性恋做广告的 T 恤衬,而这些 T 恤衬是欧洲一次同性恋集会之后剩下的商品,被当地一位不知情的商人买回了国内。另外,尼克在一次垃圾处理公司会议上还了解到,有一艘不断变换名字的轮船两年来不断穿梭在西非海岸和远东地区,向各国输出海洛因,倾倒垃圾焚烧灰尘和工业废料等。倾倒的工业废料有“2千万英磅的砒霜、铜、铅和水银”.[4]278有论者分析说,德里罗在冷战之后出版《地下世界》旨在告诉读者“超级大国利己主义的冷战意识及战争贪欲其实从未中断,这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存逻辑与运作规则。无论是冷战还是后冷战,美国都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以武力为着力点,以利益为归宿的”.[13]在工具性技术伦理观念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带着谋取全球资源的欲望迅速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