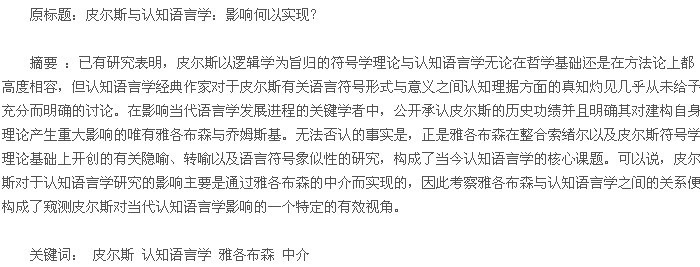
一、引言
美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皮尔斯尽管于上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回归人们的视野,但是其跨越符号学、语言学、哲学、逻辑学、数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社会学、传播学乃至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思想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知识宝藏。新世纪以来,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这位特立独行、一度被人忽略的伟大学者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努力从他的着作中发掘能够推进自身研究的理论资源。
由于语言是最为典型的符号,所以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现代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共同奠基人索绪尔就曾明确将语言学视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另一源头,皮尔斯符号学虽较之索绪尔符号学包罗更为宏富,并且以逻辑学及哲学为其最终旨归,但其中也蕴藏着有关人类自然语言的系统而精辟的观察与思考。
在当前语言学界尤其是重视语言形式理据研究的认知语言学界,学者们也开始努力在自身的研究与皮尔斯符号学之间建立各种关联,试图为本学科的发展在逻辑与历史上找到更为坚实的基础。对于皮尔斯符号学与当前正处蓬勃发展的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大多从哲学基础、语言观以及方法论维度考察二者之间的相容性,却很少有人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皮尔斯符号学思想是如何进入认知语言学领域的。从语言学史角度来看,确定学科及理论之间关系最为关键的证据是,考察相关流派经典作家的代表性着作中是否公开承认过对方的影响或者至少参引、评论过对方的着作,也就是说需要提供确切的书证。
目前,一般认为皮尔斯符号学思想是通过英美两条线路进入当代语言学领域的:一是 1920年代英国着名符号学家、皮尔斯的支持者维尔比夫人(Lady Welby)的门生奥格登(Ogden)与其合作者理查兹(Richards),他们在吸收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基础上,撰写并出版了有关语言意义研究的名着《意义之意义》,从而使皮尔斯开始被语言研究者关注;另外一条线路则是由移居美国的着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和生成语言学创始人乔姆斯基开创的。
前一路线虽出现较早,但较之后者其影响力却十分有限。原因主要有二:一来,奥格登与理查兹虽然对语义研究提出了很多创见,但他们主要以哲学及文艺学为自己的志业,更为重要的是,自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的重点在于语言系统的结构分析,语义并非当时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从而其影响力在语言学界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二来,由于二战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以及战后对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语言学在美国迅速获得发展,再加上受战争的影响,大量研究人才移居到美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到美国,与其他学科一起很快成为世界语言学的主流,至今这一格局仍未改变。
一般认为,近年来构成研究热点的认知语言学是在反对乔姆斯基所创立的生成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派,甚至有人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事实上意味着由乔姆斯基等人开创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终结,从而开启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新时代。这种说法是否有夸大之嫌,我们暂且不论,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以认知功能为取向的语言学的确是当今唯一能够与形式语言学相互竞争的语言研究范式。如上所述,在考察皮尔斯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时,人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相容之处,但同时一个令人倍感诧异的事实是—“皮尔斯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彼此无视对方的存在。”
我们认为,所谓的“彼此无视”只是一种阶段性现象(甚至可以说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通过深入考察雅各布森对皮尔斯思想的结构主义解读以及他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皮尔斯对于认知语言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雅各布森而实现的。因此,考察雅各布森与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从历史影响的角度探讨皮尔斯对当代认知语言学影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二、雅各布森对于皮尔斯思想的结构主义解读
罗曼·雅各布森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是努力在语言学与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关键人物。
在普通语言学领域,他对于语言普遍项的不懈追求不仅直接推动了以乔姆斯基为首的形式学派对于人类语言形式普遍项的探究,建立了以刻画普遍语法为目的的生成语言学研究范式,而且也影响了以格林伯格(Greenberg)为代表的另外一批学者,促使他们努力探寻人类语言中存在的实质普遍项以及蕴含性普遍规律,从而开创了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新范式。
除了上述两项广为人知的功绩之外,雅各布森在整合索绪尔以及皮尔斯符号学基础上确立的语言符号观还深刻影响了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尤其在构成当前认知语言学核心课题的语言象似性、转喻以及隐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尽管不同理论家对于符号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符号的本质在于:被我们称为符号的东西“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着的,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现实”。
如果我们把折射物称为形式,把被折射物称为该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所体现的内容,那么可以说符号学关注的主要是构成符号的形式和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即意指关系。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但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符号意义的存在与识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同研究者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对符号意指关系和过程的认识就会不尽相同,对其类别也有着不同的划分。自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们开始对符号的研究产生自觉的学科意识以来,对于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意指关系产生了两种主要的认识。一种是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的二元意指模式,并且以语言符号为各类符号的典型代表,将符号系统内部由能指与所指之间相互界定所形成的差异而产生的价值作为确定意义的关键机制。
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是符号系统中诸种成分相互区分的结果或效应,相对于系统之外的世界及符号的使用者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于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单位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接关系相互之间表现出绝对的差异,所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生活在相似的物质空间并且具有共同种属特性的人类,会使用完全不同的声音来表征看上去十分相似的概念。与索绪尔“能指 - 所指”二元符号模式相对的另一重要模式是由皮尔斯提出的“代表物 - 对象 - 释义”(representmen-object-interpretant)的三元符号模式。简要来说,“代表物”指的是符号的形式;“对象”是符号的所指对象;“释义”是符号的意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被称为“意指过程”(semiosis)。与索绪尔二元模式不同,皮尔斯引入了“对象”,从而使符号与外部世界发生了关联;其“代表物”大致相当于索绪尔的“能指”,“释义”大致相当于索绪尔的“所指”,但是皮尔斯的“释义”与索绪尔“所指”之间存在的一个显着不同是:其本身还可以构成一个符号。
用皮尔斯的话来说:“一个符号……有其特定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它在该接受者的头脑中创造了一个对应物,这个对应物或许构成一个更为高级的符号。我把由一个符号以如此方式创造出来的另一个符号称为‘释义’。”
另外,在皮尔斯看来,释义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符号自身的信息,另一个是符号使用者关于生活世界的一般知识,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而前者又不断对后者进行改造。
由于引入了本身可以进入无限延伸的符号化过程的“释义”和“对象”这两个要素,皮尔斯在符号系统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了有效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将具有百科知识的符号使用者在符号意义构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考虑了进来,从而为考察符号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的包括认知操作在内的各种理据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在雅各布森看来,皮尔斯的“释义”在意指过程中具有无限延伸性以及可转换性(或曰“可翻译性”),这种可转换性就构成了意义的真正内容。另外,皮尔斯还一再强调,符号不仅具有一个内在的一般意义,而且还具有语境意义,在具体交际中,后者的作用是使前者具体化从而顺利实现交际的目的。皮尔斯的上述符号思想对雅各布森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皮尔斯在符号意义上的这些认识,为我们把握难以捉摸的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点,因此完全可以说“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的惟一可靠的基础。”
他还感叹道,如果语言学家早一点了解皮尔斯的上述符号观以及意义观,“那么有很多无谓的争论本都可以避免。”
雅各布森还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不同于索绪尔符号学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将语言符号置入整个符号世界来加以平等考察,提出了统一的分类,这不同于索绪尔只是将语言符号作为符号的典型而孤立地观察。这种更为宏观的视角,反而使得研究者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语言符号的本质。但是不容忽略的是,作为在索绪尔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语言符号学家,雅各布森免不了带着索绪尔“能指 -所指”二元符号观来看待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论,努力在二者之间建立关联。他认为,如同索绪尔一样,“皮尔斯也将符号的‘物质属性’(material qualities)(即任何符号的‘符号形式’(signans))与其‘直接释义’(immediateinterpretant)(即‘符号内容’(signatum))明确区分开来。‘符号’(或者用皮尔斯的术语representamina)、‘符号的形式’以及‘内容’之间存在三种明显不同的意指关系。”
而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得皮尔斯区分了以下三种最为基本的符号类型:(1)相似符号: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相似关系,这种相似关系不仅包括诸如一只狗与其照片之间所具有的图像相似关系,还包括诸如地图与实际国土之间所形成的拟像相似关系(diagrammatic iconicity)以及构成隐喻映射的两个要素之间所具有的相似关系;(2)索引符号:形式与内容之间能够发生意指关系主要因为二者是相邻的,并且“从心理上来说,索引意指关系主要取决于由临近关系而唤起的联想。”例如,烟就是火的一个索引,但是这种索引关系的建立要依赖于符号使用者的常识—“有烟的地方一定就有火”;(3)象征符号: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意指关系被认为是强加的,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于它已经作为规则而存在”,而不是由于相似或者相邻而发生的,人类自然语言就是这类符号的典型代表。
不过雅各布森一再强调,虽然语言符号是典型的象征符号,但是根据皮尔斯的本意,以上三种划分仅仅是连续统上的三个不同的极点;这三种意指关系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于某个特定的符号之中。这就是说,象征符号中可以包含象似关系以及 / 或者索引关系,反之亦然;最为理想的符号是那些尽可能以同等比例包括象似、索引以及象征特性的符号。
尽管雅各布森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能将皮尔斯以哲学逻辑学为旨归的符号学理论做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但无法否认的是,雅各布森并不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去阅读皮尔斯符号学着作的。从上文的讨论不难看出,虽然他明确肯定皮尔斯三元符号观在意义研究上的功绩,但是在论述皮尔斯的符号分类时,雅各布森还是将其简化为索绪尔“能指 - 所指”的二元模式。尽管他没有使用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这样的措辞,但的确也使用了皮尔斯不曾用过的“符号形式”(signans)以及“符号内容”(signatum)这样的术语。实际上,对于自身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眼光去能动理解皮尔斯这一做法,雅各布森并不讳言。
在其专门讨论皮尔斯对于语言学研究的功绩的文章—《皮尔斯—语言科学的领路人》中,雅各布森就明确指出,“我们就完全可以把皮尔斯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真正而大胆的开拓者。”
因此他认为,一战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没能让索绪尔与皮尔斯同时出现、相互参照,应该是语言学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
其实,雅各布森将皮尔斯置入结构主义框架中进行理解,有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从理论内部来看,尽管雅各布森是公认的索绪尔结构主义主要继承者,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他们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分歧。除了上文提到,他不满意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系统与包括使用者在内的外部世界孤立开来而使得意义研究失去了有效支点以外,他还不赞同索绪尔在“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等范畴之间所做的过于绝对的二元对立划分,并且对索绪尔就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提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与线条性—持有保留看法。
而这些观点与雅各布森主张将语言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分不开的,雅各布森反复指出,布拉格学派眼里的功能(function)不是数理逻辑意义上的“函数”(function),而是指语言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是用来实现人际交往的。
另外,注重语言功能研究的雅各布森,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语言符号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同构性问题(isomorphism)。在他看来,语言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实现的功能决定的,这是他反对索绪尔将语言符号任意性绝对化而走向皮尔斯并对其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内部原因,因为皮尔斯在有关语言符号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同构性这一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使得同构性研究有了象似性这样有效的依托机制。
雅各布森移居美国以后,在承认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及符号学发展做出巨大历史功绩的条件下,也在不同场合表明自己与索绪尔语言学之间的分歧,并且有意识地从皮尔斯那里寻求理论资源来改造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这与雅各布森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有着很大关联。尽管美国与欧洲大陆在文化上同气连枝,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及文化交流,但是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人力求在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等方面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旧世界的新模式。就语言研究而言,由于研究印第安人语言的实际需要,美国人基于人类学研究模式相对独立地发展出了一套描写语言的结构主义方法。因此,可以说当雅各布森由于战争的原因被迫移居美国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环境的变化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以便尽快适应未来的生活,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不过,雅各布森对于索绪尔态度的转变也的确引起了一些争议,着名索绪尔研究专家哈里斯(Harris)就曾指出,雅各布森在欧洲大陆的时候,对索绪尔的评价主要是积极的,但是移居美国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达到了不惜曲解索绪尔以便迎合美国研究传统的程度。
因此也可以说,雅各布森渴求融入美国学术圈的移民心态是促成其对皮尔斯符号学思想进行结构主义解读并以此来发展索绪尔符号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
三、雅各布森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
一般认为,雅各布森是 20 世纪着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是他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结构主义”这个术语。
然而,如上文所述,与索绪尔不同,雅各布森认为语言系统不是独立于外部世界以及语言使用者而存在的,语言之所以具有特定的形式是由语言的功能所决定的,语言结构与其所表征的世界的结构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影响下,他将这种同构性进一步明确为语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象似关系,并且结合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系统认知观对隐喻以及转喻提出了独到的看法。雅各布森所关注的问题不仅构成了当前认知语言学核心课题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在语言的符号观、语言形式的功能决定性(即理据性)等方面的观点与认知语言学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容性。
在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及理论目标进行介绍的文献中,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往往局限于哲学基础、理论目标、工作假设、主要课题与人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于语言与思维之间所存在的符号关系深入认识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以符号学的方式来研究语言明显构成了认知语言学的基础。”
对于认知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存在的天然关系,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组织者、德国着名认知语言学家德汶(Dirven)有着深刻的认识,例如在其与维斯普尔(Verspoor)合作撰写的经典认知语言学教材《语言以及语言学的认知探索》的第一章“语言的认知基础—语言与思维”中就明确指出:“任何交际行为—不管其发生在动物之间还是人类之间—都是通过符号来实现的,从而对其进行的研究属于符号学领域。符号总是用来表征它自身以外的东西,这个被表征的东西我们称为意义。符号及其意义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关系:索引符号或索引符“指向”它所表征的东西;象似符号或象似符提供它所表征东西的图像;象征符号或者象征符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规约关系。这套符号体系是帮助人类组织世界以及他们的世界经验的一些认知原则所产生的结果。”
可能由于该书是一本教科书,所以作者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没有像一般的学术着作那样对前人的文献进行必要的参引,但是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作者秉承了与雅各布森类似的符号观。这主要体现在:(1)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指称构成符号关系的两个要素—雅各布森使用的是“符号形式”(signans)以及“符号内容”(signatum)这两个术语,而德汶与维斯普尔使用的是“符号”(sign)以及“意义”(meaning)这两个术语—但很明显他们都是在吸收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同时,仍然坚持索绪尔的二元模式。(2)如同雅各布森一样,尽管将皮尔斯构成符号的三个要素“代表物”、“对象”以及“释义”参照索绪尔体系压缩为“符号(形式)”以及“符号内容 / 意义”,但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发生的意指关系类型划分上,作者同样吸收了皮尔斯的三类划分方式。另外,尽管上述引文中没有直接体现,但是两位作者紧接着指出:“在我们称为语言的象征符号系统中,我们可以识别出与上述三类符号相对应的原则。”它们分别为“索引性原则”、“象似性原则”以及“象征性原则”;在他们看来,虽然一般语言被认为是典型的象征符号,但是语言中也存在着索引关系以及象似关系,并且这两种关系是我们人类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认知原则,是我们语言形式背后的动因。作者对于语言符号性质的这些看法,如果将其与雅各布森 1965年在美国艺术及科学学院大会上的发言《语言本质的探索》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无论是在对皮尔斯符号学的理解与化用上,还是在对语言本质的观察上,都如出一辙。如上所述,尽管两位作者此处没有明确交代自己语言符号观的来源,但是该书的第一作者德汶在其他场合反复强调过雅各布森对于认知语言学尤其是在转喻以及隐喻研究上的影响与贡献,他甚至把雅各布森称为当代认知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莱考夫(Lakoff)的“精神教父”(spiritual father)。
实际上,着名认知语言学家海曼(Haiman)就上述这篇文章对于认知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雅各布森在整合索绪尔以及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基础上提出的语言符号观以及据此而提出的语言形式的象似性动因研究,虽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所关注,但近期越来越受到众多语言学研究者的青睐,从而构成了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
雅各布森除了对构成当代认知语言学方法论基础的符号学以及语言象似性动因研究有着重要影响之外,他的另一篇论文《语言的两个方面以及失语症的两种类型》对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推进近年来人们对于转喻和隐喻的本质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篇经典文献中,雅各布森通过对失语症病人的观察,发现他们所遭受的语言障碍主要表现为两个类型:一类病人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对语言单位的选择上;另一类病人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将语言单位组织成合法语言结构上。雅各布森认为,这两类困难从病理的角度印证了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系统运作所依赖的两个基本机制的存在:一个是“以两个或者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而构成的“句段关系”;另一个是“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的“联想关系”。
句段关系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组合性操作,而联想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选择性操作。这两种语言运用所依赖的操作机制的存在有着其坚实的心理现实性基础。为此,雅各布森还提供了来自心理实验的证据:在实验当中,当被试看到“小屋”这个语言刺激时,有的被试的反应是“烧掉了”,有的是“一个简陋的小房子”。在雅各布森看来,第一种反映就是组合性的,而第二种则是选择性的表现。因此可以说,组合与选择不仅是语言系统所具有的两个本质属性,而且是语言使用者在运用语言时所依赖的两个基本的认知操作机制。与此同时,雅各布森再次将皮尔斯符号学与上述索绪尔建立的句段以及联想这两种系统关系以及运作机制结合起来,他认为“如果运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932,1934)提出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概念—‘释义’的话,这两种机制给每一个语言符号提供了两套‘释义’。”
在他看来,联想(或者说选择)机制使符号指向自身从而实现本质上是元语言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的释义,句段(或曰组合)机制使符号指向语境从而实现指称功能的释义。这篇文章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雅各布森发现索绪尔所区分的两种语言运作机制分别依赖于语言符号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similarity)以及临近性(contiguity)。在语言符号选择方面存在障碍的失语症患者其实是在语言符号相似性关系方面出现了紊乱,而在组合操作方面存在障碍的患者则是在临近性关系方面出现了紊乱,而这两种紊乱跟隐喻以及转喻两种传统的修辞现象紧密相关。这一发现,促使雅各布森对这两种常见的修辞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转喻与隐喻是人类语言所依赖的两种重要的运作机制,“话语的推进会沿着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一个话题或者通过相似关系或者通过临近关系而导向另一个话题,前者可以用‘隐喻方式’这个最恰当的术语来概括,后者可以用‘转喻方式’来概括。”
由此可以看出,在转喻以及隐喻问题上,雅各布森已经超越了将二者仅仅视为修辞格的看法,而将其视为语言运用所依赖的两个基本的机制。虽然雅各布森还没有将转喻与隐喻上升到人类思维赖以进行的两种基本方式,但是对这两个机制所依赖的经验基础—相似性与临近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可以说其基于符号学而提出的转喻与隐喻模式跟当下认知语言学的相关观点已经十分接近了。除此而外,雅各布森认为转喻与隐喻构成语言系统的两个“极点”(poles),因此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他将转喻与隐喻平等看待的做法,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和超前性。这体现在,当莱考夫与约翰逊(Johnson)两位认知语言学奠基人在 1980 年发表他们的经典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时候,语言学家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于还认为相对于转喻而言隐喻更为根本。直到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雅各布森的看法才开始为认知语言学家所关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有关转喻与隐喻的研究。
例如,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国际认知语言学会前主席克劳斯·吾威·庞特(Klaus-Uwe Panther)就在雅各布森的影响下借助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转喻理论模式。在其 2006 年发表的《作为使用事件的转喻》一文中,庞特不仅对雅各布森超越修辞学传统转喻观的开拓性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进一步确认转喻依赖的是相邻关系。另外,在雅各布森的启发下,他将转喻所涉及的两个要素(“来源”(source)与“目标”(target))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皮尔斯所提出的索引关系,建立了概念转喻的符号学模式,有效解决了认知语言学转喻及隐喻研究中因“概念域”(domain)这个关键概念缺乏统一认知标准而带来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余论
如前所述,有学者发现虽然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无论在哲学观、意义观以及符号观方面都与当前的认知语言学高度相容,但是后者似乎无视前者的存在。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应该是根据诸如莱考夫以及兰艾克(Langacker)等认知语言学经典作家的文献中几乎从未引用过皮尔斯的着作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莱考夫跟随雅各布森学习过并且在很多方面深受其影响,但是他分别出版于1980、1987 以及 1999 年的三本被视为认知语言学圣经的着作中,几乎都没有引用过雅各布森的着作,同时也没有引用过皮尔斯的着作。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况 90 年代中期以后有所改变。如上文所述,这是由于认知语言学家越来越认识到,莱考夫等经典作家在转喻以及隐喻的本质、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识别标准等方面的观点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一批学者努力从雅各布森的着作中寻求理论资源,从而积极评介以及参引雅各布森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皮尔斯的名字也开始高频率地出现在相关文献当中。可以说,在认知语言学家的着作中,皮尔斯与雅各布森是紧密相关的,认知语言学家对于皮尔斯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于雅各布森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雅各布森是皮尔斯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得以实现的关键中介。
尽管莱考夫等人在其着作中忽略雅各布森与皮尔斯的原因需要语言学史专家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皮尔斯正是在雅各布森的中介作用下而逐渐为广大认知语言学者所熟知的,因为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不仅在语言哲学观、意义观以及符号观等方面都为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方法上也为包括认知语言学在内的整个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Houser,N.,Reconsidering Peirce’s Relevance //M. Bergman,S. Paavola,A.-V. Pietarinen & H. Rydenfelt(eds.),Ideas in A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pplying PeirceConference [C],Helsinki:Nordic Pragmatism Network,2010.
[2] 郭鸿:认知语言学的符号学分析 // 外语教学 [J],2005 年第 4 期。
[3] 苏晓军:皮尔斯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相容性 // 苏州大学学报 [J],2012 年第 3 期。
[4]Koerner,E. F. K.,Remarks on the Sources of R.Jakobson’s Linguistic Inspiration // Cahiers de l’ILSL[J],1997,№9.
[5] 张留华:皮尔斯哲学的逻辑面向 [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 李伟荣、贺川生、曾凡桂:皮尔斯对雅各布森的影响//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7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