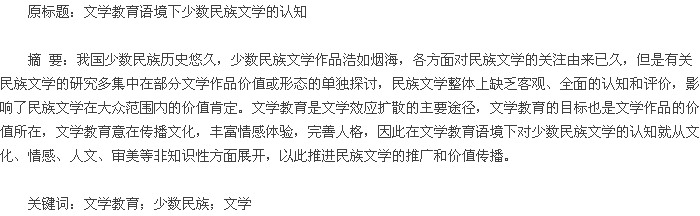
引言
从文学的本质来看,文学的起源是因人类表达情感的需要,在歌舞等肢体语言无法表达更深层次的情感内涵时,文学因其特有的包容性和抽象性而成为民众表达情感的最好方式。也正是因为文学的这种表达优势使得文学在传播时并不能很好地为众人认知和理解,另外文学还具有认识、教育等社会功能,因此文学需要通过专门的文学教育来研究和解释,文学教育的本源由来如此。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指向和当前文学教育的问题,本文把文学教育理解为:在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基础上,通过教育的方式,即阅读、讲解和讲授等方式,使受教育者领悟文学中所蕴含的审美意蕴,丰富其情感体验,完善人格,并提高文化素养和语文能力等。在此文学教育内涵界定下,文学教育期望借助文学所达成的目标便成为文学教育对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认知的依据标准。逆向思维下,对相关文学的认知也应根据以上文学教育的目标来认知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例外。我国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文学资源,从少数民族的历代古典文学、民族民间文学到当代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但因各种因素制约,有关民族文学的认知缺乏力度和广度,不够全面、客观,影响了民族文学的价值认知和推广。
根据以上文学教育的理念和目标,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需要在知识性认知的基础上从审美、人文、情感、文化等方面切入,下文的阐述也从以上几个方面展开。
一、民族文学具有民族审美特征
人类对审美最初的表达是歌舞,文学是之后较为抽象的审美表达,文学教育需要把文学中所蕴含的美感重新阐释出来,因此文学教育本身便是一种审美教育,提高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精神是文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文学教育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审美过程,是对受众的审美意识唤醒、共鸣、提升的过程。[1]
在审美的过程中,受众的人格得以完善,情操得到陶冶。有关文学教育是美育的观点,蔡元培认为人类可以在音乐、雕塑、图画、文学中找到自身遗失的情感。因为美育可以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文学教育是美育,间接上也肯定了文学本身必然是美的载体,对此,王国维有关“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言辞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另外,当下有关文学教育的美育界定也是当前不少学者的共同观点,在此观点下,对民族文学的认知必然不能离开其中的审美意蕴。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蕴表现在多个方面,文学格式、文学语言、文学内容、文学音韵、文学思想性等都能体现出文学的美感来。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审美,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于民族土壤,饱含着民族审美意识,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审美风格,具有很好的审美意蕴,如《福乐智慧》 便是民族文学饱含审美意蕴的典型例证,从思想上来看,作品以道德伦理贯穿其中,宣扬道德和正义,融汇真善美,情理相结合,推崇诚实、谦逊等美德,而从形式上来看,作品通篇也保持了整齐的对仗格式,另外在音韵上,作品也朗朗上口,给读者以美的享受,综合观之,《福乐智慧》 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味,这也是其能在维吾尔族群众中长久流传并发生深刻影响的根源所在。彝族长篇史诗 《阿诗玛》 不仅在格式上对仗整齐,具有音韵美感,在语言特色上,自然、朴素、简洁、新鲜,同时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诗歌在整体上扣人心弦,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特别是在内容上对阿诗玛的美好形象塑造,更强化了长诗的审美意蕴。文学教育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因为文化作品的审美意蕴,民族文学作品才形成了动人心魄的力量。少数民族文学源于民族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民族氛围形成了民族民众独特的审美,这种审美体现在文学作品上便是作品中的审美意蕴,不仅是文学本身的形式美,更是文学本身的美学思想,丰富的审美意味支撑着民族文学经典作品代代流传,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必然要把握其中的审美意蕴,从文学这种发现民族的美的力量,才能真正理解民族文学。
二、民族文学思考人的原始本性
文学是人学,以人为本是文学创作的永恒追求,在文学创作者的笔下,人性和人类命运是不变的主题,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表达着作者对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由于文学在对民众纵向、横向的解剖中,有关人性和人的价值探讨被一再提起,形成了文学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
文学教育需要把文学这种人文关怀的特质传递下去,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关怀来使受众有勇气反省自身,在真正意义上有勇气对世界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生命进行追问。文学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到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方面便是要注重民族文学中的人文关怀。少数民族生活的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民族文学中所展示的人文特征也有所不同,因多数民族生活地域偏远,自然环境恶劣,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与其他生活在繁华城市的人群相比较,民族生活更加纯粹更加自然,因此在很多民族文化作品中并没有现代物质方面的繁杂,以及因物质功利带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心态,更多的民族文学作品更关注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相对而言,更关注人性深处的东西,而不是在现实功利心态下多样化心理的挣扎与纠葛。以藏族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 中对傻子形象的塑造为例,作者通过“傻子”的傻把这一形象从世俗制度中脱离出来,在前提上使人物摆脱了现实生活中的困扰,使其所作所为更符合人类原始的本性,在傻子看似疯癫的言语行为中,作品用近乎直白的方式袒露了人性最深处的东西,整部作品实质是在考问人性和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充满了人文气息。在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中同样也充满了人文关怀,在作品 《越过克波河》 中,猎人蒙克因未能遵守其与老猎人卡布坎的约定,在追踪公鹿过河时,被老猎人误伤,在新老猎人的纠纷中,把人性贪婪的一面进行了展示,并指出人性的贪婪最终要受到惩罚,蒙克的悲剧便是因为他把规矩踩到自己的脚下,超过了人性的底线。有人曾对乌热尔图的 《七岔犄角的公鹿》 这样评价道:这是人性的发现,人性的勇敢,是憎的加强,爱的升腾,是力的耀武,民族文学浓厚的人文气息由此可见。
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少有酒店、高楼、汽车等现代文明的物质体现,更多的是天与地、自然与人、生命与歌唱。在现代文学在物质浮华的追求中沉浮时,在更多作品把视野局限于现实生活中浮躁心理的纠结时,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人性的关怀和思考,更凸显出沉静的气质。升华思想、人格完善是文学教育的期许,这个目标的达成是基于作品深刻的力度和对人性深层次的挖掘,没有作品的深刻,没有文学对人性的深层次发掘,文学就形不成震撼人心的力量,文学教育的目的便失却了一大半意义。负载着人性与理智的民族文学虽然有些沉重,但这种沉重却能给予人精神上的反思与升华。
三、民族文学富有炽热的民族情怀
文学以人物情感来感染读者,通过作品中丰富细腻的情感展现,读者与作品情感发生共鸣,形成丰富的情感体验,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要使读者能够体验到文学作品的情感魅力,使受众感受文学情感。文学教育对文学中的情感关注如此,则少数民族文学便不可忽略作品中的情感意义。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由于生活环境的封闭和民族聚居的特征,民族民众对民族具有深厚的情感,民族文学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文学中的情感是民族民众独特的情感体现,民族情结往往使少数民族作者在文学中表露出自身的民族情怀。不同民族传统有别,风俗各异,但是在每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都能透露出民族文学创作者对民族不变的情怀。苗族诗人潘俊岭在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 中,为民族代言,尽情抒发了自己的民族情感,虽然因社会原因,给作者带来了彷徨和迷茫,但是在云开雾散后,诗人仍然保持了其对民族的炽热情怀。[2]
张承志的作品中总是体现出了作者对生活的执着,对乡土的热爱,对民族的恋情及对未来的追求。乌热尔图自己也说:每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块土壤,他的两只脚就是踏在这块土地上,…养育我的文学土壤是大兴安岭北坡敖鲁古雅河畔的鄂温克村落,…我爱自己的民族,我的几篇小说就是表达了这种感情。[3]
不仅乌热尔图如此,在众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民族文学创作者们都尽情展示了自己对民族的热爱、对民族的担忧,对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忧虑和期望,民族的一草一木在民族文学作品中散发出故乡热土的气息。东乡族文学作品 《林草情》 中,村民模子日复一日栽树造林,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坚持了一辈子,民族民众对民族对土地的热爱跃然纸上。民族特定的文学场景展现了民族文学创作者真挚而强烈的民族情怀,这种情怀也正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民族的关注,由此民族到彼民族,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炽热民族情感,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民族民众,成为民族民众对民族坚守的血脉。
特定的民族场景才有了少数民族文学中特殊的民族情怀。正确理解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情怀,民族文学中所体现的民族情感才能被真正体验,真正拨动民族文学中的深情之弦。[3]
四、民族文学承载着多样化的民族文化
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有多重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服务现实、塑造人格等,传承文化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因此通过文学教育提高文化素养是文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学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抽象和升华,不同时代的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贴上了时代的标签,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思考是文学的突出特征。认知文学中的文化意味就必须注重民族文学的时代指向,通过时代框定,从而使文学中的文学回到其原来的时代基础中去,文学的文化性首先要从其时代性中而来。[4]
少数民族文学同样有时代性,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少数民族文学中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时代是文学创作的大背景,时代背景在文学中的烙印也需要还原到时代中才能体味其中的真味。另外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不同,因此在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要素也各有不同,以藏族史诗 《格萨尔》 为例,作为藏族文化的载体,藏族史诗历经千年社会历史的变迁,记录了历史的斑彩,最终形成了古代藏族社会的知识总汇,史诗的形成,正是在公元117年聂赤赞普被登位以后的27代中,藏族社会由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国家出现、民族开始形成、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从神的崇拜转变为英雄崇拜的历史时期。
史诗中的英雄、神话也正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夸张、想象而来,史诗的文化性正是基于其历史性,如果能够对历史时期的史实有所理解,则史诗中的历史、民族、军事等文化成分自然也可以分离出来。[5]同样, 《福乐智慧》 是尤素甫基于东黑汗王朝治国需要之下而成书的,当时的王朝既缺乏治理社会的经验,又需要统治的方法,古称为“王都”的文化古城喀什给予尤素甫充分的文化滋养,作者通过几个人物和简单的情节展现了十一世纪新疆、中亚地区的社会风貌,另外作品还具有韵律优美、节奏鲜明等诗歌特点,在历史、伦理、诗歌等方面的文化意义重大。
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在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心态和情感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乌热尔图的作品中,作者展示了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同时也描绘出了鄂温克族人古老的生活文化和社会心态同现代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新旧文化的碰撞也是文化的传承和融合。时代是民族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虚构的文学情节背后是真实的民族文化,文学教育承载着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功能,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不能忽略时代指向下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要素。
结束语
文学真正的意义在于文学所带来的心灵对话,文学教育的目的是把文学中所蕴含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传递给受众,使受众产生共鸣,体验感悟,最终升华自己的思想,因此文学教育视角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和评价更应该从其文化、审美、人文、文化等内核的东西来切入,挖掘文学中深层次的东西,从中理解民族的或者突破民族的情感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学的文字、语法结构、思维方式等知识化的表面问题,只有这样,少数民族文学中所散发的纯粹的民族精神之光才能真正为众人所感知。
参考文献:
[1] 黄 玲。 在率性与快意中升华---论李骞诗集《快意时空》 的艺术追求[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5)。
[2] 刘俊田。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民族文学论选[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1)。
[3] 吴重阳。 中国当代文学概观[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12)。
[4] 乌力更。 文化、文明、民族[J]. 贵州民族研究。2011,(4)。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民族文学论丛[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