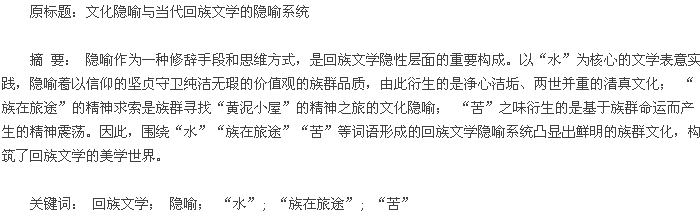
“我们常对自己喜爱的东西,对自己期望、流连、沉思的东西采用隐喻的说法,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一个特殊的焦点上,由所有类似的东西反映出的不同的光线中去观察它。”[1]( P218)从根本上说,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作家创作心理中一种自觉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回族文学中,这种隐喻思维表现得较为突出,它改变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理念,使话语蕴藉更为丰饶,也将文本所关涉的人物、情节推向审美的多方位,甚至某种具有神秘特质的话语境域中。回族文学的隐喻系统蕴含着丰富的族群文化信息,总体来看,以“水”为核心的宗教文化词语汇、以“族在旅途”为中心的思想追索、以“苦”为中心的生命思考,是回族文学隐喻系统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丰富着回族文学的隐喻系统。
一、由“水”衍生的众多文学意蕴
孔子有言: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2]
水虽没有山那样稳重、仁厚的信赖感,但是它具有刚柔相济的内在智慧; 以水喻佛,彰明佛理; 以水喻道,参水悟心; 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柔情似水,有人说女人是红颜祸水,万恶之源……关于“水”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文学之“水”俨然超脱了其本来的物理层面,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意味的重要审美对象。周作人说: “我是在水乡生长的,所以对于水未免有些情分。[3]( P116)沈从文也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4]( P7)这里,我们读解到的是”水“之于作家创作的精神之源。然而,这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在童年时期已然生根,并随着作家写作的不断成熟而被悟解到。
对于回族作家而言,”水“的内蕴有着更为独特的意义: 一方面,从文化背景上说,包括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构成机制; 另一方面,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生活背景、心理经验、审美水平等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作家赋予”水“的内在意蕴。在这个意义上,”水“超脱了常态意义上的生活之”水“,成为一种用以洁净生命与灵魂的存在。”水“之内蕴涵盖了回族文学长期以来构建的清洁话语体系和以清真为核心的宗教生活内容,这种双重特质从根本上影响着以”水“为核心的美学构造。
众所周知,《古兰经》和”圣训“是穆斯林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和指导。当其化为一种精神并内化为创作主体的一部分时,就不仅仅是生活中需要加以注意的习俗和方式,同时也成为他们审视生活、观照生命的一种视角。《古兰经》中说: ”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5]( P264)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由”水“之功能生发的由表及里、表里如一的洁净仪式。对于信道之人,”从第一天起就以敬畏为地基的清真寺,确是更值得你在里面做礼拜的。那里面有许多爱好清洁者“[5]( P264); 张承志在审视伊斯兰的陇山周边时,不无深情地说: ”在这里,水和人的关系是一种内心的精神的关系。“[6]( P210)在大西北的穷乡僻壤中,有一群信仰的中国人,水源匮乏的窘境,使他们对水的感情带有一种纯粹的圣洁感、仪式感,水之于他们,不仅是用以生存的必需品,它更具有”甘露“般洁净的生命内蕴,”无论清晨,无论将暮,回民们掀开缸盖,把净瓶用这种绝对洁净的水灌满,就悄悄地凝思举意了。“比之于新潮人士的”洁癖“、日本人的”涤心“传统,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洁净。
《古兰经》和”圣训“对穆斯林的清洁卫生具有非常细致的规定: ”信道的人们啊! 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当趋向清洁的地面,而用一部分土摩脸和手。“[5]( P77)值得注意的是,表面来看只是一种清洁的方式或程序,但是在此过程中穆斯林的念词却是一种蕴含了深刻教育意义的内容,比如洗脚时的念词是: ”真主啊! 在很多人失足的日子里,使我的双脚坚定地走在正路上。“从念词可以看出,”洁净“在回族人的视域中,是一种由外而内、将”内清外洁“的卫生模式与穆斯林的拜功合二为一的生活方式。在一种充满宗教气息的洁净仪式中,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洗浴,关注的不仅是表面的”清洁“,更是一种精神、灵魂的净化。因此,当宗教意义上的洁净仪式成为文本书写的内容时,它已然超越了以水沐浴的表层目的,而升华为回族人思考问题、审视人生的态度与意念。
其次,由”水“触发,以信仰的坚贞守候一种纯洁无暇的价值观。伊斯兰教认为,人是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人类被赋予以”代真主治理大地“的使命,故而,从信道者的角度来说,忠于安拉,使自己成为安拉喜悦的人,并且施恩于亲人,同时惠及他人,这是作为穆斯林应该具备的一种品质。当这种宗教要求内化为族群的思想意识时,便泛化为一种更为纯粹的生命品质。张承志的作品从这个向度作了较好的诠释,《心灵史》《西省暗杀考》《黄泥小屋》等作品中,为了信仰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穆斯林,在这样的辛酸经历中,闪耀的是一种圣洁的光芒。其实,对于张承志而言,由”清洁“生发的体悟是其精神资源不断拓展的内在触发点,”张承志借‘清洁’一词的理解和认识,揣测了中国回民独有的生存形式及其内隐的只可意会的独特民族心理,挖掘并丰富了此词固有的底蕴和意味,加大了该词的语言负载量。“[7]( P158)从根本上说,对这种内隐的独特心理的发掘,最初是由族群经历及宗教信仰生发出来的,而其后来的延展在很大意义上来源于”内清外洁“的宗教仪式。这一点,在回族作家的创作中亦有明显的同一性。
其三,由”水“衍生的”清真“文化。从原初意义上说,”水“的本意是清晰明了的,但是当它经由作家的艺术性创造之后,便会重新布局,从而添加、融汇进新的内容。在汉语中,”清真“一词古已有之,南北朝刘义庆就在《世说新语》中以”清真“来评论诗词,以此强调一种真实、自然的写作风格。在回族视域中,”清真“被融入了更丰富的意蕴,它是回族学者对”大传统话语的借用“中逐渐从汉文中剥离的一个词语,”是伊斯兰的最高概括,是穆斯林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8]( P101)。明末清初着名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在《正教真诠·正教章》中对”清真“有这样的解释: ”纯洁无染之谓清,诚一无二之谓真“,”夫清真之原,乃真主自立。“[9]( P166)尔后,康熙年间伊斯兰教学者马注以”清真“来阐释伊斯兰教,认为”盖教本清则静,本真则正,清净则无垢不染,真正则不偏不倚。“[10]( P43)综述前此,可以看出,”清真“之内涵是建基于”安拉独一“前提下的延展。
由此,显性层面的清真寺、清真食品与隐性层面的清真文化互为一体,形成了一道文化屏障,成为回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对于”非清真“的排斥和拒绝,意味着一种文化隔离系统的形成。因而,”清真“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遵循伊斯兰教义所规定的禁忌。玛丽·道格拉斯指出: ”禁忌有赖于某种形式的团体性共谋。团体中的成员如果不遵守它,这个团体就不能存在下去。“[11]( P3)从回族的发展历程而论,以清真为核心的精神,贯穿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诸多层面,”清真“成为回族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的统一体,并内化为回族人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石舒清在《底片》中如是描述回族禁忌: ”我们这样的纯回族村庄,总是对种种娱乐和娱乐方式有着忌讳,似乎是对人的欢乐有着一种轻蔑和警惕,好像种种欢乐中伏藏着祸端似的。“[12]( P204 -205)显然,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能歌善舞有一定的区别,回族人的沉静中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焦灼,这是一种精神自守的方式,”净心洁垢“在这里是一门必修课。
二、”族在旅途“与主体构建: 精神求索的文化隐喻
这里的”族在旅途“与”在路上“的客家人有着类似的内涵,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是一种状态,但它不是线性的单一发展的; 它是历史的,又是现在进行时的; 它是结构性的产物,又是能动的反应; 它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 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又是主体认知的建构,它不是静态的、停滞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和变化的“[13]( P18)。就回族文学来说,”族在旅途“表现为主体的信仰姿态及追求个体的生命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基于族群历史与现实境遇的反思姿态。”尤其是在穆斯林的个体生命中,最高的精神企盼就是迢迢万里的麦加朝圣,那也是具有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双重象征意义的朝圣,尽管这种朝圣对于大多数的穆斯林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然而,永远‘在路上’和‘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却成了穆斯林民族的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最高生命方式。“[14]( P42)由此,”族在旅途“之于回族文学,不仅是一种精神资源,更具有深层的文化隐喻。
先民”旅居“遗风与”魂归麦加“之愿。早期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作为回族的先民,他们的生存环境铸就了一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怀揣《古兰经》,骑着”沙漠之舟“,在浩瀚的荒野中,一边寻找水源、牧场,一边以经商维持生计,这是回族先民”在路上“的核心生活方式。在充满冒险的游牧生活中,回族先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骑士式“的文化,其饱含的勇敢、豪迈、直率的品格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审慎、谦逊、安详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族在旅途“在回族先民那里,代表的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方式,它承载着”旅人精魂“的渴家情怀和以伊斯兰教为精神寄托的信仰。
回族从先民那里继承的精神资源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潜隐的存在,它包孕着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求生意志和生命追求。张承志说: ”On the road,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是浪漫,而且是一种忌讳。旅行固然吸引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家; 是一座我奉为主题的‘黄泥小屋’“[15]( P47),这里的”家“与”黄泥小屋“,有着类似沈从文”希腊小庙“一般的隐喻意味,它是一个充满圣洁光辉的圣洁世界。对于回族而言,伊斯兰教两世并重的思想深入人心。《古兰经》说: ”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必入下临诸河的乐园,那确是伟大的成功。“[5]
”下临诸河的乐园“作为”彼岸“的一种想象性构建,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教规来鼓励、促动信徒以清洁的精神面对生命,以此获取后世的回报。诚然,这种宗教意义上对教规的恪守,使得”此岸“与”彼岸“之间具有了若隐若现的距离感,缘此,信仰的力量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支撑着信仰者在艰难的岁月里毅然不倒。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回族文学中众多的信仰者形象,他们于今世耕耘,于后世收获,不仅是一种人生追求,亦是一种精神慰藉。
”族在旅途“的存在方式。从现实层面来说,”族在旅途“是回族之边缘位置的存在方式,它是一种常态意义上的行进状态。这集中地表现为创生于边缘地带的文化空间,由创作主体身份焦虑而致的文化漂泊者群体,以及对”族在旅途“的反思、诠释。
侗族作家潘年英曾就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从根本上讲,侗族文化是完全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存在,只有在少数场合,如需要体现‘民族团结’或‘文化多元’等情景下,侗族文化才得以一种象征的符号出现于主流文化的媒体之中。“[16]( P121)其实,这不仅是侗族文化的命运,同样也是回族文化的命运。历史地看,作为回族文化的核心组成,”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史称‘盛唐'.意识形态也比较成熟,儒家学说已有千年的历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主流“[17]( P35)。由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回族先民开始了伊斯兰文化本土化的改造过程,在融汇、贯通儒、伊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事实上的”侨民“,当其真正在另一国度中生存时,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生存环境,还有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调适,由此,主动适应主流文化成为必然趋势。随着族群的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现状虽则有利于回族文化接受来自于其他文化的滋养,但从根本上说,它加速了回族”文化混血“的进程。
在这个维度上,回族文学的边缘位置以更为严峻的态势呈现出向绝境逼近的状况。张承志就认为: ”民族正在消亡。回族历史给我最大的教育是: 它本身在消亡过程中。“[18]( P3)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回族经由解放前的信教求生存、新中国成立后的信教、经商求生存,以至新时期以来的信教、经商、求知、谋发展,逐步走向开放。虽则潜存于心灵深处的宗教文化仍然是族群的精神资源,但冲击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表意实践活动,在认同建构和差异自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回族文学的突出表现就是新时期以来以”族在旅途“为核心的认同构建。”对回民而言,故乡和语言的相继遗落,信仰宗教便成了该民族确证自存的惟一方式,他们信仰了宗教,也便抓住了历史、抓住了文化,也抓住了自己的根。“[7]( P17)围绕信仰,回族作家开始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坚持、守卫、彰显这一文化,其突出表现就是立足于族群历史和命运的艺术创作。当”在路上“”旅途“”家园“等一系列兼有反思和怀旧的话题进入文学表意实践中时,它所激发的是一种族群认同焦虑。在回族作家中,有着众多的文化漂泊者,他们游弋于多元文化之中,以多种文化资源为创作的精神来源,面对母族文化,却表现出崇敬与审视的姿态,这其中,既有积极接纳异质文化,对本族群文化有充分信心的开放型作家,亦有极端的排他型作家; 既有反思与检讨并重的作家,亦有坚持本族群传统文化,在无意中传播本族群文化的被动型作家[19]( P13)。当然,就具体的创作个体来说,情况显得较为复杂。以张承志为例,在其不同作品的封面简介中,他以多种身份出现,诸如红卫兵、知青; 学者、作家; 回族、穆斯林,等等。这些身份给予张承志的是意义迥然的意味,他是”历经被汉化后寻到了回归之路,之后又能跳出伊、汉文化之束缚,程度不同地踩在多片文化上进行创作“[7]( P5)。他的创作之路客观上与其文化资源的多元性形成了有机的对应,体现出创作主体在具体的艺术创造中,在多种文化的取舍与反思中,逐渐开始反思本族群文化,并检讨文化交往中的文化精神、传统价值的损益状况,具有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
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族群文化在保持本真的同时,异质性的成分渐趋增多。以张承志为代表的回族作家对族群文化符号的重构,不仅从表面化、碎片化的族群历史中整合出族群”族在旅途“的形态,也在客观上形塑了族群文化。因此,”族在旅途“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行进形态,其根本目的在于寻找一种理想的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族群文学的多向度发展渠道。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文化的本土化,其实是”族在旅途“在坚持回族先民”驼背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黄泥小屋“.”正因为家的概念总不能形成所以才去找路……on the road,是为了找 home,’在路上‘是为了寻找安身安心的家。“[20]( P113)对于回族文学而言,它始终是”族在旅途“的一种延伸和拓展,它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三、以”苦“为中心的生命思考
从族群文学的维度来说,族群历史从根本上影响着族群文学的主题和基调,它不仅影响着族群作家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审美品格的精神向度。纵观当代回族文学,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自然背景的苍凉与族群经济生活的现状,使创作主体以”苦“为基点,介入族群生活的各个向度,由此生发的是一种坚韧、执着的人格风范和厚重却不乏精神内涵的生存状态。对于作家而言,在对族群命运的省察中,”苦“之味衍生出的是基于族群命运的审美观照。
雷达指出,”西部作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特别善于表现苍凉粗砺环境中的苦难意识和生命力的顽韧“[21],对于大部分身居西部的回族作家而言,自然环境构成了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美学质素。集冷峻、粗砺、空旷等特质于一体的自然风物,成为人物、故事展开的重要铺垫,它不仅是族群文化的载体,亦是一种喷涌如注的艺术源泉。因此,以山川风物与四时景色为构成的自然景观与族群风俗、传统掌故有机结合,赋予作品以文化的永恒生命力。自然风物给予创作主体的是一种思索的基点和参照,在特定的自然风物背后充溢着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当自然景物作为创作主体的灵感来源时,景物自身所携带的某些特质便会直接影响作品的艺术特点和风格,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进而决定作品的思想旨归。
回族作家在对自然地理环境及身居其中的子民生存境遇的体察中,从当下返归过去,由现在导向未来,并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中,反思族群的历史、当下,以此挖掘人性的多个面向。这其中,基于族群生存环境描写的审美取向的核心便是”苦“,其内涵在于: 一方面,它指自然环境方面的艰苦、苦寒,另一方面,它包含着族群及族群中人在物质贫困的境遇下,依然追求精神上的丰盈。诚然,这与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底层写作“不无联系,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同样是书写”苦“,比之”底层写作“,回族文学的关注视点所及,是族群的生活世界; 回族作家也表现绝望、无奈、迷茫的意绪,但是他们强调的是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错位,以及在这种错位中信仰的中国回族人的选择; 在书写底层回民的时候,融汇于字里行间的是一种温暖的人性,一种灵魂的震颤; 创作主体往往在”平视“审美对象的同时,保持一种同情、悲悯、珍视的美学观照。
陈晓明说: ”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就占居优先的等级,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力量。苦难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最终极的价值关怀,说到底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22]( P74)这无疑道出了苦难书写的真谛。从精神资源上说,回族文学之”苦“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族群历史,”从蒙元以后,中国回族数百年间消亡与苟存的心情史展开了; 一个默默无言之中挤压一种心灵的事实,也在无人知晓之间被巩固了。它变成了中国文化的死角。散居的、城市的、孤立的回族成员习惯了掩饰,他们开始缄口不言,像人们缄口不言自己家庭中的禁忌的家底。“[22]( P33)当了解了母族的”血路“之后,张承志毅然决然地高举”清洁的大旗“,追随母族强大沉默的背影,荷戟独行。《心灵史》作为他的一个”乜贴“,较好地诠释了他的创作初衷。作者将族群历史与宗教、人性相互融汇,在对苦难历史的书写中,将现实层面的艰辛与无奈推向更为深广的哲学层面,由此激发的不仅是价值观的调适,更是在超越苦难的维度上凸显了苦难所带来的人性的诗意境界。”有志者只可能因势利导,但不可能推翻重来。闻发之中,对民众的理解与同情,比什么都更珍贵。“[23]( P210)正是因为以”同情之理解“介入族群历史,张承志拥有的不仅是一种”平视“族群的视角,更有一种复杂地面对历史真相的品质,尤其是在”改定版“《心灵史》中,他做了大量的修正,不是立场的改变,而是一种更深入、更理性的面对族群历史遭际的诗性品质,”作为’红卫兵‘这一词汇的作者,我希望自己对革命的反省,不是流行的道德表演,而是一次立场的改变。“”是的,立场。我渴望自己从此拥有---人民的或底层的立场。“[23]( P10)张承志一如既往地坚持以”民间立场“书写民间,以民间价值作为一种值得信赖的价值归宿,《九座宫殿》《残月》等等,均是以此为基点,书写了一个个背负苦难、却拥有圣洁灵魂的回族人物群像,而在苦难的深处,潜存的则是族群得以继续向前的精神力量---信仰。
如果说张承志更多地立足于现在、回望过去,以此寻找叙事基点的话,那么石舒清、李进祥等回族作家则是以回族生存为叙事基点展开艺术创作。在他们笔下,生活于夹缝中的回族众生是乡土世界的铸造者,亦是处于话语边缘的民间存在。当现代文明以其威猛之力推开回族人生活的乡土世界时,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这种文明给予自身文化环境的冲击,更有一种被腐蚀的感觉,出于自我保护,他们在很多时候选择了退避或者回归,由此,”向城而生,向乡而存“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取向。李进祥的《换水》、査舜的《淡蓝色的玻璃》等作品在捕捉现实生活断片中,发掘了回族人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化及人性的变迁,内心产生的巨大波澜,这种变化已然超越了”苦难“之”苦“,而成为一种蕴含着涩味的生活感受和精神震荡。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更是”苦“之味的延伸和拓展,因为从族群意义上说,由”文化混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关涉族群未来的道路;对于个体而言,从生活习俗、婚姻、社交等各个方面都将涉及如何调适与坚守的问题,而其中的焦灼与无奈便是”苦“之核心所在。因此,霍达的回族书写在广泛意义上具有苦难寓言的涵义。
由此,回族文学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中,”苦“不仅是回族作家书写的内容,在更大程度上,它也是族群发展的一种隐喻,无论是个体的生存现状,还是族群历史的艺术化创造,无不在一种焦灼的意绪中延展。
四、结 语
基于前此,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和思维方式,成为回族文学隐性层面的重要构成。以”水“为核心的文学表意实践,生发的是由表及里、表里如一的穆斯林洁净仪式,它隐喻着以信仰的坚贞守卫纯洁无瑕的价值观的族群品质,由此衍生的是净心洁垢、两世并重的清真文化; ”族在旅途“的精神求索,源自于回族先民”旅居“遗风及穆斯林”魂归麦加“的夙愿,客观上,它是族群现实生存状态的艺术化叙写,亦即常态意义上的族群行进状态,成为族群寻找”黄泥小屋“的文化隐喻; ”苦“之味衍生的是基于族群命运而产生的精神震荡,由生存境遇的艰辛彰显的是信仰的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丰盈,由文化交融带来的族群心理激变表征的是对族群信仰者的敬畏。由此,围绕”水“”族在旅途“”苦“等词语形成的回族文学隐喻系统凸显出鲜明的族群文化,构筑了回族文学的美学视界。
参考文献: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等,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孔子。 论语·壅也[M].
[3]周作人。 水里的东西[A].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苦雨斋文丛·周作人卷[C].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4]沈从文。 从文自传[M]. 上海: 中央书店,1943.
[5]古兰经[M]. 马坚,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张承志。 绿风土[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7]马丽蓉。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8]杨文笔,李华。 回族”清真文化“论[J]. 青海民族研究,2007( 1) .
[9]王岱舆。 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 余振贵,点校。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10]马注。 清真指南[M]. 余振贵,点校。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1][英]玛丽·道格拉斯。 Rout - ledge 经典文丛版序言。 洁净与危险[M]. 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8.
[12]石舒清。 底片[M]. 银川: 阳光出版社,2012.
[13]周建新。 在路上: 客家人的族群意象和文化建构[J]. 思想战线,2007( 3) .
[14]赵学勇,王贵禄。 守望·追寻·创生: 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张承志。 On the Road Again[J]. 朔方,1990( 07) .
[16]潘年英。 边缘族群与文化---答安妮问[J]. 民族文学,2005( 2) .
[17]李振中。 论中国回族及其文化[J]. 回族研究,2006( 4) .
[18]张承志。 我所理解的民族意识[J]. 民族文学研究,1987( 5) .
[19]周宪。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张承志,[美]戴静。 在路上[J]. 文学自由谈,1987( 2) .
[21]雷达。 找不到的天堂[J]. 黄河文学,2006( 6) .
[22]陈晓明。 无根的苦难: 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J]. 文学评论,2001( 5) .
[23]张承志。 心灵史( 改定版)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