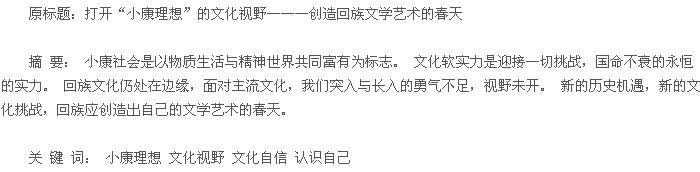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猿相揖别的标志,是直立行走,会使用工具。严格说来,这只是丛林生活的终结。
并未完全摆脱贪婪的唯我,兽性的欲求。近现代以来随着传统的人文精神被遗弃,社会愈发达,生活愈富足。人,在变幻莫测,日日翻新的现代科技的左拥右抱中,渐渐失去了理性的自我约束。丑恶、邪恶在放纵中愈加猖獗,愈加泛滥。习非以为是,习丑以为美,几乎成了集体无意识。最先进的享受,最原始的放纵,形成了逆向推动。其实质是,人被欲望裹胁下向着“丛林”回归,向着“非人”回归。人们完全放弃了对造物主的敬畏,唾弃了对天道、人道的敬重。唯我唯上,唯欲是从,人的复杂性正衍化为不可识透,难以招架的卑劣性。
《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就是生活的康宁。在“民亦劳止”首句之后。又循环往复出现了四次,“汔可小休”、“汔可小息”、“汔可小”“、汔可小安”。这是对“小康”的扩容。归纳起来,民以食为天,不仅求得温饱,使物质生命延续,还包括着休养生息,亦即精神生命的从容、愉悦、进取。这就是我们穆斯林每每见面必道的色俩目在汉语语境中的另一表达。
近百年来,白色恐怖,红色骚动,让我们小康的梦,在血污与狂躁中化为无聊的慨叹,含泪的呻吟,压抑的自虐,吞声的呐喊。那些破碎的历史记忆,对于某些人来说仍是扭曲自我的软暴力。他们仍在继续着歪斜的脚步。
改革开放以来,华夏万里,大地回春。小康社会渐行渐近。小康生活的福祉悄然潜入,润物无声。它,不再只是动听的壮丽口号,不再只是远眺的宜人秀色。
中共十八大,习总书记畅述的中国梦,一扫历史阴霾,心头重负。登高一呼,万民仰首,回眸那远去的红旗漫卷西风,跨出那小心翼翼的摸索过河。十八大,留给我们的似梦非梦,应是清醒中的认知,向往中的真切,幸福远景的透视,希望之门的洞开。从庄严的报刊、闪亮的荧屏到尽情引吭的网络,都在畅述着震烁古今的我们向往久久的中国梦,并从不同角度,建构着我们殷殷期待的,显示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梦。
回回民族七百年来的崎岖仄径,举步维艰,温饱难求。对于梦中的小康社会,我们期待得过久,回望眼,那只是无望的追求,无尽的幻灭。
小康,既是运用经济杠杆着眼于物质生活的提升,不可忽略的又是整合心灵,对美丽、自由、和谐的精神生命的重构与完善。唯有二者的兼容、并举、互动、制约,才能完成“小康”的既是凿凿事实的,又是空灵廓大的这一重大命题。换言之,“小康”当是我们大写的人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充分享有中醒神,不断升华中自警。中国梦,小康梦,应是物质与精神二梦的重合。舍弃或忽略其一,都是对“小康”的误读、误判。
回族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不昌,声闻不彰。七百多年,回族在社会生活的演进中,我们只是事实的存在。而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却没有独立篇章。仔细在历史的缝隙中搜寻,才有我们似有似无的身影。读读眼前的几本《回族人物志》,那是在凄凄惨惨戚戚的历史残片中,一些有心人甘于冷冷清清、历经寻寻觅觅之后,才完成的一部简陋的“纪传体”回族史。每每捧读,令人感慨万端,心有不甘。
回族,是以伊斯兰信士为主体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世界各个民族几乎都是民族实体形成之后,才接受了宗教,至少是民族形成过程中,宗教信仰才由蒙而具体。唯有回族是个特例,她是由于回族初民归信伊斯兰,这超越生死的同一性、两世憧憬的凝聚性,才使分散多元的个体,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回回民族。那种硬把回族与伊兰教剥离,以及回族人可以不信伊斯兰教的说法,不仅是反科学的伪命题,也是对回族大众心灵的伤害,并对回族内部的团结及中华民族的互信与和谐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
基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回族研究是以回族史和伊斯兰教为发轫、为重心。回族史与伊斯兰教研究,皆属于社会科学门类。近年回回医药、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也纳入视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是对于天道与人道理性的逻辑的思考与研究。必须承认,以形象思维方式,以情感为主宰的文学、艺术在回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未受到更多青睐。
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塑造与展示。
敞开心灵大门,走进心灵深处,才能有彼此心灵的交融。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文学艺术是和世界沟通的利器。她,活泼地、美好地、悄然地启动了闭锁的心门。消解一切隔阂,化解一切陌生,遮在心头的波诡云谲也尽在扫荡之中。
宗教与历史作为理性认知,最终归于对“道”的领悟与恪守。从教义与史训中获得信仰、获得理念,获得理性的升华,获得对两世清醒的把握与自律,应归于“道”。道者,导也,导人德操。
文学与艺术,则别开蹊径,别有洞天,别具效应。
它是以美为引线、为内核、为驱动,使人获得审美享受。艺者,怡也,怡人情性。
我曾在一篇特邀的戏剧论文《国粹京剧的文化之魂与艺术个性》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抄录如下:
道与艺,不是二元对立。中国戏曲巧妙地使之合二为一,展示出尊道崇艺的创作理想。“道”以“艺”为妙手,凭借机趣,打开心门;“艺”以“道”为春霖,从容润物,潜入性灵。受众通过可感的“艺”,妙悟无形之“道”;通过“道”的潜引,品味有形之“艺”。并形成为中华民族颠扑不破的审美惯性,审美基因。
善与美,是道与艺更为具体的,更深层次上的表述。无论天道人道,都要归结为一个“善”字。作为艺术,“美”是它的本质属性。只有“善”与“美”相绾而融于艺,才使有游戏作用的艺术实现其真价值。善与美虽属两个范畴,二者在艺术实践及其艺术成品中却不可分割。苏格拉底的“善即是美”,孔子的“尽善尽美”,则厘清了善与美的分野及其互生性,并提出了文艺创作必须严守的价值坐标。倘现有艺术门类皆如是,使当代人在物欲的狂欢中退出。或警然内视,归于人性的宁静从容;或豁然放观,寻回人际的和谐与信赖。何愁人心不古,世风沉沦。(载于《民族艺林》2013 年第一期。)上述引文,想说明对文学、艺术不可小觑,它是立国、立人、立族的根本之一。是实现中国梦、安享小康社会必须倚重的审美文化。
先说文学,它是以文字为工具的语言艺术。文学体裁一般分为 8 类:诗歌、散文、小说、民间文学、报告文学、说唱文学(相声、快板、评书、大鼓书等曲艺门类的脚本)、戏剧文学(戏曲、歌剧、话剧等舞台艺术的剧本)、影、视文学(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
诗歌、散文、小说、民间文学是回族文学的主项。
至于其余四类则是凤毛麟角。前些年有一本回族文学概观的书,把后四类文学体裁排除在外。有人代为辩护说“:戏剧、影视怎么能归入文学?”这无疑是把戏剧文学、影视文学与戏剧艺术、影视艺术混为一谈,犯了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
反观诸己,我们回族文学,只是逡巡在诗歌、散文、小说及民间文学的领域中。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张承志是当代回族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一部《心灵史》被世界性的阅读之后,回族文学因之在国门之外渐有声闻。
虽然回族众多作家,众多作品问世,在主流文坛上仍是颇觉寂寞。由于文本阅读正在失去受众。回族文学的各类文本在广大读者群中又能有几多阅读者。
由于作家个人的学术修养、人文知性、审美意识及生活积累的备料不足,深度不够、有的叙事作品对于回族生活的描写,缺乏深层的透视,只是把表层的某些“特点”展示出来。往往执着于所谓的乡土特色、回回特色,在不经意中展览落后,披露丑怪。使不知就里的读者误以为老回回竟是如此不堪。
有的抒情作品,流连风景,点染见闻。虽尽力于征辞选字之功,彩绘勾勒之妙,独不见个人性灵所在,智慧闪光。掩卷之后,在心灵上少有激赏的回味,少有世俗沦陷中获得寻回自我的动力。
还有一些作品,纳入眼底却留下某种灼痛:有的只是自我宣泄,悲喜之间无关世态人情。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批评说,你像一只鸟儿独立枝头,吱吱喳喳,叫个不停。你叫得再欢与我们有何相干。
有的煞有介事地玩弄笔墨,玩弄情感,这类文字看似多宝楼台,折解开来一片狼藉。游戏人生的轻浮与调侃人生的薄幸混合成一种怪诞,让读者在不可理喻中,导致一些人心灵失衡。有的是正襟危坐,论古说今,博闻强记,如数家珍。
由于自家只是记问之学,以致妄生穿凿,失其指归,让不少读者坠入云里雾中,和作者一样找不到北。上述虽只是“一斑”,而非“一般”,但是,对于回族文学的前景来说非是小事。回族文学创作除上述问题外,在体裁上,说唱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的创作,我们少有作为。
戏剧文学,抗战时期的话剧剧本《国家至上》填补了回族题材戏剧的空白。但作者老舍是满族人,宋之的是汉族人。我们的回族剧作家曾有评剧剧作家薛恩厚,话剧剧作家沙叶新,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在回族题材上一显身手。中国戏曲舞台有以海瑞为主角的《大红袍》,马连良最是擅演。解放后,已无声息。又是大师马连良策划主演了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却成了一场历史闹剧的导火索。两出海瑞戏,又都隐去了海瑞回族身份与回族的个性与人格。
戏剧艺术是借助舞台,综合多种艺术元素和表演手段,直面台下的当众表演。由于它是演员创作过程与观众欣赏过程合而为一。在时间上同步,在空间上咫尺可见。因此,戏剧的艺术感染力最直接,更强烈。
评剧《金沙江畔》、京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桂剧《瑶妃传奇》等都有声有色地为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讴歌。可是,这一方方舞台却很少见回族的身影。我曾看过一台所谓回族题材的话剧,除了白帽与盖头的标识之外,再无其他。
电影艺术,有过让我们心动的《马本斋》之后,再不见有其他。霍达的《穆斯林葬礼》由于其立意不为广大回族人所接受,据说曾拍成电影,有关部门顾全大局,未能投入市场公开放映。其他少数民族的《五朵金花》《冰山上来客》《农奴》等让我们惊视、惊心。反观诸己,又不免留下了缺憾与不安。
电视艺术,把每个家庭都变成了电影院。它摆脱了电影院里近乎仪式性的庄重,它无须再有电影院里群体约束下的自控。电视成了最普及、最便捷,让受众最自由、最随意,最轻松,足不出户、举手可得的传播媒介。
中国 1958 年有了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至今成千上万的电视剧跃上屏幕。回族也只有一部《马本斋》,又是几次翻拍。回族引以为荣的民族脊梁,一代英杰赛典赤、郑和、海瑞等似乎与回族题材了无关涉。每年近万部电视剧,供大众观赏,却根本见不到回族题材电视剧。
电视剧每个画面,都是由镜头语言组成的一页页书。把传递着传统精神生活教科书融入在更直观的美的境界中,让我们快快乐乐地读着,轻轻松松地品着,情思荡漾中悟着。在美妙的享受中,与高堂父母,与稚气儿孙,轻啜茶,闲摇扇,不时闲话中,不经意地让我们在陌生的世界里,寻找到别一个自我,在心灵共振中,获得人性升华。
祖国的每一角落都有回族人,对于各民族兄弟来说,身边的回回人,却总让他们有些不解。“不吃猪肉”是重要禁忌,“爱戴白帽”是重要标志。对我们的信仰、文化、历史,他们难知一二。回族人不想说,因为大多数回回人,也是雾里看花,说不分明。我们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人结构成各种关系,形成大大小小的关系网络,我们回回人,却是他们当中的“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难于被人了解,就必然容易被人误解。认知的隔膜,终于成为心灵的疏离。每年都有的类似的摩擦,大多是由于“无知”冒犯,并非出于“有意”挑衅。
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这是现代、后现代精神失据中,更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电视剧,不仅是快乐天使,是知识老人,也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精神“教父”,更是塑造自我,让各民族兄弟化解陌生、熟悉我们,深入纵深、读懂我们的潜移默化的手段。电视剧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化入观赏者一个个生活空间里。屏幕上的艺境,与观赏者的心境,在无数的重叠、互映中,必然形成心灵的交融,达到由陌生到默契的自然转换。我们有这样的优秀人才,却不见他们一显身手。在这个天地里,回族人至今少有踏进。运用电视剧这一最有魅力的艺术样式来“认识自己”及让别人“认识我们”的话语权,并没有充分地为我所用。
回族的文学艺术,家底不薄,活力不足。才人不少,未成一军,视野初开,局面狭促。这一现状由来已久,未见多少变化。令人遗憾的是个别从文从艺者,回回身份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但是,他们的作品并未给母族带来多少益处。耳闻目睹其言其行,他们爱的不是心中的母族,而是爱着母族中的自己。更有人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创作上,却用尽心机推销自己,大大伤害了回族的文化声誉。
当然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文学艺术的不少才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认知远远不足。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创作上就难有大成。古代作家、书家、画家,能沉入历史,显赫今古,有几个不是学问家。
清人周亮工《读画录》中引用了清初着名画家方亨咸的话:“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说明不肯读书,胸中空空,再努力画下去,终脱不了俗气、匠气。
清人李瑞清在《清道人论书嘉言录》中也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以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乎技,不足贵矣。”说明书法以气韵品味即书卷气为重,并非纯乎“技”。
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云“词曲虽小道哉。倘非多读书,以博其见闻,发其旨趣,终非大雅。”清人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云:“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一位曲论家,一位诗论家,都强调了为文,为诗,为曲者必须有深厚的学识。
高尔基在 1928 年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人学,是一个包罗广泛的复杂命题。涉及关乎人的一切问题。这要求文学家拥有的学识必须较之一般人更为丰厚。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大家,无一不是学者型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文学的鲁迅、郭沫若……绘画的张大千、徐悲鸿,书法的沈尹默、启功……他们艺术生命中皆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文、史、哲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它们决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质、价值和走向。它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是文学的略称,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审美文化。
史,沉浮于政治漩涡中的大众的生存史与社会的文化史;哲,是对天道与人道的解读,观照着、指导着、慰藉着百味的人生。
哲,孔孟学说是中国哲学的主轴。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者爱人”的博爱主义。孟子思想核心是仁政理想,是把“仁者爱人”的济世之心制度化。史,几千年复杂多变的中国历史,主要是爱人与残人,仁政与暴政的相互交攻的历史。文,中华民族的历史光影,折射于、贯穿于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史中,它是以审美眼光,文学手段,写下的爱与恨纽结着的一切人的心灵史。文学艺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奠基,更具体地说,从文从艺的人必须深入学习与领悟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文、史、哲。
生活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学问是作家得以直上艺术长空的翅膀。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是团结的纽带,是中国梦的主体意识。回归于传统文化,借助于中国历来的以“复古主义”为名,行开拓新路之实,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返还给人民大众,传播给西方世界,是文学家艺术家崇高而艰巨的使命。
回族学人应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应警惕尾随人后作附庸,顺眼低眉守小成的不敢作为的自卑心态。回族学界应进一步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应支持敢于直抒胸臆,不求苟合的另类发言。回族各类学术会议不少,会,文心相会;议,偏正辩议。这需要与会者秉持良知,不畏攻诽。倘各唱各调,唯是自赏,你好我好,换盏推杯,岂不是徒然地误了光阴。
全国第二届民族题材电影剧本电视剧本评奖,于今年 4 月 20 日在京颁奖,近九个月的评选,在 240 个剧本中,我创作的电视剧本《京剧大师马连良》获得了电视剧本奖第一名。被专家誉为十足“京味”,具有深厚文化底蕴,把握住时代精神,深具回族特色的“国家级”精品。
我所以耄耋之年踏入这个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领域。是因为期待过久……但是,我很自信,这自信缘于我爱我的母族,是被信仰支撑着的抖落杂质后的自信。我更坚信会有年轻人担当起领军者。
我写回回马连良,是因为他在主流社会及主流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这位大师级人物在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艺术上有着巨大贡献,并从国内到国外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其声名地位,可与梅兰芳大师比肩。
为写马连良,我首先从学术研究入手。我第一次提出了马连良、侯喜瑞、雪艳琴为“回族京剧三杰”,并将我的经名优素福给予马连良。我写出了多篇研究马连良的论文,从主流文化界到戏剧界完全认同我的观点,而且接受了“回族京剧三杰”说法。更让我高兴的是,一些汉族学者谈起马连良,总缀以“回回名优素福”。一番宣传、造势、铺垫后,我才进入电视剧的创作过程。力图从形象体系中塑造出我心目中的回回马连良。向社会公众宣示,回回人同样为主流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抓住主流文化中回回精英大做文章,就是借助他们在主流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凸显回回民族文化像。显示我们并不寒酸而是精神富有,并非褊狭而是心怀中华。我笔下的马连良,他内在的伊斯兰人格,外在的穆斯林的佳美言行,献身艺术的崇高品质及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都淋漓尽致地、艺术化地体现于电视文本中及将来的镜头里。让大众从“个别”透视出“一般”,从而重新或加深认识我心魂系之,须臾看守着的我的崇高信仰、我的伟大母族。这也是我久久沉积心底的虔诚的举意。我写马连良,有一种“炫耀”心理,但并非藉马连良“炫耀”自己,而是炫耀我的母族因信仰伊斯兰而无比优秀,因坚守正道而对伟大祖国的耿耿忠心。
回族必须在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中一显英姿。运用一切传播媒介,掌握多样艺术样式,挺入一切文艺领域,为让回族摆脱一切因不知而误读造成的伤害,因疏离而造成的陌生化,隔绝感。真诚地与各民族兄弟在彼此文学艺术之魂的相知、相爱、相融中,协力同心将中国梦化为彩色纷披的现实人生。中国梦的实现,是以 56 个民族十三亿人的团结为根基。共同富裕,绝不是民族团结的唯一纽带。真正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是基于文化的认同。每个民族都应认同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每个民族也应认同其他兄弟民族各具优长的“这一个”文化。钢浇铁铸的民族自信,赫赫巍巍的民族自觉,必将在这文化认同中扎下深根,结出硕果。共和国期待着回族文学艺术春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