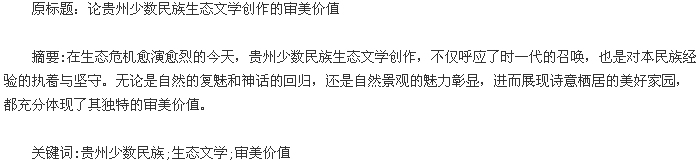
新世纪以来,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集约式的“井喷”,堪称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绿意”盎然的生态文学创作,不仅呼应了时-代的召唤,也是对本民族“经验”的执著与坚守。
20世纪50年代冯牧在评论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时一曾经指出:“李乔是一位彝族作家,虽然他是用汉文写作的,但他是在彝族人民中长大的……这位作家在表现生活这一点上,具备着别人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他对自己在作品中所安排的各种彝族人物的理解,都有着直接而可靠的生活基础;因此,他对十自己所要处理的题材,就不必像有些作家那样,首先很艰难地克服和跨越那种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的隔膜和距离。可以说这是独具慧眼的评论,文学因为主体的认同心理,注入文学题材、主题、情感、形式以无可替代的特质,迸射着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也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本文从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同体裁的文本分析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自然的复魅和神话的回归
自启蒙运动以来“祛魅”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之一。其核心是摒弃具有神秘性的有魔力的事物,祛除其“神性”,以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对世界“脱魔”—从魔幻中解脱出来,由超验神秘返归世俗生活本身。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快,祛魅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格里芬认为:“‘世界的祛魅’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亦如舍勒所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这样一来,自然不再成为令人敬畏的神圣对象,而是变成人们可以任意改造的“客体”。人们肆意地征服自然,带来了越来越深重的生态灾难。海洋生物被过渡捕捞,沙漠面积扩展、森林覆盖率下降、淡水资源医乏、甚至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随之而来的沙尘暴遮天蔽日、江河严重污染、有毒化学物泛滥、极端天气持久、PM2.5超标,人类生存的环境越来越不安全。
正是基十对现代性祛魅的严重后果的思考,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借重十本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对自然进行复魅,从而促使人们尊重自然,遵守古老的生态习俗。
彝族作家安文新的短篇小说拼申树树神》,就是一篇典型的对自然进行复魅的作品。他写生活在鸟蒙山区的彝族自古以来就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鸟蒙山区的一棵百年枫树多少年来一直是彝家人崇拜、祭祀的图腾:。
“神树,是棵枫树,四人合围粗,二十多高,千姿百态的枝娅上,砌着长形的,圆形的,大大小小恐怕有百十个鸟窝,像大伞一般的树冠,覆盖着好大一片草地。”
“人们是怎样崇拜、祭祀神树的呢?烧香,化纸,杀鸡,宰羊,磕头,作揖。谁家有了大事小事,都要去敬神树,求神树的庇佑。三月三,才是一年一度的大祭日。”
在大祭日,人们“用三根五倍子树枝,搭成一道祭门,再用一根九尺长的草绳,插上鸡毛,挂在祭门上”。然后由寨上令施祭祀的伯穆(祖传的认得彝文、会念彝经的文化人)领头,由一个寨上德高望重的族中老人当主祭,每户人家推选一个当家的男人为陪祭“大家双手捧着酒碗,随着主祭老人的动作,将碗中的酒浇在地上一齐焚香跪拜,在伯穆振振有词的祷告声中,从祭门中走过三次,然后杀羊献牲,求神树庇佑全寨清吉平安,无灾无难。”人们是这样的敬祭神树,而以此相对的是寨上有三个人,用神树树枝烧火、削神树的皮、对着神树撒尿“由十冒犯了神树的尊严,落得一瞎、二拐、三绝种的下场”。
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砍树毁林的日子里,“三报应”的前车之鉴使得彝家人没有谁敢动神树。县里下来的谢书记不信邪,亲自上阵砍神树,当谢书记把手中的斧向神树狠劲砍去时,“天晓得,神树显灵了,紧紧咬住了锋利的斧口不放。谢书记握住斧把拔呀,拔!咔嚓一响,斧把断了,谢书记稳不住脚,向后一仰,摔了个四仰八叉,脑壳正好砸在放炮仗的青石板上,鼻孔出血,口吐黄水,昏了过去”。谢书记留下了终身残疾,扑晦寨上又增加了一个报应成了四报应。
“谢书记留在神树上的斧子,至今还嵌在神树的身上,它是历史的见证,铁的见证;铁的见证最有权威性,也最有说服力,即使后来到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最最革命的人,最最不信邪的人,只要你把他请到神树面前,目睹一下铁的见证,听一下铁的事实,他会变得哑口无言,面色苍白。”
神树不倒,保住了漫山遍野的树,护佑了鸟蒙山的子}}Jb‘大跃进”后“过粮食关”,靠满山的野果没有饿死一个人;即使在“文革”疯狂的年代,青山依旧在;神树庇佑了全寨清吉平安,无灾无难。至今满山密林郁郁葱葱,留下了最好的生态环境。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有建立习俗,控制行为准则,与赋子一种制度性以尊严及重要性的规范力量。少数民族的这些神话往往是生态和谐、自然神秘的古老戒律。
苗族作家杨欧的短篇小说《大雕》中的大雕是一个有一定荒诞色彩的象征意象,它是大自然的化身,充满神秘色彩的大雕,其实也就代表了大自然的神秘和不可侵犯。小说讲述了大雕对人进行报复,亦即大自然对人进行报复的故事。陈连生、毛二、蛮子、猴子、老油条五人相约到双阳镇拉木材倒卖。五人开车前往双阳镇的路途中遇上一只大雕,蛮子等人活捉了大雕,以八百儿的高价将其出卖,分了这笔意外之财,期间只有陈连生对大雕表示出了怜悯,最终也没有参与蛮子等人的分赃活动。一个多星期后,还是这五人,在开车往双阳镇的路上,又一次见到大雕挡路,这时一车骤然失去控制,坠落悬崖,只有陈连生和其弟弟毛二得以生还,其他人全部死十非命。小说中大自然对人类进行报复的主题非常明确。人类不仅伤害大雕,而且还肆意砍伐森林,大兴土木,破坏自然家园,大雕的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为大自然复魅,正如利奥波德所言:“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5] PI93这是保护大自然的最好办法。
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短篇小说《咒语》同样表达了自然对人的惩罚。小说中“我”的父亲用套索猎住一只怀有身孕的母赓,尽管父亲悔痛不己,把母赓掩埋起来。但是从此“我”家怪事连连,先是父母亲床上突然出现一条大蛇,然后不断有小蛇光顾“我”家,屋后一大片竹林一齐开花死去;村人总能听到一种类似十赓的哀鸣;最后父亲在惶惶不可终日中疯癫死去。作家用这样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来展示大自然的伟力,其实也是为自然“复魅”,让人们敬畏自然,尊重自然。
无论是彝族、苗族还是毛南族,他们都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小说中大量神话因素的介凡“与其说是对本民族自然神话的当代再现,不如说是借助自然神话而开展的当代重构。因为在现代性文明之光的照彻下,人们剥落了信仰中的原有神话儿素,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人们拥有了蔑视神话思维的权力。·····一旦人对神话传统全盘抛弃,人就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在自然面前更肆无忌惮;而通过神话的复述,正好能重新唤起积淀十人类文化心理深处那种人与自然的原初情感意识,作家表达了恢复自然本性、拯救生态的意图,也有了一种极富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传统文化精神资源的支撑。
二、自然景观的魅力彰显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特别是诗歌改变了当代诗歌中自然描写长期被忽略的现状,彰显出自然景观的美学魅力。放眼当代诗歌,自然描写己经渐行渐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经典诗句几乎难以再现。当下诗歌沾染浓厚商业文化气息,蓝天、青山、绿水、月亮、星星等自然意象,这些不能吸引消费者一眼球的东西,对十生活在都市的新生代诗人来说简直就是恍如隔丛“自然审美维度的缺失是当代诗歌急待走出的误区,缺少了自然描写的诗歌必将影响其美学价值,并导致读者一审美趣味的粗鄙化,这在生态现状日益严峻的当下更为突出。贵州少数民族诗人对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一是贵州欠发达的省情使得贵州保留了更多的青山绿水,诗人与大自然的亲近有较好的条件;二是贵州少数民族居住的环境大都远离都市,具有更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成长的诗人更爱自己的家园;三是贵州的很多少数民族有自然崇拜观,相信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很多植物、动物是他们的图腾对象。这就不难理解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少数民族诗人为什么钟情十自然了。正是由十他们钟情十自然,他们的生态诗歌在诗学策略上,将自然的审美维度鲜明地凸显出来,营造出灵动的审美意境。如彝族诗人禄琴的《彝山》:“你茂密弯曲的黑发/从高原披散下来/溅起一片生命的歌舞/天空中飞翔的鹜/涂抹着一块块飞翔的雄姿/溟檬的世界常有山魅出没/山寨十森森的林间/彝人的血脉/在这片土地上延伸/日子凝聚成耸立的山峰”。
诗歌描绘了大自然的神奇景致,生命壮歌,原始迷人的景象。在跌宕起伏的节奏中,渲染天人合一的澄明意境,较好地实现了生态主题与诗歌文体相融合的美学效果。
布依族诗人陈亮的《所有的植物对我微笑》细致入微地展现了自然的风采:“面对春天/所有的植物对我微笑/所有的植物,包括那些多情的阳光、灿烂的花朵、清脆的鸟啼/那些透明的露珠、精致的草叶、骚动的种子/那些黝黑的泥土、猩红的虹叫、宽阔的田园/所有的植物从早晨到黄昏/都以自己的方式/深入我的内心、我的思想和灵魂/感动我,使我无比骄傲与幸福”。诗歌的字里行间充盈着大自然生命的活力,“所有的植物对我微笑’,‘所有的植物从早晨到黄昏/者IS以自己的方式/深入我的内心、我的思想和灵魂”。当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生命脉搏的跳动,与自然万物进行着心灵交流的时一候,大自然一切有生命的为、西使我们骄傲和幸福。
土家族诗人徐必常的组诗《风吹草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唯美的大自然画卷。诗人写春天的鹭鸳和青蛙,写风吹草低处一窝嗽嗽待哺的小鸟,写金秋挂满“红灯笼”的柿树,写秋天“消瘦”了的河水。在大鸟哺育小鸟的鸟窝里,诗人“看见了幸福与温暖”,与粮食“站”在一起的柿树让诗人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甜蜜,而鸟儿自由自在的鸣叫则让诗人抛却城市的喧嚣和“人心的烦躁”。在大自然的每一点启示当中,诗人都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获得心灵的慰藉。
“风吹草低”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意境,而事实上组诗当中的《风吹草低》一诗温暖的意境与苍茫的意境一样,都彰显了自然景观的美学魅力:“草低的时一候/一窝小鸟露出了嫩黄的小嘴/此时一我正好看到西下的太阳/它那张嘴也是嫩黄的/小鸟把嫩黄的大嘴压得比小草还低/偶尔抬抬头,和风就送它满嘴的鸟鸣/此时一,我看见一对大鸟从天上俯冲下来/风吹草低,我在一个鸟窝里/看见了幸福与温暖”。贵州少数民族生态诗歌还借鉴了传统的诗歌资源,使民族诗歌血脉得以衔接。中国当下诗歌在一拨又一拨现代、后现代诗歌浪潮的冲击下,诗歌创作“在内容上不触及现实生活,令注十抽象哲理的思辨;在形式上炫耀技巧难度,营造语言迷宫,越来越抽象难懂”[A] F127。对十传统诗歌中人与自然交融的景观描写很多诗人视为过时-了,诗歌创作陷入审美困境。贵州少数民族生态诗歌有效地借鉴传统诗歌表现技巧,呈现出朴素自然、妙趣天成的审美风格,如布依族诗人张顺琼的《晚景》:“投爱十天空/一天一个旧梦/一梦一个憧憬/投爱十湖水/一波一朵浪花/一浪一支春曲/投爱十黎明/答我白鸟的惆啾/万物的明媚/投爱十月光/一颗心一份欣喜/一滴泪一叶飘零”。
“投爱十天空……投爱十湖水……投爱十黎明……投爱十月光……”诗人较好地借鉴传统诗歌一咏三叹的手法,投爱十天地日月,如《诗经兼F-X》的反复咏唱。爱天地日月,必将得到大自然的回报。诗歌语言自然明净,画面淡雅清新,营造出回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读后有一种诗意的感动。
三、诗意栖居美好家园的展现
喧嚣的街道、熙攘的人流、拥挤的空间、光怪陆离的霓虹,构成现代城市人生活的场景;再加上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和光污染等等,使人们越来越远离诗意的家园。因此,贵州少数民族作家渴望找回原本属十自己的自然天性,展现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
苗族作家杨村的散文《大地的眼睛》借用了美国作家戴维·梭罗的比喻(其在著作《瓦尔登湖》中把瓦尔登湖比喻为“大地的眼睛”),来描绘云贵高原上一处高山淡水湖—雷打塘。作者一写湖岸的崖壁、梯田、开满梨花的村寨以及湖畔的捣衣石和湖上的野鸟。不但为我们描绘了雷打塘的神秘与美丽,寨民们世代与湖相依相生的美好生活画卷,还展现了诗意栖居的真谛:“我很羡慕村子上的人,因为他们每一天都与一个神秘的湖相伴。他们的祖先一定是那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现在,他们为自己这汪神秘的湖而自豪不己,这是能够理解的。即便充盈着污秽的心在这明眸一般的湖上一站,心底的琐碎也会顿然一片莹洁,像梭罗所说的一样,望着这汪湖水的时一候,我们也会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杨村不但借用了梭罗的比喻,更继承了梭罗写《瓦尔登湖》的那种情怀,满含着对一汪湖水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去展现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
讫佬族作家王华的散文《有个地方叫安沙》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家园:
“安沙依红河水而建,几十户人家挨挨挤挤,红墙绿瓦,四周偎着葱笼翠竹,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之景。”太阳下安沙女人无拘无束地在河里裸浴,足见其心灵的坦荡和宁静。安沙人热情好客,对素不相识的“外人”也留食留宿。作家笔下的安沙人从容、知足,与天地、山水、万物和谐相处着。
在散文徒进夜郎湖》中,王华更为我们描绘了世外桃源之境:“夜郎湖四面环山,陡处,如刀凿斧劈,青石嶙峋,那副威严的面孔,倒神似夜郎。缓处竹笼青翠,有零星几户人家,点袅袅几缕炊烟,鸡犬相闻,胜过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之境了。”
在作家笔下,湖水如缎一般夺目而妩媚,湖边有悠闲的钓鱼人。移船登岸,小路藏在玉米地间,农人在收包谷。竹林间,石墙青瓦小院,屋前一架瓜棚,坝上晒着红辣椒,屋里女主人正宰鹅为帮忙收包谷的人准备饭食。农家小院把夜郎湖边宁静平和的生活展现无遗。
这样与自然默契的文字让人深味到生命之源的真纯,生存之本的可亲。讴歌人与自然的和谐,展示家园的美好是这些散文的主旨。
苗族作家完班代摆的散文《牵着鸟的手》更将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展现到极致。在尧上这个讫佬村庄中,“我”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妹‘这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没有忧郁,也没有痛苦,没有陷阱,也没有设防。”鸟类自由地恋爱,歌唱,与人类共同栖息在美丽宁静的山水间。
牵着鸟的手,即人类聆听鸟类的歌唱和心声,爱护它们,与它们和谐相处。尧上每年都举行“敬雀节”,这个少数民族独特的节日既是远古的回响,又是未来的呼唤“我以为,敬雀节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简单习俗,它己经超越了习俗本身,而成了人类共同的财富。同样地,它也超越了历史时一空,而暗合了当今社会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主题。”。
“我希望这种感动能够恒久地持续下去,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能主动地牵着鸟的手,并能与鸟亲切地交谈,倾听鸟类深情的歌唱。”这种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让人性回复到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那种灵性空间,重新获得了丰盈之美。
海德格尔说:“大地是承受者一,开花结果者一,它伸展为岩石和水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四季轮换,是昼之光明和隐晦,是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气的温寒,白云的飘忽和天弯的湛蓝深远。大地上,天空下,是有生有死的人。; f97 P9‘哲人的思考总是切中要害,天地之间,人不过是有生有死的生物之一,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共生共存共荣。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以对本民族“经验”的执著与坚守,敬畏自然、赞美自然、追寻诗意栖居的家园,“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十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对十生态文学而言,这是最贴切的描述。
参考文献:
[1]冯牧.谈《欢笑的金沙江》.文艺报,1959.(2).
[2]人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工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二联书店,1998.
[4]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M].上海:上海二联书店,1992.
[5]利奥波德.沙乡年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口].前沿.2009.(9).
[7]袁园.新旧_纪生态诗歌论.南都学刊,2009.(3).
[8]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重庆:西南师范人学出版社,1997.
[9][10]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部元宝编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