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古典美学“厚”范畴的已有研究成果
时间:2015-03-26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5237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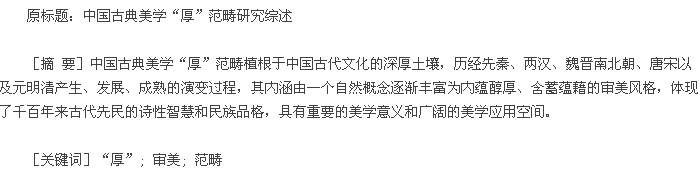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重要的衍生范畴,目前关于“厚”的研究多集中在各个历史时期,例如对“温柔敦厚”、“气象浑厚”、“厚出于灵”等,而尚无专门性的研究专着出版,“厚”范畴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因此,为了理清“厚”范畴的研究现况,拓展“厚”范畴的研究格局,丰富古典美学“厚”范畴的研究,本文拟对“厚”范畴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评价,由此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厚”之源起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的产生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土壤。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从农耕文化和传统美学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厚”产生的文化根源,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促成了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重视审美主体实践,并对土地无限依赖、尊敬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传统儒释道美学孕育了柔韧、温和的审美品格。“厚”由对土地的自然朦胧意识发展到君子以“厚”比德,产生诸如“德厚”、“仁厚”的观念。随后,“厚”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普通百姓,以“厚”论百姓之德,形成了一系列以“厚”为核心的词汇。
“厚”随之从论人进入诗文、书画领域,并渐趋稳定,由一个道德范畴逐渐演变为审美范畴,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并在整个古代中国社会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厚”之演变
“厚”范畴的发展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及元明清时期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学术界目前的探究,多集中在从“厚”的各个历史阶段来考察“厚”的文化特性。
先秦时期是“厚”的萌发期,“厚”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出现并成为君子道德评判的准则。而“中国古典美学谈艺术的创造,从来都是将美与善、真联系在一起的。”
[1]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2]对“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姚素华在《君子之道“善”而“厚”——— <诗经 > 义理梳理》一文指出: 《诗经》集中反映了“君子”的德行,强调“善”和“厚”,在低层次上要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而在高层次上讽谏君主帝王,施仁政稳固社稷。
“厚”可以理解为仁厚、忠厚,沾染着儒家道德伦理思想。
汉魏南北朝时期是“厚”形成的初始期,“厚”主要表现为“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具有政治教化的社会功用,“厚”并未真正进入审美领域。陈咏红在《“温柔敦厚”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一文中分析了“温柔敦厚”产生的文化背景,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迎合了中国士人的文化心理和需求,是统治者用于疏导民众的一种方式。而董雪静《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则在肯定“温柔敦厚”具有政治教化功能的同时,也指出“温柔敦厚”在魏晋南北朝刘勰那里开始具有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功能。此外,单芳《论“温柔敦厚”诗教与宋词的崇雅倾向》和饶毅、张红《唐宋诗之争中的“温柔敦厚”说》从“温柔敦厚”对唐宋诗词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入手开展研究,促使诗歌批评不断深入完善。洪申我在《“温柔敦厚”论》中对“温柔敦厚”美学思想的历史演化、社会存在基础、意识形态影响以及心理学理由作了细致阐述,梳理了“温柔敦厚”这一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强调对“温柔敦厚”这一美学思想的基本态度: “温柔敦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必因它与封建正统伦理关系密切而否定它,更不能因封建社会把它抬到不恰当的地位而否定它所具有合理成分。而夏秀则在《温柔敦厚的伦理内涵及其现代意义》中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温柔敦厚”观,认为“温柔敦厚”为当代人所面临的心理失衡、人格冲突问题提供了反思和突围的方向。
唐宋时期是“厚”发展的成型期,“厚”在诗、词论方面主要表现为“浑厚”,并逐渐从政治教化的社会性走出,开始强调审美主体的主观经验,“厚”的审美特性开始得到关注。诗论方面,付晓芹《< 沧浪诗话 > 论盛唐气象》、梁桂芳《杜甫与盛唐气象》分别论述了盛唐气象“浑厚”的特点和盛唐诗歌“笔力雄壮、气象雄浑”的总体风貌。董雪静在《严羽“气象浑厚”审美论》中指出:
“气象浑厚”概括了盛唐诗歌的风格特征,并在宋代成为普遍使用的美学范畴。朱熹用来赞扬人格审美境界,姜夔提出“气象浑厚”是诗人追求的目标和诗歌审美的理想境界,严羽用“气象浑厚”集中概括盛唐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浑厚”的内涵不断丰富。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对“浑厚”作出总结: 在诗论中,“浑厚”主要指阳刚之美的一种诗歌风格,表现出一种朴实宏大、浑成自然的审美特点。……“浑”是诗歌外在的艺术风貌特点,“厚”是诗人内在的生命精神特征,故厚为“体”,浑为“用”,二者和合为一,既反映出创作主体深厚的人生修养和健旺的生命精神,又与其作品整体的艺术风貌完美融合、浑然一体,并表现出一种余味无尽的审美特征。
[3]词论方面,“厚”的发展则偏向对作家词风和词作艺术风格的影响。“厚”范畴含蓄蕴藉、沉郁浑厚的美学意义开始形成。南宋末年张炎在《词源》中提出“浑厚和雅”的主张,这是“厚”范畴首次在中国词论史上被正式提出,并开始强调作品的艺术风格。于东新、韩红雁在《浑厚和雅清真词———周邦彦词艺术风格论》以及董雪静《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都指出“浑厚”是指情感表达上的沉郁情思和谋篇布局的缜密法度。
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走向衰落,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艺思想和文学体裁趋于多样化,“厚”范畴的发展开始进入成熟期,一系列以“厚”为核心的诗、词、书、画论出现,并最终在明末清初达到全盛,使得中国古典“厚”范畴进一步完善、成熟。
首先,诗论方面的“厚”发展到清末,开始从强调审美主体的内在修养转变为追求审美主体内在情感和外在审美形式的统一,“厚”逐渐演变为一种成熟的审美风格。出现了晚明竟陵派“厚出于灵”、清初贺贻孙“无厚之厚”以及潘德舆的“厚必出于性情”等主张。关于竟陵派“厚出于灵”的研究,董雪静认为钟、谭二人在诗歌美学史上第一次把“厚”作为一个明确的美学范畴提出,追求艺术风貌的浑厚蕴藉,具有重要意义。李桂芹在《“厚”竟陵派的诗学审美理想》中从创作主体、过程以及作品风格等方面指出了竟陵之“厚”的审美内涵。
郜卫博《竟陵派诗学观探幽》认为: 钟、谭以“厚”、“灵”论诗,追求诗歌的平和冲淡,反映了晚明竟陵派学古并重、崇尚性灵的诗学思想。清代初期贺贻孙以“厚”为原点,形成了“神厚”、“气厚”、“味厚”的美学范畴体系,并首次提出诗歌的最高境界“无厚之厚”,建构了其独特的美学“厚”范畴理论体系。邱美琼《贺贻孙诗学批评中的诗“厚”论》、董雪静《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都指出: “神厚”、“气厚”侧重于创作主体的充实情感和学术涵养贯注于诗文所取得的艺术效果,而“味厚”则侧重于欣赏者所获得的审美体验与感受。同时,贺贻孙进一步完善了“厚”范畴的外延与内涵,阐述了与诗“厚”类而不同和对立相通的相关范畴,例如“富”、“肥”、“蛮”以及“薄”、“淡”等。清代中期潘德舆提出了“厚必出于性情”的诗论主张。阚真在《关于“厚”与“质实”—对〈养一斋诗话〉的一点看法》中指出,《养一斋诗话》追求诗歌的“厚”和“质实”,强调诗歌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上韵味深厚、充实质朴。而王英志《清代中叶诗话选评》、张文萍《论〈养一斋诗话〉对诗歌艺术风格的要求》则论述了潘德舆的“厚”的主要渊源,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指出: 潘德舆的“厚”关注主体和作品的思想内涵,要求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服务封建政教,反映社会现实。
其次,清代中后期,词论方面的“厚”在词学理论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以“厚”为核心的观点,主要有“以无厚入有间”、“有厚入无间”、“厚而清”、“折中柔厚”、“温厚以为体”、“以厚为要旨”等。关于刘熙载“寄厚于轻”的研究,滕福海在《< 艺概 > 的“寄厚于轻”论———刘熙载“寄言”说研究之二》中指出了“寄厚于轻”论的特点,认为“厚而清”即内容充实且运笔空灵,体现了阴柔与阳刚,优美与壮美、婉与劲相统一的美学思想。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认为: “寄厚于轻”主要是针对艺术风格类型的问题而阐发的,“厚而清”追求实厚之空,是对前代美学思想的超越和升华,符合中国古代审美取向实际。关于谭献“折中柔厚”的研究,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指出: “折中柔厚”的“柔”是指用婉约温和的比兴手法,展现柔美优雅的意境和形象; “厚”则指作品立意深刻,有醇厚典雅的气韵。“折中柔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词论的诗教原则和词的社会功用。方智范在《谭献“复堂日记”的词学文献价值》、杨柏岭在《忧生念乱的虚浑———谭献“折中柔厚”词说评价》对“折中柔厚”的理解与之类似,在此不做赘述。此外,关于陈廷焯“温厚以为体”的研究,孙维城《论陈廷焯的“本原”与“沉郁温厚”———兼与况周颐重大说、谭献柔厚说比较》认为,“温厚”虽来源于谭献“柔厚”论,但“温厚”的儒家诗教色彩较浓厚,起到了推尊词体的作用。同时,对“温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否定。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指出: “温厚以为体”是对创作主体情感的要求,强调创作主体要有儒家传统道德人格之“厚”,从而使得作品具有“悲怨而忠厚”的思想内蕴。
“温厚”既是思想尺度,也是艺术标准,追求一种委婉深厚的艺术境界,可以看作是传统儒家的人格标准、诗学观念和审美原则在词中的延续。关于况周颐的“以厚为要旨”的研究,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指出: 况周颐所说的“厚”,是指在作家性情醇厚和学识修养温厚基础上所追求的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刻丰富。
曹明升《“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的核心范畴》从宏观角度出发,对清代“厚”的整体展开研究,把清人词境中的“厚”分为主体之厚与本体之厚,认为“厚”不仅是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也是整个词学批评的核心范畴。“厚”这一范畴以其深厚的理论内涵和表达方式,在清代词学尊体的过程中具有独特意义。
最后,关于书论、画论方面“厚”的研究,董雪静在《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厚”范畴论》、《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有详细阐述: 作为书法美学较为后起的范畴,“厚”是在诸如筋骨、笔力、肥厚等传统书法范畴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主要指一种笔力遒劲、端正圆润的书法品格。书论“厚”以碑学中兴为界,其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尚未完全经过书法家的理论抽象的“厚”,此时的“厚”成为一种书法品格和普遍的艺术追求。后一阶段的“厚”经过雅化,成为清代以来中国书法的重要风格之一,有着强烈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清代后期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着作如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刘熙载的《艺概·书概》等成果丰硕。董雪静在论文中还指出书法美学中的“厚”所具有的力量感、丰腴感和立体感的审美特点。
此外,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还对画论中的关于“厚”的笔墨技巧作了阐述: 第一,积墨法。一些画论家认为积墨法更易取得层次分明、滋润深厚的艺术效果。第二,浓墨法。用笔头饱蘸浓墨后速画,滋润、活脱,可使画面厚重有神,而且有苍劲浑厚、雄劲大气的意境。第三,干墨法。蘸墨水较少的干笔法更容易得到使画面沉厚质实的效果。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先秦时期的萌芽,由一般的自然概念发展到两汉时期的“温柔敦厚”观初步形成,“厚”具有一定的政治教化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藻之风盛行,“厚”由品人过渡到论艺,进入审美领域; 唐宋时期,“厚”范畴开始从社会政治功用的角度走向对审美主客体的追求,以“浑厚”为中心的子范畴在诗词论方面不断发展; 明清时期,“厚”范畴的发展走向成熟,一系列以“厚”为核心的诗论、词论、书论、画论出现,“厚”范畴在创作主体、创作过程、审美主客体及审美鉴赏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美学价值。
三、“厚”之内涵及美学意义
从“厚”的文字学起源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对“厚”的解释有两个,一个是“后土”,一个是“日子”。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指出,一方面,《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山陵之厚”,表示山陵与大地的厚度,“厚”从后从土,与“薄”相对,表示厚薄义。另一方面,释为“日子”,随后演变为“味厚”,以品鉴食物味道来比喻审美鉴赏。
从“厚”单个美学范畴而言,董雪静在《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中指出,“厚”通常是指诗歌内容深刻、格调醇厚的艺术风格。从主体论角度,“厚”强调对作者的人格修养和学识的积累; 从创作论角度,“厚”要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讲求“思沉力厚”和“以无厚入有间”创作技法; 从作品论角度,追求“厚”在作品中“意之厚”、“气之厚”的表现形态; 从鉴赏论角度,追求艺术作品的内涵意蕴和情感韵味的含蓄蕴藉,关注审美主体对艺术作品的吟赏和体味。
“厚”范畴与中国古典元范畴诸如“元”、“道”、“气”等以及核心范畴例如“风骨”、“清空”、“变通”、“意象”等相比,只能是一个偏向风格论的衍生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位置并不高,且理论张力较为有限。但就其发展演变的历程看,“厚”范畴却在主体创作、艺术功能、作品风格和审美鉴赏等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基始性和指涉力,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的子范畴,例如拙厚、浑厚、温厚、柔厚、雄厚、忠厚、厚实、厚重等,其美学价值不可忽视。而“美总是有个性的,中国古典美学自然也有自己的民族个性,研究中国美学,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美学的历史个性,从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丰富宝藏中,试着去探析民族心灵的脉搏跳动,……了解一点中国民族美学思想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发展社会主义的艺术和整个精神文明。”
[4]“厚”范畴背后蕴藏着千百年来古代先民的诗性智慧和民族品格,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厚”范畴的美学内涵仍在不断丰富,走向更广阔的美学应用空间,在品评创作主体人格修养和道德境界、鉴赏文学艺术思想内蕴的醇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1]陈望衡. 中国美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 10) .
[2]董雪静.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论[D]. 上海: 复旦大学,2006,( 63) .
[3]王振复. 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21) .
[4]郑钦镛,李翔德. 中国美学史话[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相关内容推荐
- “幻象”的美学资源与美学本体观2015-11-24
- 朱光潜对约翰·罗斯金美学思想的质疑2015-05-16
- 成中英美学观点诠释美学2016-10-26
- 生态美学的自然主义价值观探析2015-03-11
- 顾恺之美学观的当代价值分析2015-10-21
- 明代生命美学的语境、内容及特征2014-11-15
- 禅宗休闲美学思想及其对传统休闲文化的影响2015-09-01
- 中国风水文化中的审美特点探究2016-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