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美、悲、喜的精神分析
时间:2015-03-11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7124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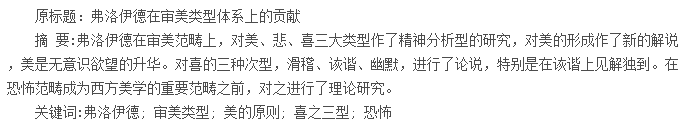
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在创建精神分析并将之作为人文科学的基本思想之时,美学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关于梦的分析和关于艺术的分析,构筑了一个庞大的美学体系。本文着重讲弗洛伊德对西方美学中在审美类型体系上的贡献。西方的审美类型体系,从亚里士多德始,基本构成了美、悲、喜的三个方面。在近代,普莱士(UvedalePrice)和赖特(ichardPayneKnight)等在同代学人论美的基础上,把美运用于自然美,创造了如画(Picturesque)这一具有时代的范畴,柏克和康德则用崇高,把悲的类型作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推进,霍布斯(ThomasHobbes)、康德(ZmmanuelKant)、里普斯(TheodorLipps)、柏格森(HenriBergson)都把对喜的类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阐述。到现代,美、悲、喜又有了重要而剧烈的变化。弗洛伊德在审美类型的古今巨变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美的类型里,他提出了美之构成的新原则。在喜的类型里,他提出了喜的三大亚型,滑稽、诙谐、幽默,特别是把诙谐放到了喜的重要位置上。对悲的类型,他提出了恐怖主题,并对之作了理论分析,使之在20世纪的后期,成为一个重要类型。
一、美得以形成的原则及其性质
西方美学认为,社会和自然中的美,都有功利因素夹杂在其中,是不纯的,而艺术则去除了功利的杂质,从而集中地、典型地、纯粹地体现了美。因此西方美学的美,主要是艺术美。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1908)中,对艺术之美是怎样形成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了新的论述。一言蔽之:艺术是幻想原理、梦的方式和艺术法则的统一。
艺术对人的功用,在本质上与幻想是一致的。摆脱古希腊以来的摹仿传统,超越巴尔扎克、左拉的艺术观念,讲求艺术与虚构认同而非与现实认同,已成为20世纪美学的发展现实。在弗洛伊德这里,虚构转为幻想。幻想又有自己的特点。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和一般人的幻想一样,其基本动力,在于其尚未被满足的欲望。艺术家或一般幻想者的愿望根据其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各异,但总结起来,无外乎两类:一是野(雄)心,即想提高自己的地位;二是性愿望。愿望的内容构成幻想和艺术的内容。弗洛伊德举了一个幻想例子:“我们假设一个贫苦孤儿的情况,你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在那儿他也许能找一份工作。路上,他可能沉湎于白日梦之中,这个白日梦与产生它的情况相适应。他的幻想内容也是这类事情:他找到了工作,得到了雇主的赏识,成了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被雇主的家庭所接纳,娶了这家年轻漂亮的女儿,然后成了企业的董事,首先是作雇主的合股人,后来是他的继承人。”[1](P33)
在这个幻想里,雄心和性的内容是很明显的。优秀作品《俄狄普斯王》中的雄心和性的内容一样明显。
幻想和艺术的内容是未被满足的欲望,这欲望往往是以时间三维的方式来组织的,即“利用一个现时的场合,按照过去的式样,来设计未来的画面。”[1](P33)如在贫苦孤儿的例子中,他得到雇主的地址(现在)引发了他对未来的设想,而未来的画面,又完全是以自己过去的生活图式来描画的,他“重新获得了他在幸福的童年时代曾占有的东西———保护他的家庭,热爱他的双亲和他最初钟情的对象。”[1](P33)弗洛伊德用这一模式去解释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按照真人画的,但她那使多少批评家殚思极虑的神秘微笑,只有从画家的童年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那正是画家孩提时期他母亲的温馨的微笑。
艺术内含着幻想原理,但艺术和幻想又是不同的。人一生内心都充满着想象,在儿童时期就做游戏,长大了,不能做游戏,于是用幻想来代替游戏的功能。但儿童以游戏为荣、为乐,并不掩饰自己的游戏,成人却为自己的幻想感到害臊、羞耻,总要把自己的幻想隐藏起来。艺术则是面对公众的,当艺术家把本要隐藏的幻想转为能够面向公众的艺术时,他用梦的方式对幻想内容进行了改装,经过梦的改装,“缓和了幻想中显得唐突的东西,掩盖了幻想中个性化的起因。”[1](P139)
在《俄狄普斯王》中,弑父意图改装为命运的强迫,在《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犯罪意图被置换为叔父的犯罪。讲一句题外话,《俄狄普斯王》中,主人公“承认了自己的罪,他受到了惩罚,好像这些完全是有意识的罪行。就我们的理智来说,这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是在心理学上却是完全正确的。”[1](P160)
艺术使人克服了幻想中的自我厌恶、自我责备和自我羞愧感,在艺术中,本能欲望得到了美的转化。
这一方面是靠梦的化装方式,另方面则是靠艺术的形式法则。艺术不同于日常幻想,也不同于梦中幻想,其重要一点就是它具有自身的形式特征。自康德以来越来越为人们所首肯的一个观点就是,形式仅凭本身就有一种审美特征,就能引起审美快感。因此,幻想转化为艺术时,它已遵循艺术美的规律,以一种取悦于人的审美形式表现出来。当人的欲望经过梦的组织方式,又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之时,面对艺术,人们一方面享受艺术形式的直观快乐,另方面又从具有美的形式的作品中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不必自我责备或感到羞愧。
总而言之,艺术就是幻想内容、梦的改装、美的形式三者的统一。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形式美学中的形式成了梦的改装。在《释梦》(1900)一书中,弗洛伊德讲了梦的内容是无意识的欲望,就是在梦中,意识的检查作用虽然比清醒时弱多了,但还是存在,无意识欲望之所以逃避意识的检查而得以从梦中出现,是经过一整套化装方式的,即四大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凝缩(condensation)和置换(displacement)。凝缩即显梦的内容比隐意简单,好像是隐意的一种缩写体似的。凝缩的方法大致有:(1)某种隐意元素完全消失;(2)在隐意的许多元素里,只有一个片断侵入显梦之中;(3)某些同性质的隐意元素在显梦中混合为一体。凝缩作用构成了显梦中的溶合物,包括溶合人物、溶合意象、溶合符号。
置换有两种方式:(1)一个隐意的元素不以自己的一部分为代表,而以较无关的其他事相替代;(2)其重点由一个重要的元素移置到另一个不重要的元素上。这样,梦的重心即被移置,从显梦上就很难体会出隐意。梦内容虽然是以一种化装的方式出现,但是当人们意识到显梦后面的隐意之时,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愧羞之感的,而艺术在方法上是梦的化装,在内容上是无意识欲望,但却因其有美的形式,而把这两方面都予以提高,当无意识欲望和梦的方式在艺术中出现的时候,艺术中美的形式把二者都予以升华。因此,什么是美呢?美为什么会感动人呢?原因为:一方面无意识欲望感动了人的内心的隐密深处,另方面美的形式给人以感性的愉快。环视整个艺术史,艺术的改装原则分为两个类型,即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在古典艺术中,幻想内容是以理性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需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探查出隐蔽在形式里面的幻想内容即可。在现代形式中,幻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是非理性的,变成了梦的直陈,如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派的艺术家那里,但凡经过改装的显梦都还要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分析,现代艺术型的改装当然也还是要进行分析的。但无论是古典艺术还是现代艺术,都是用美的形式去表现无意识的欲望内容,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可以说,美,是无意识欲望的升华。
二、喜之三型与基本原理
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27)中研究喜之三个主要类型:滑稽、诙谐、幽默,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论述了这三个类型的基本原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包含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为一体而又相互作用的心理结构。本我是人的原始本能,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性本能,即爱本能;一是死本能,即攻击本能。本我是生命的活力所在,是人的各种行为的最后根源和决定因素。
本我无惮社会的道德和律令,只顾追求自己的满足,构成无意识的内容。自我是我经过家庭训练、社会交往和与现实接触而形成的个人人格,代表人的常识和理性,它一方面使本能的欲望适应现实的需要,以现实允许的方式去满足,另方面对本我不合现实的冲动则施予压抑。超我是由父母、老师及社会教育而内化为个人的道德理想。它是一个具有父母一样的权威和社会权威一样的制裁力量的监督者。它不断以内疚和犯罪感来对付人违反、偏离理想的行为。超我既与自我一道协力压抑本能的原欲要求,而当自我偏离理想时也对之予以批评,施以控制。正是这样的心理结构,是美学之喜的基础。弗洛伊德对美学之喜的三个类型:滑稽、诙谐、幽默,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述:一是关于喜剧之笑之所以产生的心理能量原理;二是关于喜剧之笑之所以产生的心理结构关系。前一个角度的基本理论是:“诙谐中的快乐产生于压抑消耗的节省,滑稽中的快乐产生于观念(关于贯注)消耗的节省,而幽默中的快乐产生于情感消耗的节省。”[2](P225)
这一理论涉及精神分析特有的心理能量,讲起来既复杂又不易被理解,简单地讲就是,心理中无意识欲望本应被压抑,但诙谐却让其可以被释放,自我已经集中起来以用于压抑的能量因而被节省,笑由之而产生。在滑稽中,自我本要按正常方式认真地看对象,突然发现不能以正常方式去看,自我已经集中起来用于认识的能量被节省,笑由之而产生。在幽默中,自我本要用一种悲的情感去看对象,但对象的对悲景的拒绝和对快乐原则的坚持,自我已经集中起来的情感能量被节省,笑由之产生。为什么在三种喜的类型里,节省的心理能量会以笑的方式释放呢?这就与第二个角度,心理结构有关了,严格地说,它与美学之喜的一般理论相连,美学对喜的基本假设是主体高于对象,这个高于,是主体站在社会的正常尺度,而对象处于低于社会正常的尺度,成为笑的对象。弗洛伊德把这一基本原则进行了精神分析的解释。正常与低于正常成为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意识与无意识(自我超我与本我)的关系。在滑稽中,成人型自我占主导地位,在诙谐中,无意识的本我得到突出,在幽默里,超我的力量得到了强调。
弗洛伊德把滑稽分为三种。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三种视点。第一种滑稽的笑是通过对象与主体的比较。用主体的成人之眼看到了对象的儿童之态。即另外的人的动作或形式或心理机能或性格在我看来显得像儿童。如对象之蠢如一个懒惰的孩子,对象之坏如一个淘气的孩子。这是滑稽的正形,对象这种低于正常呈现让观者发笑。第二种滑稽的笑是把焦点集中在对象上。通过对象自身的比较,即他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孩子。有成人之形却呈儿童之态。这里只从对象去看,何以令人笑。其本来应当是成人却情不自禁地显为儿童。夸张、模仿、贬低、陋相,都属此类。正如儿童有意模仿成人会显得可笑,成人有意模仿儿童也显得可笑。而成人显出如儿童般的窘境,都与儿童不能完全控制其身体功能相连,而漫画性的夸张则与儿童缺乏比例感和对数量关系的无知有关。第三种滑稽之笑是把焦点集中在主体上,通过主体内部的比较。即我将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个孩子。这其实是自己的有意识追求和无意识抵抗,在无意识胜利之时,呈现为孩子相,但立即回到成人意识,站在成人立场上,于是对自己所呈现的孩子之相感到好笑。这里虽然引进了新的理论框架,但对滑稽理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增加。但有了新的角度。弗洛伊德主张,儿童在儿童阶段因纯粹的快乐而发笑,但“儿童的快乐动机在成人身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滑稽感”[2](P215)。人对一个人的滑稽的笑是因为:第一,重新发现了他身上的孩子气;第二,像自己儿时一样,“笑总是适于成人的自我与儿童的自我之间的比较。……滑稽的东西总在婴儿一面。”[2](P215)
滑稽是人重新获得已逝的童年的笑。把这一点放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之中,即人心是本我、自我、超我进行激烈斗争的战场,那么,滑稽之笑就具有了心理平衡之功用。
幽默是人面对不顺乃至悲惨境遇时呈现出来的乐观态度。如当一个犯人被带上绞型架时,说:“不错,这个星期的开始是多么美好。”在幽默中,任何一种不好的恶劣的悲惨的现实都是能给他带来快乐的。幽默,是对现实中给人带来不快和痛苦的一般效果的拒绝。在这一拒绝中,显示了主体作为自我的胜利,无论怎样的悲惨境况,都不能破坏快乐心境,都妨碍不了主体对之进行快乐的反应。在这一胜利中,主体是成人,在正常尺度上,而整个世界是儿童,是低于正常的尺度。幽默之笑是主体对低于正常尺度的世界之笑。最为重要的是:一方面主体决心把本我的快乐原则进行到底,快乐原则是一种本能的力量,另方面,主体把对快乐的坚持作为一种主体的理想,超我的功能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在幽默中有了一种在诙谐和滑稽中没有的尊严。人在面对悲境时,把本我(的快乐原则)升华为超我(的理想原则),在二者的联合作用下,幽默就产生出来。
诙谐是弗洛伊德最具有新意之处。诙谐的形态与现实相关,弗洛伊德把诙谐分为四类:一是带色(与性有关)型的(比如民国时代的香烟广告:一个美女对一支烟说道:吸来吸去,还是他好);二是攻击(具有敌意)型的(评论一位不会交友的人:他,跑在墙头上去拉屎:狗友都相不到一个);三是愤世嫉俗(亵渎神圣)型(王塑小说里,一位党支书对要申请入党的女青年说:你要入我这个党,得先让我入你那个裆,你不让我入你那个裆,我就不让你入我这个党);四是否定确定知识的(如说:他真是个大人物,完全符合:屁股上面插帚把———伟【尾】大)[2](P216-217)。这四种类型都明显地低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正常尺度,这个低于让诙谐呈现为一种与“正说”不同的“胡说”,而这“胡说”又以艺术的语言进行,因而引起愉快的笑声。诙谐的愉快根源于童年时游戏的快乐,当已经成年了还以童年快乐的方式出现,呈现为一种内容上的“胡说”。胡说的后面是无意识的欲望,当这一欲望受到正常的意识的压抑而不能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以诙谐的方式突破压抑,冲了出来。但无意识的内容不能以原有的方式直白地冲出,而只能以诙谐的方式才可以出现。由于诙谐的实质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斗智斗勇,因此,诙谐的工作方式在本质上与梦的工作方式相同:充满了凝缩、置换、变形。梦是以形象为主,诙谐是以语言为主。因此,诙谐主要体现为文字游戏:双关语、隐喻、歇后语、俏皮话……诙谐的技巧就是在正常的知识中在本不相似的东西中发现暗含的相似性,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把在正常的知识中本不同类的东西联结在一起,这一联结具有语言之妙,这诙谐之妙让人低于正常的“胡说”得以出现。诙谐的出现让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得到了释放,意识与无意识,本我与自我超我的紧张冲突就在这欲望的释放中,得到了缓解。笑声正是缓解的完成。
三、神秘和恐怖的基本原理
悲在新时代的表现有多种类型,20世纪前半期,以荒谬为主,20世纪末到新世纪,恐怖成为一个主题,而弗洛伊德在1919年,就写了《令人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呈现了恐怖的基本原理。对恐怖成为悲的一个重要次型作了理论上准备。世界不仅是在理性规律中运行,而且也有妖、魔、鬼、怪出入其间,当人一旦认定有后一世界,而这一世界的形象又在前一世界中呈现出来,恐怖产生了。作为美学的恐怖则是为了认识、克服乃至战胜现实的恐怖而产生出来。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就面对恐怖问题,他把恐怖与神秘并在一起,并以精神分析的方式予以解谜。
神秘和恐怖在德语里有一个二而一的词Unheimlich(在英文里被直译为unhomely,或意译为uncan-ny),弗洛伊德通过一系列的词源考察和分析,指出其词义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义,既是:熟悉;又是熟悉的反面:陌生。而一个事物之所以带来神秘和恐怖,正是在于,其对人而言,既是熟悉的又是不熟悉的。
而且是由熟悉转为不熟悉。一个看似熟悉的东西,其实却是不熟悉的,正是在这不熟悉被意识到的这一刻,神秘和恐怖产生了出来。熟悉后面的陌生本来是被掩盖起来的,现在却显露出来,这一时刻,理性的现实世界与非理性的想象世界之界线消失了,两个世界合为一体,恐怖由之而生。
恐怖现象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对象的双重性质。这与上面讲的恐怖实质相关。所谓双重性质,即它是理性思维中的熟悉对象,为理性、规律、知识所把握,又是非理性思维中的陌生对象,与妖魔鬼怪相关联。由熟悉到陌生的转化,即妖魔鬼怪世界透露出来之时,两个世界合为一体,人、物、事显得既熟悉又陌生,恐怖由此而产生。第二,当人的头脑中感觉似乎存在一个妖魔鬼怪的世界,而在身之所处的理性世界中出现相同现象重复之时,就感受到了这一世界的气息,比如,一个人去旅行,上火车,座位号62,进酒店房间号是62,存物品,得牌号是62,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都有62这一数字出现,这时一种蹊跷不安开始出现。
弗洛伊德认为,神秘和恐怖从人类来说,来源于原始时代的心理残余,从个体来讲,来自于儿童时代的心理残余。首先,与儿童和原始人的自恋有关。其次,原始时代的泛灵论把万物认为一体,儿童心理是原始心理的复演,也有万物一体的特点,认石头玩具有生命,觉鱼虫鸟兽有人情。原始心理在理性之后的残余和儿童心理在成人之后的残余,成了在理性成人世界中产生一瞬间视理性的熟悉之物为非理性的陌生之物的基础。“原始信仰总是与幼时情节相紧密相关,而且,实际上它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的,”[2](P276)
在现实中,这二者的界线经常是模糊的。再次,人的死本能和死亡恐怖,与原始巫术魔力残余思想和儿童的幻想思想相结合,冲进成人的理性思想里,进而让妖魔鬼怪陌生世界渗透进来。最后,被弗洛伊德认为从儿童时期特有的阉割恐怖,在成人意识里的继续,具体体现为具有西方特色的恐怖形象:可以独立活动的断头、断肢、断手、断脚。在精神分析里,原始与理性、儿童与成人的区分,又是以无意识与意识的斗争、压抑和反压抑的较量的方式呈现出来,“当受压抑的幼时情节因某种印象复苏,或者,当已被克服的原始信仰似乎又得到证实时,我们便体会到神秘而恐怖的情感。”[2](P275-276)
西方美学的审美范畴体系,从古希腊到近代到现代到后现代,一直在变化着,而弗洛伊德的审美范畴研究,对这一还在进行中的演变,起了甚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奇,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2]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M]∥常宏,徐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 相关内容推荐
- 顾恺之美学观的当代价值分析2015-10-21
- 宗白华美感思想中“合”的精神探究2017-03-07
- 城市环境美的生态、个性及设计维度分析2014-09-11
- 康德关于崇高美学的分析及其现代价值2014-11-01
- 中西审美观、审美精神及审美情趣的对比分析2016-01-26
- 从《拉奥孔》入手分析古希腊悲剧中蕴含的真正美2014-11-15
- 宗白华与方东美对“生命情调”和艺术精神的切合2014-09-11
- 尼采美学中的酒神音乐和酒神精神2015-09-21
- 上一篇:中国美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别现代美学
- 下一篇:中国美学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