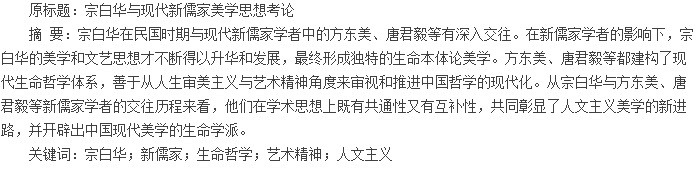
宗白华与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有很深的交往,在思想上彼此亦有交锋,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很少关注,目前仅见2 篇论文对此有所阐述。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在与现代新儒家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下,宗白华的生命哲学思想和艺术理论才不断得以升华和发展,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学与美学体系。新儒家中的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等,都颇为关注生命哲学,善于从人生审美化与艺术精神角度来审视中国哲学,重建现代生命哲学体系。虽然现代新儒家阵营里各家观点并不一致,彼此之间甚至对立,但是总的来说,20 世纪现代新儒家在思想上深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思想彰显出昂扬的生命创化精神和艺术情调,充满着“生命哲学”和“艺术哲学”的双重色彩。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命意蕴在现代新儒家身上得到了高度的激发和弘扬。换句话说,现代新儒家重视阐释、发微与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并试图将中国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融入现代世界哲学与文化的建构之中。
方东美、唐君毅都曾与宗白华过从甚密,彼此之间交往频繁。本文拟从三者的交游事迹和思想渊源来探讨他们的学术建构之路。方东美曾是宗白华在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二人都在1920年代中期进入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方东美于1947年赴台讲学,1948年受聘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后没有再回大陆;宗白华于1952 年调到北京大学,二人前后共事22年(1925—1947)。唐君毅于1928年由北大转学于中央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宗白华,并听熊十力授《新唯识论》。由此看来,宗、方是同事,唐是二者的学生,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可以成立的。另外从他们三人的学术思想看,这种深层次的思想契合是很明显的。
一、宗白华与方东美对“生命情调”的共赏
方东美(1899—1977),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享有“民国以来,我国在哲学上真正学贯中西之第一人”之誉。方东美自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1913年入桐城中学,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同学。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1年赴美留学,1924年于威斯康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任职于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1926年受聘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教授,与宗白华成为同事。方氏先后撰有《科学哲学与人生》、《哲学三慧》、《中国人生观》、《华严宗哲学》、《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等著作,被誉为世界级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另外,方东美在艺术上也具极高的才情,自铸伟辞,尤工于诗,有《坚白精舍诗集》流布,存诗千余首,时享“诗人哲学家”之美誉。其诗兼有“清刚鲜妍之美”(朱光潜语),其艺术思想与美学观念深邃丰赡,值得探究。方东美曾说“难能哲匠亦诗翁”,诗情与哲思本难兼备,而他却要“移情睿哲作诗人”,因为他认同怀特海“哲学与诗境相接”的观点以及桑塔耶那 “伟大的宗教境界即是诗之降凡人间”的主张。在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宗教、哲学与诗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脉相通的:三者同具崇高性,而必藉生命创造的奇迹才能宣泄发挥出来”。方东美认为,健全之哲学精神、优美之诗歌艺术与崇高之宗教情操三者可以交融互贯,因此“诗之功能在于做人生之大梦”,而世上唯有真正的诗人“才能做最美的人生之梦”。方东美一生服膺“乾坤一戏场,生命一悲剧”的名言。所谓诗是“生命之梦”,即是说艺术是生命精神的体现,他的《坚白诗集》就是其“生命哲学精神”的显现。
从相关史料看,宗、方二人既同为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且有很深的交谊。当代学者彭锋说:“宗白华与方东美同为中央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并且有很好的交往。据宗白华的儿子回忆,宗白华与方东美常常相互串门聊天。熊十力也在中央大学短期授课,在中央大学有一批追随者(如唐君毅等),同时与方东美有更早的交情。在这种环境下,宗白华当然能很快、很深入地了解熊、方二人的思想并且受到他们的影响。”
另外,宗、方二人最早都是在对柏格森研究中接受其生命哲学思想影响的,但宗白华的生命哲学思想似乎有更早的渊源,他在1919年就发表《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而方东美则在1922年夏以论文《柏格森生命哲学之评述》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获硕士学位。有学者指出:“宗白华的思想也可能对方东美产生过影响。宗、方二人之所以常常串门聊天,与他们哲学观点上的相似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所谓“宗、方二人更多的可能是互相影响”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另外还有资料显示,方东美在1947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曾对宗白华的美学尤多称许。
宗、方二人的交谊还可以从抗战中方写给宗的“佛头”诗见出端倪。方东美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写下《倭逼京师宗白华埋佛头于地下》一诗,诗云:“庄严兼相好,断颈不低头。身受唐人拜,心萦汉域愁。艰难怜往劫,险恶愍来忧。羞闻 木,戚戚隐荒邱。”
关于此尊“佛头”的典故,1983 年宗白华在《我和艺术》中曾回忆说:“记得三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偶然购得隋唐佛头一尊,重数十斤,把玩终日,因有‘佛头宗’之戏。是时悲鸿等好友亦交口称赞,爱抚不已。不久,南京沦陷,我所有书画、古玩荡然无存,唯此佛头深埋地底,得以幸存。今仍置于案头,满室生辉。”
宗白华因喜爱这尊佛像而得了“佛头宗”的绰号。宗白华弟子游寿在1979年为宗白华八秩寿辰所作的诗中也有“秦淮访清赏,灿烂石像尊”两句,游寿解释说:“师尝独访秦淮古肆,一日得青玉石大佛头,于是开筵宴客。四面视雕像光景,发挥瞬间艺术宏论。”
这段话交代了这尊佛头的来历。宗白华在1979年4月11日《复游寿书》中提到“案头灿烂石像尊犹俯视我作此书”云云。由以上证据可以显示,宗、方之交并非泛泛,二人在思想倾向上也有许多共同点。
1938 年,宗白华在《〈哲学三慧〉等编辑后语》中对方氏鸿文《哲学三慧》给予高度评价,由此见出二人哲学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宗白华以司空图《诗品》中的“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诗句来赞颂方东美的这篇《哲学三慧》,方氏这篇文章论述了中国、希腊、印度这三种民族精神与哲学智慧。宗白华说:“哲学家所瞑想探索的是一个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及其命运。”中国在古代接受了印度文化,近代又遭遇西洋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和人生增加了丰富内容,同时也产生诸多难题和危机。因此“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近几十年来诸多中国思想家感兴趣的问题,而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方东美的《哲学三慧》,可以见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确是有所进步。《哲学三慧》是用文言写成的哲学论文,文字艰深难懂,内容闳博深奥,因此宗白华又推荐读者可以先参看方东美的另一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宗白华认为这是“一本文章流丽,内容丰富的发阐近代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著作”。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宗白华的影响。方东美是现代中国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哲学家,他所建构的文化生命哲学系统的独特贡献在于,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方东美一生的学术思想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899—1936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受儒道文化的熏陶和杜威、怀特海等影响,而致力于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科学方法来诠释中国文化,《生命情调与美感》、《科学哲学与人生》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36—1948年为第二阶段,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致力于生命哲学的阐发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宣扬,深化了对中国文化、道德和艺术的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人生哲学概要》等,这与宗白华这一时期的“艺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激发民族心灵的“幽情壮采”,焕发出文化救国的极大热情。1948 —1966 年为第三阶段,方东美赴台,并先后多次赴美讲学,逐渐由西方回归东方,这一阶段代表作有《生生之德》、《中国人生哲学》(英文版)等。1966—1977年为晚年讲学阶段,在人生的最后十年,方东美的讲学成果最为丰硕,《华严宗哲学》、《中国大乘佛学》、《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英文)等著述代表了晚年方东美融汇儒、释、道、西自成一家的哲学气象。方氏始终以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为旨归,以世界化的学术襟怀对待各宗各派,以人文主义的融贯方法统摄诸家之学,站在“最高峰”上重建以生命为本体的哲学体系。
由此可见,方东美以西方柏格森、怀特海哲学为参照,提倡中国哲学与文化应回复先秦儒家道家广大和谐的生命气度,以及大乘佛学中的华严境界。方东美的生命哲学、比较哲学和美学思想对宗白华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二人都对世界哲学的多元互补格局以及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生生之德”极为推重和激赏,显示了他们在哲学心灵上的共通性。
二、宗白华与唐君毅对艺术精神的相契
唐君毅(1909 —1978),四川宜宾人,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唐氏1928年从北大转学进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学习,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宗白华等,并曾听熊十力讲授《新唯识论》等课程,而得忝列门墙。青年时代的唐君毅还曾受到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思想影响。1950年赴香港,与钱穆等创办新亚书院。1958 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了被称为海外现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人生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
从宗白华与唐君毅的交往看,师生二人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相当深刻的相互影响。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在1944—1945年前后唐君毅曾让其妹唐至中到中大去旁听宗白华的美学课,唐至中去听过多次。这足以说明唐君毅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认可和推许。唐君毅于1978 年2月在香港九龙浸会医院病逝,宗白华在1983年6月19日写给唐君毅之妹唐至中的信函中回忆与唐君毅的交往:“回忆旧游,无限哀悼。抗战中因敌机炸重庆,曾同迁居嘉陵江上,朝夕相晤。所写关于中国文化精神一文尤为心赏。”
其中还提到一事:“聘许思园、牟宗三是君毅提出,我赞成的,后来方东美心中不满。”
唐君毅与方东美亦有很深的思想渊源,1928年唐君毅与程石泉二人同时投入方东美门下,他们都喜欢古希腊悲剧哲学,喜欢欧陆哲学家尼采、叔本华和英美哲学家布德利、桑塔耶那、詹姆士、杜威以及怀特海等人的哲学著作,“师生经常在东美先生石婆婆巷的寓所畅言所怀,忘其所以”。
宗白华在1939 年的《〈中国哲学中自然宇宙观之特质〉编辑后语》中说,唐君毅的这篇文章精辟地解剖和系统地叙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与精神特点:“在民族思想空前发扬的现代,这种深静的沉思和周详的检讨是寻觅中国人生的哲学基础和理解我们文化前途的必要途径。”宗白华提倡一种各尽其美、至于至善的文化精神。他希望“优美可爱的中国精神”能在世界文化的花园里绽放出奇光异彩。“我们并不希求拿我们的精神征服世界,我们盼望世界上各型的文化人生能各尽其美,而至于其至善,这恐怕也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唐君毅的《心灵之发展》长文发表在宗白华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渝版)1941 年第131 —134 期,宗白华在为唐文所写的“编辑后语”中说:“近代自然科学发现了天文学的大宇宙和化学的小宇宙,一切质力和自然律。在向外探索和控制自然的知识上是相当圆满了,然而可惜的是这科学家自己的精神人格在这唯物的宇宙观里,没有了地位。”浮士德式的探求宇宙之究竟的悲剧态度实在是代表了近代西洋科学家的精神,然而“我们能否再从这唯物的宇宙观里寻回自己和自己的心灵,使我们不致堕入理智的虚无或物质的奴隶,而在丰满的充实的人格生活里,即爱的生活里,收获着人生的意义”。这就是唐君毅的文章所给我们的启发。1943 年唐君毅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由正中书局出版,1944年2月23日的《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259 期)发表了宗白华推荐唐君毅此书的文章,即《介绍两本新书(二)》。宗白华说:“唐先生在《学灯》上发表过他的《人生之路》长篇论文和其他。他的丰富的哲学修养和精辟深透的见解能用明白细密的文字为好学深思的青年说法。
我们现在的确需要思想上的深化和情感体验上的深化。”唐君毅对于“中西哲学及其文化精神”的问题作了一番“颇为精到的分析”。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由中华书局1944 年出版。全书分生活之肯定、心灵之发展、自我生长之途、人生的旅程等四个部分。《学灯》以前也刊发过《生活之肯定》与《心灵之发展》两文,宗白华在细读过该著后写下《介绍一本人生哲学书〈人生之体验〉》(1945)一文,说:“深感此书能以文学风趣写出深刻的人生思想和人生体验,炎夏读之,如到清凉晶莹之世界。”
宗白华认为唐氏此著是继承了柏拉图、庄子以神话寓言来表现“最深不可名言的哲学体验即人生意境”的传统,唐君毅在书中也以中国古典诗词来表现人生、心灵、人生之路、人生价值及理想人格等等抽象的哲理。唐君毅自己对于本书为何不用最确切的概念和寓言来表达真理解释道:“真理似乎是把光,不但放射于一方面,而也放射于多方面的金刚石般的东西。”因此“只有不确切的才是富于创造性的”。宗白华对这种以诗喻理的写作风格显然是持赞同的态度,他自己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论文中也是用了这种“以诗论理”的方式。他说世上有两种好书,“一种可以增富你的知识,一种可以影响你的生活态度,开拓你的胸襟”,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无疑是属于后者的。
另外,宗白华还推荐了此书的姊妹篇《道德自我之确立》等。
唐君毅先后受到方东美、宗白华、牟宗三等老师们的影响,其一生徘徊于东西哲学之间,旨在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道德人文世界。其治学不拘一家之说,但用力最深的是中、欧、印三大文化思想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精神价值。唐君毅始终立足于中国式的人生文化立场,开辟生命之境界,阐扬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以启导向上超越的心灵九境为目的。宗白华与唐君毅的哲学、美学、艺术思想相关的有三个方面:文化哲学、艺术精神、生命境界。这里就宗白华与唐君毅关于中国艺术的精神价值的探讨作一比较。
五四以来,对中西文化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唐君毅从20 世纪50 年代初开始对人文精神的艰难探寻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大力宣揭。深受牟宗三、方东美、宗白华等诸位师长影响的唐君毅,在其名著《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试图通过申论中国哲学智慧来阐发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他一方面梳理了中国文化的演进历程,一方面又阐述了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宇宙观、心性观、道德理想、宗教精神以及形上信仰、文学艺术的精神等。他力图通过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对照,以中西文化思想之异质性为背景,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宏观描述。也只有在跨文化比较的视域下,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才能得以凸显。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呵护情真意切,对中国文化之展望亦令人振奋。该著对五四后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多有采撷,如熊十力、牟宗三论中国哲学,钱穆、蒙文通论中国历史与政治,梁漱溟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论中国人的生命情调与美感等。
宗白华与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基本精神的理解上有“心心相印”之处。唐君毅1943 年发表了《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一文,与方东美、宗白华的艺术哲学思想如出一辙。唐君毅指出:与西洋近代文化中科学精神渗透到文化之各方面相比,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艺术精神弥漫于中国文化之各方面”。
他认为:西洋哲学方法重思辨与分析,中国的哲学方法重体验与妙悟。“艺术的胸襟是移情于对象与之冥合无间,忘我于物,即物即我的胸襟。艺术的意境之构成恒在一瞬,灵感之来稍纵即逝,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中国哲学方法上之体验在对此宇宙人生静观默识,意念与大化同流,于山峙川流鸟啼花笑中见宇宙生生不已之机,见我心与天地精神之往来。这正是艺术胸襟之极致。中国哲人之妙悟哲学上至高之原理,常由涵养功深,真积力久,而一旦豁然贯通,不待推证,不容分析,当下即是,转念即非。这正如艺术意境之构成,灵感之下临于一瞬。”
这段论述与宗白华、方东美的生命艺术观念是何等的契合!唐君毅曾指出:“艺术创作即是沟通内心外界,精神与物质 ,超形界与形界之媒介。艺术精神融摄内心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而使人于外界中看见自己之内心,于物质中透视精神,于形而下中启露形而上。”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强调内外之道的相合,精神与物质的相融,在“形色”中见出“性天”,以形下之器来彰显形上之道,中国哲学思想是最具有“艺术性”(审美性)的观念体系。
由此可见,宗白华、方东美与唐君毅师生三人关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基本观念是非常切近的,这应该也是三人在思想观念上相互欣赏、彼此影响的善果。从宗、方、唐三人的交往事迹和相互影响的历程可以见出,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既有共通性又有互补性,共同彰显了现代中国美学的人文主义新境界。
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开辟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生命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