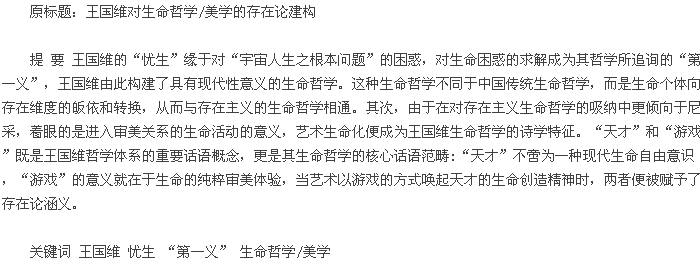
一般而言,学界对王国维的诠释首先从其旷世命题———“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①开始,这缘于他在“可信”和“可爱”之间的左右探询和上下求索中,寄寓了深重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安顿身心的精神诉求。我以为,破解这一命题首先应该从王国维所追询的“第一义”入手。② 如果说,“可信”与“可爱”的冲突源于王国维的“忧生”情怀,所谓“忧与生来讵有端”( 《欲觅》) ,那么,“第一义”用王国维自己的话说,“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③ 亦如此言: “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即在其作为新的基点———生存之本的基点的开端,也就是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与审美理念是一种根基性内涵的重新开启,在此意义上,王国维美学是审美现代性的开拓。”④也即,“第一义”或“生存之本的基点的开端”,所指向的是一种生命哲学( 美学) 范畴。
一
如前所述,生命体验的痛苦与文化选择的困惑促成了王国维的“忧生”情怀。“忧生”以致衣带渐宽,从而固守着对存在的体悟,为生命的困境找寻出路。这意味着,“可信”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可爱”这一问题被提到生存层面乃至生命本体存在的维度。
无疑,以“生”为本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儒家经典《周易》是中国生命哲学的源头,《周易·系辞传》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其“生生不息”的哲学观把整个世界看成是大化流行的生命现象,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生命性的理解。如果说儒家的重生主要是侧重于肯定宗族、群体性、社会性生命的保存,那么道家特别是庄子强调的则是生命个体的价值与自由。道家的理想人格是“人貌而天虚( 心) ”( 《庄子·田子方》) ,“天心”直指天的自然本性,亦即宇宙自然的生命; 所以庄子论道讲究“与天为一”( 《庄子·达生》) 、“将返于宗”( 《庄子·知北游》) ,要求人们不断地从各种人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人与自然融通的无尚快慰,体验宇宙生命自由自在的无限乐趣,从而达到人与宇宙生命的完全契合,使自我复归于真实生命的本体; 而“天道”的运行因此必然落归于“人道”,与“道”化一的境界才是生命存在的终极归依; 在道化生万物、人复归天道的运行中关注的是人的真实生命和现世存在,故而道家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最为接近。
禅宗的“禅”也是以生命为主体,禅宗的“心”所指的是生命的开关,所谓“心心相印”是印证整个生命,“以心传心”即为生命的感应; 其实佛教的宗旨便是帮助众生了解生命的意义,充实生命的内容,禅宗因此强调圆融之境———生命意义的圆满; 其中,圆就是禅,或,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圆融一体,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冥然合一; 心本就是圆,只有圆融无碍,才能体悟天地之心,去伪存真乃至圆悟圆觉,领悟和把握自己的本心,实现一种生命活动的最高存在方式。
王国维的“忧生”固然与本身忧郁悲观的天性有关,但更多的却是生命个体向存在维度的皈依和转换。尤其是,他在“可信”和“可爱”之间的左右探询和上下求索中意识到,长期以来个体性生命都在传统生命哲学的关怀之外,如,即便是强调个体自由的庄子,“庄子和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尚缺乏西方的‘独立型自我’的环节。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庄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缺乏西方美学思想中自我表现、自我创造的特点,而往往流于宿命论( 当然,他的宿命论也不是绝对的) 。”①正是借助于叔本华等的生存意志说,王国维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完全是个体的生命困惑。……而‘人生之问题’的核心,就是源于个体生命困惑的‘忧生’,……中国美学历史中‘石破天惊’的千古一问: 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 就是与‘忧生’俱来的生命困惑。”②易言之,王国维对生命意义的现代性理解超越了传统生命哲学的疆域而与现代人文主义———具体说,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表现形态———生命哲学的价值观念接轨。
广义的生命哲学是指关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学说。它首先关涉的是人的生命存在或者生存问题; 其次,它赋予人的生命存在以一种存在论意义,亦即把生命意向提升为宇宙世界的本原和本质、或者本真存在,把握这种生命存在状态主要取决于诸如“直觉”“观”“领悟”等非理性方式,而不是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狭义的生命哲学所指的是西方 20 世纪以柏格森、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思想学说,它在批判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机械论和决定论、解放人类思想方面的巨大意义是借助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来实现的,所以这个名称可以归纳当时出现的各种从生命原则出发来反对传统哲学的思想,乃至于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叔本华是生命哲学的奠基者。对于后来者而言,叔本华对生命意义既渴求又绝望的矛盾有三方面的理论意义。其一,它强化了现实苦难的存在,强化了生存意义的丧失作为问题的严重性。其二,它在人的生存本性上召唤反拨性的观念。……其三,它实际上已显示出: 苦难是相对的; 生存的意义和理由是可以找到的。”①尼采认为生命意志是宇宙的形而上本体,生存、生命的本质就是展示个人的创造力; 进而从审美化角度为生命的创造力寻找价值所在; 尼采强调,生命的意义首先为艺术所确立,有着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无论抵抗何种否定生命的意志,艺术是唯一占优势的力量,是卓越的反基督教、反佛教、反xuwuzhuyi的力量。”②尼采甚至用艺术维护生命的价值来对抗传统的理性主义,不惜以生命对抗一切、否定一切来创造悲剧化的人生境界,实现了他所谓的“价值之重估”。海德格尔面对现代人失落自我,彷徨无依的生命异化状态,指出生命一种栖居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存活,尽管他通过对死亡的深切认识与行动来体现生的意义,但仍然希望建设一种安顿生命的终极归宿,憧憬着一种“诗意地栖居”的境界,故而他的生命观与庄子的生命观颇为接近; 庄子主张生命存在的终极归依是与“道”化一,而“达生”作为一种体悟之路,由于贯通了大道的障碍使得生命主体指向“道妙自然”的极境: “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 《庄子·庚桑楚》) ,这便是天地之大美或诗性栖居的境界。惟其如此,学界将生命哲学确认为存在主义的思想来源。
总之,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经典存在主义者认为,现实存在是非本真的,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的关系是对立性存在不是本真的存在,而是异化的存在,因为在主客对立之中没有自由可言,不仅人与自然的对立没有自由可言,而且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从而也没有自由可言。本真的存在不是现实存在,而是可能的存在、应然的存在,它指向自由。本真的存在何以可能,就在于超越现实存在,也就是超越主客对立的状态,进入物我一体,主客合一的境界。③
二
问题其实在于,王国维的生命困惑和对困惑的求解与中国传统生命哲学认定的“性本善”不同,而是将“欲望”视为与生俱来的本体,“生活之本质何? 欲而已矣。”“欲望与生活、苦痛,三者一而已矣。”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⑤ 生活的本质是欲望,欲望的后果只能是痛苦,这既是叔本华的推论也是王国维的体验。在此,王国维面对的是世界,追问的则是人生; 他思考的已不是人世的缺陷而是个体生命本身的缺陷和痛苦,这意味着,王国维转而通过向个体性存在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忧生”的困惑。“王国维突破与超越传统伦理道德与政治社会的界限而直达生存本质层面的追本溯源———世界人生之根本、‘宇宙人生之真理’的探究。那么,置身于世界与本土历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大境遇中,在相异的文化背景之下,在错落的精神层面上,在对生存本质的重新领悟与洞透的根本的层面上,王国维美学与西方审美现代性交错而契合了。”①不过,相对于叔本华的只是将艺术作为生命意志的一种表现形态而言,王国维更服膺的倒是尼采。“尼采和叔本华对生命现象的不同观照是值得深究的论题。……苦难与快乐的同一、个体毁灭与生命升华的同一是尼采生命哲学的核心。……在尼采思想中,毁灭与快乐的同一首先是观照性的艺术现象、审美现象。”②正是在这里,王国维从叔本华而转向尼采: 在艺术生命化的自我定位下高扬非功利的诗性人生与价值自觉,来化解生存的困惑,超越生命的忧患。
不难发现,尼采的“酒神精神要求个人站在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位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个体生命,‘一切价值重估’的最高标准是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二者都立足于生命本体的观照,强调在艺术中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个性自由,体现的是一种审美人生。”③无独有偶,王国维哲学( 美学) 思想亦充满着浓烈的生命体验色彩,其《〈红楼梦〉评论》写道: “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 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这样的听曲悟境,颂篇明性,具有一种生命存在本身的诗意。在他的心目中,“美术”( 艺术) 是人类生命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在这种美的创造与表现之中,人类感到了一种与天地相合,与宇宙并生的快乐。艺术的作用就是使人臻于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境地,只有在艺术境界中,才有可能摆脱欲望的束缚、造就一种新的精神生活方式与健全的人格,洞见“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它为卑微渺小的生命个体提供了审美超越和意义追寻的途径与可能———一种审美化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语) 。所谓“美术文学非徒慰藉人生之具,而宣布人生之最深意义之艺术也。”④亦如王国维在《端居》一诗中所写: “虢我聪与明,冥然逐嗜欲”。王国维明白,聪与明,嗜与欲,在现实生命中不可能像庄子所说那样能够通过“心斋”“坐忘”摒弃掉,只有在艺术世界中方能物我两忘,生命的价值方能实现从生存的事实向存在的意义和状态问题延伸。当王国维将生命关怀寄寓在艺术审美中时,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对于生命信仰之维的建构历程,或者说,以艺术生命化方式展开了生命美学的逻辑思路。
而王国维之于尼采相通之处就在这种艺术人生背景下观照自我生命存在。也可以这么说,王国维对哲学的解读始终是和对自我生命的探索相伴相随,但当他意识到个体生命无力承担思想和学说的全部重量时,便只能退而求其纯粹———到艺术去寻找慰藉,亦即尼采的“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⑤它着眼的是进入审美关系的生命活动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是否可能,在于能否回归自由、澄明、本真状态; 艺术的内涵是否丰厚,在于能否达到超越状态,这种超越状态是是空间的、循环的、往复的; 它决定了艺术的生命力不在于与时俱进,而在于不断回归。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极力推崇李后主,是因为他将个人的亡国之痛、身世之感与人类共通的情感在审美境界中融化为深挚的生命体验,并将词的“境界”加以诗意升华,其人其作之于历史便有了超常的意味。
对于纠缠在“可信”与“可爱”中的王国维来说,心与物/意识与存在、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垠的隔阂是人生无法超越的矛盾,他试图摆脱“忧与生来讵有端”而走向回归精神家园的路途: 其中也经历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式迷惘,体验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焦灼,最终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和恬然中适得其所; 人终于豁然大悟: 只有真谛之光的烛照才能使人摆脱异化现实的束缚进入自由的理想境界———澄明之境。于是,艺术生命化或生命艺术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或诗就在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象征背后隐伏着永恒的意义———这不仅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也是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
三
毋庸赘言,当王国维追询“第一义”的过程中,往往将自己悬置于高处不胜寒———“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地,此种感悟与体验无形中增加了其生命践履的悲剧性,这或许就是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歌德写《浮士德》呈现出的“天才之痛苦”。“王国维是以‘天才’来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天才往往因鹤立鸡群而孤独,……文艺是天才痛苦的反映与解脱”。①究其实质,王国维的“天才”观不啻为一种现代生命自由意识,彰显出非功利的艺术至上倾向。“王国维所说的天才,不是在生存竞争中具有超常博弈能力的人,而是能够关注人心活动的人。出于竞争的欲望,人们的知识变成了力量; 但因为心的关注,天才把知识升华为生命的观照。”②由于将生命存在从以往赖以凭藉的“理性”或“天理”中剥离出来,归属于诸如? “欲望”的生存层面,灵魂的焦虑乃至痛苦便会随之而至。“‘天才’的灵魂痛苦只能在‘游戏’中得以解脱。倘若‘天才’是指维系于人与意义维度的生命的内涵,‘游戏’就是指的维系于人与意义维度的生命的特征。”③游戏的根本意味也就在于人的生命的纯粹审美体验,故王国维断言“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有余,於是发而为游戏的。……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④正如着名的荷兰学者胡伊青加在《人: 游戏者》中所说,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兴起而展开的。从存在论意义而言,游戏是生存实践的最本真样态,是本真的人以最轻松的态度做的最严肃的事情; 它源于审美并能创造与超越,因而关涉对人的生命自由本质的理解。“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 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①游戏因而表现为生存论意义层面的“游戏说”。由游戏论发展起来的审美游戏论实质上关涉审美创造或艺术创造的生命本质特征。
比如在席勒那里,他将生命主体性与生命和谐性统一起来,将审美目的论与存在本体论统一起来,认为审美与游戏是相通的,正是在审美中才能摆脱任何外在的目的,而以自身为目的,心灵各种内力达到和谐因而是自由的。于是,审美游戏论被提升到存在本体论与价值论的高度。换言之,游戏作为人与世界深层交往的精神实践活动,人只有在游戏冲动中才能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制,在无限创造和精神超越中达成对存在本真的敞亮和对生命自由本质的理解———“此在”的澄明,这种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它颇似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本然状态———“此在”的澄明。
对于游戏海德格尔也有精辟的言说。1958 年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质》一文中指出:
“时间―游戏―空间的同一东西( das selhige) 在到时和设置空间之际为四个世界地带相互面对开辟道路,这四个世界地带就是天、地、神、人―世界游戏( weltspieal) ”,海德格尔在多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谈到“四方游戏说”,使其成为其后期哲学与美学理论的一大亮点。② 而“游戏”在西方美学中历来有“无所束缚,交互融合,自由自在”的内涵,在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境界中,万物浑然一体并处于生机勃勃的涌动和不停息的运化之中; 没有僵化的体系也无现成化的方法,海德格尔将这种新境界谓之“Ereignis”( 大道) 。③ 只有在这种本真存在状态中人才能走向真正的澄明之境。当作为其中的人或“此在”乐此不疲地嬉游于“栖居”之境时,恰似庄子的“逍遥游”。
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存在或世界的本性就是游戏。海德格尔之所以赞叹并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地栖居”,是因为“诗意地栖居”是一个自我人性显现、自我人生敞开、自我人生领悟、自我实现的生命体验过程。相应于这种新境界,海德格尔提出以非概念性的“思”来征服形而上学,克服存在的被遗忘状态( 这两个方面在海德格尔看来本身就是一致的) 并作为哲学终结以后人们体认世界的方式。“思”与“大道”是共属一体的,大道之显现自身为“诗”,领会这大道之显现就是“思”,而诗、思、道圆融一体的终极境域就返归到天地神人之四方游戏境界,这也是人类的“诗意地栖居”或“审美性的存在”。④ 而在王国维那里,“这一立基于‘势力之欲’的‘游戏’理念则使王国维关于艺术与美的创作超越任何社会政治道德的功利目的而具有了存在本体的内涵”。⑤总之,当王国维从游戏的视角切入生命与艺术,其艺术理念高扬宇宙的生命精神,其文化理想也浸染着浓郁的生命情调。连王国维的“自沉”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亦印证了其游戏说: “文学、美术不过成人精神的游戏”,或许可以说,王国维的“游戏”说给人启示的是: 只有当文学( 艺术) 在充分意义上是文学( 艺术) 的时候,它才游戏; 只有当作家游戏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创造者。①综上所述,在对“第一义”的追询中王国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对于生命信仰之维的建构历程,或者说,他以艺术生命化方式完成了生命哲学的逻辑思路。而艺术生命化属于一种观照世界和体认人生的方式———在艺术审美维度赋予生命存在以超越性意义。皆因,艺术和审美无非是个体生存的对应之物,个体生命活动只有通过艺术和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艺术和审美活动只有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乃至王国维最终的“自沉”亦可作如下观: 社会发展也好,历史进化也罢,文化尤其是艺术和审美却具有天然的恒常性。当王国维凝聚了 20 世纪初唯他独具的文化风范和艺术精神后,其生命所拥有的恒常性消解了生命本身所置的历史时间性———王国维恰好是艺术永恒和生命存在的象征。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将死亡作为先行自身的生命存在的必然取向时,王国维的“向死而在”无异于将修炼和升华后的生命定格为文化的审美维度和存在的本真状态。“正如在历史面前王国维是清醒的一样,在死亡面前王国维是智慧的。……生命由此抵达了相当审美的涅般,而且因为涅盘的审美性质,……生命的审美又会变成观念的演绎。由于如此深入的生命体验,王国维走向昆明湖的脚步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沉重那么凄掺,而具有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平静和愉快。”②在此意义上,王氏的“自沉”不是所谓“文化遗民”的“遗世”,而是“醒世”———一种对“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的生命感慨。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