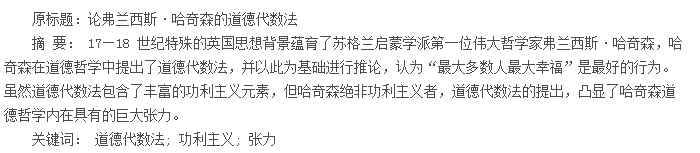
英国着名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 1748—1832) 在《政府片论》中说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1],从此之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为功利主义思想的口号,广为流传。事实上,对边沁的研究显示,普利斯特列( 1733—1804) 和贝卡里亚( 1738—1794) 这两位对边沁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都曾读过哈奇森( 1694—1746) 的作品并公开表示深受其影响,哈奇森研究专家英国学者斯哥特据此指出,在边沁的道德哲学中,“通过普利斯特列和贝卡里亚,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公式可以追溯到哈奇森”[2]273。事实上,惟有通过哈奇森,英语世界才第一次知晓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不过,哈奇森提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理论方法不是推理,而是计算。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道德代数法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方法,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于由它所产生的结论,而不怎么在意这个方法本身。事实上,道德代数法在哈奇森道德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值得认真探究。什么理论背景推动哈奇森提出道德代数法? 道德代数法的内容是什么? 如何评价哈奇森的道德代数法? 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本文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以期对道德代数法的理论背景、理论内容和理论地位进行系统阐释与评价。
一
哈奇森之所以独创出道德代数法,固然与个人天赋有关,然而更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哈奇森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既“现代”又“古典”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社会变革的时代,更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这个时代之所以属于“现代”,因为这是一个经验主义哲学的时代,也是一个现代自然科学方兴未艾的时代,更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现代性直接为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奠定了诸多基本规则与秩序。
这个时代之所以属于“古典”,因为古典主义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复兴,为了和古希腊时代的古典主义相区分,这种在新时代复兴的古典主义被称为“新古典主义”。道德代数法是新古典主义与现代精神高度融合的产物,哈奇森时代的“古典”与“现代”是道德代数法得以诞生的重要精神背景。哈奇森全部道德哲学非常忠实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部精神面貌,时代造就了哈奇森,使之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第一位伟大哲学家[2]2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3]。
随着 1688 年“光荣革命”的到来,英国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大幕,也让新古典主义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美丽画卷。新古典主义开始于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终于 1798 年华滋华斯和科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哈奇森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时代。这个时期的人们普遍对古代着作抱有极大的兴趣,古代斯多葛派的思想在 18 世纪的英国广泛流行,塞涅卡( Seneca) 、爱比克泰德( Epictetus)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的着作在整个 18 世纪一版再版[4]317。追随莎夫兹博里,哈奇森对古代着作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复兴斯多葛学派的诸多思想观点,然而,对他而言,复兴古代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是为了当代,为了对时代面临的伦理困境或道德难题找到解决之道。在这个时代,人性被视为纯粹的自私,“自爱”是惟一的伦理原则,霍布斯、曼德维尔等人都极力拥护这种思想。然而,如同莎夫兹博里,哈奇森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回到过去”[2]155,即回到古希腊,尤其是回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为此,哈奇森曾耗费了大量时间来翻译马可·奥勒留的作品。
在新古典主义的时代背景中,通过研读古希腊斯多葛派思想家们如西塞罗、塞涅卡、艾比克泰德、奥勒留的思想,哈奇森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观,而且从中“复制”[2]275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这个口号。斯多葛主义给哈奇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宇宙观: 组成整体的每个部分都在适当的位置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能,它们有机并自然而然地服务于整体善,若单独看每个部分所做的一切,它所体现的就是整体和部分的完美统一,在任何既定的宇宙结构中,这种完美分工所展现的是由平衡、秩序与和谐而生的宁静与富足。哈奇森发现,基于斯多葛式的整体视野,反驳时代流行的自爱说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不仅如此,对斯多葛学派的深入研究还使得哈奇森得以从中“复制”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这个说法最早可以上溯到斯多葛派的“世界公民”( Citizenship of the World) 一说,通过对西塞罗、塞内加、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等人思想的综合发展,哈奇森使它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世界。在哈奇森频繁引用并一再赞美的《论义务》一书中,许多地方已经暗含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说法。总之,正是基于晚期斯多葛学派诸多观点,哈奇森创立了道德代数法,“人们都知道,哈奇森喜爱道德代数学,只要注意到哈奇森的学说复制了晚期斯多葛主义的某些观点,就很容易理解他会很自然地通往功利主义的公式。”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通过复制晚期斯多葛主义的思想就会自然而然通往功利主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考虑哈奇森所处时代的另一面,即 17—18 世纪英国的“现代”特征。
哈奇森生活的时代,其现代性精神气质主要体现为经验主义哲学的盛行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经验主义对哈奇森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把哈奇森讨论道德哲学的视野限定在经验领域,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直接给哈奇森提供了由洛克所开创的“感官”理论。经由对洛克的“感官”的继承和改造,哈奇森把“感官”的理解从 5 种外在感官扩展至多种内在感官,并创造出荣誉感官、美的感官、公共感官等词汇。但是,基于经验主义的限制,哈奇森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从直觉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内在感官术语,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内在感官具有“直觉主义的名称以及非直觉主义的运用”[2]271这个特点。自 17 世纪 50 年代开始,牛津成为了英国和欧洲的科学中心,英国洛克曾为居住在此的着名科学家波义耳担任过助手,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为人文科学提供了方法论榜样。“从尼古拉斯 · 哥白尼 ( 1473—1543) 到艾萨克 · 牛顿( 1642—1727)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中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本质的解释和我们获得关于它的知识的方式。这些变革对于哲学具有空前的意义。”[4]50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用几条原理和公式就把各种物理现象统一起来,并计算出任意物体的运动状态。鉴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部分人文科学家也极度崇拜数学,笛卡尔、霍布斯、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乃至早年的康德等都在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数学,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在数学领域内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数学家。卡西尔指出,“在近代的开端,知识的理想只是数学与数理自然科学,除了几何学、数学分析、力学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能当得上‘严格的科学’之称。因此,对于哲学来说,文化世界如果是可理解的、有自明性的话,似乎就必须以清晰的数学公式来表达”[5]。胡塞尔认为 17 世纪的西方哲学“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 哲学把精密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6]。洛克曾断言,伦理学完全可以像数学那样推理演绎。莎夫兹博里也相信,如同自然科学可以进行定量研究一样,道德也是可以计算的。在这个崇拜科学和数学的时代,哈奇森的哲学思考也浸润了自然科学的光芒,他的哲学着作打上了浓厚的数学烙印,他尝试用数学分析和公式运算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在《对美、秩序等的研究》中,哈奇森“用数学方式”[7]15表达了自己用观察和归纳的方法所发现的美的根源。在《对我们的德性或道德善的观念根源的研究》中,他更是清清楚楚地引入数学计算法,通过一系列公式对我们的道德程度进行精细的计算,并由此得出了有关道德程度之计算的一系列“公理”[7]131,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道德代数学”。
二
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 哈奇森道德哲学表明,受道德感官( Moral Sense) 认可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在历史上,道德感官由莎夫兹博里第一次在《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提出,不过他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论证。通过继承与批判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思想,哈奇森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证,并据此而衍生出很多类似的其他各种内在感官,如公共感官、荣誉感官、美的感官等。美的感官的功能在于进行美与丑的区分。道德感官的功能在于进行道德判断。哈奇森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美的感官进行美丑区分的根据或基础是什么? 道德感官进行道德判断的根据或基础是什么? 通过研究,哈奇森不仅找到了美的基础,也找到了道德的基础。仁爱不仅是道德感官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也是全部道德乃至宗教的基础,总之,“爱的一般原则是一切明显的美德的基础”[7]119。据此,衡量一个行为道德程度的大小,事实上就是衡量仁爱的量,该量越大,道德程度就越高。因此,在哈奇森看来,可以借助一些数学公理“找到一条普遍准则来计算我们自己或他人所做的全部行为的道德程度及其全部因素”[7]131。在计算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共有 5个,即公共善的量 M( Moment of Good) 、私人善的量或利益 I( Interest) 、仁爱 B( Benevolence) 、自爱 S( Self-love) 以及道德主体的能力 A( Ability) 。能力( A) 既可以产生仁爱与公共善,也可以产生自爱与私人善,同时,它既可以引起道德善,也可以导致道德恶,因此,在涉及道德善与道德恶的全部计算公式中,能力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仁爱( B) 所指向的目标是他人或由众多他人组成的公共善,因此,公共善的总量和道德总量可以视为是一回事。公共善或道德总量( M) 是哈奇森道德哲学中道德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他从经验主义哲学视角继承了古希腊斯多葛哲学的整体主义世界观,经验世界是哈奇森讨论公共善或道德总量( M) 的基本边界。在判断道德行为的道德程度时,哈奇森虽然较为关注公共善或道德总量( M) ,但他从未单纯根据这个量来评判行为的道德程度,相反,他强调说道德动机才是道德与否的标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奇森虽然重视从动机出发研究道德判断,但寓于经验主义理论边界的制约,哈奇森从来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动机论者,它所谈论的动机是受公共善的量( M) 或私人善的量( I) 制约的动机。如果道德主体给道德受体带来的恶大于善,这时候,不管道德主体如何证明自己拥有仁爱或高尚的行为意向,这种仁爱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建立在对公共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能否进行正确的判断,构成了道德主体道德能力( A) 的一部分,因为错误的判断使我们看见仁爱的意图或动机被恶意地运用而不加以阻止,不仅是能力有缺陷的表现,而且会直接把该行为变为恶的行为。哈奇森非常有信心地说,一个在公正意义上考虑整体的人,仁爱很强烈,就不会陷入这样的行为,更不会对他人推荐这种行为。同样,倘若道德主体基于公共善而放弃了私人善,甚至使自己遭受了私人恶,从而失去了推进公共善的能力,这种行为尽管出自高尚的行为意向和行为动机,但它“可以真正为恶”[7]126。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哈奇森在道德哲学中列出了与道德计算有关的 6 个公理,通过对公理进行推演,哈奇森列出了可以用于计算行为之道德程度的两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是 B =MA。由于公共善或道德总量处于仁爱或能力的复合比率( M = B × A) 中,在测量行为的道德程度即仁爱( B) 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是道德总量( M) 以及道德主体的道德能力( A) ,因此,B =MA就是用来揭示计算行为之道德程度的第一种方法。如果把这个公式量化,可以得出结论: 一个行为的道德程度和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量( M) 成正比,和主体的能力( A) 成反比。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可以轻易完成道德行为,那么这个行为道德程度不高。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弱,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道德行为,那么,该行为所包含的艰难困苦、忍耐、毅力等正是高尚品格的集中体现。由于仁爱( B) 同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量( M) 成正比,那么,当能力( A) 相等的时候,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量( M) 越大,行为中的仁爱( B) 就越大。对于由相同的能力引起的同一个行为而言,享受善的总量的人数越多,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量( M) 就越多,因此,该行为体现的道德程度即仁爱( B) 就越高,而仁爱( B) 越高,就说明该行为越好。据此,哈奇森得出结论,“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那种行为是最好的行为”[7]127。
在列出了第一个道德代数公式后,哈奇森还考虑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自爱( S) 以及由自爱所导致的私人善或利益( I) ,并由此而创造了道德代数法中的第二个公式,即,B =M ± IA。对于自爱所引起的私人善或利益,如同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量处于仁爱和能力的复合比率中,它也处于自爱和能力的复合比率中,因此,I = S × A。在道德领域内如何处理公共善( M) 和私人善或利益( I) 之间的关系,既是哈奇森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哈奇森个人学术思考面临的理论难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构成了哈奇森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和哈奇森同时代的曼德维尔曾在《蜜蜂寓言》中宣称,支配人类一切行为的情感动机单单只有自爱,道德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一种东西,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道德只不过是政治家利用自爱来愚弄大众的巧计罢了。哈奇森创作道德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反驳曼德维尔这种观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反驳曼德维尔的过程中,哈奇森并未笼统地反对一切形式的自爱,他所要反对的是曼德维尔把出自自爱的巧计确立为道德基础的做法,他要为道德找到不同于自爱的情感基础,因此,他道德哲学的目标在于证明,道德真实地存在于人类生活中,道德的基础是仁爱而非以自爱为基础的花言巧语。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就要做一个仁爱的人,但这并非意味着,需要彻底放弃自爱。
在他看来,自爱是有边界的,其边界就是“公共善”。
在边界之内,若自爱与整体善一致,虽然人的行为是为了私人善,但是由于有益于整体善,因此这种行为是尊荣和高尚的行为,这种时候,倘若缺乏这种自爱,不仅谈不上道德,相反是一种恶。对处于这个边界之内的行为,若要计算其道德程度,涉及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道德主体追求的公共善有利于实现或增加自己的私人善或利益的情形,在考察道德善的总量时,必须加上自爱的因素,即 M = ( B + S)× A。这个公式可以作下述推理: M = ( B + S) × A→M = BA + SA → BA = M - SA → BA = M - I → B =M - IA。第二种情形是道德主体追求的公共善不利于或有损于自己的私人善或利益的情形,在考察道德善的总量时,必须减去自爱的因素,即 M = ( B -S) × A。这个公式也可以作下述推理: M = ( B - S)× A→M = BA - SA→M = BA - I→B =M + IA。上述两种情形中的道德代数法可以合并成一个公式: B=M ± IA。这个公式清晰地表明了两层含义: 其一,在衡量行为的道德程度时,自爱虽然不是道德的基础,但拥有自爱的人,绝非不道德的人; 其二,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最重要的不是完全消除自爱而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需要处理好自爱( 私人善) 与仁爱( 公共善) 的关系,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既可以为了公共善而放弃私人善,也可以不这样做,若对比 B =M + IA与 B =M - IA这两个公式,可以发现,在哈奇森道德哲学看来,虽然在同等能力条件下放弃私人善的行为中所包含的德性要多于后者,前者因此比后者更高尚,但这只是量的区分,不是质的差异。
B =MA以及 B =M ± IA这两个公式是哈奇森为我们指明的计算行为道德程度的方法。立足人性,通过对这两个公式进行分析,哈奇森注意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在 M 永远不会等同于 A,即使尽了最大努力,道德主体的有限能力决定了该道德主体不可能使所有人获得最大幸福,也就是说,B 永远小于 1。哈奇森说,只有神能做到 M =A,对人而言,M = A 或 B = 1 永远是一个理想与目标,他借用斯多葛学派的观点说,“被假定为无罪的存在物,通过尽其最大能力追求德性,可以在德性上与诸神等同”[7]134。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有限的存在物,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的道德感官会作为最圆满的高尚行为推荐给我们选择的是: 这种行为显现为对我们的影响所能企及的所有理性主体之最大以及最广泛的幸福拥有最普遍而无限制的趋向”。
三
不可否认,哈奇森道德代数法包含着丰富的功利主义元素,但是,哈奇森绝不能据此被视为功利主义者。在功利主义者眼中,任何行为,若不能给人带来功利,就不是道德的行为。哈奇森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说,“道德的观念不会出自利益”[7]88,“我们对道德行为的知觉必定不同于对利益的那些知觉”[7]86。德性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中的某种规定,这种规定可以“先于源于利益的全部理性”[7]112。
不仅如此,哈奇森还发现,我们基于道德对他人产生的喜爱,有时候甚至会超越利益。例如,假如我们的邻国深受暴君压迫,我们的市长带领市民同暴君进行反抗,最终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使这个国家在财富上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尽管邻国的财富超过了我们,但我们仍然会带着极大的敬佩之心对我们的市长报以浓厚的好感,这种好感就体现了对利益的超越。这其中的原因,哈奇森解释为,道德判断的标准绝非外在的功利,而是内在于人自身的道德感官。作为一种感官,在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道德感官具有和任何其他感官一样的特性———直接令人感到快乐或痛苦,即,无需了解得以发生的原因,感官知觉就会直接令人感到快乐或痛苦。“我们很多敏锐的知觉都直接地令人愉悦,也有很多直接地令人痛苦,而不需要对这种快乐或痛苦产生的原因有任何了解,也不需要了解对象是如何引起苦乐的,或者说了解与它有关的诱因,也不需要明白,这些对象的使用可能导致什么样的进一步的利益或危害。”[7]5由道德感官而来的感官判断所具有的即时性和直接性使人在未能了解道德行为的利益得失的时候就可以产生道德快乐或痛苦,并根据这种苦乐感进行道德判断,哈奇森据此反复强调,道德与利益没有关联。
虽然哈奇森的道德哲学文本充分显示,哈奇森不是功利主义者,但在思想史上,人们却往往倾向于把哈奇森同功利主义联系起来,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家从哈奇森汲取了大量的养分,而且更在于哈奇森道德哲学内部所呈现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可以描述为道德代数法的功利气质与哈奇森道德哲学的非功利出发点之间的不一致,即道德情感的功利计算法和道德的超功利性特征之间的矛盾。历史显示,这个矛盾对哈奇森道德哲学产生了巨大损害,使这种哲学体系丧失了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并为此在思想史上被广为诟病,并使哈奇森远离了一流哲学家的地位。
哈奇森对道德的研究始于美学研究,通过研究美的根源,他发现,人们在审美过程中,经由美的感官( Sense of Beauty) 这一内在感官,我们可以知觉到一种超越一切功利后果的内在快乐。由于和人的情感有关,人的道德行为是所有美的事物中最美的事物,由道德之美所产生的美是最高的美。作为美中之最,它当然也具有一切美的事物共同具有的美学特征———会令人产生超功利的审美快乐。哈奇森之所以研究道德问题,除了反驳曼德维尔从而为莎夫兹博里辩护这个目的之外,直接的理论动机就是他希望探索道德之美的根源。在探索过程中,哈奇森发现,令道德感官产生道德快乐的行为就是可以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我们的道德感官推荐给我们的“最好的行为”,因为这是道德代数法展示的结论。道德代数法中所涉及的多种计算因素,均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其中丝毫不包含哈奇森在理论建构之初所提出的非功利美学特征,不仅如此,它甚至严重背离了道德行为的非功利美学特征。事实上,哈奇森最终接受了道德代数法的结论并把它视为道德感官进行道德程度判断的准绳,这充分说明,哈奇森深受时代的影响,尤其深受他所处的时代中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康德曾说,“没有什么比哲学家摹仿几何学方法给哲学带来更大的损害”[8]。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前后不连贯之“硬伤”,可以视为哲学家模仿数学方法给哲学带来损害的最好例证。
事实上,人类的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由于具有超功利的美学特征,是不可以计算的,这个看法得到了晚年哈奇森的呼应。晚年的哈奇森在《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的第 3 版以及在稍后再版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中缓和或删除了前面两个版本中出现的数学语言。哈奇森删除的内容不仅包括正文中的数学符号,而且包括道德代数法中的 6 个“公理”,然后用“箴言”代替了“公理”一词,不过,在页边标题中,“公理”一词仍然存在[9]。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说明,随着对道德情感问题研究的深入,哈奇森注意到了道德情感的不可计算性,也隐隐约约发现了休谟后来所说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之间的区分,注意到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法只能分析自然对象,不能分析人的行为或动机,也不能用来进行道德计算或道德评价。推理和计算只属于科学世界、自然世界和事实世界,解决这些世界中的问题就需要用到推理和计算的方法,一个越善于推理和计算的人,就越能把这些世界中的问题处理得比较令人满意。最善于推理和计算的人就最有可能成为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是最有道德的人,因为道德和人的情感有关。晚年的哈奇森在第 3 次的再版中,删除了学说中的数学语言,这表明,他试图把善恶、正义等问题从科学范畴中清理出来,给它们划定独立的领域。不过,尽管哈奇森有过这种努力,但历史已向我们揭示,在哈奇森全部道德哲学中,这种修订只是相当微弱的变化,并且很快淹没于时代的大潮中,未能引起评论家们的足够重视。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种修订不重要,或者说,可以受到忽视。如果我们相信,“真理、事实、真假等认识论的概念不能应用在道德领域; 道德与认识之间、价值与事实之间没有共同之处。伦理学既不同于物理学的经验陈述,也不同于数学的逻辑演绎”[10],如果我们坚信道德哲学具有“前科学性”[11]294特征,如果我们相信以伦理学为内容的道德哲学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11]4,如果我们确信科学为论证所支配,而道德则起于直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哈奇森的这种修订相当重要,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种修订而推测,晚年的哈奇森已经明晰地认识到,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只属于“价值世界”,不属于“事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互有边界的世界,而他的修订也从反面说明,年轻的哈奇森没能对这两个世界划定清晰的界限。
参考文献:
[1]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 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