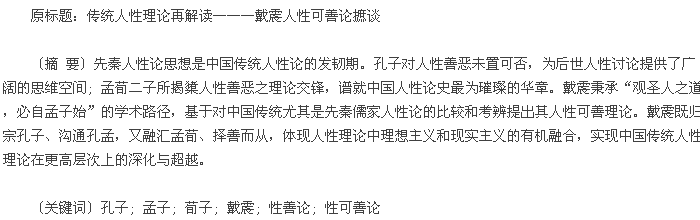
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这个人性论命题后,后人围绕人性论的争辩从未间断。“通观整部《论语》,仅《阳货》篇中有那么一句话: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然而,就是这样一句言‘性’的警句却成了空前绝后的儒家人性论的启示录,几乎所有关于人性善恶的论争皆从这里导源,又向此处回流。”
〔1〕众所周知,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许许多多旨趣不同的人性学说,诸如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子( 硕) 的性有善有恶论和韩非的人性自私论等。秦汉以降,诸如杨雄的性善恶混论,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论,程朱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陆王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所谓“四句教”的人性一元论,都可以在先秦人性理论中找到各自思想源头。在众多人性论说中,孟子的性善论由于较为符合人们的心理愿望和精神需求而突出重围,被视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观点。戴震坚持人性善论,确切地说是一种人性可善论,戴震的人性理论比较鲜明地体现出远绍孔子、融汇孟荀的理论特色。
一、远绍孔子: 戴震人性可善论的理论滥觞
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论语》中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断语,孔子虽未明说人性善恶,但是社会中善恶现象显而易见,不仅有孔子所提倡的“仁人”、“善人”、“君子”和“五美”,更不乏孔子所摒弃的“佞人”、“小人”、“乡愿”与“四恶”。所以,孔子人性论说中已经蕴含了人性是善是恶的多种理论可能。而在戴震看来,由于孔子对于善恶的鲜明态度,孔子的人性理论中又蕴含并肇启着孟子的人性善论思想。他确信孔子和孟子一样都是性善论者,“远绍孔子”成为戴震人性可善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 一) 孔子也是人性善论者
我们来看戴震的一段论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人皆可以为尧、舜”,谓之性善,非尽人生而尧、舜也。自尧舜至于凡民,其等差凡几,则其气禀固不齐,岂得谓非性有不同? 然存乎人者,皆有仁义之心,其趋于善也利,而趋于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然则孟子固专言“人之性善”,且其所谓善者,初非无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 孟子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习至于相远”,孟子所谓“梏之反复”,“违禽兽不远”,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
〔2〕对于孟子的性善论,戴震也是从人们熟知的“气禀”之说,提出并阐释人性为善基础上的等差和不一,既相信人性“无有不善”,不善则违逆人性( “逆性”) ,又承认人性之善只是“等差之善”( 圣凡有别) ,进而指明孔子所谓“相近”正是一种“等差之善”,只有善良之程度差别,而非人性善恶之别。孟子肯定人因先天具有与禽兽“几希”之别的仁义礼智“四端”而人性为善,之所以有人“违禽兽不远”,全在于他“放其心而不知求”之故,这又与孔子所谓“习至于相远”若合符节。
我们知道,孔子只言“性相近”,却并未明言人性是善是恶; 孔子以“习”论“性”,却未具体说明何处相远? 人性到底是大善与小善的等差之善,还是有善有恶的善恶相混。在戴震看来,孔子的人性论就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性善论倾向,我们再来看一段戴震自设问答:
问: 孟子之时,因告子诸人纷纷各立异说,故以性善断之; 孔子但言相近,意在于警人慎习,非因论性而发,故不必直断曰善欤?
曰: 然。圣贤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语,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无人性”,稍举其善端,则曰“此犹有人性”。以人性为善称,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协于孟子,而言性转穿凿失之。无人性即所谓人见其禽兽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论语》言相近,正见“无有不善”; 若不善,与善相反,其远已相绝,何近之有! 分明性与习,正见习然后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归性。凡得养失养及陷溺梏亡,咸属于习。
〔3〕鉴于“性相近,习相远”的诠释,戴震指出孔子也是性善论者。事实上,孔子关于人性的论述并不仅局限于《论语》中的寥寥数语,据《孔子家语》记载,已出现不少讨论人性的文字。随着《孔子家语》被证实不伪,〔4〕有必要将之纳入孔子人性论说考察的资料之中。择要如下:
公曰: “何谓圣人?”孔子曰: “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 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5〕鲁哀公问于孔子曰: “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 “分于道,谓之命; 形于一,谓之性; 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 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 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
〔6〕第一段文字中,“情性”并用,这在《论语》中不曾出现,但《诗经》已有“吟咏性情”诗句,《周易·乾卦》中也有“‘利贞’者、性情也”的说法,而孔子非常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似乎可为孔子说出“性情”二字、讨论“情性”等人性问题提供可能与佐证。
第二段文字,与《大戴礼记·本命第八十》文字应为语出同源: “分于道,谓之命; 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 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终也。则必有终矣。”〔7〕据杨朝明考证,曾被视为曹魏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其实是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所整理,并且认为: 王肃“为《家语》作注,是《孔子家语》正式研究的开端,王注也就成为《家语》的第一个注本,他为今本( 孔安国本) 《家语》的流行作出了特殊贡献。”〔8〕相比而言,《孔子家语》中“故命者,性之始也; 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一句,要比《大戴礼记》更为符合语言逻辑,也更加严密。虽然《大戴礼记》要晚出于孔安国《孔子家语》,但由于散佚而成为残编,所以不及《孔子家语》完整。清代考据家王念孙主张应依据《孔子家语》增补《大戴礼记》方可使得文义畅通是有道理的。戴震所校注的《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为清代《大戴礼》研究奠定了基础。戴震屡屡称引《大戴礼记》中“分于道,谓之命; 形于一,谓之性”的经典命题,凸显了其人性思想远绍孔子、以道( 命) 论性的理论特质。假设《大戴礼记》与《孔子家语》这两段文字果真出自孔子之口,由于显比《论语》人性论丰富必然大大深化孔子的人性理论。
孔子是否是个性善论者,现代新儒家学者徐复观也持肯定态度,他说:仅从血气心知之处论性,便有狂狷等之分,不能说“性相近”; 只有从血气心知之性的不同形态中,而发现其有共同之善的倾向,例如: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子路》) ,“古之狂也肆,……古之矜也廉,……古之愚也直”( 《阳货》) ,“进取”,“不为”,“肆”,“廉”,“直”,都是在血气之偏中所显出的善,因此,他才能说出“性相近”三个字。性相近的“性”,只能是善,而不能是恶的……。把性与天命连在一起,性自然是善的。
〔9〕徐氏的上述见解颇有见地,虽然指出戴震的“血气心知”有“狂狷之分”,但与戴震所见基本相同。实际上从孔子对于“仁”的关注和论证已经昭示他努力要为人们塑造一个成己成物、仁智双全的仁者理想人格。孔子既然如此推崇“仁”,认定仁内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之内,虽然他并未明说人性即仁,但他对于人性显持一种乐观向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诸如“善人之道”、“道人之善”即是明证。
( 二) 孔子又是人性可善论者
从孔子的“性相近”中,戴震读出“性善论”的内在意蕴,而从孔子“智愚”之辨中又窥知“人性可善论”之真谛。孔子承认人有智愚之别,将之纳入人性讨论,诸如“惟上知与下愚不移”的智愚之辨历来争议不断。以戴震之见,孔子的“性相近”其实就是性善论,而对孔子“惟上知与下愚不移”之说也作出另种解读。他认为“下愚之不移”非“不可移”,犹如孟子要人们“求放心”一样,认为孔子并非否定“下愚”者通向“上知”的通道,前提当然是要“下愚者”通过努力“慎习而贵学”以求不断改变自己,实现“欲仁”与“君子”目标。戴震说:
《论语》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惟上知与下愚不移。”人与物,成性至殊,大共言之者也; 人之性相近,习然后相远,大别言之也。凡同类者举相似也,惟上智与下愚,明暗之生而相远,不因于习。然曰上智,曰下愚,亦从乎不移,是以命之也。“不移”者,非“不可移”也; 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君子慎习而贵学。
〔10〕戴震所以强调人性、物性之别,目的在于突出人性在善良方面之“相近”。
戴震也承认人有智愚之别,尤其“上智”与“下愚”更有先天( “命”) 因素,并非后天习得,当然这远非戴震特意强调; 与孔子认为“上智”与“下愚”不可变动( “不移”) 不同,戴震相信人们可以实现由愚而智。他之所以将“不移”诠释为“非‘不可移’”( 意即“可移”) ,意在强调智愚之间仍然具有可变性,而变化的途径在于“慎习而贵学”,源于个体自身的主动有为和努力选择。这种智愚的可变性也同时体现人性所具有的向善和择善的品质和可能。戴震在此所论“上智”与“下愚”“非‘不可移’”,显然已经超越孔子和前贤的认识。孔子认为“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这与他对于“上智”与“下愚”的定义有关。孙星衍在《问字堂集》中所作“上知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的解释应该比较符合孔子原意,这里所言“生而知之”者就是孔子心目中“圣人”,连孔子都自称是“学而知之者”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论语·述而》) 那么“困而不学”的“下愚”又何谈成为“圣人”呢? 以现代科学观之,人们智愚确有参差之别,另外孔子实际所关注的重点更多是针对“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的大多数者,而这些“大多数”则由于后天学习( “习”) 而轩轾有别( “相远也”) 。再看程朱理学家如何为孔子人性论作辩护? 朱子继承二程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旨在为千差万别的人性表象寻找背后根由。朱子认为,“性相近”,是从气质之性上说,通常所言善恶智愚之相近。这些气质之性虽有美恶之别,但起初相差并不甚远; 导致后来人性相差甚远的原因在于人们后天的“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对于孔子所谓的“不移”,朱子认为,“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这又与程朱所肯定的“无不可移”相矛盾。针对门生的疑问,朱子解释道: “盖习与性成而至于相远,则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虽至恶之人,一日而能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夫岂有终不可移之理! 当从伊川之说,所谓‘虽强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朱子语类》卷四十七) 程朱从理学家的角度借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命题去讨论孔子的人性论与智愚观,虽然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与解释力,但由于他们将其归之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必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因此受到了戴震的指责与批判。戴震跳出程朱“天理”的束缚,认为“苟悔而从善,则非下愚矣; 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以不移定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11〕从上述“智愚之辨”可以看出,孔子的智愚观不在于执着“上智与下愚之不移”,而是要强调“中人”( 介于两者之间) 之“习至于相远”。戴震审观其奥,将智愚纳入善恶,认为“苟悔而从善,则非下愚”,上智下愚之“不移”由于“悔而从善”权变为“无不可移也”,由此彰显孔子人性可善论的思想倾向,当然也成为戴震自身人性可善论的思想渊薮。
二、融汇孟荀: 戴震人性可善论的创生路径
作为人性善论、人性恶论两大代表,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开拓性地位,成为后世人性论研究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归宿。孟荀人性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有机内在地统一于传统儒家人性论,从而为戴震融汇孟荀人性精髓进而形成自己人性可善论提供思想基础和创生路径。
( 一) 孟荀人性论思想之异同
1. 孟荀人性论之“异”
( 1) 人性来源不同: 天人观的分歧决定了孟子、荀子不同的人性观。孟子坚持“天人合一”,他认为: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 在此,人道源于天道,人心皆有善性; 他又从人的先天资质处论性: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孟子·告子上》) 此处“情”字可释为天生资质,体现了孟子所强调的先天人性善论思想。朱子则以“情”论性,认为“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比照朱子所论,戴震指出: “‘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情,犹素也,实也。”〔12〕也就是说,孟子是从人的天生资质( “情”) 论性。与孟子所言相反,荀子主张“天人相分”。“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天论》)荀子将天道与人道分别为二,认为应从“人道”,从人之初“生”处论人性。荀子虽然也以“天”说“性”,“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荀子·性恶》) 不过此处之“天”并非形上之天,意即“实然”之天,与孟子偏重于道德意识的“应然”之天迥异。总之,孟子是从人之先天本性处肯定人性为善,荀子虽然也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但他更为明确地将人性之恶归于后天的“顺是”而为。
( 2) 人性指向不同: 研读《孟子》文本,人们不难看出,孟子不是从实然和当下层面而是从应然和理想角度去看待人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人性先天具有善端,不过要实现真正的良善还需要自身的“存夜气”、“求放心”。所以,孟子人性善论并非指向当下,而是寄诸未来,人性善本质上表现于一种可能性,因而称之为“人性可善论”更为贴切。荀子却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 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恶”不分等差,不论圣凡和君子小人皆是如此。“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 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荀子·性恶》) 不过,荀子也不忘为人性恶设定一个“顺是”的前提,假如人们没有“顺是”,结果则并不一定趋于“恶”。所以,荀子的性恶论也只是一种倾向和可能,因而称之为“人性可能趋恶论”更似恰当。由此可见,两大思想家各自从对立的两个方面陈述不同的人性取向和定位。
( 3) 人性特质不同: 孟子荀子在人性论问题上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质,前者表现为理想主义倾向、而后者更有现实主义关照。孟子尽管不否认自然欲望,但更偏重从人的社会属性去讨论人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1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此处引用孟子的“性命”之辨与其人禽、心性之辨共同构成孟子理想人格论,与后两者强调人类之于禽兽的绝对优越性和现实成就理想人格的普遍平等性相关联,“性命”之辨则表明道德实践主体的相对局限性。而荀子从人的“耳目之欲”去阐发人性。“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 荀子因为看到人之“生而即有”且“顺是”而恶的种种欲望,进而认定人性为恶,以此主张要用“礼义”“师法”去化掉人们身上的动物性和恶性。荀子坚持人性圣凡平等,“圣可积而致”,从而把理论视野从孟子的“即心求性”转向外在的“起礼义,制法度”之“师法之化”。
2. 孟荀人性论之“同”
孟荀人性论不仅有“异”,而且有“同”; 既要深挖其“异”,又需探究其“同”。
( 1) 赓续三王之道: 孟荀都倡导尧、舜、禹三王之道,认为凡人只要努力,同样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认为“尧舜与人同耳”( 《孟子·万章上》) 。荀子在人性论上也是一个平等派,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尧舜还是桀跖在人性起点上均为“恶”。荀子所以要强调“人之性恶”,旨在证明“其善者伪也”和“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结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就其立论之所本而言,是同源; 就其立论的宗旨而论,是异途而归。”〔13〕所以,同赓三王之道就成为孟荀人性论的最后归宿。
( 2) 同认周孔为宗: 孟子不仅盛赞周公“古圣人也”( 《孟子·公孙丑下》) ,而且私淑孔子,以“近圣人之居”为豪: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离娄下》) 荀子虽曾批评诸子,却对孔子盛赞有加,他说: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 《荀子·解蔽》) 孟荀二子正是通过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思想不同阐发而形成各自人性见解,共同成为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重要代表。
( 3) 成圣路径相同: 荀子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与孟子所称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圣路径并无二致。孟子倡性善,荀子主性恶,但是后者也隐含着人( 性) 向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以追求向善作为自己理论目标。他们都将成圣成贤的机会归于人们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两位大师因此而殊途同归。
孟子告诫人们: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荀子同样认为: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荀子·性恶》) 由此可见,荀子并非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还是一个倡导“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的理想主义者。
( 二) 孟荀人性论思想之融汇
1. 孟荀人性论思想的双重特性
孟子的人性论是在与告子人性论争以及经由荀子人性恶论的驳辩中彰显出正反双重特性。荀子的性恶论也因为将批评性善论作为其理论的立足点和突破点,同样具有两面性。就正面意义而言,孟子主张性善论,将人性的先天可能具有的善端推崇与高扬,为形成中华民族好善恶恶、豁达向上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发挥着重要作用。告子以生论性,顺从自然,只能使人与动物为伍,人类独有的价值和道德理想暗淡无光。方东美评论道: “有关性无善无恶说( 中立论) ,或性法自然论,若依近代科学来看不无理由,但若落实到人生哲学则缺点极大,因为我们对于人生,必须从价值方面肯定其意义,而不能将价值漂白了变成中立。”〔14〕以孔孟所开创的君子人格成了中国人追求的道德楷模,锻造了中国人乐善好施、彬彬有礼的民族气质。如果说孔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以用他开创的“仁学”来标识,那么孟子的人性善论和大丈夫追求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重要塑造者。“在儒学发展史上,性善论第一次明确了良心本心是自己成就道德的根据,开通了心学的先河。”〔15〕荀子性恶论将人性与动物性进行比较,既讲到了人与动物的共性,也讲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其认识人与人性的思路和方法达到了历史上未有的高度; 荀子对人能群和分的原因进行探讨,对于社会礼义法度和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对于社会稳定、人性完善的积极肯定都表现出荀子人性理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孟荀二子两大人性论的局限性也同样显然。至于性善论的负面意义,杨泽波将之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容易陷于流弊,二是容易趋于保守。孟子以心善论性善,性善论的根基在于良知和本心,而良知和本心又有难以把握的特点,以致出现了很多问题。发轫于孟子之学的陆王心学尤其阳明后学束书不读,高谈心性,走向狂禅,流弊丛生,以致遭人“儒生误国”之诟病。性善论同时还易于使人趋于保守,而当习俗和外在的礼内化为心中之理进而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时甚至就可能发生后来戴震所批评的“以理杀人”的恶果。
〔16〕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孟子“这种将崇高的道德价值直接融注于人的本性之中、将其断定为人之为人的标志的理路,难以避免地会导致对前者的淡化和遮蔽。其发展到宋明理学那里,导致对人欲的彻底否定并不是完全偶然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脉络和必然性。”〔17〕荀子的人性论在劳思光看来,虽然也有“重理旧说,益以新解,以抗诸子之言”的历史担当,但他未能“内补孔孟之说,外应诸子之攻”,“未能顺孟子之路以扩大重德哲学而言,是为儒学之歧途。”〔18〕原因在于“荀子倡性恶而言师法,盘旋冲突,终堕入权威主义,遂生法家,大悖儒学之义。学者观此处之大脉络,则益可知荀学之为歧途,固无可置疑者。”〔19〕很显然,劳思光是站在孟子的道德主体理论立场,肯定价值意识为自觉心所本有,德性实为价值意识发展之结果,自然对荀子以欲性论人性,忽视人性中“价值自觉”层面表现出不满。总体来看,荀子过分强调了从耳目之欲讨论人性,没有将“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视为人的本性,也没有认识到人之气不同于水火之气,人之生不同于草木之生,人之知不同于禽兽之知,从而得出人性恶论的主张。
2. 戴震人性可善论的理论品质
戴震人性可善论思想不仅归宗孔子,更是融汇孟荀,体现出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理论品质。首先,归宗孔子,推崇“易”论,为戴震人性论提供了思想源头,而对孔子“性相近”和“上智与下愚不移”创造诠释表现出戴震与孔子共同的人性可善论倾向。在人性来源上,戴震以“天道”与“阴阳”论性: “道有天道人道: 天道,阴阳五行是也; 人道,人伦日用是也”〔20〕; 天道与人道并非截然两途,两者由于“性”而发生关联,“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21〕就是此意。戴震又将天道归于阴阳五行,赞同孔子《易》论,主张回归孔子所赞《易》太极、两仪之本指。戴震正是站在孔子“易”论的基础上,反对被宋儒弄得极为玄妙的“无极而太极”之论,将人性从天上拉回到人间。“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22〕这是戴震哲学着作中对于“性”所作的最为明确的定义,此处“性”所包括的人性与物性,虽然由于分得的成分比例有所不同,但它们均由阴阳五行之气所形成的血肉气质和心灵知觉。当然,人之性最为戴震所关注,他借用《易经》所说“完成与体现‘道’者就是‘性’”,认为人类出生以后所做的事情、所具有的能力和所彰显的道德一切均以人性为其基础。至于戴震对于孔子“性相近”和“上智与下愚不移”论的独特解读,前文已述,此处不赘。
其次,融汇孟荀,择善而从,表现出戴震人性可善论兼收并蓄的理论特色。
诚如前言,孟荀人性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为两者有“同”,才有融汇孟荀的可能; 因为两者有“异”,才有择善而从的必要。戴震晚年所以着述《孟子字义疏证》,正是因为“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23〕受益于韩退之“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的启发,戴震潜研孟子着作,肯定与赞赏孟子的性善论。他说: “孟子以闲先圣之道为己任,其要在言性善,使天下后世晓然于人无有不善,斯不为异说所淆惑。”〔24〕再有,戴震主张以“性善”去诠释孔子的“性相近”,反对程朱割裂孔孟、误读孔孟的做法,他设问道: “今以孟子与孔子同,程、朱与荀、扬同,孔、孟皆指气禀气质,而人之气禀气质异于禽兽,心能开通,行之不失,即谓之理义; 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实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然则程、朱之学殆出老、释而入荀、扬,其所谓性,非孔、孟之所谓性,其所谓气质之性,乃荀、扬之所谓性欤?”〔25〕戴震强调认为,孔子与孟子一样同是人性善论者,而程朱所抬出的“如有物焉”的“天理”实际上背离了孔孟“人性”,他们的人性论说实际上“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26〕虽然孟子的人性善论对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人文意识与文化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人们对于它的理性反思和创造诠释也从未停止。戴震特别关注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能不能之与可不可”( 即可能与现实) 的关系问题。那么,戴震如何看待荀子的人性恶之论呢? 他认为:
“荀子见于圣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学而后善,顺其自然则流于恶,故以恶加之; 论似偏,与‘有性不善’合,实兼公都子两引‘或曰’之说。”〔27〕这里,戴震既指出荀子性恶论的思想来源,同时又批评荀子人性恶论之偏颇,致使人性与礼义“阂隔而不通”,认为“荀子知礼义为圣人之教,而不知礼义亦出于性; 知礼义为明于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极则,适所以完其自然也。”〔28〕可见,戴震对于荀子的“尊圣人”、“重学崇礼义”深为契合,赞赏荀子“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者,又知礼义之极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在是,圣人复起,岂能易其言哉! ”〔29〕诚然,孟子与荀子在“尊圣”、“重学”等方面存在着显然的思想交集,戴震对于上述“能不能之与可不可”的关注也正说明如此。针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之论,戴震进一步解释道: “以‘人皆可以为尧、舜’,谓之性善,非尽人生而尧、舜也。自尧舜至于凡民,其等差凡几,则其气禀固不齐,岂得谓非性有不同?”〔30〕戴震虽然认可孟子的“性善论”,但同时也指出此乃一种“等差之善”,这为后天的学习教化提供了前提和必要,人们因此也更易理解孟子所以提出“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以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内在原由。同样,荀子虽然主张“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但对于如何成为圣人则认为“能不能之与可不可”不可等而视之,他说: “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 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31〕荀子虽然坚持“人之性恶”主张,但“其善者伪也”和“涂之人可以为禹”旨在表明,人们只要通过“师法”与“礼义”就可以或可能成为禹这样的圣人。戴震正是通过孟荀这种成圣目标乃至成圣途径之“同”来抉发他们思想中所内在蕴含、也同为其自己所接受的人性可善论思想。总之,孟荀二子人性论之思想交集及其理论得失成为戴震融汇孟荀、创生自己人性可善论思想的重要蓝本。
由此观之,孔子对人性善恶不置可否,为后世人性讨论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孟荀二子的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争锋,谱就中国传统人性论史上最为璀璨的华章。正因为先秦诸子们头脑碰撞,思维接力,共同熔铸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轴心时代”,他们对于人性问题所作出的卓然思考,为后世学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和精神养料。戴震以回归先秦儒学为宗旨,经由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之考辨和镜鉴提出自己的人性理论。戴震的人性可善理论,既归宗孔子、沟通孔孟,又融汇孟荀、择善而从,还有直面程朱、针砭时弊,戴氏以血气心知论性,充分肯定被荀子以至程朱所鄙视的耳目鼻口四肢之欲,矢志不渝“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的圣人之道,谋求人性理论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融合,实现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深化与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