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军事伦理从神伦到人伦的思想变迁
时间:2014-05-07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9041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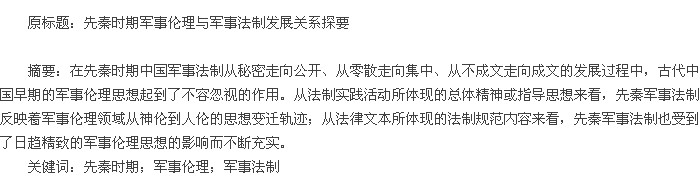
中国军事法律制度自夏、商时期开始产生,前后相延,构成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中国法制发展受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制文明的冲击,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制度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嫂变,但在同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涵仍然被保持下来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内在作用。本文拟从中国先秦时期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演变着手,探寻和发掘指导先秦时期军事法制发展实践的思想基础,冀或有补于中国传统军事法律文化研究的不足,有益于我国军事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一、先秦时期军事伦理思想变迁轨迹
任何战争行为,都将造成敌对双方一定程度的损害结果,如参战人员的伤亡、战争失败的可能性等。具有独立理性思维能力的军人个体对各种损害结果的预测,势必影响到其拥护并投人战争的程度与状态,除非战争策动者能够提供战争在价值上的正当性,即合理性与有根据性,才能有效集结起充足的精神资源与物质资源。战争正当性的价值论证,必须获取来自伦理层面的有力支持,因而,战争行为从其产生之初即与伦理密切联系。在原始淤昧时期,虽然人类低下的思维能力水平并不可能产生相对独立的伦理思想,但现代学者仍然不难发现,其时亦必定存在某种伦理观念客观地约束着战争或被利用为依据以解释战争行为。此后的文明时期,伦理思想之于战争的上述作用更是表现得益发显着。
先秦时期军事伦理思想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夏、商与西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夏、商时期的军事伦理思想脱胎于原始社会的神伦观念,西周时开始发生前述从神伦到人伦的转型,而春秋、战国时期以人为本的军事伦理思想则已基本成型。以下将分别对两个时期军事伦理思想中关于战争的动因与规律观念、道德价值观念、道德理想观念等方面的内容加以描述,试图在对比中展示出一条较为明晰的思想变迁轨迹。
1.夏、商时期军事伦理思想概貌
由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夏、商时期战争行为的性质已然有别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间发生的纯粹为原始宗教信仰(图腾、祖先神、至上神崇拜)或依据宗教信仰而进行的以争夺生存资源和血亲复仇为目的的部族征战行为。然而,统治者在统治中却仍然借用了原始人类关于战争的神伦观念。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对自然界及自身存在的思维理解能力仍然十分低下,神的存在不可或缺;况且,统治者也正好可以利用神伦思想来解释战争,强化对军人意识与行为的控制。夏商时期关于战争的军事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战争的动因与规律观念。在战争的动因方面,体现为“神要战”的观念。《尚书·甘誓》:“……有肩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灭其命……”把战争的动因归结于“天”.《甘誓》可看作是夏商时期战前动员的典型范本,而指出并论证战争的动因是“神要战”,发动战争、投人战争是神的旨意,正是这类战前动员令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在战争的规律方面,体现为“神决定战争胜负”的观念。《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商人凡事莫不通过占卜向神请示。发动战争的可行性和战争结果的胜负无疑是“国之大事”,自然不免更应向神请示、祈祷,以决定行动或指导作战,或降福赐力。通过对这类文本记录的解读,我们可以发掘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胜负由神所决定的观念。
第二,战争的道德价值观念。既然战争的动因源于“神要战”,那么,夏商时期人们对战争行为进行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只能是“神意”,符合神意地以战争“讨有罪”是“善”,不合神意地发动战争或者违背神意地不实施战争的行为均被视为“恶”.因此,当统治者与神意相沟通,得到“神要战”的指示后,参战人员唯一的信仰支撑与行为选择只能是“为神战”,战争背后的利益目的被不同信仰-不同集团所信仰的各不相同的部族神的意志-的冲突所掩盖。
第三,战争的道德理想观念。和平的理想观念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无论统治者对于战争的真实态度如何,表面上都必须把战争打扮成讨伐有罪、不得已而为之之事,如果有排除战争而又能达到利益目的的可能,往往便会放弃战争手段,以“不忍”为标榜。如神农不忍征伐夙沙氏、帝舜不忍征伐有苗氏以及商时周部落的先王古公旦父避敌徙国均是这类事例。
2.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军事伦理思想概貌
西周时期,周人通过战争推翻并取代了商人的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人们立郡遇到一个难题:究竟有没有天命?如果有,拥有天命的商何以败亡,本无天命的周何以致胜?为解决这一难题,周人在伦理思想中引入了“德”的观念,将“以德配天”作为接受天命的条件。依此,历史即可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商的先王有德,故天命归于商;商末统治者“不敬厥德”,故天命归于有德的周。这样,难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是,周人毕竟还是从战争以及统治更替的历史过程中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而且正是在同一历史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伟大,认识到若要长久地保有天命,就必须“敬德保民”退“王者须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隙可乘,心气以获取天下人的支持。这是人们对战争进行考察的视点开始从神转向人自身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引发了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众多的思想家作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言人,更多地关注本阶级、阶层-群体的人一的利益,即便统治者主观上依然更倾向于借助神伦思想以便轻易地实现思想控制、强化统治,但社会的变革以及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对“人”,(群体意义上的人)的意识的唤醒,神伦思想已不再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而仅仅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这一阶段关于战争的以人为本的军事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战争的动因与规律观念。在战争的动因方面,体现为“人要战”的观念。人(作为整体的国家、家族、阶级、阶层)的利益需要被直接认同,战争的动因从神意的掩盖下解脱出来并恢复其本来面目。吕尚的军事伦理思想中就包含了“注重人事,不信天命”的内容,如武王伐封时,“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惟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人的利益需要(如战机)与神意相冲突时,可以不信天,不畏神,置神意于不顾。这在夏商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孔子更是舍弃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对鬼神世界采取了“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在战争规律方面,西周时“德”的观念已经体现了统治者对民心的重视:“德”不过是统治者为收拢民心而在战前、战中和战后运用的手段与遵循的原则。春秋时孔子强调“民信”是立国的首要基石。战国时期兵家诸子的着述无不看重人于战争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明确了治军的指导思想,设计出一系列的治军原则和方法。此时,神意不再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意义。虽然在最初也只是具有形式上或心理上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统治者的德行和作为德行结果的民心向背。
第二,战争的道德价值观念。一旦人们认识到战争因人的利益冲突而起,那么,对战争行为进行的道德价值判断便不再可能依赖于神意。人们开始以“义”、“利”为标准,将战争区分为“诛”与“攻”,即正义战争与侵略战争。而事实上,义与利的区别实质上不过只是长远利益或更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短期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之间的区别。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寻求战争正当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已被归结于“人”,参战人员行为选择与信仰支撵转变而成“为人战”为人间正义或是为小集团利益而进行正义性质或是侵略性质的战争。
第三,战争的道德理想观念。在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成为社会主要活动形式的历史条件下,和平的观念仍然深人人心。如老子认为兵是“不祥之器”,毖子主张“非攻气”管子认为“兵攀者危物也”(《音子·参惠》)。他们均主张战争只有在抵抚侵略或讨伐不义时方可进行。较之夏商时期人们关于战争的理想观念,内容九近雷同,但深究其本质,还是可以发规二者对于战争行为选择与否所考虑的因素存在着到底是“顺神愈”还是,顺民心妇的差异。
3.先秦时期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简评
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行为,总要求特定的伦理形态与之相随而行。人们对于战争的诸多内在伦理要素日趋深刻的认识,决定了与之相关的伦理形态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粗略到精致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先秦时期战争行为相适应的先秦军事伦理患想,在中国古代军事伦理文化发展史上,尽管只能定位为一种早期的、萌芽和生成状态的伦理形态,(祖)然而,其形成与发展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上述历程。不仅如此,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发生的急剧变化,导致了军事伦理思想领域的复杂演进,尤其是实现了从附属子宗教意识的神权天命道德观念到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的蜕变,标示着其对于中国古代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莫基与导向作用已经初现端倪。
先秦时期伦理思想变迁的突出特点,体现为人的初次觉悟,即人们在对重大向题进行思索的时候,毅然地将目光从对虚幻的神的关注转而投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发现了宗法意义上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人,从而为中国古代自秦汉以至明清伦理思想沿着一条“以人为本”的路径向前发展莫定了基石,其意义当不下于清末之际西方民主宪政、“个人本位”的冲击而引发的人的二次觉悟即个体意识的觉醒。此外,如果透过古代中国伦理思想上述粗线条的宏观发展趋势而深切注视其中主观层次的内部变迁及其与其他某些社会现象(比如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将会发现这一过程远比我们的想象复杂得多。这种透视不仅具有伦理文化史学研究上的价值,也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存在作为社会关系和行为之调控手段的法律矛而且;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夫童度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这个规则首先表巍为匀惯,后来便成了法律。”,而恩格斯在《家庭、私肴制和国象的起源》一书中多次提及原始社荟的法律,并认为国象的产生只是促使了“特别的法律”,即维护自己高居于社会之上的特权的法律的产生,可见,“社合没有法律”。
二、先寮时期军事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1.中国军事法律制度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认为,法的产生是杜会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法得以产生的最终根像。这一论断得到了广大法学研究者的认同。但是,传统的法津起源理论中,“原始社会役有法律”的论点,却不能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了更多有利的实证材料,相反地,由于其不符合人类学研究所显示的原始社会实际状况,因而在当代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被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法律人类学将一个杜会是杏存在解决争端的机关、通行的裁决程序以及实施裁决的机关确立为该社会是否存在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中国法制史上的“刑始于兵”,客观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起源的表层特征。关于“兵”(战争)与“刑”(法律)的关系,一般的理解为:第一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大刑用甲兵”,“大者陈之原野”、其二,刑罚种类产生于战争,墨、荆、殡、宫、大辟等各种刑罚构成的刑罚体系,最早就是由童尤部落及其嫡系苗民在部族征战中为了统一号令和奴役战败的异族所创制,后来又广泛地实施于部族内部;其三,最早的法律规范作为军事行动的组织和号令工具而出现,“师出以律”.“刑始于兵”将“私力救济”性质的部族战争错认为“公力救济”的刑罚,在理论上显得牵强,同时其也未能从根本上揭示法律起源的最终根源是隐藏在部族战争背后深层次的物质生活条件或经济原因,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但是,其至少较为准确地描述了战争之于古代中国法律起源的直接意义。正因为战争与古代中国法律起源间具有上述紧密的联系,古代军事法律制度成为了中国法制史上最早的法律制度。
如果说古代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族征战中形成的刑罚体系只是古代军事法律制度的萌芽,那么人类社会进人文明时期后,军事法律制度最早被确立起来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典籍记录了人类文明社会早期的社会情形。
《尚书》收录了攻伐有启氏的战例中夏启所作的《甘誓》:“……有鹰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灭其命。今予维恭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其中不仅具备了完整的规范形式,从规范内容、制定者和执行力的角度来看,也具备了法律规范的特点,而且我们也无法否认其实施中必然存在某种简洁但却不失神圣的裁决程序。在古代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及至文明社会早期,立法习惯的特征是,“描事制刑”,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在这一时期,军事法律制度即使不是唯一的也至少是最为主要的法律制度。当中国法制史发展到成文法时期及至此后的封建社会,由于军事始终是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因而军事法律制度也始终在“诸法合体”的法典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先秦时期军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在中国法制史上、军事法往往和普通法棍杂在一起,没有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从先秦时期并始,服从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各种军事法律制度已具雏形。以下将从军事刑法、军队组织编初和兵役制度以及故争法则等几个方面概括描述这一时期的发展概况。
第一,军事刑法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童尤与苗民创制的五刑可以看作是萌芽状态的军事刑法。奴隶社会初期,临事制刑的习惯,出现了零散的军事刑法法律规范,如《甘哲》、《汤誓》等;《周礼》记载,西周时期适用的刑法被称作《吕刑》,其中就有“军刑”,即军事刑法,主要内容为惩治不听军令、邦谋(间谍)、杀戮俘虏、抢掠百姓等行为,在,“以刑统罪”,的形式下事实上已经构建起比较完替的军事犯罪行为体系;到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刑法在军事法中仍然占较大比重,春秋末期“成文法”开始萌芽,现在,郑“刑书”、晋“刑鼎”、李慢《法经》的内容已无据可考,但从湖北去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所提供的资料来看,战国时魏“奔命律”(即)和继承了《法经扮篇格局的《秦律》之“杂律”(刚〕,都包含了军事刑法的内容。
第二,军事组织编制和兵役树度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战争日益经常化,出现了专门组织和指挥打仗的军事首领,“在军事首领周围集结了一批亲信,这些人勇敢善战,是从事战争的核心力量”侧外。但是,当时毕竟还不可能产生脱离生产的军队和职业军人,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军事组织编制和兵役制度。夏商时期统治者在建立和强化国家机器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奴隶主阶级的军队,并设置六卿掌管军事,构筑起最基本的军事组织编制制度;西周时期王室设置了庞大的常备军队,建立起师、旅、卒、两、伍的编制体制,实行由士族每家一人备征、十家一人轮流服役的“民军制”,奴隶制度下的军队组织编制和兵役制度已经比较完善;春秋战国时期,军队组织编制制度进一步完善,如设立了军权、政权分离的文武分职制度等,春秋时齐国管仲制定了军队组织和行政组织二位一体的军政制度,在兵役制度方面实行士族出兵及在工商者和农民中选兵的制度,在战国时期则开始实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逐渐扩大了服役对象的范围。
第三,战争法规则的发展。战争法是调整国家间战争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物。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战争的经常性,各政治实体之间在战争中产生了对战争行为加以一定限制的需要,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战争习惯规则,这些规则虽然并不等同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战争法,但是,古代战争习惯规则中所包含的某些原则、规则经过发展之后已经获得新生而融人近现代国际法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战争权由神惫赋予,因而没有形成作为主体协议而戒的限制战争权的战争习惯规则,而进人文明社会后,为政者多以仁义、非战为标榜,为避嫌起见,各国不敢贸然蹄结战争条约,故史籍中关于鸽争条约的记载并不多见,但战争事实不可回避,于是逐渐产生了对战争加以限制和规定的规则、习惯,如关于战争的开始和结束,在战争中对敌国军队要做到旗鼓而战、丧乱不伐、处险不薄,对子敌军个人要做到礼遇乱君、禁杀俘虏、埋葬死亡,对于敌国人民要做到不得攻击和杀害平民、不得破坏和烧毁房屋、不准毁坏乐器、手工艺人的等。先秦时期军事法律制度发展简评占先秦时期是中国军事法律制度产生、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调整军事社会关系的军事法律、军事法制从无到有,无疑是一场革命;进人奴隶社会,军事法制逐渐发展;从春秋时期开始,延续到战国时期以及秦朝,军事法律从秘密走向公开,从零散走向集中奋从不成文走向成文,初步形成了封建主义的军事法律系统,这是中国军事法制史上的又一场革命。此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较长的一段时期(自秦汉至清末)之内,中国军事法律制度虽然仍然在不断发展和逐渐完备,并且经历过几次大的变革而日趋精密,但在性质上一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直到清末时期在西方现代法律思想和法制文明冲击下开始的军事法律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先秦时期中国军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两次革命,其在中国军事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这一时期的发展,已经开始初步展示出中国军事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社会政治布经济的发展,随着战争形态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新的军事法制开始生成并逐渐成熟起来,最终取代原有的军事法制”而中国传统军事法制一以贯之的若干特征也从中得到体现。
三、先秦时期军事伦理与军事法制发展关系评说
1.伦理在其初期事实上属于观念而非规范、实践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客卿制的实行为“士”的阶层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促便实践理性成为这一时期军事伦理的基本特征。春秋战国是一个,“天命”观念迅速崩演、实践理性迅速崛起的时代,旧的礼制所维系的价值观的坍塌,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事功”的实践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新的伦理观念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儒、墨、道、兵、法诸子着述中都不乏对军事伦理的有益探素,学术上关于人性的探讨加深了对伦理关系中道德主体的认识,“人必自为”、“审时趋利”的观念已为社会普遍接受。
就兵家而言,则要求“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篇》),一切应本着对国家、对军队高度负贵的态度,根据实际利益的大小进行战略决策,具有明显的实践理性色彩;先秦法家基于“占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王盆》)的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任其力而不任其德”(《商君书》),把实践理性发展到了极致。先秦时期高度发展的实践理性思潮在历史上一方面造就了开放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把专尚刑法、崇尚亭功的三晋法家推上了历史的前台,造成了政治行为中的酷烈作风和思想上反文化主义倾向的泛滥。《荀子·议兵篇》和《吕氏春秋》中的兵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伦理实践的高度总结民对战国实践理苟运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然而这些理论探索成果未被秦国的同志者所采纳,秦政可以看成是先秦法家实践理性恶性发展的结果,先秦实践理性思潮盛极而衰之后,西洋神学思想悄然复起,不为无因。但是,先秦实雄理性思潮对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心理和伦理信念的思想资源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2.先秦时期军事法制思想蕴洒于各个阶级的思想家们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之中。战争行为的特殊性产生了对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军事伦理加以规范化、赋予强制力的需要,因此,成文的军事法制应运而生,这一过程的积极意义是社会其他领域的“以礼人法”所无可比拟的。从军事伦理(蕴涵有早期的军事法制思想)到军事法制的逻辑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事实则凸显为,文明社会尤其是宪政时代以来,军事伦理的某一部分内容逐渐被提升、反映为军事法制,并作为法的精神用以指导国内军事立法和国际战争与人权保护立法,强化军事秩序,规范战争行为。当然,从军事伦理到军事法制的逻辑模式,并不表明军事伦理与军事法制之间具有机械意义上的一致性,甚至即使对于作为提升对象的具有广泛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那一部分伦理思想内容而言,仍须经历统治者的利益分析、观念上的过滤选择以及技术上的修正、调整或补充方能进人军事法制的界隅。但军事伦理与军事法制之间的传承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
3.先秦时期军事伦理思想对于军事法制的发展作用不可忽视。先秦时期军事法制所经历的从秘密走向公开、从零散走向集中,从不成文走向成文的发展过程,固然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战争形态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所决定,但是,同是适应上述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军事伦理思想,对于军事法制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更为直接。从法制实践活动所体现的总体精神或指导思想来看,先秦军事法制从“神本位”(夏商时代)到“家本位”(西周、春秋)再到“国本位”(战国时代)的发展(即),尤其是战争法则中人道主义信念的呈显,无疑反映着军事伦理领域从神伦到人伦的思想变迁轨迹。从法律文本所体现的法制规范内容来看,先秦军事法制也一定受到日趋精致的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不断充实。例如,关于“如何发挥战争中人的重要作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西周时期的军事伦理只能从决策指挥者的角度思考,停留在提出以德行和宣传教育收拢民心的层次上;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则不仅更加充实了以上内容,还能够从其他主体的角度进行思考,将所有主体细分为民、军、敌、夷,再将“军”细分为将帅、士卒,从而形成了更加细致的伦理思想内容,如爱民思想、将士平等思想、将帅选拔思想、军人赏罚思想、人与武器相结合的思想、军人职责观念、对敌的攻少口为上观念、对少数民族的华夷一体观念等,以此为指导,军事行政管理、组织编制、指挥、军人奖惩等制度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进一步充实了军事法律制度体系内容。
4.先秦时期军事伦理思想从神伦到人伦的转型,实质上也是实现了以文化为主导的军事伦理向以经济为主导的军事伦理的转型。人(群体的人)的意识觉醒后,人们认识到战争的动因是人的利益需要,任何战争的后果必然是形成一种体现为一定利益格局的新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秩序,因而,对特定的军事伦理思想的发掘必须置于特定的利益格局之中进行。这种方法对于准确认识军事伦理指导下的军事法制发展的最终动力(经济因素)将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顾智明。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
[3]戈尔丁。法律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6]陈学会几军事法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7]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M].北京菇律出版社,1999.
[8]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孙玉荣。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0]余子明。中国军事法制史的基本规律和特征[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3):58. `.
[11]杨浩。春秋战国时期军事伦理理念的煊变[J].怀化师专学报,2001(1):40.
- 相关内容推荐
- 影响当前军事伦理教育广泛开展因素2014-05-06
- 灾疫伦理学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的积极功能2014-07-07
- 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的学术价值和启示2016-09-09
- 阿昌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观2014-12-22
- 毛泽东军事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原则2014-05-07
- 工程师社会伦理责任的由来、问题及强化途径2015-03-11
- 农村伦理道德失范的原因及解决策略2015-11-23
- 中西方家庭伦理问题及对策结语与参考文献2016-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