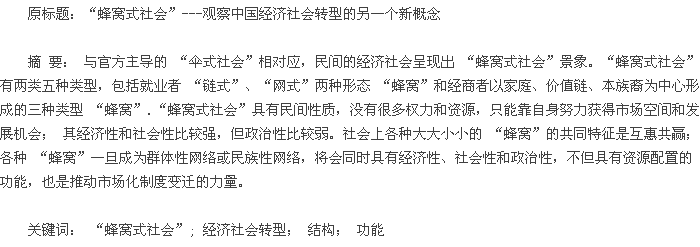
一、研究缘起和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至 2010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经济增速令世人瞩目,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学者试图破解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团,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即如何实施市场转型。
经过多年思考,笔者于 2014 年提出一个解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 特别是市场转型)的新概念--- “伞式社会”.① 此观点提出之后不久,就得到一些同行的欢迎,笔者深受鼓舞,愿意继续深入探讨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特别是市场转型) ,这次献上 “伞式社会”的姊妹篇---关于 “蜂窝式社会”的探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的是: 在中国的巨大市场转型中,普通老百姓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普通老百姓是受益者,还是受损者?
二、研究假设、理论基础与实证材料来源
( 一) 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观察中国这么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特别是市场转型) ,光有 “伞式社会”这么一个概念显然是不够的,基于对立统一学理和学术概念配套的考虑,笔者打算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 特别是市场转型) ,提出至少一对新概念--- “伞式社会”用于观察 “官方”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蜂窝式社会”用于观察 “普通老百姓”自我开展的资源配置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由官方主导的经济社会是一种 “伞式社会”.在中国各地 “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大大小小的各种庇护伞状结构,表现出明显的 “伞式社会”特点。“伞式社会”的结构包括国家级、省级 、地州级 、县级、乡镇级等五个层级,对下属企业是一种“父爱式庇护”、对合资企业是一种 “亲戚式庇护”、对私营企业是一种 “朋友式庇护”等三种功能,简称 “五三·伞式”结构与功能。
平民老百姓的经济社会生活是一种 “蜂窝式社会”.它是指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权力和特权都将会出现转移,即从拥有权力和特权的管理者手中转移到普通的直接生产者手中,平民老百姓的获利机会和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会增加,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会提高,于是,个体工商户、小商小贩、私营老板、蓝领工人、办公室白领人士、职业经理人、自由职业者等不断增多。对这种老百姓参与度较高的市场发展情况,我们将之比喻为 “蜂窝式社会”,即每个平民百姓都像辛勤的蜜蜂那样,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构筑属于自己的蜂窝。
简言之,笔者试图用 “伞式社会”和 “蜂窝式社会”这两个 ( 一对) 新概念,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 “官方”和 “民间”两个不同的重要侧面。本文中,主要探讨普通老百姓自我开展的资源配置和如何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活动的。
( 二) 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
1. 理论基础提出 “伞式社会”和 “蜂窝式社会”这样一对新概念,其理论源泉和学理基础包括卡尔·波兰尼 ( Karl Polanyi) 的 “三种经济类型”理论、① 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理论、② 中根千枝的 “纵式社会” 理论、③ 格兰诺维特 ( MarkGranovetter) 的 “网络分析 ” 理论、④ 倪志伟( Victor Nee) 的 “市场转型”理论、⑤ 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 理论、⑥ 科尔曼 ( James S.Coleman) 的社会资本理论⑦等七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对这些理论进行详细阐述。
2. 基本思路一般认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两只手: 一只是看得见的手--- “政府”.可以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政府官方权力的资源配置功能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只是看不见的手--- “市场”.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市场对资源、要素的配置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李培林提出还有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李培林的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社会结构转型的作用,特别是分析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关系及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上述几种理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 特别是市场转型) 通过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四种: 权力、资源、市场空间、发展机会等。
3. 本文的实证调查及其材料本文使用的实证材料及其田野调查资料,包括笔者最近十几年来的实地调查,如 1995 年在天津的调研,1996 年在海南琼海市和贵州凯里市的调查,2001 年在北京市和深圳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2007~2008 年在青岛市、呼和浩特市、昆明市、深圳市等 4 个城市的调查,2011 ~ 2012 年在海南的调查,2013 年在贵州凯里市和广州市的调查等。
三、“蜂窝式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根据上述几种有关理论,权力、资源、市场空间、发展机会等这四种影响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官方社会 ( “伞式社会”) 和民间社会 ( “蜂窝式社会”) 将分别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笔者认为,代表官方的 “伞式社会”拥有较多的权力和资源; 代表平民百姓的 “蜂窝式社会”虽然没有很多权力和资源,但依据自身努力争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城市里出现了两件大事: 一是城里涌进了大量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二是城里冒出了大量的个体工商经营户和私营企业。
本文中,笔者主要从就业性视角分析流动人口的 “蜂窝式”结构与功能,从经营性角度探讨个体工商经营户和私营企业的 “蜂窝式”结构与功能。从这两个维度剖析中国社会的这两个典型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清楚中国 “蜂窝式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 一) 就业性 “蜂窝”结构及其功能
基于笔者对城市流动人口 10 多年的调查研究,外出务工者自行建构 “蜂窝”的主要原则是互帮互助,其主要表现为 “链式”和 “网式”两种 “蜂窝”形态。①1. 外出就业者为何需要有自己的 “蜂窝”( 社会资本)
一个人离开农村地区,闯进不熟悉的城市里,靠什么才能够混到一口饭吃、有一个安居的小窝呢? 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人应该拥有良好的体力、一定的劳动技能或知识、一定的资金等经济资本,才能在城里安身立命。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外出务工经商除了经济资本之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资本 ( 如社会关系) .②我们 2001 年对 207 位北京市外来打工者的问卷调查显示: 他们能够获到目前工作的途径,比例最高的是依靠亲戚介绍 ( 占 35%) ,其次是依靠朋友介绍 ( 占 25%) ,两者合计 60%.可见,外出打工最主要的途径是利用自己的 “强关系”③ ( 如亲戚、好友) .④由以往研究中曾有的一位深圳保安的案例⑤可见一个人从西部偏僻的农村地区跑到东部地区繁华的城市找工作,光凭一身力气和不怕困难外出闯荡的念头,是完全不够用的,还需要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上述那位来自贵州的侗族小伙子,因为以前多年在外当兵,与老乡联系较少,所以,第一次到深圳打工没有靠得上的亲友和老乡。因此,才体会到 “找工作要有人带,好落脚,好进”.一个人离开家乡刚出来到不熟悉的城市谋生时,特别需要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帮忙。
当他第二次闯深圳时,由于有了老乡和朋友介绍工作和热心帮忙,不像第一次那样,在当地不好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可以预料,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小伙子当过兵、干过保安的工作资历,可以成为他未来就业的重要资本。
一个人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关系资本在城市就职中会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这种关系不但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责任,这种双方相互之间紧密的关系和明显的责任,可以让任何一方发出求助的时候,能够得到另一方的帮助或资源。人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就像银行里的存款一样,随时都可以取出来使用 ( 类似 “人情信用卡”) .⑥2. 外出就业者建构 “蜂窝”的三个发展阶段根据我们 1996 ~ 2013 年在海南、贵州、北京和深圳、广州等多地的观察和调查,外出就业者 “蜂窝”结构及其功能大致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先遣式”个体外出就业。这是人们外出闯荡的第一步或试探性时期。比如,笔者 1996 年在贵州省东南部一带的调查发现,20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地个别不满于现状的年轻人在听说深圳办特区搞改革开放的宣传后,就不管天高地厚,开始独自来到深圳特区闯荡。这些无所畏惧的先遣者,在新的城市里没有可以利用的人际关系,主要靠着自己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和年轻气盛的精力,有不少人从做小工开始,单打独斗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条件下,闯到陌生的城市找饭吃,靠一个人的胆量和力量打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其风险也极大。可以想见,个人先遣式外出就业的结果必然是,成功的个案寥寥无几,值得称道的经验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失败和教训。
第二阶段: “链式”群体外出就业。这时个体先遣式的闯荡阶段已经结束,在前者的不断摸索和积累下,已经建立起了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经过第一批个人先遣式外出就业者的多年开拓和逐渐积累,开拓者的家属、亲戚 ( 有时还包括其朋友、同村人、甚至同乡) ,不但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外出务工或经商成功的信息,而且可以顺着第一批外出者这个可以依赖的强关系,尾随着开路先锋迁移到同一个城市,形成了“链式”群体外出就业。在先遣者个人强关系的牵引或带队下,这些后来者自然地形成了一条外出就业的链条,我们也可称之为 “带队式”群体外出就业。相对第一阶段个人先遣式外出就业而言,第二阶段的 “链式”或 “带队式”群体外出就业,由于有了先遣者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就业经验,跟随开拓者的关系链条外出的后来者,既有现成的社会关系和就业信息可以利用,也有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其风险降低了不少,其成本也大大减少了。
第三阶段: “网络式”群体外出就业。这是在第二阶段 “链式”或 “带队式”群体外出就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外出就业第三阶段,此时社会关系得以进一步扩展并形成网络,具有群体“网络”的支撑。每一个迁到外地的就业者的身后,不但有一连串由家人、亲戚等血脉或姻亲相连的链条,而且还有在这些血缘或姻缘关系基础上扩展出来的人脉关系,如邻居、同学、朋友、同村人、老乡、同事、同行、老板等非血缘、非姻缘关系。这个横向人际网络源于也基于纵向的人脉链条,不仅使先遣者而且使后来者获得更多的人际网络作为在城市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依托。①3. 外出就业者的 “蜂窝” 结构及其功能在市场化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权力、资源、市场空间、发展机会等是影响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四种重要因素,政府及其行政官员拥有较多的权力和经济资源,平民百姓没有掌握什么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如何获得一点市场空间、发展机会呢? 对于一穷二白的外出打工者来说,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利用自己与生俱来或先赋性的资源 ( 如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 以及传统行为规则 ( 如互帮互助的家庭道德伦理) .这些先赋性的资本和传统性的规则,正是城市外来者首先建构起群体性链式 “蜂窝”,接着建立起群体性网络式 “蜂窝”的社会基础和规则基础。
从整个社会来看,民间的 “蜂窝式社会”是如何在官方 “伞式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在政府主导和搭台、资本唱戏的市场转型中,无权无势的外出就业者要想自己搭个的 “蜂窝”,不是一日之间就能够做到的,需要经过一个摸索的过程。在最初的个体“先遣式”外出就业时期,连自己最亲密的亲人好友都指望不上,因为缺乏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其成本和风险都很高。简言之,在第一阶段,外出就业者根本没有构筑 “蜂窝”的条件和可能。
到了第二阶段,先遣者像一只蜂王,带着工蜂般的亲朋好友一起外出就业,这时就有条件自己构筑 “蜂窝”.这种带队式的群体性外出就业,是一个以领队者为主、采用 “链式”关系将同群人连接起来、共同构筑 “蜂窝”的过程,其建构 “蜂窝”依托了一定范围的人际关系基础,即带队人的家人、亲戚等有血缘、姻缘关系的人员。进入第三阶段,由于外出就业的群体性关系网络越织越大,其网络范围已超越了血亲和姻亲的关系,有足够的条件建构起网络式 “蜂窝”.具有群体性 “网络式”的第三阶段,不但结束了第一阶段 “个人先遣式”形单影只的局面,而且逐步超过了第二阶段 “链式”群体性网络局限于血亲和姻亲关系的局面。群体性 “网络式”社会资本,不但拥有先赋性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而且还经过不断开发扩大到了许多非血缘关系、非亲缘关系,如邻居、同学、朋友、同村人、老乡、同事、同行、老板等后天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式 “蜂窝”比链式 “蜂窝”能够结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系,其社会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外出就业者所建构的由小到大的“蜂窝”结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按照 “差序格局”原理逐渐形成的,并且在 “蜂窝”机构内能够聚集和分享越来越多的资源。总之,外出务工者自行建构 “蜂窝”的主要原则是互帮互助,其主要表现为 “链式”和 “网式”两种“蜂窝”形态。民间的 “蜂窝”式社会可以成为官方 “伞式”社会的补充部分而存在,两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为什么外出就业者需要建构这样一种共享式、互助性的 “蜂窝”结构呢? 卡尔·波兰尼在 《伟大的转折》一书中,将人类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 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② 那么,这三种类型的经济生产方式与外出就业者建构 “蜂窝”的三个发展阶段有什么关系呢? 从经济方式或经济制度来看,对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意味着脱离农村互惠式的自然经济制度,进入到城市里陌生的等价交易的市场经济或/和政治性的再分配经济,为了在这套城市里强势的经济方式或经济制度中找到安身立命的空间,外出打工者首先利用的是从家乡带来的、已有的互惠经济方式,接着通过群体性链式和网络式 “蜂窝”等群内制度性的共享方式,逐渐在从再分配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空白地带找到了立足之所,或者嵌入到制度化的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边缘地带。
可以说,在市场转型中,对现有旧制度的突破,始于个体性的突围,接着是群体性 “蜂窝”式不懈的共同努力,这两者都是非制度性的行为,借此最终才能形成了制度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换言之,一方面,新制度的建立,来自个人或群体非正式的努力或试错,即新制度有一个从非正式到正式的制度化变迁过程; 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个体,到群体,到整个社会的过程,即从原生性到制度性的调适过程。
( 二) 经营性 “蜂窝”结构及其功能
经笔者多年的调研与观察发现,经商者的“蜂窝”主要有三种类型: 以家庭为中心的互惠互利网络、以价值链为中心的合作共赢网络和以本族裔为中心的互惠共赢网络。
1. 家庭式 “蜂窝”: 以家庭为中心的互惠互利网络
对家庭,普遍流行的看法为,它是夫妻俩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一起居住和生活的地方。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经济市场化转型是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商业行为,不必依托家庭。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不重视家庭的经济功能。然而,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学者,普遍认为,家庭不仅具备了各种显着的社会功能,而且其经济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古德( William J. Goode) 曾指出: “人们常常忘记现代家庭也是一个经济单位,即使它已不再是一个农作单位”.① 贝克尔 ( Gary S. Becker) 也指出: “在一切社会,包括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家庭仍然对相当大的经济活动---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承担责任。”②
( 1) 家庭商业是城镇市场化的开路先锋。1996 年,笔者在海南省琼海市做调研时了解到: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个体工商户作为最早的一批市场主体,在城镇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 1983 年时,有 2 836 户,3 449 人; 1990 年增至 5 746 户,77007 人。为什么家庭商业会成为城镇市场化进程的开拓者呢? 笔者认为,其政治、经济、社会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镇 “个体户”是一种应运而生的产物。一方面,家庭商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指令性计划不能贯彻到底的经济单位,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最为薄弱的领域,自然地也就成了城镇市场化最早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家庭经济也是现实中最受压抑的经济单位,无论是城市里的私营商业,还是农村的家庭经营,都到了濒临灭绝的程度。③ 私营的家庭商业被压抑得越久,其复活的欲望就越强烈,一旦政府解除禁令,它们就像雨后春笋般快速生长起来。
第二,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很强大,第一批的市场化萌芽和变革发生于而且也只能发生于那些不触动既有的经济利益和制度结构的行业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个人或家庭的自发性努力,个体工商业和私营服务业在城镇中获得了较早、较快的发展。
第三,家庭式私营商业之所以能够复兴,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即国有商业和集体商业因为经营不善、经济效益降低,正在走下坡路。在城镇市场化初期,由于市场开放了,公营商业失去了独家经营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不适应存在着牌价和市价之间价差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因为机构僵化和臃肿、组织和人员成本高,其市场竞争力也逐渐下降了。④第四,家庭商业的社会性基础是 “家庭”式的经营。笔者 1996 年在琼海市看到了很多“夫妻开店”的例子。李培林认为,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而言,家庭不单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组织形式,也是他们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就像工厂或公司是企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一样; 而家庭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是家庭式经营的组织管理规范,就像工厂或公司的科层制组织管理规范是企业的组织管理规范一样。⑤
( 2) 家庭商业与利他性的家庭伦理。经济学一般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社会学、人类学等非经济学科认为,在家庭式商业中,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设是不灵验的。经济学通常将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分开来看,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家庭式经营中,这两者是很难分开的。家庭式经营不仅是追求利润和家业延续的经济行为,而且也是追求爱情亲情和家庭幸福美满的社会行为,对上述这两个方面,身为一家之长的私营业主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
为何家庭商业中存在有明显的 “利他主义”倾向呢? 笔者在海南省琼海市的调研表明: 私营业主们之所以愿意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忙忙碌碌,是为了使家庭的共同生活过得更美好、是为了让子女有更好的未来。这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经营动力。
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观点是由贝克尔在 《家庭经济分析》(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家庭商业主以经营收入为经济来源,对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健康及其他人力资本等进行投资。① 家庭可以超越个人短暂的生命,维持着世代相传。家庭里的每一代人来到这个人世间的起点,都是上一辈人多年奋斗和积累的成果。身为父辈如果不为子女的生长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就会愧对自己肩上的家庭责任,也很难获得下一代人的尊重。至此,我们从社会学意义上,对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利他性的家庭伦理,给出了一个较好的解释。
在家庭商业中,资源配置的原则是 “互惠互利”,而在市场上正像资源配置的原则是 “追求利润”.② 因此,我们看到: 在市场上,不同的家庭商业主作为利益主体,都在对外进行展开竞争,极力追求自身利润,而在家庭内部,户主对家庭内部成员则采取互惠互利的利他主义原则,追求共同的利益。可以认为,利他主义是家庭生活,甚至是群体生活的 “自然法则”之一。
( 3) 家庭商业的交易成本与 “蜂窝”式亲缘网络。③ 笔者近 20 年来在多地的调查显示:愿意给白手起家者援助或支持的,绝大多数是家人或沾亲带故的亲戚 ( 如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亲戚) ,有时是已有长期交情的老同学、老战友、好朋友。
为什么在创业者尚未成为功成名就的企业家,既没有较多财富也没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不太计较得失或过多考虑风险,就无私地给予他各种帮助 ( 如给创业资金) 华裔美籍人类学家许烺光 ( Francis L. K.Hsu) 认为,相互依赖是中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特别是,在亲属关系网络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非常明显。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都十分明确,被赋予的东西要回报 ( 尽管回报的时间也许很迟) 也是十分明确的。④ 与政府、企业不同,家庭商业的资源配置,主要不是依靠政府行政指令、法律规章制度、市场供求关系等,而是依靠血亲和姻亲关系,以及家庭伦理规范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家庭亲属关系、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等非制度化规则,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家庭或家族的商业活动在亲缘网络内,以某个家长或某个德高望重的人为中心,每个人都被固定在由家庭和亲属联结的关系网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形成了一套类似 “蜂窝”式的装置: 一家人可以按着 “有钱大家赚”的规则,使一家之内的所有成员,都有机会共同努力并分享其好处。
在这种大家共生共荣的 “蜂窝”里,人们通过 “一家人”和 “圈内人”共同的隐形关系网,可以在资金、供货、人力、客户等几个方面随时共享信息或相互支持。在经营领域方面,亲戚好友们也会有意无意地从事同一个行业或相关的行业,以便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或互通有无。比如,笔者 1996 年在琼海市访问了服装经营户H.⑤ 他表示只熟悉服装行业,对其他行业不是很熟悉,对今后的营生既不想扩大经营,也不想转行。笔者认为,H 不想破坏现有的稳定发展局面,是因为如果他转行或扩大业务,不但会失去现有的亲缘互助网,而且会一下子找不到可靠有效的支持力量。在家庭商业活动中,亲缘网络内的这种互帮互助、互利互惠,表现出来是一种交换,但其本质却不一定是一对一等价的经济交易,也不是短期的、一次性的买断式交易,而是一种交织着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换的过程,是一种包含着亲情的社会经济交往和长期交换的过程。
当市场化尚不成熟、市场制度尚不健全时,基于亲缘网络的 “蜂窝”型资源配置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家庭商业的发展会相当活跃。家庭商业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网,类似一个基于亲缘网络式的 “蜂窝”,按着一套家庭伦理道德规范行事,家庭内和亲属间既不需要讨价还价,也不需要签订契约,这套人们世代相传的习惯性行为规则和伦理道德,既可以减少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2. 价值链式 “蜂窝”: 以价值链为中心的合作共赢网络==在此笔者以在琼海市对家庭工业①的调查资料为实证材料,分析以价值链为中心的合作共赢网络 ( 即价值链式 “蜂窝”) .清末时期,琼海市的家庭手工作坊、匠铺就遍及城乡,涉及陶器、造纸、皮革、铁器、制糖、造船等 30 多个行业。1952 年,家庭工厂增至 37 家,产值突破百万元大关,达 103. 77 万元。1954 至 1956 年,经过合作化和公私合营改造之后,家庭手工作坊里有 420 名雇员被精简回乡务农。1962 年,各墟镇从集体工业中调整出22 家,作为家庭手工业单独经营,自负盈亏。
1966 ~ 1976 年 ( “文革” 期间) ,家庭工业都被当做 “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家庭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1984 年,全市有家庭工厂 4 440 家,从业人员7 141 人,总产值2 547 万元。② 正当许多国有企业和工厂的经济业绩持续下滑,出现严重亏损,甚至停产之时,私营家庭工厂却在昼夜不分地开动机器生产,力求在市场上割分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小 “蛋糕”.这种由个人及其家庭自发推动的私营家庭工业,怀着没有敌意的 “反抗”心理,③ 悄无声息地冲破了现有僵化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逐渐发展成为小巧精干、富有竞争力的市场新主体之一,④ 不断推动着市场转型和制度变迁。
家庭工厂的主要特征和功能之一是: 将亲缘网络关系交往的那套伦理道德规则,从家庭工厂内部,扩展到它与供应商、批发商、零售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 反之,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对这个家庭工厂,也会采取同样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处事规矩。家庭工厂、供应商、批发商、零售商四方之间,形成了一条价值链,⑤ 并以家庭工厂主为主、以价值链为主线形成合作共赢网络,即家庭工厂、供应商、批发商、零售商等四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建构起来的 “蜂窝”,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链式 “蜂窝”.家庭工厂主就是一个个价值链式 “蜂窝”里的小蜂王。
1996 年,在琼海市,一个受访的家庭工厂主对笔者说:我们的产品在全岛各地都有。我们主要通过各市县商品批发部门经销,也通过其他各种渠道推销。我厂与经销商从来不订合同,全靠讲信用。利他也是利己,利他也是给自己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⑥家庭工业比上文所述的家庭商业将亲缘网络的行为规则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之中。家庭工厂主就像蜂王一样,以价值链为主线,与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逐渐形成了互相信赖的关系网络。对家庭工厂来说,这套逐步建立起来的价值链式 “蜂窝”,作为一个较为稳定可靠的供、产、销网络关系,不但是它进行采购、生产、经营和销售的可靠关系网,而且是它与供应商、批发商、零售商等三方之间高效合作共赢的运行方式。
3. 族裔式 “蜂窝”: 以本民族为基础成员的互惠共赢网络==少数民族从边疆民族聚居地区迁往人口异质性较高的城市,是否都会变成 “碎片化”群体?在四川各城市的调查显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彝族依然带有强烈的家支观念。在彝族内部,同一家支的人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互帮互助、互相支持、互惠互利; 两个家支的成员之间发生矛盾和纠纷时,每个家支都会保护自己家支的成员;在对待外民族上,特别是在与其他民族 ( 如汉族) 发生纠纷时,不论是非曲直,所有成员都要一致对外。①( 1) 从单个企业来看,其经营方式、聘用员工等带有民族性。2001 年,我们在北京对民族特色私营企业调查时发现: 它们主要聘用本民族同胞,因为本族人了解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会讲本民族语言等。比如,在北京的傣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苗族等民族特色餐厅,由一个本民族的服务员给顾客介绍具有本民族特色风味的饮食,更能够使食客感到真实而可信。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些年在北京城区西部有一个腾格里塔拉酒楼,下设有一个 “北京腾格里塔拉艺术团”,共聘用了几十名蒙古族舞蹈和演唱演员。② 近两年,在海淀区魏公村一带开了一家敖包会,以演出鄂尔多斯婚礼为主,也聘用了几十名蒙古族演员。③ 这两个蒙古族餐厅在北京都算是比较有组织、有规模地使用本民族同胞的例子。又比如,在一些朝鲜族经营单位 ( 如韩国烧烤店、韩式美容美发店、韩国食品店等) 里,来了韩国或朝鲜族客人,店内人员如果可以用韩语或朝鲜语与顾客交流,可以增加顾客的亲近感和满意度。对 87 位来京务工经商的朝鲜族的调查显示,他们都在朝鲜族特色私营企业里工作,有 81 位会讲本民族语言---朝鲜语,比例高达93. 10%.
2001 年笔者在北京的调查也发现,总体来说,外来的少数民族对亲友的依赖程度比汉族要相对高一些。对从小生活在边疆农牧区、对城市不熟悉的少数民族来说,离家进城从事非农业工作是一件大事。在陌生的城市中,如果没有任何亲友提供住宿、饮食、或工作等之类的帮助,他们就不会贸然离开家乡前往城市。除非有亲友在要去的城市里,并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他们才敢于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④( 2) 从同一民族整体来看,其经营特色具有民族性。从边疆地区来的少数民族,如果在城市中创业,开办民族特色私营企业是主要的形式之一。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可以依靠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关系网络,独自或与他人共同创业,这不但可以让自身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且给所在城市带来别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创业型企业具有 “民族性特征”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进入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市场营销和企业经营中,因 “民族性特征”而在市场上与众不同,这种 “差异化”正是吸引顾客眼球的重要因素。这些创业型企业的 “民族特色”正好满足了多元化需求市场上的 “空白点”或“缝隙”.
笔者依据 2007~2008 年在中国一些城市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影响不同民族的 “经济文化类型”⑤ 转变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青岛市朝鲜族、呼和浩特市蒙古族、昆明市会泽回族等一些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中的经济文化类型,出现了从 “原生态型”向 “市场型”的转变。其中,青岛市的朝鲜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是 “依附-移植式”的、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是 “创新-移植式”的、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是 “半自创半融入型”的。比如,在内蒙古,一大批蒙古族离开草原牧区,迁移到呼和浩特市区,牧区和市区两者虽然存在着差别,但是,两者都没有脱离蒙古族自己的草原民族文化地盘。这样,在共同的蒙古族民族文化大背景下,蒙古族一旦离开牧场来到城市,开展商业化的饮食服务、民族工艺品商贸等经济活动,推动草原产品的城市化和市场化。一方面,他们正在呼和浩特形成相对集中的经营聚集区; 另一方面,他们自然地就会把牧区和市区联系起来,将牧民的来源地和流入地联系起来。概括来看,蒙古族的移民和民族企业家,在城市中正在创建一种新型的经济文化类型: 一头是草原牧场,另一头是牧区之外的市场(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内的各城市市场,甚至整个中国市场和外部更大的国际市场) .这些蒙古族的民族企业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成为了城市与牧区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工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之间的 “联结体”.它们在经营方式、社会身份、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很明显的民族性。①( 3) 形成族裔式 “蜂窝”的社会性基础。
2001 年,笔者在北京对朝鲜族、蒙古族、藏族、傣族所经营的家庭式小企业 ( 如餐厅、理发店、美容店等) 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些从外地来北京的少数民族业主所雇佣的员工,绝大多数是本族人,而且多以自己的家人如丈夫、妻子、子女和年轻的家族亲戚为主。其中,朝鲜族的民族特色私营企业比较多,② 也比较典型。这些例子说明了,朝鲜族创业与经营者,从家乡来到北京如何利用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作为社会资本,雇佣员工的情况。③由此可见,将社会关系作为社会资本来利用的主体并不是就业者,而是那些创业与经营者,他们就是一个个族裔式 “蜂窝”的小蜂王。
表面看,族裔式 “蜂窝”的社会性基础与一般 “蜂窝”的社会性基础,都是依托于社会关系网,两者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族裔式 “蜂窝”与一般 “蜂窝”的社会性基础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族裔式 “蜂窝”的社会关系网带有民族性,即其社会关系网通常只限于本民族之内,以本族人为基本成员,建立互惠共赢网络。
4. 经营者的 “蜂窝” 结构及其功能==由上述分析可知,经商者 “蜂窝”有三种主要类型: 家庭式 “蜂窝”、价值链式 “蜂窝”和族裔式 “蜂窝”,他们共同的基本原则都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这些大大小小的私营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的成长,不只是靠做生意赚钱之类的经济能力,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私营民族企业及其经营者具有一定的民族资源,即显着的民族文化特征、独特的民族语言、民族价值观、家庭和亲缘关系、社区关系等,④ 这些特征使他们在离开家乡之后,在城市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蜂窝”,以获得创业资本、廉价劳动力、商业信用等,开展一些商业活动和企业经营。⑤ 在越来越多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有一定实力的情况下,在本民族各式大大小小的家庭式 “蜂窝”和价值链式 “蜂窝”的人脉基础之上,会形成本民族商业群体。
本来,“蜂窝”式网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功能比较强,但政治性比较弱。如果一个民族的企业和企业家的 “蜂窝”网络,已经形成了这个民族的商业群体,那么,这个民族的 “蜂窝”式网络将有可能在原先具有的社会性、经济性基础之上,增添一种新的功能---政治性。这个民族的商业群体领袖将可以把代表这个民族的民间愿意与代表官方的政府机构衔接起来。于是,会出现一些民族商业团体的领袖与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性联系,或个别民族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个人性联系。总之,“蜂窝”式社会一旦具有民族性,其政治性将不可忽视,可以说,族裔式“蜂窝”不但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是一种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力量。
四、总 结
本文中提出的 “蜂窝式社会”这个新概念,是与笔者 2014 年提出的 “伞式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 一) 对 “蜂窝式社会”概念的通俗性阐释和总结性描述
为什么把普通百姓比喻为 “蜜蜂”,把他们的经济生活比喻为共筑 “蜂窝”
第一,普通百姓像不知疲倦地采花粉的“蜜蜂”一样勤劳,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乡农村务农,还是来到城市讨生活,都是依靠自己辛勤的双手,留着辛苦的汗水,自力更生地谋求生计。
第二,普通老百姓虽然既没有像 “政府官员”那样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也没有像 “富有商人”那样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导致市场转型,出现了很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老百姓可以通过就业或经商,挣到钱,获得自身的发展。即他们可以像勤劳的蜜蜂那样,日夜不停地采集花粉, “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酝酿和收获着属于自己的甘甜蜂蜜。
如果没有市场化,普通老百姓不会有这么多市场机会。第三,在巨大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既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他们是相互联系来生活的,各位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会像蜜蜂那样一起共同建构起一个蜂窝( 关系网或交往圈) .很多时候,这些 “蜂窝”多表现为以某个家庭或家族为中心构成一个关系网或交往圈。俗话说: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即同一关系网或交往圈的人,会相互联系,一起建构一个共同的互惠共赢网络,以便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分享市场转型的红利。第四,每一个看不见的关系网或交往圈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每一个 “蜂窝”都有一个 “蜂王”带领着或多或少的 “工蜂”,不断地在窝外辛劳地采集花粉,回到窝内与自己伙伴一起共同建筑属于大家的“蜂窝”.第五,普通老百姓自发地形成的这些大大小小的 “草根”关系网或交往圈 ( “蜂窝”) ,在政治上没有很大的权力、社会上没有拥有很多的资源,通常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为常用的行为规范,勇敢地去争取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并在市场转型中形成了一些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民间机制。第六,普通老百姓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关系网或交往圈 ( “蜂窝”) ,虽然是看不见的或无形的,但是,它们已成为非官方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蜂窝式社会”是经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 二) 主要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就业性和经营性两个视角,分析了五类 “蜂窝”基本结构与功能,包括就业者 “蜂窝”有链式和网式两种形态,以及经商者 “蜂窝”有以家庭、价值链、本族裔为中心三种类型。简称 “二五·蜂窝”结构与功能。“蜂窝”式关系不但涉及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社会关系,而且涉及都市社会和商业社会中的陌生人的关系,不但涉及关系网络中的社会性交换,而且涉及人们的经济性。这些看不见的交往圈或关系网,虽然各种各样,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不是无主之网,与每个蜂窝都有一个 “蜂王”类似,这些大大小小的关系网都有类似 “蜂王”的领头人。这些领头人对其关系网或交往圈通常具有一定的引领或指导作用,但他们大多都是无冕之王。他们有时可能是一位家庭户主,有时可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有时可能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市场转型与资源配置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问题。①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是一种 “二元结构”:代表官方 “大传统”的政府主导 “伞式社会”与代表普通百姓 “小传统”的民间 “蜂窝式社会”,那么,这两者是一直处于分离状态,还是会有一定的衔接? 具有民间性质的 “蜂窝式社会”没有很多权力和资源,但依据自身努力争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 其经济性和社会性比较强,但政治性比较弱。当社会上的各种“蜂窝”由很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大,形成了群体性网络、地域性网络②或民族性网络。这些群体性或民族性 “蜂窝”将有可能在原先具有的社会性、经济性基础之上,增添政治性这一种新的功能。即社会上各种基于网络关系的 “蜂窝”,一旦具有群体性或民族性,将同时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它们不但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是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力量。由此,基于一定规模 “蜂窝”的群体或民族,其社会团体就可以与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起组织性联系,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简言之,与 “伞式社会”自上而下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制度变迁不同,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行为,如果试图参与资源配置和推动制度变迁,必须要形成群体性或民族性 “蜂窝”式社会结构,才能形成影响力或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