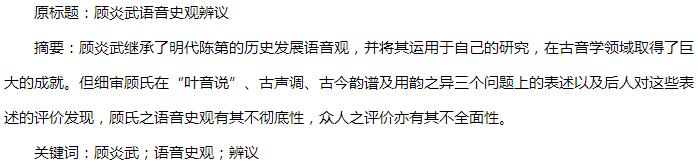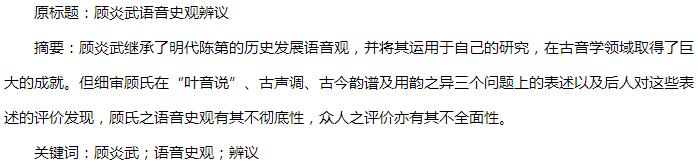
在汉语古音学研究方面,第一个明确提出语音时空观的是明代的陈第。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批判“叶音说”时指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1]7这句话道出了语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原理,即语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陈第的这一论断为汉语古音学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顾炎武继承了陈第的历史发展语音观,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古音研究领域,在研究汉语语音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分析《诗》韵、离析《唐韵》、归纳古韵部、创立入配阴声格局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综观顾氏的古音理论以及后人对此所作的评价,我们发现顾炎武对“叶音说”的批判、对古声调的认识、对古今韵谱及用韵之异的态度这三个问题上,人们对顾氏的评价以及顾氏本身的观点表达都存在一些不足,有再认识的必要。
兹试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叶音说”
“叶音”亦即“协音”,又称“协句”“协韵”.
语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诗经》时代的语音,到了汉魏六朝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诗经》中本来押韵的文句,六朝人读来就不押韵了,于是他们采取了改读今音以求声韵和谐的“取韵”“协句”“协韵”的作法。如陆德明于《召南·行露》“何以速我讼”之“讼”字下引徐邈注曰:“取韵才容反”;于《邶风·燕燕》“远送于野”下注曰:“野,如字,协韵羊汝反。沈(重)云协句宜音时预反。”此时的“协韵”是具有拟古性质的,从中可见时人已经注意到了语音的古今差异。因此,张民权说:“六朝人‘取韵’和‘协句’注音,标志着古今音观念的初步形成。”[2]2六朝之“协韵”到宋朱熹时习称“叶音”,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六朝时期的“协韵”相较,宋人之“叶音”有与六朝相一致的一面,即基于古今语音变化而改读今音以就古韵。如《诗经·鄘风·相鼠》第一章朱熹注曰:“皮,叶薄何反;仪,叶牛何反。”皮、仪二字以今音读之本亦押韵,朱熹之所以注上叶音,目的就是指明其古音如此。但同时宋人之“叶音”也有为求押韵和谐而滥改滥协的一面,如“家”字朱熹在《豳风·鸱鸮》“未有室家”下注“叶古胡反”;在《周南·桃夭》“宜其室家”下注“古胡、古牙二反”;在《召南·行露》第二章“谁谓女无家”下注“叶音谷”,在第三章“谁谓女无家”下注“叶各空反”.同一时代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同的叶读音,甚至在同一作品的不同章节叶音竟然也不同。这种随意性很大的叶音与早期带有拟注古音性质的协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因此,戴震说:“唐陆德明《毛诗音义》,虽引徐邈、沈重诸人,谓‘合韵'’取韵‘’协句‘,大致就《诗》求音,与后人漫从改读名之为’协‘者迥殊。”[3]313
“漫从改读”的叶音说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得古今语音变化发展的道理而强以今音读古《诗》。对此,顾炎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其失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之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者,而改古人之文而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4]5同时,在《音论》中顾炎武继承了明代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音发展观,明确指出“古诗无叶音”.在这个论题之下,顾炎武引用了宋徐蒇、元戴侗、明陈第等人的观点,从文字谐声、经典用韵等角度批判了“叶音说”,指出上古诗文押韵用的正是“古正音”,不存在“叶韵”的问题。例如,顾炎武引戴侗的观点说:“经传’行‘皆’户郎切‘,未尝有协’生‘韵者;’庆‘皆’去羊切‘,未尝有协’敬‘韵者。如’野‘之’上与切‘,’下‘之’后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韵也。”[4]33由此可见,顾炎武批判“叶音说”的理论依据即今音不同于古音的语音发展观。学界对于顾氏的这一认识持肯定态度。
同时,顾炎武还曾说:“愚以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又如箕子《洪范》则以’平‘与’偏‘为韵。孔子系《易》,于《屯》于《比》于《恒》,则以’禽‘与’竆、中、终、容、凶、功‘为韵;于《蒙》于《泰》,则以’实‘与’顺、巽、愿、乱‘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4]37在顾炎武看来,古诗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二与正音不合者”,主要是受了方音的影响,读这些诗的人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这种行为“虽谓之叶亦可”.有学者认为这是顾炎武批判“叶音说”不彻底的表现。如朱晓农说:“顾氏并不是彻底反对叶音的,他只是不赞成宋儒那种全面叶音。他所确定的韵脚在他的古韵系统中如能得到解释,则用一个确定的读音;如碰到解释不了的情况,则归之于方音,解决的办法就是’叶‘”[5].
笔者认为顾氏的这一作法与他反对“叶音说”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他这里的“叶”与宋儒所谓的“叶”名相如而实不相如。宋儒所谓的“叶”是从纵的时间的角度着眼而将本来按古音读起来押韵的字改成了今音,其结果是假若用作诗时代的语音标准来衡量,本来押韵的诗句被改得反而不押韵了。顾炎武“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叶亦可”的“叶”是从横的地域的角度着眼的,意思是有些古诗用韵存在方音要素,即使按照作诗时代的标准正音来读也仍不押韵,于是要改而依据古地域方音来读,以恢复其押韵和谐的原貌。简言之,宋儒之“叶”是没有认识到语音的时代变迁而改古音以就今音;顾氏之“叶”是认识到了语音的时地差异而改古正音以协古方音。顾炎武对前者的批判以及对后者的提倡说明他深刻地领悟并贯彻了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音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