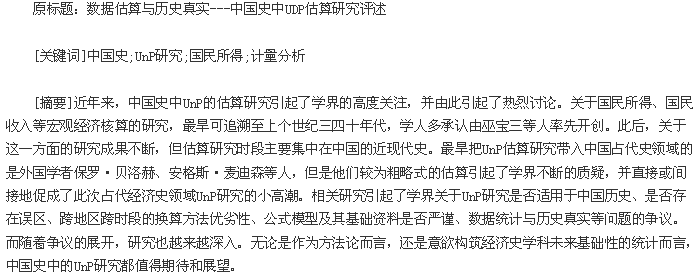
自19世纪以后,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总体经济规模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UNP)、国内生产总值CUDP)、人均UDP等统计指标来表达。但迟至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全面的国民收入账口①。在西方,关于国民核算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得很早,真正意义上的UDP核算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西蒙·库兹涅斯所做的规范及其出版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31^-1938》一书②。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大大促进了国民核算体系的全面发展③。二战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重视国民收入核算工作。需要注意的是,UDP这个概念的兴起及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理性国家政策等核心因素密不可分①。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史学科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计量统计的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显得越发重要。
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③史家巴勒克拉夫也说过:“经济史永远具有计量化的方向。”⑥吴承明则不断重申:“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统计的都应尽可能做计量的分析。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计量分析才能具体化,有时并可改正定性分析的错误。”⑦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学界掀起了一股U DP估算研究热潮⑧,这无疑对于中国经济史未来的研究会有长足的影响。实际上,关于中国历史UDP估算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己开展。其后,经济史学界又有一批学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把UDP估算的时问范围由近现代拓展至古代。至本世纪初,关于中国史UDP估算统计的新成果不断出现,颇引人瞩口。与此同时,史学界对于UDP估算的方法问题也不断地予以关注和检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关于中国经济史中UDP的估算统计与方法论探讨齐头并进。这种理论实践与方法探讨并重的局面无疑会有良性互动的效果。本文首先将系统地回顾学界己有的UDP统计估算成果,对相关评论及反思予以考察,然后提出笔者的看法。倘有缺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回顾:中国史中GDP估算的研究
中国史中关于UDP估算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是1940年代由巫宝三先生开创的①。当然,早在巫氏之前也有一些学者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作出一些简单的估计。如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中,对中国1925^-193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过简单估算。此外,还有刘大钧在《中国战前国民收入初步估计》、《中国国民收入(1931 ^-1936)—一项探索性研究》等文中,有关于193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初步估计②。据巫氏自己讲,德国学者Dresdner Bank在1926年也做过一个很粗略的估计③。尽管如此,就统计数据和力-法而言,只有巫氏的研究才具有体系性和开创性。因故,笔者也赞同巫氏是最早一位专论中国史中国民所得的学者。
1930年代后期,巫氏有感于中国国民所得研究的滞后,萌生了亲身研究此课题的念头。在涉览了许多相关资料之后,巫氏首先完成了关于国民所得研究的思路及所用方法论问题,其后成书为《国民所得概论》。1947年,巫氏及其团队关于国民所得估算的研究成果最终成稿出版。
在这部负有盛誉的著作中,巫氏首先说明了国民所得的相关概念及其估算的方法,并对11项涉及国民所得的绝大多数行业进行分门别类的估计,最后还分析估算了当时消费和投资两项内容。巫氏的估计重点放在1933年,他初步估计这一年中国国民所得为19 946百万元,人均所得仅为46元。其中就产业结构而言,农业是占比重最大的行业,为61 0o,此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中国国民生产能力之低,实足惊人①。当然,巫氏的估算实际上是囊括了自1931年至1936年的国民所得、各行各业的数值及比重、国民所得可支配收入等,并绘制成表,一口了然。然由于其他年份资料及可靠程度不及1933年,所以该书标题仅标示1933年,此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
《国民所得概论》一书发行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瞩口。费正清认为:“此书是对中国国民所得现有的最详备的估计。”联合国1948年出版的《各国1938^-1947年国民所得的统计》中的中国部分,即采用此书的估算结果③。当然,该书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质疑。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西蒙·库兹涅斯就认为该书估值过低⑥,后巫氏在认真吸取各家意见之后又对原来的结果进行了修订,修正之后的1933年国民所得值增加了373万元,较原数增加了1. 800。不过,修正之后的结果并未改变他原有的估计和分析⑦。
值得注意的是,巫氏在此书所用的“国民所得”概念,并非完全是我们现在通行的UDP或UNF概念,但它可近似理解为国内净产值。国民所得接近于UDP,而可支配国民所得则接近于UNP,均可泛指一般的国民收入⑧。由于概念以及统计材料等因素所限,巫氏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检验其国民所得值:一是增加价值法,另一是消费及投资法咬!。此两类方法也与我们较常使用的生产法、支出法等相近。总之,巫氏的先行研究开创了中国史中国民收入研究的先河,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数据支持,以至于吴承明称誉道:“(此书)首创这个研究领域,沿用至今,无出其右者。”②1950年代,身居国外的张仲礼在其一部名作中利用官方、非官方的材料、海关资料及日本调查报告等材料,对1880年代的国民收入(UNP)进行了粗略估算,统计了农业、矿业、制造业、运输业、金融、贸易、住宅、政府服务、绅士等行业的净产值。据他估计,此一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80亿元(约合27.8亿两白银),人均为7.4两白银,农业占总产值的60.100,制造业为7.200,流通行业占8.900,其他服务业占23.5%张氏的研究成果在欧美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广为人知,成为后来欧美中国学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之一。
1960年代,关于中国史中宏观经济的估算统计渐增,如刘大中、叶孔嘉的《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年一1959年》(1965);费维凯的《中国经济,1912^-1949))(1968),以及他为剑桥晚清、民国史所写的经济章节;拍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1969)0 1970年代,有埃克斯坦的《中国经济的发展》01975),拍金斯主编的论文集《中国近代经济的历史透视》01975),罗斯基的《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展望))(1978),雷诺兹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1850^-1980》等①。这些宏观估算大体集中在中国的近代时段。其中较引人关注的是刘大中、叶孔嘉的研究数据。刘、孔二人用产业来源法估算了1933年及1952^-1957年的国内产值,书中估计,1933年国内总产值为298. 8亿元③。此结果与巫氏的数据相差甚大,因而立即成为当时学界的一桩公案。关于这场争论的详情,可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相关论述⑥。此书出版后同样引起了较大反响,其数据多被引用,尤其是关于1933年的数据。同时该书也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费维凯就称该书是对中国1930年代经济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关于中国史UDP估算的研究呈现勃兴之势。研究的时段也由过去较为集中的中国近现代史逐渐向中国古代史领域拓展。其中,在近代史领域内有罗斯基在《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1989)一书中利用刘大中、叶孔嘉、Arthur " N " Yong等人原有的数据进行修正之后并得出的估算结果⑧。刘佛丁、土玉茹等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1997)一书中对1850年、1887年、1914年分别作出了估算,他们估算的结果也是建立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中日国民核算组对于1840,1894,1911,1920,1933,1936,1946,1949年中国的UDP进行了估算。通过估算数据他们质疑了学界一些己有的成见⑨。吴承明、屠光绍、丁世询等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收入也进行过分析⑩。此一时期UDP的估算研究,在古代史领域影响较大的有安格斯·麦迪森、保罗·贝洛赫@、刘瑞中等人的估计。其中,麦迪森的数据为人们所熟知。他估算了中国自公元元年至口前的UDP总量、人均UDP量等数据,其估算结果曾广为引用,但其估算的依据及方法存在很大的缺陷⑩。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麦氏的研究数据多是推测性的结果,但他的研究启发并引起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古史UDP估算的兴趣和热情。至于贝洛赫对于中国古代史UNP的估计,或许是最早的,但其研究依据比麦氏还薄弱,更不足信①。刘瑞中的研究是建立在与同时段英国相比较的基础上。他粗略估计了18世纪中国的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并以1700,1750,1800三个年份的数据与英国进行比较。他认为18世纪早中期,中英的差距不大,但工业革命后两国经济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刘计算国民收入所采用的方法是比例推算法,根据组成国民收入的各产业(农业和非农业)所占的比重来推算数值,而他所采取的农业比值是根据了刘大中、库兹涅斯等人的结果(农业占64 00^7000),来假定18世纪中国的农业所占比重②。刘所采用的估算方法较为简单,其结果显得十分粗糙。刘逛就认为他的缺点在于:未换算成当代的价格,不利于进行跨时段和跨国比较③。
近年来,中国史中UDP估算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引人注口的是李伯重关于18世纪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UDP的精细研究,刘逛关于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1600^-1840年)的研究,管汉晖、李稻葵关于明代UDP及其结构的分析,刘光临关于宋明问长时段国民收入变动的氢测性研究等①。
李伯重的研究是建立在他对明清江南经济史谙熟于胸的基础之上形成,比较而言,他的估算最为精细。他通过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来计算、验证其估算的1823^-1829年华娄地区的UDP } HDI值,并得出独特而富创意的结论。据他估算,1820年代华娄地区的UDP大致为1300万两。当时人口总数为56万,人均U DP为23.2两。1820年以前华娄的UDP比1820年代华娄的UDP要高出近3000。通过数据分析,他得出结论:"19世纪初江南经济己经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而是-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近代经济。历史上的江南地区一直为自身经济成长做着各种允分的准备。”③李伯重的研究相较于学界其他同类研究成果而言,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不再以中国这样宏大的整体作为估算对象,这就避免了疆域、人口等概念的含混与不明,而这恰恰是UDP估算的先决之一⑥;二是选取的时问段较为合理,短时段的选取不仅方便于收集资料,也较能体现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者还注意与前十年相比较);三是不单纯依靠UDP数据来分析贫富程度及发展指数,并引入了HDI指标,这就为完善UDP估算及史学计量统计研究开启了新思路;四是不仅把史料与数据结合起来计算UDP数值,而且纵观作者的研究意图可知,明确的问题意识贯穿这部著作的始终。上述几点,允分体现了李伯重把计量方法带入经济史,又超越单纯估算计量而进行综合分析的特点。
刘逛的研究也是近来U DP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公元1600^-1840一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一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UDP的估算》出版的一个很重要口的,是为了与安格斯·麦迪森等最新研究成果对话,并在允分利用经济史学科发展至今在各领域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加上他个人的估算、修正,得出关于前近代UDP总量、人均UDP。 UDP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并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较。
他还试图从经济总量来分析明清工业化转型困难的缘由,体现了其对经济史学科的深层思考,并试图超越单纯的经济总量。据刘逛估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U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不到五分之一。1600年我国UDP总量约为780亿美元,之后逐步下降,到清初开始缓慢增长,1840年最高时超过1300亿美元。从人均数据看,1600年为388美元,1600^-1730年我国人均UDP波动较小,基本上在380美元上下,之后逐步下降,1840年为318美元⑦。刘逛试图修正麦迪森、贝洛赫等人对于中国UDP的过高估计,值得肯定。关于此点,樊树志在该书序言当中写道:“(该书)可以看做中国学者对这一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一种回应,其价值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
管汉晖、李稻葵对于1402^-1626年明代阶段性(10年一期)的U DP进行了估算,并与18世纪的英国进行比较。他们的研究显示,明代整体经济增长不快,年均UDP增长率仅为0. 2900;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农业占UDP比重平均为8800,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00;政府税收与UDP之比为3%到900,平均为500,明中叶后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支出的60%到90 0oCi>。其中,他们对货币之问用黄金定价法及比例推算法进行的换算值得瞩口。但是,该项研究因对手工业产值估计不足,并忽略教育、公共服务等行业,被认为可能存在严重的低估②。
刘光临估算了1121^-1880年问中国国民收入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并以白银和米进行折算。他的研究是从人均货币总量和实际工资两个角度展开。然而,面对如此长的时段,他搜集的资料只有272个实际工资样本,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只有64个成体系的样本。据此,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收入在宋清问呈U字形,高峰出现在北宋末期和清代乾隆朝,而明代在大部分时问处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谷底。清代国民经济在1819世纪发展突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这与当今最新的研究成果十分吻合③。总体来看,作为总体趋势性的把握,此成果价值较大,但由于其数据数量严重不足,因而缺乏说服力。
二、审视:学界对于GDP估算的看法
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不断推进,国内外学者在应对前瞻性的话题时往往有着共同的敏感性。对中国经济史而言,UDP估算无疑是个前沿性的国际课题。对于这样一个不新不老的学术热点,学界在瞩口的同时,也对中国史中UDP估算研究的未来发展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2008年12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召开经济史沙龙,专题讨论中国史中UDP估算研究问题①。
2011年5月,由学界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史中U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引起了许多学者关于此问题的探讨③。此外,除了前文所列论著的专门书评外,亦有其他学者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大体而言,笔者将近期讨论的要旨归为以下三点:
1一些学者在允分肯定当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史中UDP及相应数据库的迫切性,以期更好地提升经济史的总体水准,并与国际研究相接轨对于中国经济史而言,UDP估算无疑需要大量的原始数据。陈争平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迎难而上,取得了可供学界借鉴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的重要鞭策;比较而言,中国近代经济统计和U DP估算己成薄弱环节。为此,他建议立即开展近现代经济统计的相关工作,并提出建立“两库一丛书”计划,分别为原始数据资料库、修正数据资料库和在修正数据基础上的研究丛书⑥。
史志宏、陈毅也开展了关于19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总量估值的课题工作。他们提出从基本史料出发重建历史数据的口标,对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地力志(据说有2000多种)等进行筛选查阅,并得出了超迈前人的数据量。口前该项工作尽在进行当中⑦。
颜色以供需关系来比喻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需求与国内学者研究的供给,并表达了对UDP统计同行的钦佩之情。他强调,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史中严谨而又扎实的数据和计量研究成果十分重视,希望中国学者能尽快建立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社会共享的历史数据资源库①。
管汉晖认为,中国史中UDP估算的意义不容忽视,因为对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定量化的整体研究,不仅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古代经济史发展特点的一大原则。他强调,只有对UDP、人口增长、人均U DP、经济结构、政府规模、资本积累等进行全面了解,才能完整把握整个经济的全貌,进而以此为起点,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②。
2.许多学者继续分析了涉及UDP的比较方法、资料利用、模型适用等,以便更好地完善未来UDP的估算统计。
吴承明介绍了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丹尼(E " D " Denisin)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分析力法”,他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制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问才能显现,而且不可计量。经济史家要辅之以逻辑分析,或可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总体论史学方法,才能对历史做出正确的分析③。
土玉茹、土哲介绍了平价购买力法(简称PPP)在经济史中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将UDP估算进行跨国比较的时候必然涉及货币换算问题,折算过程则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汇率直接结算,二是按照不同时期的货币购买力进行问接折算。按照汇率换算有其天然的劣势,因为汇率实乃政治经济多方面影响下的产物,落后国家的货币一般较“软”,有时候不能真正反映不同国家问UDP相对大小。
因为这方面的考虑,麦迪森采取了购买力平价法,但学界对其多有质疑。他们通过构建模型并加以验证,指出平价购买力法在研究中国长时段历史中具有不确定性和极大的风险性,进而认为在实际的研究中要坚持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而不应该本末倒置地先用某种理论模型推算宏观的结论再去做微观的解释①。
刘逛对跨国换算法继续进行了探讨。他分析了贵金属直接换算法、直接购买力评价法、1933元一麦迪森法、UDP比较法、当期实际收入法(这三种称为问接推算法)、当期购买力平价法的利弊得失。他以1600年的1两白银为例,按直接银价法换算的数值最小(等于1990年5.78美元),按直接金价法换算后为61. 55美元,按金价和物价指数调整后约19.59美元,按只估计实物生产部门价格的直接购买力评价法约33.39美元,考虑服务业后约36.67美元;在问接换算法中,"1933元一麦迪森法”换算的数值最大,合89.75美元,按U DP比较法换算约72美元,按当期实际收入法换算约42. 41美元,按当期购买力平价法换算为85.87美元,并认为最后一种方法是比较可靠的方法③。
彭凯翔探讨了UDP中几种价格核算的问题。他指出,在估算跨地区的UDP时,用横向平均价格容易带来总值的高估,而估算一定时期的年均UDP,若用估计期的平均价格计价,其偏差方向与估计期的长短有关。另外,采用年均价而不考虑季节性等问题,可能带来UDP结构估计的偏误。最后,作者还讨论了传统经济中市价、所得价与影子价格等计价标准的选取问题。他旨在提醒研究者注意这些价格核算方法中的扭曲问题⑥。
刘巍对近现代经济史学界中统计所采用的方法进行了梳理和辨析。他在研究中借鉴美国计量经济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在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下,估算出了1927^-1930年的UDP值,并采用价格、货币量等数据建立了总供求数量模型。实际研究的体会使他反思了数据模型与前提条件、误差以及数据的验证等问题⑦。
除了一些方法讨论之外,关永强还对近代UDP核算中的资料问题进行了辨析。他认为,现存可资利用的民国大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质量参差不齐、取样不够完整等问题,再加上中国地域和行业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加以甄别、修正和核算。作者还选取了具体的调查报告予以说明①。
3.另有些学者对UDP估算的方法、估算数据与历史真实问题进行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检讨杜峋诚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可供资用的准确历史数据,因而需要估算,然而口前的“UDP"却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认识和估算的思路进入了误区,偏离了“UDP”的规范定义,中国经济史“UDP”研究中的具体方法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他认为巫宝三的研究开创了UDP认识误区的先河。本来,UDP的定义是所有进入市场的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没有进入市场的则不应该计入,但巫氏的研究把没有进入市场的一部分物品也计入进来。该项研究以净产值的估算数掉换了“市场价值”的概念,并且以“所能支配的货物与劳役”的定义来替换“进入市场”的定义。此后的刘大中、叶孔嘉及最近的刘逛等人都犯了这个毛病②。
我们认为,杜氏的提醒非常重要,可以说给学界打了一剂清醒针。在实际研究当中,不少学者忽视了这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性原则,因而造成现有的UDP估算绝大多数偏离现实。不单如此,杜氏认为,这些问题的背后折射着学界在口前中西共通的话语下,对中国传统社会二元对立现实的漠视、对中国经济的过分夸大以及对于UDP这个概念的自从使用。杜氏具体以明代“一条鞭法”为例,分析这种赋役变革使民众被迫纳入市场交易,加之市场的乘数效应,数字应该较大。这种由非市场转变为市场,必然使UDP有较大差异,而在管汉晖、刘逛等人的估算中并没有显现。其实,关于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赋役行为从而使市场虚假繁荣的问题,早在土家范批评弗兰克的文章中就有较具体的论述③。
此外,杜氏还对麦迪森的随意估计、口前跨国换算方法忽视比价变动、数据模型中的各项基础数据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值得注意。最后,杜氏主张多做基础的资料积累和数据积累工作,如同为建高楼而先打地基。在所运用的方法方面,应该是不拘一格的,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应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而被采用,但在基础数据积累薄弱的情况下慎用①。
土家范在多个场合下批评了许多人对于数据的不审慎。他指出,麦迪森、彭慕兰、弗兰克等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估,往往令中国学者难以理解。他认为史学研究无疑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包括计量统计)的新鲜输入,但更要讲究进入历史情境。历史学者应凭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借助于史料,以实证回归“历史现场”。针对经济水平的核算问题,他指出治史者倘没有一定的乡土生活阅历,很容易出错。例如,计算江南农民的亩产收入,常常不区分此类数据是稻谷还是白米或糙米,更不考虑同一区域自然条件的甚大差异,以及由灾害程度带来的收入风险;而在折算产粮或织布收入时,取的又是市场销售价,而非商家收购价与季节差价;在估算其生活水平时,又忽略诸项成本费用的算入,以及来自政府方面的法内法外税费负担。仅就上述说到的种种收支“误差”,就决非小事一桩③。
针对UDP研究现状及批评,倪玉平清醒地认识到分歧和争论的存在,认为相关研究确己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同时也有继续探讨的空问。他还提出未来UDP估算的三原则:第一,要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第二,要注意数值估计的合理性;第三,要有历史感⑥。
三、展望:数据与学科的契合。
巴勒克拉夫曾说过:“对于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⑦其中,对历史上的UDP进行推算和研究,就是这种趋势的突出表现之一,其相关成果与论争成为近年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不过,因为UDP实际是由众多行业数据整合而成的一个概念,因此研究中需要特别谨慎。对于古代史研究中的UDP而言:估算它,需要特定的公式模型;比较它,又需要特定的计量方法。无论是基础数据还是公式模型,都需要我们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展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UDP估算与研究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1.重视批评和质疑。
为了摆脱困境,现代西方史学不断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使得史学研究呈现各种新的发展趋势,其中之一便是史学的计量化。由于经济史较早地经历了计量化的过程,因此西方史家对于历史计量的优缺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巴勒克拉夫认为,计量史学只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地区,并在追求更为客观的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史学家对于各种因素的把握十分重要①。在这里,他还是强调史家作为独特个体在应对史学计量化的过程中所需的能动性。马尔祖斯基则认为,历史计量并没有改变研究的方法,狭义的计量史学有必要加上横向分析和纵向系列,即加上对某一类现象和有关现象形成结构的整体分析②。在我国,吴承明同样对于计量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计量化的结果只见数字和函数的演进,而难以有效地看见整体结构的变化。因而他主张计量经济学方法适用于检验己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③。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中国史中UDP的研究有其局限性。因此,在未来的UDP估算研究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学界口前所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公式模型问题、基础数据问题、跨国跨时段比较方法问题、数据与历史感问题等,同时也要重视前辈史家所提到的计量因素与整体结构之问的关系。此外,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杜峋诚所提出的UDP误区及其是否适用等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古代UDP估算研究的先决条件。诚如其所提醒,UDP这个概念是现代国家为了“数口字管理”的需要而创造的,而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问无疑有着很多区别。然而,关于古代是否拥有市场经济且是否能进行一定的计量估算,却是可以讨论的①。就口前的研究而言,各家或多或少都把未进入市场的那部分产值都计入了UDP当中,这对于整体数据的准确性而言无疑有所偏差。当然,这对于古史中UDP的估算研究而言,可能有点苛责求全了,因为在实际操作中能否区分进入市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2.整体未必大于部分之和。
ULIP虽说是个数据整合而成的完整概念,然而如果对ULIP的各项产值数据进行拆分,则很容易看出各项数据其实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意义。例如,计算ULIP过程中涉及的物价数据(尤其是粮价)就是市场的直接反应。成系列的物价数据能够体现市场的整合程度,反映着整体经济的兴衰和周期性特点③。再如,不同货币之问的比价更是体现了市场发育的程度,众多的货币比价数据也能够看出市场运行的优良情况。农业、人口、土地数据作为古代经济史中的基础性数值,一直较为重要,它能够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在ULIP的估算当中,这都是很重要的数值。此外,工商业、金融业、教育行业等数据,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完善程度。加之我们可以对各项数据所占的比重进行横纵向的比较,这对整体经济的认识程度无疑有所加深。因而,中国史中ULIP的估算研究把学界的视野带上了整体而又富于多样化的数据网络之中。纵使学者本身对于最终的ULIP估算的准确性无法确知,但他对其收集的各项数据无疑较具信心。整合而成的ULIP数值作为总体数未必大于各项数据之和。
3.注意与中国经济史学科相契合。
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较适用于检验经济史学科中己有的定性分析,而非创立新的论点,故中国经济史中UDP估算研究需要注意与这个学科的研究进展相切合。对于中国经济史而言,以往的研究往往注重从长时段来关注经济发展的变迁和新进展,因为只有从变化中才能抓住经济史跳动的脉搏。因此,许多学人对诸如唐宋社会变革、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近代经济变迁、历次经济危机①等问题较为执着。未来的UDP估算研究也可以关注经济史这类涉及中国史关节的阶段性变迁问题,以相关研究成果检验或反驳相关的看法,从而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并进入国际史坛,与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深入对话。当然我们更希望未来的UDP估算研究能够着眼地区性差异,注意短时段与长时段的结合,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把计量统计及方法带入中国经济史学科当中,并与之相契合,从而超越单纯的计量统计。当然,这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
4.谨防UDP自大症。
近年中国的UDP热同麦迪森有很大关系,他是口前中国学界政界妇孺皆知的人物,很多人都喜欢引用他的一些观点。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最有影响力的结论是:中国UDP在公元元年占世界UDP总量的26. 200,公元1000年时占22. 700,公元1500年时占2500,公元1600年时占29. 200,公元1700年时占22.300,1820年时占32. 900。在麦迪森看来,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逐渐落后于世界。尤其是最后-个数字,几近荒谬,但大家却最愿意对这个数字津津乐道。
麦迪森的上述结论之所以为人们乐意接受,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他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估计,同人们心口中曾经的“大国”观念藕合;第二是因为我们以前总习惯于描述性研究或定性研究,因此中国历史在人们的心口中始终是模糊的,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麦迪森的研究满足了人们的这个心愿;第三,拿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历史相比附,而实际情况是,麦迪森重点研究的是现实,历史只是他说明现实的手段。
如前文所述,很多学者对麦迪逊的数据都表示了质疑。但即使他的数据正确,国人常有的大国心态也使我们忽略了他的一些其他更重要的数字和观点。他的几个重要数字是:公元960年赵匡J}}称帝时,中国总人口是6000万,人均UDP为450元(1990年美元,下同);此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仅3200万,人均UDP为422元。到13世纪末南宋灭亡时,中国总人口己达1亿,人均UDP为600元,而欧洲此时人口为5200万,人均UDP为576元。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的人均UDP是差不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中国仅略高于欧洲;但因为中国人口是欧洲的两倍,因此,中国UDP总值也是欧洲的两倍。但此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到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中国的人均UDP仍为600元,也就是说,在南宋以后漫长的四五百年问,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停滞的;而此时欧洲的人均UDP则己攀升到927元,接近经济起飞的阶段。麦迪逊在肯定中国经济体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后,又明确指出:西欧在14世纪的时候人均生产水平己经超过中国,“在15和18世纪之问,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让给了欧洲”③;此后就人均UDP而言,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是停滞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麦迪森还批评了那种认为在1800年时中国还遥遥领先于欧洲的观点,指出有些学者所用数字是猜测甚至是伪造的①。麦迪森从历史长时段解释了中国近代落后以及西方崛起的的原因,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他的这些重要观点。这分明是民族虚荣心在作怪,或者说患上了UDP自大症!
以上对近年来学术界中国历史上的UDP估算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和反思。不容否认,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引入UDP计量研究方法后,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促进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认识。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因为中国历史资料的局限、数据的缺乏等因素,这种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需要格外谨慎。口前采用此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多为非历史学者,其研究结论有待检验。我们期待更多的历史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更期待历史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携手,从而使中国经济史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