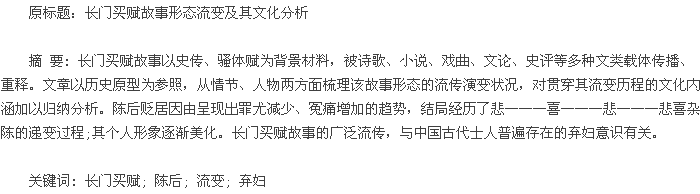
孝武陈皇后贬居长门、奉黄金遣司马相如作赋悟主的故事以汉代史传、骚体赋为背景材料,自梁朝成型以来,被诗歌、小说、戏曲、文论、史评等多种文类载体传播、重释。本文以历史原型为参照,从情节、人物两方面梳理该故事文本形态的流传演变状况,对贯穿其流变历程的文化内涵加以归纳分析。
一、故事形态流变
( 一) 情节: 买赋缘起与结局
两汉时期长门买赋故事尚未形成,但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已见记载。《史记·外戚世家》记汉武帝陈皇后为大长公主之女,其母扶助刘彻登基有功,是以骄贵; 闻卫子夫大幸,恚而几死,激怒武帝; 因巫术媚道渐觉,遭废黜。《汉书·外戚传》对废后一事又有补充,言其罪坐巫盅祝诅,罢居长门宫,十数年后乃薨。《史》《汉》又皆引述平阳公主语称其以无子故废,与媚道巫盅之说有所抵牾而未加说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相如微时与妻子卓文君沽酒临邛,因辞赋见赏于武帝,得授官职且以赋讽谏; 《汉书》又记其乐府合诗、御前视草诸事,强化出赋宗词臣的身份。《长门赋》不见于正史,南朝《文选》载之,如信其出自司马相如之手①,亦应作于西汉; 然武帝阅赋、废后复宠之事不见于史册。可以说,汉代是长门买赋故事的历史原型阶段,正史传记为故事形成作出铺垫,其矛盾晦涩之处给后人留下了想象与重释空间。
从现存材料来看,南朝梁代是长门买赋故事的形成期。
萧统《文选》录《长门赋》有序称陈皇后因妒退居长门,闻司马相如工为赋,奉黄金百斤为其夫妇取酒,遣相如作此篇; 赋成,武帝果悟,复幸陈后。序文“孝武”实为刘彻谥号,陈后复幸于史不和,显系后人据赋伪作。陈氏媚道巫盅之罪亦被隐略,“善妒”没有背离《史记》《汉书》。《长门赋序》包含了两个主干情节: 陈后买赋以悟武帝,相如卖赋得金取酒。从时人接受情况来看,后者更能体现出重心意义。卒年略晚于《文选》成书的何逊作《咏早梅》诗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②,不知是否依据《赋序》。稍后庾信《幽居值春诗》有“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陈朝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诗》亦云“长门得赐金”。但从故事结构上看,二者双峰并峙,并无主次之分,此为陈皇后角色地位的突显提供了可能性。
隋唐两宋,“卖赋得金”的故实时常出现于吟咏司马相如的主题作品中,文人亦多引之为典,表现才华与知遇处境。
但与此同时,买赋主体陈皇后的命运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关注。一方面,陈后买赋的原因有所改易。《史记》《汉书》及《长门赋序》中,陈氏之所以谪居长门,皆为有过在先。骄妒、无子、媚道、巫蛊等,虽轻重不一,在传统社会作为废后因由俱有其合理性。而初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长门怨”解题略去以上罪过,仅云“及卫子夫得幸,后退居长门宫”[1],暗示陈后幽居的原因在于汉武帝喜新厌旧。而晚唐李亢( 或作李冗、李伉) 撰文言小说集《独异志》中,又有陈后色衰见弃一说,不仅毫无主观罪责,反而多了一重以色事人、色衰爱弛的悲哀。
另一方面,此时多数作品对《长门赋序》中陈后与武帝破镜重圆的美满结局表示质疑乃至否定。武周年间乔备作《长门怨》诗,以“还将闺里恨,遥问马相如”作结,并不言及上赋复幸之事。稍后《乐府古题要解》称武帝见《长门赋》而伤怀,复幸阿娇数年———“数年”二字微妙而关键,强调出陈后因赋复幸的暂时性以及最终失宠的必然性,圆滑地消融了《赋序》与汉史的龃龉。司马贞《史记索引》认为此赋乃相如所作,但“复幸”非实。唐代宗时期,牛僧孺《玄怪录》之《柳归舜》甚至借来自汉宫的仙鹦鹉“阿苏儿”之口,转述阿娇泣歌: “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 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2]。“君王不顾”成为此期长门买赋故事悲剧结局的重要着眼点。南宋辛弃疾《摸鱼儿》写到: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谁诉”实为“无人诉”,隐约道出帝君之寡恩。又有王铚《白头吟一首》: “请把阿娇作近喻,到底君王不重顾。若知此事为当然,千金莫换长门赋。”
此外,司马相如亦有二三其德之失———《西京杂记》记其欲聘茂陵女为妾,见文君《白头吟》乃止———故相如之薄幸也被视为买赋博宠失败的原因。晚唐崔道融《长门怨》始开先河: “长门花泣一枝春,争奈君恩别处新。错把黄金买词赋,相如自是薄情人。”南宋林希逸又作《金买长门赋》: “谁买长门赋,闺愁不自禁……语妙钱何惜,宫闲恨转深。文君因自笑,我有《白头吟》。”“恨转深”暗示以金买赋之无益,末二句引申出相如的负心之举。
唐宋时期亦有作者对赋成复幸抱以积极心态,如崔道融另一篇《长门怨》曰“买得相如赋,君恩不可移”,南宋范浚《读长门赋》曰“黄金取酒奉文君……赋成果得大家怜”。但无论从数量亦或知名度来看,此类作品缺少主流意义。况且崔诗表面上持肯定态度,然结合“长门怨”之题,更像是冷宫弃妃在哀怨中的主观幻想与渴望,并非既定现实。
元明清时期,长门买赋故事在被诗文作者广泛题咏、引作事典的同时,也成为司马相如剧的重要关目。从现存剧目来看,关于陈皇后的贬黜原因,除清代朱瑞图《封禅书》写其护驾失力见怒于帝外,其余诸作多未逾越前辈言说范畴。明代韩上桂《凌云记》谓宠幸渐衰,明陈玉蟾《凤求凰》、清黄燮清《当垆艳》二剧将性妒作为失宠、贬居的正面理由,然前者借杨得意之口言及“蛾眉招妒”,后者陈后唱词有令“千古美人同声一哭”[3]的婵娟薄命之戚。明孙柚作传奇《琴心记》谓子夫争宠、色美反弃,明末清初袁于令《鹔鹴裘记》称因伺祭厌胜见贬,又令陈后自云“子夫夺宠”,清许树棠《鹔鹴裘》中被卫子夫诬以巫盅,椿轩居士《凤凰琴》亦云遭群小进谗;与此相关,元代萨都剌《题二宫人琴壶图》、明代邓原岳《燕市七歌效杜同谷体其十》、佘翔《咏史》、宋应升《宫怨》咏及长门买赋事,皆寓蛾眉见妒之意。
《琴心记》《鹔鹴裘记》《封禅书》《凤凰琴》《鹔鹴裘》《当垆艳》六剧以相如赋成、皇后复宠收结,其余语焉不详。明谢肇淛撰文言传奇小说《江妃传》写汉武帝时江家庶女得幸于君,后失宠,学陈夫人奉金求相如作赋,赋上而不见省,幽死长门宫,属于从买赋故事脱化出来的次生悲剧,但以陈氏买赋成功复幸为潜台词。诗文中的长门买赋故事体现出悲乐参半的意味,悲观态度的着眼点以“相如薄情”最为普遍,乐观者多出现于对相如才华及多情的赞美中。与隋唐两宋相比,元明清文学提及“君王不顾”的比重较小,而将“蛾眉争宠”作为难得复幸的原因之一。
明清以来大量涌现的史注史评、杂考笔记、文集诗话等多意识到《长门赋序》与正史记载的出入,并对此加以揣测论述。认可“复幸”者有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清洪若皋《梁昭明文选越裁》、薛福成《庸庵文编》、佚名《史记疏证》引金甡语等,王氏释以正史失载,薛氏谓“后虽别在长门宫,而帝不时临幸”,金氏释以“复幸不复位”。否定者有明郭正域《选赋》、清顾炎武《日知录》、何焯《义门读书记》、赵翼《陔余丛考》、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等,顾氏、何氏断定《长门赋》为后人拟作,陆氏则认为赋序乃相如自家杜撰,亦如子虚、乌有之属。
( 二) 人物: 陈后形象
两汉正史皆吝于交代陈后才貌,相反,恃功矜贵、骄妒恚愤使其不免给人留下一无是处且不择手段的印象,与武帝的关系亦难以看出些许温情。现今题名“长门赋”作品的主人公在怀人自悲之中表现出幽怨、多情以及明显的卑柔态度,与马、班笔下集妒恚、媚道、巫盅于一身的废后形象差异极大。此无名“佳人”类于“王公贵族喜新厌旧之弃妇”[4],并不确定为陈皇后,姑列于此作以参照。约作于建安前后、托名班固的志怪小说《汉武故事》又记陈后名阿娇,由“媚道”附会出阿娇与女巫楚服“女而男淫”的同性恋关系,延续正史思路将其丑化,亦不同于《长门赋》所写“佳人”。
梁代《文选》之《长门赋序》中陈后无媚道、巫盅之罪,且将其“颇妒”之因归于“得幸”,给人以“色有余而德不足……所获罪者惟妒”[5]之感,也暗示出陈后与武帝的感情基础,不同于汉代正史中政治联姻的居功自傲; “愁闷悲思”以及武帝悟而复幸的结局强化了二人的夫妇之爱; 《长门赋》之“佳人”的种种动人情态也尽可归陈氏所有。陈皇后脱离了史家笔下妖魔化的罪妇形象,渐富于人情人性色彩。
隋唐两宋时期买赋故事中的陈皇后形象对比历史发生了更大的偏差,不仅巫盅、媚道略去不提,骄贵恚妒也几乎荡然无存,仅李白《白头吟》其一有“阿娇正娇妒”之说。吴兢、李亢赋予其旧人见弃、色衰失宠的命运,辛稼轩词中更由善妒者变成被妒者。但总体看来,陈氏作为凄楚哀怨的冷宫弃妇,依然缺乏鲜明的面貌与个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陈皇后与班婕妤体现出行为类比、形象重叠的倾向①。
《汉书·外戚传》中,班婕妤是才德兼备、理性自持的贤妃典型,与陈皇后之骄狂悍妒截然不同。但后代诗人却关注到了二人作为深宫弃妇趋于一致的悲剧命运与愁怨心理,“相如”“长门”“黄金”“买赋”等,常与代表班氏的“婕妤”“长信”“辞辇”“纨素”“秋扇见捐”并列一诗。北周入隋的卢思道作乐府诗《有所思》云: “长门与长信,忧思并难任……怨歌裁纨素,能赋受黄金。”唐代皇甫冉《婕妤怨》、曹邺《代班姬》、罗隐《闲居早秋》、柯崇《宫怨》及南宋杨皇后《宫词》等同属此类。
明清相如戏剧中陈皇后皆以正面角色出现,与《史记》《汉书》之骄蛮罪妇判若两人,亦比《长门赋》及唐宋诗词中的悲怨佳人具体可感。陈氏多被剧作者描绘成容德才性俱佳的贤后,蛾眉招妒、诬谗见弃的内涵比重增加; 即便提及善妒、厌胜,亦不吝笔墨地写其娇艳聪慧与思君深情。此期有作者将长门买赋故事中的陈皇后与班婕妤连类书写,不仅仅作为宫怨典型,也有了女才坤德的比附意味,如晚明屠隆《读西陵草歌为余友周元孚内子作》称“阿娇自赋长门怨,班婕含思题纨扇”[6],清代曾燠《明宣德胡后牙印歌》称“长门赋又无相如,纨扇词亦非婕妤”[7]。
至此,我们不难归纳出长门买赋故事的流变轨迹。从历史原型出发,陈皇后的谪居因由呈现出罪尤减少、冤痛增加的趋势; 对应着两汉———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的时代发展顺序,其结局经历了悲———喜———悲———悲喜杂陈的递变过程; 陈后在买赋故事中的个人形象逐渐美化。
二、长门买赋故事与弃妇文化
长门买赋故事得以广泛流传,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人一种渊源已久的文化心态———弃妇意识有关。“家天下”的统治制度将宗法血缘作为邦国与家族共同的组织基础,中国古人很早即萌生了家国一体、男女同构的思维理念。《诗经·大雅·思齐》将“家邦”并为一词,《周易》之《家人卦》透露出“正家”与“天下定”的因果联系,《坤卦·文言》将“坤”训为地道、妻道、臣道,以顺承“乾”之天道、夫道、君道。儒家“三纲”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邦国之“臣”与家庭之“妻”皆处于支配从属地位,故而易被等同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