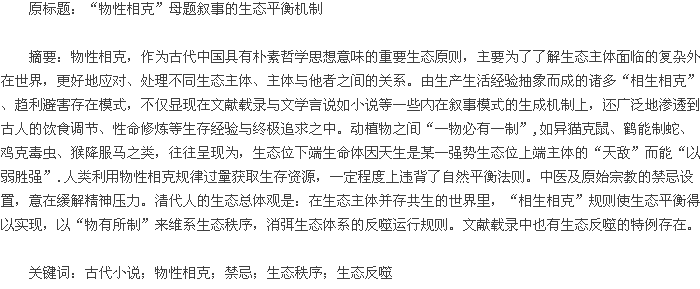
物性相克,作为古代中国具有朴素哲学理念的重要生态原则,主要为了了解生态主体面对的复杂外在世界,更好地应对、处理不同生态主体、主体与他物之间的关系。由生产生活经验抽象而成的诸多“相生相克”、趋利避害存在模式,不仅显现在文献载录与文学言说如小说等一些内在叙事模式的生成机制上,还广泛地渗透到古人的饮食调节、性命修炼等生存经验与终极追求之中。两者互动生成物性相克母题的文化演化轨迹,其中久远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中医智慧以及五行生克宇宙生成等理念交融生发,共同构成丰富复杂的生命体存在价值。
一、动植物“物性克制”原则的理性认知
源自于生存智慧实践经验的“物性相克”法则,原本仅仅是大自然协调生态平衡、制约个体超越生态承载力无限膨胀的潜规则,后来在人类探寻世界的艰难历程中得以认知并进而科学归纳。
科学与前科学元素并行不悖的生存法则,对古人的生活生产形成了物质、意识及行为法则的多重影响。中国古人对此的认知可做如下分类:其一是动物之间的“一物必有一制”,这是古人对于生物界自然生态现象观察所得出的精辟概括。唐代传闻毒蛇受制于虾蟆状的怪物:“恒州井陉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昆鸟鹚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1](卷四百五十九《北梦琐言》)
这里的“天意”当为“上天(神)的意志”;也指“自然”,即为“大自然的意志”.但在此,毒蛇因其剧毒伤人得以独占山谷,虾蟆毒杀蛇,其毒远在蛇之上,人类或其他生物其实照样难以在山谷中生存。这是生物扩展生存空间延续种群的普遍表现,只是此类毒物因恐惧而获得人类的格外观照。而物类相克的道理,被当成人类认知世界获得生存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进而关注到蛇畏惧蜈蚣。这是一个今日难以观测到的细微生态现象,但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唐代之前不难遇见:“《庄子》言即且甘带',即且,蜈蚣;带,蛇也。初不知甘之义。后闻昆山士子读书景德寺中,尝见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跃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动。蜈蚣以左右须入蛇两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谓甘者,甘其脑也。闻蜈蚣过蜗篆,即不能行。盖物各有所制,如海东青,鸷鸟也,而 独 畏 燕。象,猛 兽 也,而 独 畏 鼠,其 理 亦然。”[2](卷六)“物各有所制”的现象,即进化论所倡扬的“丛林原则”,也即强者生。这里的“蜈蚣”貌似体力上是弱势生态主体,但拥有剧毒的体液与灵巧的体态,反而成为形制天生是强势生态主体的“天敌”,能“以弱胜强”.外表上看到的“强势”与“弱势”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制人”、“为人所制”才是几乎不可更替的生物竞争原则。
其二是植物能克制昆虫,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花椒(胡椒)能对付毒蝎,雄黄可让偷袭来的蛇毙命。某过路人在大石边遍体青伤而死,但一个肩负椒囊的老叟却安然无事,而大石下有巨蝎死,原来“椒性辛辣,足以制耳”;村寺中的大蛇也因为遭遇了一个贩卖雄黄的,变得酥软不能动而被杀。[3](卷六《药性制毒物》)这实际上就是白蛇系列故事小说中,许仙受法海所赠雄黄让白素贞现原形叙事的民俗背景。植物一般处于生态位的下端,往往是动物的食物;但植物自身的物理属性,如液汁、气味等,使之拥有自身种族的保护与属性延续的必要条件,因而能抗御毒物,无意之中成为另一种族的得力工具。人类中心的拟人化书写,无意中传播了“物性相克”观念。
其三是某种合成物质如酒、雄黄等对昆虫有克制功能。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称:“王沂公之先为农,与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饮,先后至失酒,顾草间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与血,怒而饮焉。昏闭倒卧,明日方醒,视背傍积虫成堆,自是无虫终身。”饮蛇酒而此后“百毒不侵”,开启了武侠小说服食增功力的思路。如郭靖吸食梁子翁宝蛇之血后,终生于毒有了免疫力。承接上述思路,清人也揭示某些物质对某类生物、物质有较强妨碍作用。这不仅是生活经验的实用性总结,也是“物有所制”的警示和印证:“驼粪烟,可杀蚊虫壁虱。槐树生虫,雷鼓于下则尽落;以芦束置青石上,筑之易碎;芦席盖碑,经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铁器与柏木尸气,故妇人带入丧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炉插线香,灰实不入,松易倒,惟二头俱燃,灭一头插之,易入不倒。围炉炭烈,分开易灭;不分又炽,用毛纸一幅,置于火顶,烧过灰存,则火不焰而四布。”[4](卷二十《物之生克》)
其四是某种食物引起不良反应,甚至中毒,也往往有对应的东西可以化解,此为“物性相克”的反向思维。元人称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汤药,担心 内 有 荆 芥 等 药 材,否 则 能 使 人 胀 死,等等。[5](卷十《食物相反》)而在一些相对偏远、物候出产与中原差异较大的地区,博物就特别需要。明代陈全之敏感地收录称:“高、廉等处多毒虻蜈蚣,被伤者服香白芷、五灵脂、雄黄末,蓝淀汁敷之。蜈蚣入喉,小猪儿断喉取血,或鸡血饮之,再饮生油一口即吐出。蛇入口并七孔子,割猪母尾沥血口孔中即出。卒为蛇绕不解,用热汤淋之或人尿治之。”[6](卷一)这些牵涉到特殊生态主体习性的知识,实用性强,了解其克星后可备不时之需。
其五是超越“物性相克”的生存生活经验,运用于交感巫术思维的法术。对此,民俗学家概括为“秽物驱邪”法术,可分三类:牲畜粪便、人粪尿、与女人有关的秽物驱邪。这些物质往往与医方联系:“几乎所有的牲畜粪便都可治疗夜啼、客忤儿等儿科疾病。这类疾病在巫医看来多与中邪有关……几乎所有的牲矢都可医治皮肤疾病。这一现象与古代巫术传统密切相关。西汉巫医已经惯用豕矢、鸡矢、鼠壤涂抹漆疮,他们的咒语明显地反映出这一巫术意识,即漆鬼像人一样害怕脏臭,使用这些秽物就可以把漆鬼赶走;漆鬼逃走,漆疮自可痊愈。”[7]而关键在于,所用“法物”为何?能否常备手边以应不时之需。又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载:“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熙宁初罢之。后有妖人登大庆殿,据鸱尾,既获,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盖彘血解妖术云。”而动物物种属性间相克的原理,也多从自然界现象中体验并发现。这具有一定前科学性的法术,神力与物理相结合。
其六是实战需要也在召唤“物性相克”母题的普世性。《禅真后史》写骨查腊败阵逃窜,被一汉子手持木匣阻定去路:“匣里突地跳出一串黄鼠来,满地打滚。骨查腊那马见了,蓦地里打了一个寒噤,浑身黑毛根根竖起,把四只蹄子一堆儿蹲倒,伏地不动。骨查腊心慌,挥鞭乱打,那马紧紧闭着两眼,莫想他移得一步。”放出黄鼠的关赤丁了解“马见了黄鼠惊伏不动”,由于“西番黄鼠与中国不同。……黑夜间钻入马耳内扑食其虱,直钻耳根深底,其虱不尽不止,故马屡被鼠伤,血肉淋漓,数日不吃水草,伤重死者有之”.[8](第三十一回)如果不是对西域草原生态文化深入了解,购买良马亦“田野调查”,怎能想出如是妙策?文本穿插此类具有知识性的博物之笔,调节了叙事节奏,有效避免了单纯叙事的枯燥冗长,也暗示了“物性相克”的普遍存在。
二、“物性相克”叙事的制敌伦理指向
作为文本存在的物性相克叙事,一定程度上昭示着母题模式的普世性;而如此普遍性、实用性极强的生态制约原则,载录中存在超越生态主体间的利害关系,融合了叙事者的社会伦理观念。
这种多维的伦理观照,主要有如下指向:
一是,王权威势及社会等级观念扩大到生态位上下端物种关系,如异猫克鼠载录较明显。明代景泰初“西番”(东南亚)贡奉异猫威震群鼠的传闻称:西番贡一猫,经过陕西庄浪驿时,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谪为驿丞,派译员问猫何异。使臣请试,即将猫罩于铁笼放在空屋内,“明日起视,有数十鼠伏笼外尽死。使臣云:此猫所在,虽数里外,鼠皆来伏死。盖猫之王也”.[9](第十五卷)此处神化了的“猫王”竟有如此辐射性威力,是人类眼中的动物世界典型。传闻提供者朱彰,“原交趾(越南)人”,更意味深长。传播基础仍是中土人认同的“猫辟鼠”生态常理。褚人获《坚瓠秘集》卷一引《湖海搜奇》,也讲述曲阜衍圣公仓廪中巨鼠为暴,吃掉许多猫,而“西商”所携之猫索价50金,保证除害。双方立文契,巨鼠果然中了猫的埋伏被啮喉,“鼠哀鸣跳跃,上下于梁者数十度,猫持之愈力,遂断其喉,猫亦力尽,俱毙。明旦验视,鼠重三十余筋。公乃如约酬商”.[10](第十五册)两两比照,生态关系认知则一样。蒲松龄的书写,则将故事发生空间场景更换为“宫中”.但明伦点评:“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伺其懈也,一击而覆之,啾啾者,勇不足恃矣;呜呜者,智诚可用矣。”[11](卷六《大鼠》)其只是肤浅地从技术层面、过程上来解读大鼠之“怒”与狮猫之“智”.其实,上蹿下跳,彼此体力消耗大致相等,狮猫最终得胜,因其毕竟是“猫”,而猫乃是鼠克星。民谚:“八斤半的狸猫能捕千斤鼠。”故事中的“大鼠”当然是其种群中卓异的“异类”,一时间能超越物种局限而吃掉不少猫,但潜在的生态原则是“物有所制”.猫能制鼠须真正的“猫”,受制者(鼠)的厄运或迟或早,纵使再“大”而凶,最终也脱 离不了带 有 “食物链”意 义 的 生 态 伦 理原则。
二是,与民间宗教、民俗崇拜结合,神化动物属性的辨识力与判断力,如鹤能制蛇。动物世界之中的“物性相克”,还进入到人们疗治怪疾顽症的经验载录之中。陆粲《庚巳编》卷三写王某患癫疾,自感病灶在腰,但他偶到后圃,群鹤争啄其腰下,仿佛病好,而原处死一大蛇。人们由“鹤善啄蛇”推测因果,哪怕群鹤象征式地讨伐一番,也能为患者根除病症。鹤的辨识力与除病能力除生物本身属性外,也与鹤为神仙坐骑有内在联系。作为神仙体系中的一员,鹤能感知到患者病灶,通过“啄”这种类似“点穴”的功夫杀死病灶而疏通体脉。“通则不痛”,正是道教神仙及民间神医疗病理论的核心内容。
三是,作为社会伦理正义与邪恶观念的体现者,如鸡克毒虫。《西游记》第五十五回昴日星官(鸡神)收服蝎子精(悟空、八戒先后被蜇),不需争斗而结局自现。因前者属救护取经将要成为真佛者,而后者则是阻碍取经人的邪魔。承此,清代《聚仙亭》(《混元盒五毒全传》)写金奶奶与红面妖僧斗法,口念神咒,请昴日星官下界捉妖,也是锦毛红公鸡现形,鸣叫就能令对手蜈蚣精、蜘蛛精失去反抗能力。[12](第九回)鸡为人类驯养的“六畜”之一,是蜈蚣、蜘蛛等毒虫的克星。成精作怪的毒虫必须由昴日星官(大公鸡)收服,别的神只不好使,这就使“物性相克”的生态原则融合了社会正义与伦理等级观念。
四是,动物的习性被赋予“报恩”的人伦意蕴。清代《绣云阁》写蜈蚣能口吐毒烟,截住三巨蟒去路,致白蟒被蜈蚣铁杵击毙。[13](第五十一回)虽然实际上多半是由于蜈蚣作为蟒蛇天敌,狭路相逢必要拼个你死我活,也是一种蜈蚣向猎物主动进攻的自然生态现象。但在人类中心思维定式掌控下,文本以人的伦理推看蜈蚣斗蛇的行为,意义更深。被豢养十多年,两只蜈蚣终于在野店危途的情境中得逢报答主人的良机,显然基于“物必有制”、蜈蚣制蛇及昆虫报恩叙事。
五是,生命体自身神秘感应力的生命伦理书写,如猴能降服马。《西游记》中玉皇大帝何以偏要封孙悟空为“弼马温”?因猴和马属一对难舍难分的“冤家”.马与猴的渊源早见于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称《舍利护多罗》(兽医书)说“马受了烧伤,用猴子油可以治好”,果因马群遭遇烧伤,所有猴子被杀而为马疗伤。[14]
用猴子的生命来延续马的生命,这是佛教的救度精神,此姑不论。民间信奉猴在马厩,马可辟瘟疫,猴马两者又相辅相成。干宝《搜神记》称,将军赵固爱重所骑赤马,马腹胀而死,郭璞得知就让门吏转达说可医活此马,派二三十个持长竿健儿东行30里,遇丘陵林树状若社庙,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得一物急持归,果得一“似猴而非”之物带回,此物嘘吸马鼻,马即起而奋迅鸣唤。此故事经《晋书·郭璞传》改写吸收,后为《艺文类聚》《太平广记》等收录。马的生命存续有赖这似猴之物,从救治动作看与交感巫术有些渊源。宋代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指出:“养马家多畜猴,为无马疫。”此为“物性相生”,猴可令马健康,马对猴的臣服则是对生命本体的敬畏。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七《獭祭寄》引《采兰杂志》:“西域有兽如犬,含水噀马目,则马瞑眩欲死,故凡马皆畏之,名曰马见愁.宣宗时国人献其皮,帝赐群臣,编为马鞭,一扬即走,谓之不须鞭.”这一“如犬之兽”实际上是以折损马、扰乱马的生存状态来控制马。何以体小的“如犬之兽”能靠喷水成为“马见愁”?其死后之“皮”亦有控马威力?这部分地揭示出生命体相生相克的内在神秘性。
综上,作为“物性相克”的生态原则,在文本载录中悄然地将社会伦理精神介入到小说的情节结构之中,赋予小说中母题叙事以正邪“斗法”、身份象征等人伦色彩,由此使古代小说的审美逻辑超越了社会的善战胜恶、正义者战胜非正义者的人伦规范,融会到了大自然的生态伦理体系中,使某些预期性的、必然性的解释和归因有了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