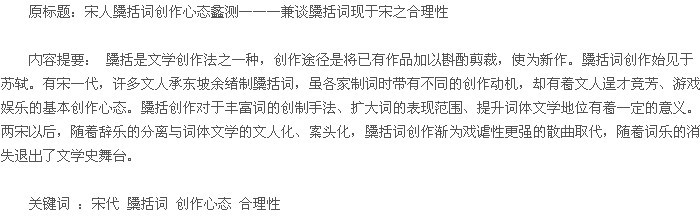
“櫽括”之“櫽”亦作“檃”、“隐”或“檼”,括亦作“栝”。《荀子·性恶》言“,枸木必将待檃括、烝、矫,然后直”;《韩非子·显学》曰,“虽有不恃隐栝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淮南子·修务训》云,“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檃括之力”。“櫽括”本意为矫揉弯曲竹木等使之平直或成形的器具。《文心雕龙·镕裁》言,“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引申为剪裁组织文章的素材。而在宋代“,櫽括”则是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将之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尽管化用前人文章诗句进行创作已是诗家寻常事,如王勃《滕王阁序》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本自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全词化用古乐府《莫愁乐》和刘禹锡《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乌衣巷》;晏几道《临江仙》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实为五代翁宏《春残》诗中原句。然以前人诗文为底本并通篇加以改造的“櫽括词”创作,则始见于苏轼。苏东坡有《哨遍》(为米折腰),篇前序云“: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童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此是“檃括”首次作为文学术语出现。“檃括”亦有多个别名,可“简称‘括’,如吴潜的《哨遍》‘括《兰亭记》’;或曰‘填’,如晁补之《洞仙歌》‘填卢仝诗’;或曰‘改’,如贺铸《蝶恋花》‘改徐冠卿词’;或曰‘补’,如刘袤《临江仙》‘补李后主词’;或曰‘增’,如程节斋《水调歌头》‘增坡诗’;或曰‘裁’,如米友仁《念奴娇》‘裁成渊明《归去来辞》’……”自东坡后,櫽括成为了两宋词人并不陌生的一种作词手法,很多文人尝试创作此体,但各家心态却多有不同。
一、个人创作动机论
关于宋人创制櫽括词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从文体内部渊源来看,应与宋人将诗度为曲的风起相关”,此外“,唐宋科举士子以‘帖括’形式读书来应付科举考试”,櫽括词的产生也与这种帖括形式有关系。这种见解有一定的道理。然宋人制櫽括词既有普泛的心理趋向,亦有个人独特的创作动机。兹以东坡、山谷为例分述。
首论东坡。有观点认为东坡作櫽括乃因“作者赏爱其词,期望通过‘改体’达到流播目的;(櫽括词)可以传递作者当时当地的心情;这也是作者试验通过一种新的体式传达心声”。此说可取,然可补充。根据《哨遍》(为米折腰)篇前序言,可知东坡此篇作于“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此时的他虽遇政治逆境,却能泰然处之,此种心态在其《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即有表露。张偓佺贬谪黄州然心胸坦荡,于江边筑亭纵览山水,快然自适,毫无悲情,这种风度为东坡所激赏,故作此词。词曰“: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此不仅是对张偓佺的钦佩,更是对自我的鼓励。苏轼筑雪堂之举,即与张偓佺筑快哉亭有异曲同工之妙。东坡《雪堂记》曰“: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盘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我其子归。”
此时的苏轼尚未至知天命之年,却言在世已五十九载。六十即为耳顺之年,人至此龄,心态静淡,东坡此说或是对这种心境的向往。《雪堂记》即展现出其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精神风貌。苏轼被贬后窘困的生活状态与平和的人生态度同他一直盛赞的陶渊明归去田园时相仿,故其乃以彭泽《归去来兮辞》为底本,创作了《哨遍》,借此来表达自己知命乐天、不为外物所累的人生态度。词云: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 归去来,谁不遣君归。 觉从前皆非今是。 露未曦。 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 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 但小窗容膝闭柴扉。 策杖看孤云暮鸿飞。 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 归去来兮。 我今忘我兼忘世。 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 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 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 念寓形宇内复几时。 不自觉皇皇欲何之。 委吾心、去留谁计。 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 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 此生天命更何疑。 且乘流、遇坎还止。
东坡颇有陶潜风范,此词亦得《归去来兮辞》之神髓。黄庭坚“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实是确评。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曾言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东坡博学高才,创作上常不拘于已有之艺术规范,推陈出新,且往往能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东坡曾模仿陶彭泽、李太白、杜工部甚至黄山谷的创作风格,达到了“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的境界。此种櫽括创作即是其打破常规,探索以文入词法的一种尝试。
如赵翼所言“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而从词体本身来讲,东坡有着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词“别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他一方面将诗词并论,认为词为诗之苗裔,以提升词体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认为词须自是一家,创作者要文章与气节并重,拥有自身的美学品味,勿步人后尘。其“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之批评即显示出他重“气格”的创作主张。
而苏轼以名篇为创作蓝本的櫽括词既使词体文学趋于文人性的雅化、提升了词体文学的地位,亦展现出他自身卓然的品格,是其对“别是一家”说的践行,亦是对词创作手法、表现功能的开拓,达到了胡寅《酒边词序》所说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的境界,建立起了新的美学风范。
再论山谷。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有櫽括欧阳修《醉翁亭记》的《瑞鹤仙》(环滁皆山也),词云:环滁皆山也。 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 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 翁之乐也。 得之心、寓之酒也。 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 游也。 山肴野蔌,酒冽泉香,沸筹觥也。 太守醉也。 喧哗众宾欢也。 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 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山谷之作是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文学主张的实践,展示出创作上求新求变的自觉性。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其所谓“点铁成金”之“铁”,即指前人已用之语,经作者的重新构思,另成佳作。而“夺胎者,因人之意,触类而长之。“”换骨者,意同而语异也”。晏几道活用翁宏之语,受到谭献“千古不能有二”的赞誉,而对于“流水绕孤村”,虽然晁无咎言“此语虽不识字者,亦知是天生好言语”,然用在隋炀帝诗中,却未成绝唱。此即体现出作者再创造的价值。黄庭坚的櫽括创作虽有追步东坡的意味,但亦在东坡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其《瑞鹤仙》(环滁皆山也)不仅是櫽括词,更是“福唐独木桥体”。所谓福唐独木桥体,指的是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通篇基本使用同一个字为韵脚。《山谷琴趣外编》另有黄庭坚《阮郎归》一首,注云“效福唐独木桥体以作茶词”,词云“:烹茶留客驻金鞍。月斜窗外山。别郎容易见郎难。有人思远山。
归去后,忆前欢。画屏金博山。一杯春露莫留残。与郎扶玉山。”此体通篇叶一韵,宛敏灏指出:“《阮郎归》为四均的令词,每均有上、下句,下句住韵。今在住韵处用同一‘山’字,所以称为独木桥体。”张德瀛《词徵》云“,福唐体者,即独木桥体也。创自北宋黄鲁直《阮郎归》用‘山’字……”山谷首制独木桥体,而在櫽括的基础上添加福唐独木桥手法,展现出他“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创作精神。山谷制福唐独木桥体词后,宋人亦有仿作,《全宋词》中除山谷创作外,另收录了 16 首福唐独木桥体词作,分别为赵长卿的《瑞鹤仙·归宁都,因成,寄暖香诸院》,辛弃疾的《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柳梢青》(八难之辞),石孝友的《浪淘沙》(好恨这风儿)、《惜奴娇》(我已多情),林正大的《括贺新凉》(环滁皆山也),刘克庄的《转调二郎神》及其和词共五首,李曾伯的《瑞鹤仙·戊申初度自韵》,方岳的《瑞鹤仙·寿丘提刑》,蒋捷的《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瑞鹤仙·寿东轩立冬前一日》、《声声慢·秋声》。而在这些词家中,黄庭坚、辛弃疾、林正大、刘克庄、蒋捷同时亦有櫽括作品。文人这种制福唐独木桥体的做法同制櫽括词有着相似的创作心理,即游戏和逞才。
二、普泛创作心理论
宋代文人尚雅亦不鄙俗,在肩负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同时追求个性的自由。因而他们既重视严肃的、服务与社会的正统文学,亦对带有戏谑性质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娱宾遣兴的词,流行于勾栏瓦舍的说话、戏文、嘌唱、杂耍等兴趣盎然。他们常以文字为游戏,于文字中展现才气。“所以韵愈押得‘工’,话愈说得俏皮,自己愈高兴,旁人愈赞赏……苏东坡的名句如‘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之类,黄山谷的名句如‘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在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之类,都是好例。”“宋诗的‘兴趣’,是文人癖性的表现。这个癖性中最大的成分是‘诙谐’,最缺乏的成分是‘严肃’。”
正因如此,黄庭坚说苏轼“素好谑谐,其学问文笔之气,郁郁葱葱散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而苏轼则言山谷“以真实心出游戏语,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二人游戏类创作颇多,《词林纪事》引《东皋杂录》云:“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作郡守,有宴会。座中营伎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命呈牒东坡。东坡索笔题减字木兰花于牒后,暗用‘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于句端。子中笑而许之。”词云:“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此为藏头创作。苏轼亦有通篇回文《菩萨蛮·闲情》:“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而黄庭坚有半篇回文《西江月·用僧惠洪韵》“细细风清撼竹,迟迟日暖开花。香帏深卧醉人家,媚语娇声娅姹。姹娅声娇语媚,家人醉卧深帏。香花开暖日迟迟,竹撼清风细细。”回文词的写作限制较多,如:每句首末两字必须同韵;平仄要能在倒转时不发生障碍;两字构成的词要选择颠倒后仍能成意,或与邻近的字结合另成新意;全首要成纹理;一句倒转后要能表达另一层意思。这样带有游戏性质的创作是文人展现才力的一种手段,很多文人愿意一试。“程大昌、曹冠、姚述尧、朱熹、辛弃疾、汪莘、徐鹿卿、刘学箕、林正大、葛长庚、刘克庄、吴潜、方岳、马廷鸾、蒋捷、刘将孙、程节斋等人”,都有櫽括类创作,“《全宋词》还收录无名氏的櫽括词”。
众词人中,林正大可堪大力制櫽括词的文人,今存此类作品四十余篇。其《风雅遗音》自序言“世尝以陶靖节之《归去来》,杜工部之《醉时歌》,李谪仙之《将进酒》,苏长公之《赤壁赋》,欧阳公之《醉翁记》,类凡十数,被之声歌,按合宫羽,尊俎之间,一洗淫哇之习,使人心旷神怡,信可乐也。而酒酣耳热,往往歌与听者交倦,故前辈为之櫽括,稍入腔律。如《归去来》之为《哨遍》,《听颖师琴》为《水调歌》,《醉翁记》为《瑞鹤仙》。掠其语意,易繁而简,便于讴唫。不惟燕寓欢情,亦足以想象昔贤之高致。予酷爱之,每輙效颦,而忘其丑也。余暇日阅古诗文,撷其华粹,律以乐府,时得一二,裒而录之,冠以本文,目曰《风雅遗音》,是作也,婉而成章,乐而不淫,视世俗之乐,固有闲矣”。指出自身创作有效仿先贤之意,而较之世俗之乐,又添了些许风雅,故曰《风雅遗音》。虽然林正大的创作“用韵颇杂又非永嘉乡音,破句律平仄处亦甚多。佳者不过十首左右。有两三首几不成韵语也”,但其创作一方面表明宋人对新体的追求,同时亦彰显出文人间的竞芳之意。“酬唱的风气在宋朝最盛,在酬唱诗文人都欢喜显本领,苏东坡作诗好和韵……仍然是韩愈好用拗字险韵的癖性。”
櫽括创作虽非酬唱“,着墨加工的地方,可多可少,相当自由”,但易有画蛇添足或去精存粗之弊,颇有难度。刘将孙《沁园春序》曾言“,近见旧词,有櫽括《前后赤壁赋》者,殊不佳。长日无所用心,漫填《沁园春》二阙,不能如公《哨遍》之变化,又局于韵字,不能效公用陶诗之精整,姑就本语捃拾排比,粗以自遣云”,认为己见已有櫽括《赤壁赋》之作难称佳作,遂填新词。清张德瀛《词徵》言“贺方回长于度曲,掇拾人所弃遗,稍加櫽括,皆为新奇。常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均体现出宋人制櫽括体时普泛的求奇炫才媲美之意。今存多篇櫽括《归去来兮辞》的词作亦可为佐证。各家之作虽词调不同,风格各异,然绿肥红瘦,终各有态。
林正大有《括酹江月》:问陶彭泽,有田园活计,归来何晚。 昨梦皆非今觉是,实迷途其未远。 松菊犹存,壶觞自酌,寄傲南窗畔。 闲云出岫,更看飞鸟投倦。 归去请息交游,驾言焉往,独把琴书玩。 孤棹巾车邱壑趣,物与吾生何恨。 宇内寓形,帝乡安所,富贵非吾愿。 乐夫天命,聊乘化以归尽。
米友仁有《念奴娇》(裁成渊明归去来辞),云:阑干倚处。 戏裁成、彭泽当年奇语。 三径荒凉怀旧里,我欲扁舟归去。 鸟倦知还,寓形宇内,今已年如许。 小窗容膝,要寻情话亲侣。 郭外粗有西畴,故园松菊,日涉方成趣。 流水涓涓千涧上,云绕奇峰无数。 窈窕经丘,风清月了,时看烟中雨。 萧然巾岸,引觞寄傲衡宇。
叶梦得有《念奴娇》(南归渡扬子作,杂用渊明语)云:故山渐近,念渊明归意,翛然谁论。 归去来兮秋已老,松菊三径犹存。 稚子欢迎,飘飘风袂,依约旧衡门。 琴书萧散,更欣有酒盈尊。 惆怅萍梗无根,天涯行已遍,空负田园。 去矣何之窗户小,容膝聊倚南轩。 倦鸟知还,晚云遥映,山气欲黄昏。 此还真意,故应欲辨忘言。
而杨万里有《归去来兮引》八曲,不仅是櫽括创作,更是以组词的形式抒发情感。且以《归去来兮引》这个词牌来作词的,除杨万里此首外,现存并无他作。虽然暂且不能否定此为杨万里自度曲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较小,一是据现存作品看,同时代人全无同调作品;二是杨万里本人并未显示出对词创作的如此热情,以至于着手自度曲。这可能只是他依据词的形式特征和样式特征,专为改变《归去来兮辞》而创出的形态。
三、论存在之合理性
王若虚《滹南诗话》言“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贺裳《皱水轩词筌》云“东坡櫽括《归去来兮》、山谷櫽括《醉翁亭记》,皆堕恶趣。天下事为名人所坏者,正自不少”,均对櫽括词作提出了批评。然此种评价实有偏颇,因为“人对文字游戏的嗜好是天然的,普遍的。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的意味,诗歌也不例外……就史实说,诗歌在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一直维持到现在,不曾断绝。其次,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的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正如清王士祯《花草蒙拾》所言,“词中佳语,多从诗出。如顾太尉‘蝉吟人静,斜日傍小窗明’,毛司徒‘夕阳低映小窗明’,皆本黄奴‘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若苏东坡之‘与客携壶上翠微’(《定风波》),贺东山之‘秋尽江南草未凋’(《太平时》),皆文人偶然游戏,非向《樊川集》中作贼。”而櫽括词所具有的风神摇曳的美感,正源自于其游戏的成分。
刘学箕在櫽括苏轼《赤壁赋》的《松江哨遍》序中对櫽括创作存在之意义亦有所陈述:“周生请曰:今日之事,安可无一言以识之?余曰:然。遂櫽括坡仙之语,为哨遍一阕,词成而歌之。生笑曰:以公之才,岂不能自寓意数语,而乃缀缉古人之词章,得不为名文疵乎?余曰:不然。昔坡仙盖尝以靖节之词寄声乎此曲矣,人莫有非之者。余虽不敏,不敢自亚于昔人。然捧心效颦,不自知丑,盖有之矣。而寓于言之所乐,则虽贤不肖抑何异哉。今取其言之足以寄吾意者,而为之歌,知所以自乐耳,子何哂焉。”
前人已有某种情感的绝佳表达,今人櫽括,传情益易,解之亦易。此即艾略特所言“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赏鉴就是赏鉴对他和以往诗人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就是他前辈诗人最足以使他们永垂不朽的地方。”
櫽括词重“合律”。东坡制《哨遍》的目的之一即“使就声律”,以便“使家童歌之”。东坡亦有櫽括韩愈《听颖师琴》的《水调歌头》,篇前序言“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櫽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方岳《沁园春》櫽括《兰亭序》篇前序“汪疆仲大卿禊饮水西,令妓歌《兰亭》,皆不能,乃为以平仄度此同,俾歌之”,可见文辞与音乐的结合在櫽括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这种“向上一路”不仅包括词的文学性,更有对外在音乐的强调,乃是其词体文学“自是一家”主张的外在表现,亦启后人无限法门。
两宋之时,词经周邦彦、姜白石等人的雅化,已成为可堪与诗并立之文体,亦可登大雅之堂,不需再借名篇之力以提升地位。加之词体文学与音乐渐渐分离,案头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而新兴的杂剧与散曲不仅可演,戏谑意味更为强烈,故成为文人逞才的新爱。因而两宋以后,櫽括创作便较少出现“,在《全元词》里,仅有白朴的两例”。櫽括词渐渐消失在了文人的创作领域之中,成为了文学史上的追忆。





